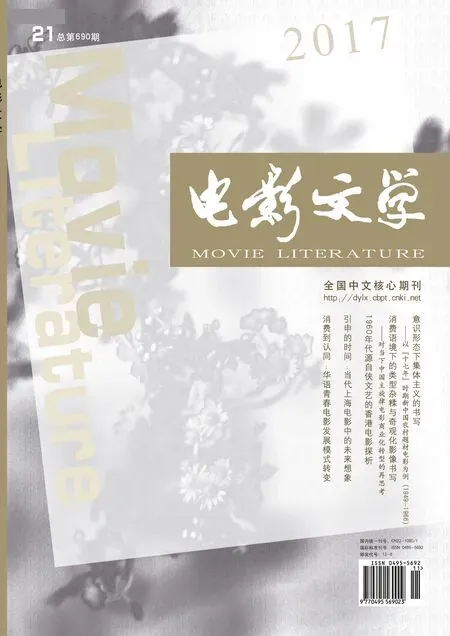电影非主流视觉文化的时代性
2017-11-16熊十华九江职业大学江西九江332000
熊十华(九江职业大学,江西 九江 332000)
非主流文化的盛行为国产电影注入了很多新鲜元素。更可贵的是,看似搞怪的剧情却蕴含着极具启示意义的内涵。近年来,这种类型的影片可谓层出不穷,其以超高的社会反响成功地凸显出新型电影视觉文化的优势,令观众津津乐道。
一、非主流视觉文化之说“妖”
“地反物”是《说文句读》中对“妖”的称呼,《左传·宣公十五年》中写道:“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因为害怕自然界的未知领域,才臆想出了“妖怪”这个产物,一般与灾难和瘟疫联系起来的,大多都是比较灵异的事件。妖怪的气质、性格和形态随着神、鬼、人在志怪小说中形象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着调整,比如,《聊斋志异》和《搜神记》相比,人和妖之间的区别不再那么明显,妖和人一样,不只具备情义和道德观念,有时比人更加突出。从《聊斋志异》中衍生出的影视作品有很多,但其中的妖怪大多呈现出梦工厂的形象风格,和传统志怪小说中描述的妖怪形象大相径庭,不过,让妖拥有人的谋略、情义和忠诚等特质,对世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符合蒲松龄“以妖为镜,讽刺世人”的初衷。
《捉妖记》里的妖怪形象萌趣十足,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的妖怪相比具有很大的区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山妖充满了残暴的戾气,十分骇人。《捉妖记》中的妖界发生叛乱,妖后为了生存不得不逃到人间,人和妖在这里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关系。有趣的是,妖怪来到人间之后,不管是忠心护主的前朝旧部,还是新皇的鹰犬爪牙,它们在人间生活的时候完全遵守人类的生存法则和价值观,用“类人”或者“假人”的外皮包裹“妖”的真身。就像是老谋深算的葛千户,它在妖怪的外皮上整整套上了五层人皮,如此才得以以人的视角和思维在人界生活,这样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告诉我们:妖怪要比人类低级。考虑到这样的认知,在这样的世界里,人和妖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妖是作为人类里的“异类”或者“假人”而存在的。以这样的观点看《捉妖记》,那么这部电影所讲述的就不是所谓的正与邪、压迫与反抗的故事了,而是一个关于自我救赎、驯服异类的故事。
男女主人公因为童年往事都比较排斥妖怪。男主人公宋天荫的父亲原为御前带刀侍卫,却将宋天荫留给一群披着人皮的妖怪村民后不辞而别,这样就导致宋天荫觉得作为捉妖的天师是不能够和自己的至亲骨肉生活在一起的。女主人公霍小岚在12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在捉妖过程中被妖怪所杀,自此之后,妖不仅是她要抓捕的对象,也是她的杀父仇人。或者可以这样说,男女主人公失父和丧父的童年经历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妖怪的认知。
小妖王胡巴是借由宋天荫的肚子出生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它和男女主人公产生了一种别样的“父子”“母子”关系,在这段关系里,男女主人公成为绝对的“长辈”。宋天荫在照顾胡巴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弥补了他的失父之痛,通过和胡巴的亲情关系缓和了他对妖怪的仇恨和恐惧之情,他从一个捉妖的天师变成了一个驯妖、养妖的长辈。在保护胡巴的过程中,他明白了当年父亲为何会不告而别,从此便对父亲的不告而别释然了,彻底走出了自己被父亲抛弃的阴影。
福柯式的规训和惩罚并不适用于这种驯化,这种驯化属于一种情感上的双向感化。宋天荫并不只是孕育了胡巴,他还用自己的血养育了它,他希望胡巴能体会到他的切肤之痛,从此能够被驯化而不食人血。在电影的结尾处出现了令人欣慰的一幕,小胡巴没有吃兔子,而是选择了吃枣,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奢望这个新妖王不再以人为食?电影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四钱天师罗刚和妖怪胖莹、竹高的关系变化,双方在打斗过程中从之前的针锋相对慢慢地变成了惺惺相惜,甚至竹高还舍身忘我地拯救罗刚,由此捉妖师罗刚对妖怪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从捉妖转而去护妖。宋天荫养育胡巴的过程中,感化了胡巴;竹高舍身救罗刚,感化了罗刚,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妖王不再食人血,天师不再捉好妖的双重感化。
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这个双重感化的大结局使人们开始相信人妖和谐共处的世界终究会到来。不过,仔细回味后可以察觉,这种感化式的驯服危机四伏。胡巴放弃兔子改吃枣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得到男女主人公的肯定,因为吃素并不是它的天性,可是在人类的认知里,吃素并不代表善良,吃荤也并不代表邪恶。如果胡巴不再考虑人的安全,而是释放自己的天性,那么只靠感化是无法对自己的天性进行压制的。这种感化的压抑毫无契约精神可言,属于不稳定的、冲动的平衡关系。
二、非主流视觉文化的深入
《捉妖记》中主要的喜剧情节来自男女主人公传统角色的对调,从传统的夫唱妇随变成了妇唱夫随,特别是宋天荫怀着胡巴时候的情景,充满了喜感。小胡巴在电影中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所以它是无性的,跟天使一样。如此《捉妖记》想象中的中性家庭就由无性婴孩、女汉子和男煮夫构成了。
我国近期的都市影视剧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角色设定:男性毒舌、俊美,但娘娘腔;女性干练、爽快、利落。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撒娇女人最好命》和《我的早更女友》。所以,在现在的文化环境下,人们开始争相讨论关于“女汉子”和“男人消失”的话题。
《新周刊》关于“男性消失”的课题曾先后做过两期:一个是347期的“男人没了?”。上面写道:“和性别相比,男人更是社会角色的代表。男人应该承担起主流价值观的职责,担当起社会的道义,是家庭的支柱,不仅要有顶天立地的气魄,还要有宽容大气的品德。中国的男性人口要远远多于女性人口,但在很多领域内,女性代替男性成为绝对的主导者。这样的结果就是男人的退化造成的。他们虽然拥有对世界的绝对控制权,却失去了价值观和精神层面的担当。”另一个是401期的“如何装一个男人?”。这一期的落寞和无奈更加突出:“现在的男人缺少了价值观和精神层面的担当,将金钱视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只知沉迷于自己的男性特权和荷尔蒙,却不理会自己应承担起的责任,空有男性的性别,毫无男人的担当。”
虽然“女汉子上位和男性消失论”这一命题在现实生活中被多次证明是假的,就好像招聘的时候,企事业单位对于男性职员更加欢迎,但是我们也的的确确看到,在现在的文化语境下,男性被塑造得愈加柔和,而女性则愈加刚强。人们对于男女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固化的认知,中性的审美观成为一种新趋势。现在,假设一种气质因为性别的原因而受到限制,那么这种限制将会影响到个人的发展。
《捉妖记》中就对这种性别置换进行了应用,而且这样的设定并不是为了表演,它是在大众的理解范围内对这种中性家庭的可能性进行讨论。宋天荫从小腿就有毛病,一直生活在永宁村,在失去父母的庇护后,他是在何种情景下学会煮饭、缝补这些生存技能的呢?霍小岚则恰恰相反,在失去父亲后,她为了保护自己就必须有男人的气魄。或者可以这样说,男女主人公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气质对调,是因为童年父母亲的缺失造成的,而不是为了简单的喜剧表演。在这里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被再次证实,性别身份并不是恒定的,也不是促进行动产生的原动力,性别的身份是一种暂时的社会状态,十分脆弱。
这两个气质对调但互补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内,各自的特长代替性别气质成为家庭分工的标准。甚至后来宋天荫升级成为一钱天师,开始同霍小岚一起承担社会分工,但这两人的家庭分工仍没有发生改变,这个家庭和普通的家庭相比,在流动性和抗击打能力方面更加有优势。从小妖王的出生和成长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伤害胡巴,而是将它当作至亲骨肉来抚养教育。
《捉妖记》中男女主人公的性别角色对调给电影带来了很多笑料,比如胡巴是从宋天荫的嘴巴进入到他的肚子里的,然后也是从嘴巴里出来的,宋天荫实质上并没有经历痛苦的生产过程。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这场中性家庭实验性的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个性别对调的家庭在生存能力和价值观上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三、非主流视觉文化的未来
胡巴这一萌趣十足的动画形象无疑是《捉妖记》团队给予观众最大的贡献,观众对于胡巴这样长得软萌、性格乖巧的形象根本就把持不住,十分喜欢。考虑到胡巴的表现,这部电影应该改名叫“撒娇记”。在电影的整个叙事结构中,胡巴与故事情节的推动基本无关,主要工作就是“卖萌”。
毒舌和卖萌是现在流行文化中的两个主要趋势,一个是以攻击性为卖点,一个是以可爱无害为卖点。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较快,人们需要情感上的慰藉,而这正是卖萌文化产生的最根本原因,一个软萌可爱的形象在抚慰观众情感方面十分有效果。形象越萌,观众就越喜欢。不过电影人物在对萌进行展示的时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动画形象,卖萌不应该仅仅是简单地对着镜头表演,乞求观众的赞赏。
美国最近的动画大片都在致力于塑造一个超萌的形象代表,比如机器人大白(《超能陆战队》)和小黄人(《神偷奶爸》)。还有就是我国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江流儿,也是一个典型的小萌童。五官柔和、大眼睛以及长相友好是这些形象在外貌上的特点,而性格上的特点就是执着、单纯、死心眼。不管是他们的性格,还是外貌,都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不过,不管是大白、小黄人还是江流儿,他们在电影中的“萌”都是参与到电影的情节叙事的。就像《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唐僧形象,由传统的啰唆变成了小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设定十分自然讨巧。
但胡巴在《捉妖记》中的作用就只有卖萌,如此就导致电影的动画形象和人物故事在这里产生了中断。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捉妖师向世俗发起挑战,对妖进行道德感化的故事,胡巴在这个故事里就只有卖萌,和故事的整个叙事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的萌甚至弱化了电影前半部寓言故事中的感化意义,所以胡巴的萌非但没有给这部电影加分,还影响了这部电影的价值意义。
对于这点,我国的动画电影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在对人物形象进行设计的时候,不能只考虑角色卖萌的需要,还要将角色的卖萌置于故事的情节中去,让这个“萌”承担起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让这个角色在这部电影中除了萌,还能够有其他作用。
四、结 语
以非主流文化为主题的电影非常具有创新性,无论是叙事情节的设置,还是视觉效果上,都达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比如,想象出的家庭、长得奇形怪状的妖怪形象等,看似无厘头的剧情和人物设定,却隐藏着“大爱”般的高尚精神。这也是非主流视觉文化电影的最大特色,更是其吸引观众的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