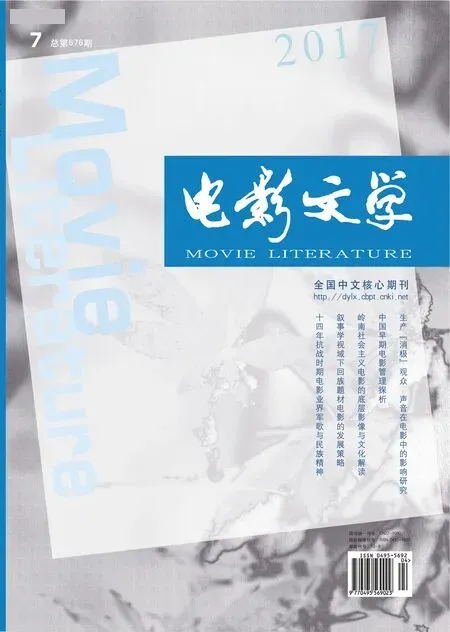论吴天明《百鸟朝凤》的文化叙事冲突
2017-11-16王委艳
王委艳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自2014年杀青到2016年公映,其间经历太多“磨难”,影片的遭遇与片中唢呐的遭遇互为隐喻,展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矛盾。吴天明对于电影犹如影片中唢呐王焦三爷对于唢呐的情感,他说:“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它诠释了艺术家对于生命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2014年2月,在《百鸟朝凤》精剪完成一个月之后,吴天明导演猝然离世,其后,影片历经太多坎坷,勉强公映而票房惨淡,直到出品人方励惊天一跪,情况才得以逆转。无论是对于吴天明个人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百鸟朝凤》都可谓是一种悲壮的坚守。
一、影片中的文化叙事冲突
影片呈现了对渐行渐远的传统文化的思考。在当今这个时代,传统文化式微,消费思潮盛行,这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性忧虑。影片《百鸟朝凤》为我们呈现了处在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的文化矛盾。影片通过几个方面来呈现这种矛盾:
其一,城乡矛盾。影片选取了吴天明熟悉的陕西黄土高原为背景,这应该是吴天明对小说《百鸟朝凤》最大的改编之处。有学者认为吴天明以《人生》开启中国西部片的审美方向:“《人生》这部影片把西部黄土高原上的民俗风情推向了世界,并且把西部高原大自然的雄浑之美与西部人心灵善良质朴之美融为一体,一下子就在人们的心中确立了西部影片的审美观念。”并指出这种审美方向是“远离政治,追求表现人性的审美内涵。人们在自然状态下谋求个体生命本能的宣泄和释放。作品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民族审美意识和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时的一种自发的反抗意识”[1]。
诚如斯言,影片《百鸟朝凤》以陕西黄土高原,黄河岸边金、木、水、火、土几个村庄为背景,叙述了传统文化的变迁过程。唢呐王焦三爷作为“百鸟朝凤”的唯一传承人,他要做的是将他认为的“匠活”唢呐传下去,并且保证继承人能够像他一样,不计利害、品德纯正,有一股对“匠活”的坚守精神。因此,他选择了游天鸣而非天分更高的蓝玉,因为他明白,天分代表不了坚守,相对于必须用生命坚守的匠人精神,天分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弥补的。事实上,焦三爷没有看错人。但焦三爷没有看清这个时代:他坚守的事业实际上与古老中国的农耕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当农耕文明式微,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大行其道的时候,处于农耕产业的农民实际上再也难以用“躬耕+手艺”的模式来生活了。再加上现代娱乐方式的多元化,更使传统曲艺的处境雪上加霜。事实上,焦三爷的徒弟们正是这样逐步逃离农村走向城市的。
其二,金钱利益与道行规矩。像《变脸》中的变脸王“传男不传女”的手艺人行规,焦三爷对继承人的选择更具有普世情怀。为了把唢呐这门“匠活”传下去,确切地说,把“百鸟朝凤”传下去,焦三爷处心积虑,他一遍遍考验游天鸣,他想寻找一位艺品和人品俱佳的、“能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的接班人。在“传声”仪式上,焦三爷决定把他的绝活“百鸟朝凤”传给游天鸣,也是看到游天鸣的艺品和人品,并把人品放在了第一位。面对汹涌的市场经济,对行规德行操守的坚守显得那样奢侈与悲壮。同样面对金钱塑造下的当今社会,焦三爷、吴天明们多少显得有些孤单,那些过去纯粹的、让人敬畏且不会随便表演的仪式,已经变成了当今挣钱的演出,甚至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山村也难以幸免。那些令我们敬畏的信仰,正在和曾经携带这些信仰的文化形式严重分离,正像焦三爷的唢呐那样,面对金钱利益,道行规矩还剩下多少呢?
其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在庆寿的时候,游家班遭遇洋乐队,景象惨淡。传统唢呐在洋乐队的冲击下生存艰难,各个村上的红白喜事不再请游天鸣他们去吹唢呐,就连村头的聋子死后也请洋乐队而不请游家班的唢呐了。洋乐队只不过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中国社会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太多浅层次的现代文化泡沫被大规模复制,而其内在的精神内涵却并没有随之建立,空洞的能指符号支撑起一种虚幻的繁荣,而传统文化在这种冲击中式微并逐渐退出,随之退出的还有优秀的精神遗产。
综上所述,影片中为我们呈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冲突。它实际上是传统农业文明以及建立其上的价值规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变得脆弱不堪。坚守传统文化及附着其上的精神价值,成了一种悲壮的行为。曾有论者不无乐观地指出:“中国文明建立在农村人口一贯压倒城市人口的基本社会建构上……但是,当今天这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无法辨认农业社会的本来面目的时候,却不能不相信,中国的文明和文化真的到了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时候。”[2]但这个“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过程注定是一个痛苦的挣扎过程,一方面是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一方面是新的价值观并没有随之建立。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优秀的传统文化,坚守优秀的传统价值,才是《百鸟朝凤》的核心所在。
二、道德冲突与中华礼乐文化
中华礼乐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不曾中断。礼乐文化倡导和谐,《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里强调了礼、乐之间的关系,即和谐和秩序必须统一才能达到礼乐相济,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乐业。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把仁作为礼乐的基础,恢复礼乐首先要使人“仁”。因此,修身是一切根本。事实上,当前的中国社会,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价值成为判断一切的标准,这种工业之“技”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植入了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文明之中,但我们并没有随之建立起工业文明契约精神之“道”,价值失范带来的恶果正一遍遍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演。这种冲击表现在多方面、深层次,已经严重动摇了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基。《百鸟朝凤》为我们呈现了多重的道德冲突。影片中的有些道德冲突是围绕礼乐文化展开的。
首先是师徒矛盾。传统民间艺人的师徒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维持这种关系的是传统的道德规范与行业规范,而非契约。因此,当经济价值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规范的时候,实际上这种靠道德伦理维持的师徒关系就变得十分不稳定,影片中就为我们呈现了这种状况。比如焦三爷怒扇二师兄。吴天明非常清醒地揭示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民间艺术传承方式的道德危机。此外,这是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对农耕文明的碾轧,使建构其上的精神价值正一步步走向消亡。“在社会现代化的巨大变革中经济价值成为衡量一切东西的根本标准,曾在乡村社会中占据统治性地位的传统礼仪和伦理秩序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失去了此前的规范作用和崇高地位,随着‘礼崩’而来的必然是‘乐坏’。”[3]
其次,行业规矩遭到破坏。游天鸣为儿时的同学——木村的长生结婚吹奏,但他并没有享受到接师礼。游天鸣和焦三爷对行规遭到破坏耿耿于怀,师父焦三爷连声说:“没规矩了,没规矩了。”传统的礼节正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成为一种被认为无足轻重的存在。礼崩会产生乐坏的结果。以往,唢呐艺人为送葬吹奏,孝子贤孙跪倒一大片,那不是对艺人的敬畏,而是对礼乐的敬畏。
最后,“百鸟朝凤”的道德内涵。“百鸟朝凤”作为唢呐名曲,本来是一种欢快的曲子,在影片中被吴天明改为大悲的曲子,即是为了烘托曲子的严肃庄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改动使该曲子蕴含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不但德高望重的人才配享此曲,而且只有德艺双馨的人才能够继承此曲。因此,当焦三爷说自己死后四台唢呐足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坚守的民间艺术家谦逊的美德和对中华礼乐文化精髓的理解。
综上所述,中华礼乐文化其核心价值在于人的修为,“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 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礼记·礼运》)。这种把礼义放在人生价值之首的传统礼乐文化与当今的资本价值下的金钱评价机制水火不容,礼乐文化失落源于这种根本性矛盾,而表现在日常行为方面则是道德冲突与价值失范。
三、票房与艺术:《百鸟朝凤》的悲壮选择
本文开头说过,《百鸟朝凤》作为吴天明导演的遗作,已经将自己对电影艺术的坚守融入了影片对焦三爷形象的塑造之中。在当今电影市场以明星、金钱、炒作等为基础,以夺取票房为目的的大环境下,对艺术的追求似乎变得无足轻重。吴天明说,他选演员不是选择最贵的,而是选择“对的”。为票房还是为艺术一直是电影导演最头疼的选择,这种选择随着电影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变得越来越现实。且追逐利益已经成为电影的主流。因此,导演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用于选择明星演员。明星演员的片酬如今已经成为天文数字。有的电影直接靠明星支撑,在艺术性、叙述技巧方面则谈不上有所作为;有的则用蹩脚的叙述去讲一个“明星故事”。电影界已经变得浮躁不堪。
影片《百鸟朝凤》充满了怀旧情结,这些怀旧情结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
首先是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我们注意到电影开头设定了1982年,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处于现代与前现代临界点的年代,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没有被破坏,建立在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价值观念也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流。影片给我们呈现了黄土高原乡野之美。农民在田里劳作,没有机械化等现代生产工具,闲适、充满田园温馨。师父和师娘每天做得最多的就是下地劳作。影片对师娘表现最多的是她的纺线与织布,这使影片充满了对传统男耕女织生活的某种诗意表达。
其次,农民对手艺(技艺)的敬仰。游天鸣之所以被父亲送到焦三爷那里学习唢呐,主要原因是他父亲小时候想学唢呐但没有师父收他,他要在儿子身上圆这个梦。残酷的饥饿记忆在中国农民心里形成一种潜在的意识:灾荒饿不死手艺人。这些艺人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行规和传承规则。《百鸟朝凤》通过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人们价值观念的极速变革,呈现这些民间技艺在农民心中的位置逐渐滑落的过程。
最后,淳朴简单的学艺过程。影片表现了焦三爷收徒的“考试”过程,如从瓢中吸水、吹鸡毛、口中吸水吹木板等,这些考试简单有效、充满乐趣。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焦三爷带着两个徒弟到芦苇、野花、野草丛中静听鸟语,师徒模仿鸟叫,相互唱和。这是影片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笔。吴天明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式微、对当今不良社会生活方式的忧虑。一个有追求的电影人的担当精神通过纯净的电影语言表达了出来。
上述这些充满怀旧情绪的电影镜头,是通过朴实的叙述方式表达的,吴天明在电影中并没有在叙述上耍各种花样,而是以传统的线性叙述呈现故事的发展脉络。吴天明通过简单的叙述和电影镜头来对抗现代化的电脑制作,用充满浓烈情感的艺术追求来诠释他终身坚守的艺术原则。在票房与艺术中,他毅然选择后者。吴天明说:“过去我拍农村片,现在拍城市题材,其实都是一根筋,那就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种关注,就是所谓忧国忧民的情怀。”[4]吴天明导演的“一根筋”表现在《百鸟朝凤》中,是否可以解读为对电影艺术传统价值的一种坚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