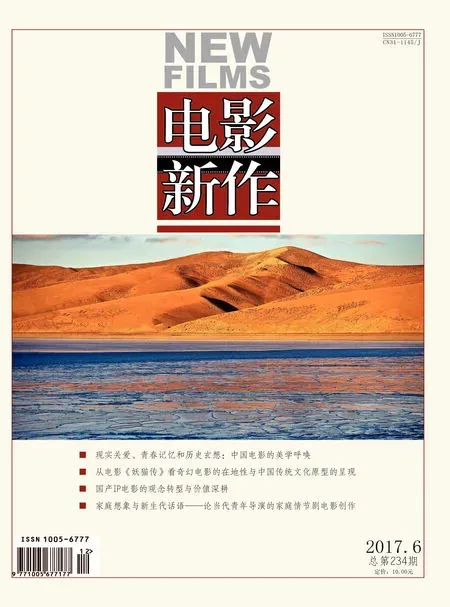近十年我国影像身体研究的主要脉络
2017-11-15付筱茵王小萌
付筱茵 王小萌
身体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是身体的社会建构论,即身体既是生理身体,更是社会身体,社会历史文化参与了规训和控制身体的过程。对于身体的研究从尼采开始已经有所勾勒。他认为身体是“权力意志”的体现,真理、知识和道德都起源于身体,是一切价值的起点。其身体研究成为后现代身体反叛的开端。福柯建立了身体政治学与空间理论的联系,论述了知识、权力与空间对于身体的规训与控制,其身体哲学的要点一是权力与身体之间的隐秘联系,二是身体中的狂暴力量——自由意志。鲍德里亚对身体的社会批判性给予了关注,凸显了身体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视觉地位。①认识到身体的社会批判性的还有布尔迪厄。他指出身体在社会发展中被延伸为形式的存在,身体的形态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②索亚认为作为空间主体的身体,规定和体验着空间。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的生存开端于身体的生产这一说法,空间成为对身体进行压迫规训的场域。福柯、鲍德里亚等西方学者将身体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研究高度,为影像身体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石。
国外对影像身体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劳拉·穆尔维、梅洛·庞蒂、维维安·索布切克、帕特里克·富尔顿、吉尔·德勒兹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继承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指出电影播放的场景为“窥视”的空间,观众和银幕之间形成“看”与“被看”的关系。其隐含的基本前提为“观看者是男性、客体为女性”,论证了“视觉快感”只能为男性所享。身体理论是现象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该理论的集大成者梅洛·庞蒂发展了胡塞尔的“身体意向性”的观点③,为影像身体理论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阐释了“知觉-身体”这一概念,指出影像的意义是由观影者身体的感知而来,既不存在透明的、脱离身体的纯粹意识,也不存在纯物质实体的身体,只有灵肉一体的“肉身”。影像中的“感觉”并不通过理智思考和纯粹意志构造,而是源于观者对于影像的身体化感知、对于影像情绪的“身体化赋形与读解”。④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理论被以维维安·索布切克为代表的电影现象学派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述,她在《眼目所及·电影经验现象学》中探讨了电影的“身体性”问题,即影像本身既是被观看和感知的客体,也是“创作”与“感觉”的主体。“在电影院里,总是有两种体化的视见行为,两种体化的视野构成了电影经验的可理解性和意义。电影的视见与我的视见并不同一,但却遭遇在一个分享的世界里,构成了一种不但内在主体呈辩证关系,而且互主体之间呈对话关系的经验。”⑤他的“电影身体说”“体感经验说”等电影现象学理论在世界电影理论中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帕特里克·富尔顿指出银幕上的人包含具体的肉体、角色所依附的躯体和个体抽象实质存在的主体。他分析了电影的欲望系统,并探讨了电影展示和引发身体的含义的过程。吉尔·德勒兹从身体哲学和身体创造学的角度论述了身体在影像空间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电影是通过身体来完成与精神的缔结,并独创性地提出了“身体电影”的概念。⑥国内的影像身体研究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
一、身体美学研究
当消费成为主流时,社会呈现出一种审美化的外观,身体被规训为合乎大众消费需求的标准审美产品,被注视、被消费、被塑造、被建构,成为新的社会规训手段。通过购买和交换,身体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成为被商业资本裁决的对象,坠落为享乐主义的消费机器。审美社会的转向与消费主义有着深刻的关联。消费主义文化的历史发展中隐含着审美生活转向的文化逻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的蔓延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改变了人类审美的既成文化环境和背景,使得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粟世来指出,以符号和影像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摧毁了文化的界标,使艺术和审美的自律性被打破了,美学的封闭性开始向实践性领域和文化语境充分开放,审美转向了广阔的感知领域,转向以视觉影像和快感体验为核心的生产,鲜明地表征着消费文化语境下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正进入鲍德里亚所谓的“超美学”或“后美学”时代。⑦在充斥消费主义、视觉工业的“后美学”时代,电影中的“身体”及审美问题被进一步激化与凸显,电影中的身体美学也被国内学界予以高度关注。有关影像身体美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意象化身体研究、受虐身体研究、奇观化身体研究和明星身体研究。
(一)意象化身体研究
洪艳指出,尊重“感官”快乐的基础上,借用身体美学试图将感性和理性看作一体的努力,既能理解影像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也能理解电影美学的变迁。⑧意象化身体的美学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满足了电影创作对身体美学的需求,符合身体影像的审美需求。第二,具有人物的形塑功能,建构起电影中的影像身体,赋予了影像身体独一无二的面目。第三,参与故事结构,成为影片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电影建构身体形象的方式各不相同。刘丹、黄宝富、夏小兵分别从青春电影、体育电影和恐怖电影的身体美学建构和消费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电影中意象化身体的美学功能。刘丹对近五年青春电影中的身体图像进行了剖析,认为在主流群体年轻化的趋势下,任何来自社会的变化都能在青年人的思想上和身体上得到体现。青年导演们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体验,用“欲望的、物质的、被规训的和暴力的”意象化身体表现青春,并通过分析青春躁动的身体欲望,来探索流动的影像中欲望的疏导方式。该研究丰富了国内青春片中的身体研究。⑨在对体育电影的研究中,黄宝富运用了人类学、技术学及文化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对强壮健美的感性身体意象进行了解析。他认为体育电影不断“询唤”起一种审美的深度文化的想象关系,作为一种励志砺行、催人向上的电影类型,在激情激烈的身体对抗中,展现了体育比赛中训练有素的审美身体的速度和力量,体现了人类顽强的生命意志、坚韧的拼搏精神、永不言败追求梦想的叙事取向。⑩夏小兵将恐怖电影中的身体意象分为物化的、异常化的以及幻化的身体意象,从外在和内在两种表现方式对恐怖电影中的身体意象所传达的审美意义进行了反思。对恐怖电影中的身体意象所传达的审美意义进行了反思:恐怖电影中的身体意象以及表现方式对传统审美观念中“以美为美”的观念而言是一种颠覆。这种颠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恐怖电影身体意象所呈现的是一种艺术恐怖;其二,恐怖电影中的恐怖身体意象能促使负面情感的宣泄;其三,恐怖身体意象能使人在有距离的审美观照中获得审美愉悦。
针对某一导演进行的意象化身体研究有:周慧芳的《梅洛·庞蒂身体美学视野下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尚振巍的《汤姆·福特电影中的身体美学》、李松睿的《身体的美学——史蒂夫·麦克奎因的电影世界》、周霁的《存在·权力·归宿:李安电影的身体美学》。周慧芳从多维存在的身体、作为语言的身体等方面,对基耶斯洛夫斯基叙事电影中的意象化身体进行分析,揭示其电影中蕴含的与梅洛·庞蒂身体美学理论殊途同归的身体意义,明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相对于好莱坞商业电影所呈现出的对身体意义的超越性理解。尚振巍认为汤姆·福特电影满足身体作为客体的审美考量。“身体”不仅仅是传统西方哲学家观念中的作为客体与对象的“机器”,也是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李松睿指出麦克奎因在他的第一部长片《饥饿》中,就已经创造出一种颇为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即在处理政治性的议题时,表面上极力淡化题材本身的政治色彩,借助身体去传情达意,营造出极富冲击力的视觉语言。而实质上,在这一过程中,原本被影片所压抑的政治性却通过画面中的身体得到了更为有力的传达。柳改玲从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等层面,指出李安试图从人体美学让人们看见男性情绪扭曲与女性身心变化。而周霁从宏观视角揭示了李安影片中的身体在各式符码和隐喻中被层层包裹的现象,想要揭示电影的本质问题,必须经由意象的桥梁走向导演思维。
(二)受虐身体研究
电影暴力美学在20世纪60年代应运而生,并在90年代发展为一种艺术审美。影像身体美学为“暴力美学”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前提,身体符号成了“暴力美学”电影的流行语言。徐光淼追根溯源,指出了电影暴力美学发展的起点,即人们长时间面对现实中遭遇的壁垒和激烈的竞争,以及消费文化的消极影响,需要一个渠道来排遣现代人内心的失落、压抑和焦虑。这种身体演绎的“暴力游戏”更能突破自身,有力地刺激了心灵,更能感知自身的存在,暴力观赏也成为电影中的一道特殊的景观。此外,他还揭示了暴力美学的启示性作用,对待拥有“中性”特质的暴力美学,只有坚持发掘暴力中的艺术美,在批判的语境中继续展现暴力美,在市场规划下发展健康的身体文化产业,美学才会真正符合现代精神的内涵。
电影暴力美学大多依赖于受虐身体的视觉呈现。正如金守波在关于武侠片的研究中,厘清了暴力美学的缘起——为了电影艺术创作的需要与故事情节的发展;暴力美学的终极目标——表现美,暴力只是一种形式、一种途径;暴力美学意境的表达要遵循一个道德标准——武侠电影中始终信奉的侠义精神。他肯定了徐克武侠电影对暴力美学的渲染,指出这是徐克电影成功的要素之一,与美国西部片中展现的赤裸裸的、人肉横飞的杀戮有本质不同,徐克的电影一直试图通过电影中的暴力镜像展现来消解影片中暴力行为导致的影响。此外,《风声》《秋喜》等谍战片中也出现了大量受虐的身体奇观。杨柳在指出受虐身体为人诟病的消极影响时,也肯定了电影暴力美学的商业观赏性。“当酷刑成为电影制造惊悚效果的主要手段和影片营销的卖点、暴力身体奇观冠冕堂皇地成为消费对象时,中国式谍战片就不可救药地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中。”她解释学者对酷刑的争议实则是对身体奇观与信仰力量、身体与灵魂的哲学关系,是二元对立还是矛盾统一的看法不同所致。
当然,身体暴力不仅仅表现为受虐式的身体奇观。刘丹认为暴力化的身体在青春电影中常常被含蓄地呈现,与一般电影对暴力喜好血腥、变态、夸张的表现手法不同,青春电影不刻意渲染暴力美或暴力丑,而是通过“暴力化”的身体喻指成长中必须要经历的伤痛,这才是青春电影中“暴力化”的身体所要表达的意义。
(三)奇观化身体研究
周宪在视觉文化的理论视野下归纳分析了动作奇观、身体奇观、速度奇观和场面奇观等四种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奇观,并进一步指出,“奇观作为一种新的电影形态已经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电影样式或类型,成为当代电影的‘主因’”。近十年对奇观化影像身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画电影和3D电影上。对于动画电影中奇观化影像身体的研究,以冯学勤最为突出,在他的《身体经验与身体意识:〈料理鼠王〉造型及动作设计细读兼谈身体美学对本土动画创作的意义》《身体美学视野下的动画艺术——以〈机器人总动员〉为例》这两篇文章中,首先表明了身体美学与动画艺术的关系,即“身体美学不仅对属于外观、表意和表象层面的“运动中的身体”进行关注,同时也要求对动画创造和赏析过程中主体的审美经验品质做出探索和描述。”其次,区分了塑造静态身体和动态身体的要求:动态身体与静态身体相同点在于“解析力学关系”的过程中都采用夸张、变形、扭曲、突出等手法,动态身体的动作设计更多与视觉思维有关,要考虑到身体运动的方向、位置、空间、速度等因素,实现身体动作的力学表意可能。再次,详细解读了“身体经验”和“身体意识”两大关键词,并指出,身体意识就是对感性经验之身体维度的重点强调。对于审美接受者而言,这种身体意识的获得既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审美愉悦的方法,同时也获得以自身的身体反应为评判标准的合法权利。对于双方而言,身体经验本身就是双方日常经验及审美经验形成交流和达到共鸣的主要媒介。他从身体经验和身体意识出发,对富含身体意识的美学符码进行解读,提出注重角色身体塑造的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趣味,并希望对正在成长中的国产CG动画有所启示。通过对身体塑造的分析对动画设计者自身的身体意识、身体经验和自由想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就身体本身思考运动问题,更要将身体放置在剧情、场景和道具的关系中思考身体的运动。对于动画制作者而言,身体意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把握不同类型的感性经验,更意味着更具差异性、更为新鲜的美感经验的获得可能。
在对3D电影的探究中,秦勇认为多维立体电影是一种最注重身体感知的大众文艺媒介形式,以身体化审美的方式扮演着恢复人的身体感知全面性的角色,观影中注重视听的电影美学开始向注重全方位身体感受的身体美学转向。汪黎黎重点指向3D电影的“沉浸性”,表示这种“沉浸性”是通过制造身体与幻影的交互感、将幻境空间最大限度地延伸并取代现实空间、让知觉系统持续浸泡在“超真实”的奇观体验之中等感官刺激手段带入并维持的。汪黎黎认为最根本的是,3D电影通过模拟人眼的立体视觉原理,制造了观看者的身体“在场”。这种“在场感”,就是我们不仅看到了事物,而且强烈地感觉到它们与我们身体的关联,我们不只是被动的观看者,还具有与周围事物组成的环境进行互动的功能。这种身体“在场”效应,使传统电影主要致力于实现的“思维沉浸于故事”转变为“身体沉浸于场景”;依靠叙事策略、步步为营的“诱导式沉浸”转变为凭借让观众“置身”于仿真空间而立竿见影的“自动式沉浸”。
王一川曾表达了对此趋势的担忧,多数国产大片都更多地仅仅满足于身体美学的效果营造,而忽略了心灵美学的效果呈现,常常让人的感动起于身体,但又不得不止于身体,而无法向人的更高的心灵境界逐步攀升。当然,这种身体美学与心灵美学之间的分离局面不只是电影界独有的,而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愈益显著的普遍性症候。真正迫切的是应该深入反思我们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及其症候,而如何尽早消除这种分离之痛,则取决于大众深入反思的力度和果断救治的决心。
(四)明星身体研究
艾利斯指出,电影的观看由三种行为构成,“观众观看银幕的行为、摄影机的拍摄角度、电影演员互看的行为”。这三种行为是明星认同的重要条件。所以,银幕的身体与银幕外的文本共同建构了明星身体。电影明星研究中针对“明星身体”,国内的相关研究在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拓展及更深的研究。
1.影迷与明星身体的关系
比较重要的研究是霍龙·简科维奇的《大众电影研究》,他曾提出四个有关明星研究的基本问题:第一,明星如何产生意义;第二,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第三,为什么观众会认同明星;第四,观众如何采取不同的方式认同明星。当观众的观看心理与之产生互动时,明星的经济价值和产业价值就显示出来了。影迷与明星身体文化的关系研究应运而生。国内学者徐文明采取电影史研究方法和文化研究方法,从实证研究视角及其现实构建方向探讨明星与影迷的关系。他将影迷与明星的身体文化置于电影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内进行史料搜集与研究,同时将明星身体置于让其形成和消费的社会关系中加以探究,从社会文化症候中寻找明星身体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意义。影迷群体对影星的集体认同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对于“追星史”的研究是影迷与明星身体互动关系研究中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重新审视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明星制度、中国电影明星的身体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2.产业和传播学角度
申中华探讨了电影明星复杂的符号结构体系和生成机制。他首先区分了明星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指出明星的身体符号、气质符号和形象符号的关联。其次分析了明星制造的过程。在一般演员—电影角色—媒介形象—明星等身份转换过程中,明星的身体、气质和象征符号不断生成并持续传播,明星的符号价值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耀眼的明星。再次,重点解析了明星符号传播的两个路径:一是在商业电影的类型片中的频繁演出,强化身体、气质和象征符号的传播。二是穿梭于各种交际场合,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强化明星符号的传播。最后,指出有关明星制的理论探讨必须回到对电影本质的认识上,将“明星制造”的过程视为明星符号的塑造、流动与传播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明星的培养、成长和使用等电影创作传播机制,重视电影角色在形塑明星身体形象和符号中的基础性作用。
3.明星政治身份研究
李鹰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解读身体在影像文本与政治领域所具有的不同秉性,以及两者互为牵掣的微妙关系。他分析身处政治议题中的明星对其银幕的身体呈现以及文化消费的接受情况之间的关系,论证了“两个矛盾”:其一为明星用身体博得关注,但当其被涂抹上“政治身份”的外表时,身体的呈现反而受到限制。其二为政治性身份的赋予本是二度“明星制造”,可让明星以政治性身份参与社会表演,但制造的结果不全然导致对明星文本意义建构有利的结果,也有可能毁誉参半。
4.从电影史的角度考察女明星身体
如刘宏球的《女明星:身体解放、都市景观与观众欲望——论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现象》、魏建亮的《女明星的身体叙事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译制片在中国的流行》,揭示女明星身体与此一时期中国文化精神之间的隐秘关联以及女明星、电影和都市的同构关系。
电影将展示重点放在明星身体之上,满足了观众观赏的心理需求,成了缺失信仰的现代人的“精神偶像”,恰恰不利于中国电影艺术的健康发展。王英莉、王志敏梳理了新时期中国电影身体文化建构中的缺陷和悖论:一是明星身体作为噱头鼓吹出来的票房无法掩饰中国电影文化的内在危机,二是身体的过度开发带来了大众文化的价值危机和生态危机,真正的身体并未得到充分的表达。如何重构中国电影文化的未来,是研究身体文化的主要目的和落脚点。董雪飞认为好莱坞电影中的明星身体资本的实现是通过对暴力行为的展演来完成的。程功认为在“新都市电影”中,明星塑造的新趋势是呈现男明星的身体、表现男色消费。好莱坞影星的暴力动作抒发了男性焦虑,都市一代的男性更多表达了个体与城市的矛盾。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新都市电影”中的明星身体,都点燃了看电影人的欲望。
二、身体社会学研究
身体的社会性决定了身体形象和身体的活动方式必然要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控制,身体不仅仅是身体,而是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等相联系的意义载体,是各种力量发生和开展的基本场域。一旦研究者们以身体审美这一文化现象来剖析当代消费文化的内涵时,则不能将其归类为身体美学范畴,而是一种社会权力的探究,研究便在无形中从影像身体美学滑向了影像身体社会学。
陈犀禾提出的“国家理论”,广义上可以指一切对电影和国家关系的理论思考。具体到新中国,是指主张把电影作为一种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的电影本体论思考。它可以体现在电影批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等各种形态中,但其核心原则是把电影功能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了一种从功能出发的电影本体论思考。该理论既是对过去电影身体社会学研究的总结和归纳,又为新的相关视角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于国内电影的身体叙事较为拘谨、克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意义断裂。研究者对国内影像身体社会学的研究以单篇学术论文研究较多,虽然文本各异,但都将“身体理论”与“国家理论”缝合,形成了新的身体社会学视角。借助陈犀禾提出的“国家理论”,万传法梳理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将民族国家的构建同身体的自我生产同构起来。在探讨电影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文章着重通过“身体”的介入来对此加以重新考量,借助于女性身体的表演来具体分析中国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民族国家理论形态。汪振城指出多数影片达到了双重叙事的目的:一方面,使对身体的发现成为影片情节叙述层面的核心推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将身体形象在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设置,身体符号成为文化、社会及历史等多重维度中的意义载体。王永收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证明了电影所表现的背景并不局限于本身意义,必然会与社会、历史、政治等相关,因而创作者对空间的多层面处理和表现,必定以与之联系的身体文化意义作为旨归。崔丹运用古今对比的方法分别对身体、身体叙事和电影身体叙事进行了概念梳理,按照时间顺序对建国后十七年、改革开放等时期电影的身体叙事变迁的过程进行描述,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深入分析消费时代电影身体叙事转型的原因,并对电影身体进行新的构建。李强运用中西方的身体理论学说,结合意识形态和时代思潮解读张艺谋电影,将“身体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后,发现了时代政治、国族意识在身体上的运作,同时张艺谋电影的身体叙事也为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他肯定了张艺谋为身体叙事开创新维度的历史作用,并使其身体叙事成文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李强的另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张艺谋电影的身体叙事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电影展示的影像身体、明星身体构成多重镜语,表征了新时期中国30多年来理性启蒙、现代化进程、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等多种文化价值观的流变。张畅在李安电影的研究中,指出了李安的影片用“身体”意象迎合了大众世俗而享乐的观赏品味,折射了李安在西方语境中的父权现状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传统父权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尴尬和无奈。在历时性审视的基础上,李晓灵、王晓梅进行了空间生产和身体言说为主体的共时性考察,两位研究者认为,上海、北京等城市显然已成为民族家国话语、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图景的指代。二人从民族家国的失落与身体的焦虑、政治化隐喻与身体的缺席、无地域性想象与身体的迷失三个方面,彰显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畸形繁荣的大上海城市欲望本我、道德自我和理性超我的历史冲突。
三、身体写作研究
在“身体写作”这一研究类别中,导演对于身体的书写脱离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公共话语和宏大叙事,转而关注和诉说女性的私人体验。侧重女性的自我表达与书写。
“身体写作”是女性为拒绝男性话语的压制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策略,其首要贡献就是集中从身体的层面对男性话语封锁进行了突围。“身体写作”坚守女性立场,秉承性别反思和性别抗争的创作态度,倡导一种推翻男权中心话语的新语言,从而让鲜活的女性生命体验得以涌动和表述。尽管它的叙述对象主要是纸质的文学文本,但随着文学式样的翻新,在当下国内电影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女性在影视文化中的作用,她们可以直接以身体来叙述,因此女性“身体写作”在电影中具有了决定的意义。国内有关女性“身体写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电影个案的研究。例如,张莹的《女性:生存与文化的困境——黄蜀芹电影作品论》、许苏和梁长荣的《“女性写作”视域下的自我表达——徐静蕾电影中的女性意识探析》以及徐雅宁在《还没盛开就要枯萎吗——试论徐静蕾作品半途而止的女性写作》。
张莹认为,女性导演以“回到自己的屋子”的“身体写作”方式,使女性寻找自己话语的叙事策略得以完形,并通过独特的经验内容对男性话语提出挑战。赵凤玲在研究徐静蕾电影时指出,徐静蕾以自己的身体语言,在银幕上书写具有独立人格理想和文化精神的主体形象,这是中国电影文化的一大进步,肯定了女性言说自我和塑造主体的更多可能性。但是“身体写作”理论在当前的影视文化中出现了误解和歪曲:“身体写作”的初衷是为了提倡妇女解放,但到后来却演变成束缚妇女解放的一把枷锁。徐雅宁发现了徐静蕾作品中存在着“女性写作”不彻底的问题,以及“反男权”叙述的欲语还休、对男性归宿的欲拒还迎等现象,甚至还体现出向消费文化审美误区滑落的趋势,并提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已不再是物质的匮乏和机会的缺失,而是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供借鉴。这是女性导演对“女性写作”创作实践的浅尝辄止的原因。
【注释】
①王士霖.当代中国电影研究述评[J].文化艺术研究,2015(03):88-92.
②吴秀瑾.化品味与庸俗批判:布尔迪厄文化思想论判[J].东吴哲学学报,2001(04):241-282.
③张再林、王建华: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与刘宗周的“意”的学说[J].江海学刊,2016(04):30-40.
④刘辉.影视媒介中国家形象的构建[J].学习月刊,2013(01):34-36.
⑤汪振城.电影空间中影像身体的美学功能[J].中州学刊,2014(03):166-171.
⑥王士霖.当代中国电影研究述评[J].文化艺术研究,2015(03):88-92.
⑦粟世来.消费主义与审美生活转向[D].华中师范大学,2006:4-5.
⑧洪艳.从身体美学看文学经典的影像存在[J].中州学刊,2009(02):231-234.
⑨刘丹.身体的图像——2010年以来青春电影的身体叙事[D].陕西师范大学,2016:16-18
⑩黄宝富.论体育电影的身体美学[J].当代电影,2008(03):1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