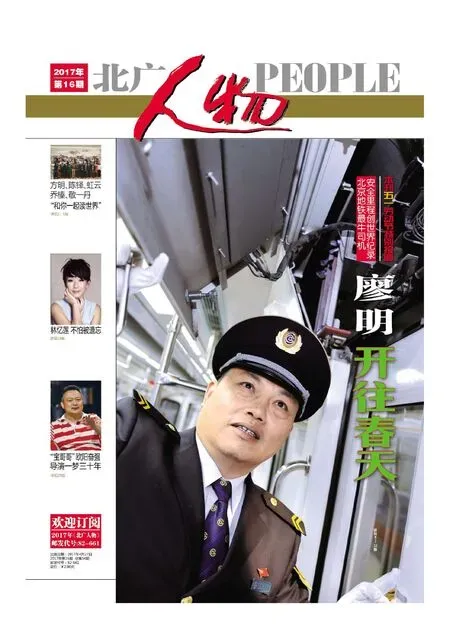史铁生:有限中的无限可能性(上)
2017-11-15
史铁生:有限中的无限可能性(上)
本文的作者朱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1968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写小说。1978年至1983年在《中国青年》当记者。1983年至1993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当编辑、编辑部副主任,曾在《人民文学》推出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1988年至1989年在《读书》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因喜好古典音乐,于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了《爱乐》杂志,并以笔名林逸聪编著了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起,开始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是1979年,先读到《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与《午餐半小时》,再骑车找到雍和宫大街26号,认识史铁生的。这两篇小说是铁生创作的开端。雍和宫大街26号院很小,容不得树,两间房,前后屋,有一小段轮椅通道,铁生住在后屋。那时他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常为他阻客,还不熟时,我每次去,他都是在很不情愿的前提下,才给我开门的。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最早发表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办的内部杂志《春雨》上,原叫《之死》。铁生那时和刘树生、刘树华兄妹走得很近,这小说似乎是刘树生拿到《春雨》的。在这本《春雨》上,还发表了刘树生的《爱笑的人》和刘树华的《感情》。《感情》是我到《中国青年》后,经手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午餐半小时》则最早发表在西北大学的《希望》上,《希望》是当时办得很火的一本大学生文学杂志,主编方兢。他也是曾到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
这两个篇幅都不算长的小说,其实写的都是尊严问题。
在《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中,法学教授称“之死”,这个“之死”来自契诃夫的《一个官员之死》,指卑微。铁生写了"文革"批斗会上,教授夫人因同情“走资派”而引发的恐惧,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先从容不得欺骗到陷入欺骗,后又背上难堪的符号,得了脑血栓,终因精神紧张、无法松弛而死去了。这个"死"其实是尊严的丧失,铁生感慨的是一个知识群体的悲哀,他的小说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一开始写,就有执着的思辨要表达。小说中“之死”的夫人“用自由言论把言论的自由弄丢了”的见解,今天读来仍然深刻,“本来他还可以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自从他自由言论了后,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这是典型的史铁生式的诘问。
《午餐半小时》表面看只是描述了类似“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那种感觉——那些如泥塑、草芥般,本来在沉闷沉睡的空间里似乎连嘴脸都没有的众生们,到午餐半小时时才一一苏醒过来,有了自己的鼻子眼睛,真实的脸上油彩。最后,一声悠长的“冰棍儿”,又将人们从忘我中抹杀回到泥塑中去。这是在低矮的老屋里劳作的底层的百姓,且都已年过半百了,唯那“瘫痪的小伙子”,还没有回到泥塑中去,这个“瘫痪的小伙子”应该就是铁生自己吧。铁生尝说,一个人的活,是因为他还在辨别“活的是个什么劲儿”。在这个黯然的空间里,他有一种自尊要被淹没的感觉。我去过那个街道小作坊,他在那里画过彩蛋,画过仿古家具上的图案。沿着雍和宫的红墙,胡同很窄,进到屋里,确实看不清人的脸色表情。最早见铁生的记忆,我就定格在他离开小作坊,与我一起回家的场景——从他那个小小工作台上下到自己的轮椅里,手提起空空裤管里那条没有知觉已经萎缩了的腿,收拾好那些管子,然后摇着轮椅出屋。
出了屋就感觉阳光格外的亮。那时,胡同里还没有那么多人,他摇着轮椅,膝盖上盖一件旧棉袄。我推着自行车,雍和宫红墙衬托着我们。宫里有檐角的风铃声传来,上空有清亮的鸽哨,这是他小说里常写到的。回到家,他父亲开门,他把车摇进小屋,把自己从轮椅挪到床上,他不愿别人帮忙。我能感觉到他的敏感,他不愿看到哪怕是朋友同情、安慰的眼光,这就是他的自尊。他不愿让人视他为残疾,因为,视为残疾就有安慰,有安慰就意味着不平等。他后来写过一篇短文叫《康复本义断想》,他说,康复的本义应是,使残疾人“失而复得做人的全部权利、价值、意义和快乐”。
《午餐半小时》后,他又写了《没有阳光的角落》。写一个单纯、天真的女孩王雪像一束强光,照亮了这个本无光照的低矮作坊。当初我读这篇小说,被感染的是其中的歌声——舒伯特的《菩提树》、伊萨科夫斯基的《灯光》,还有《老人河》,都是《外国民歌200首》里的。这是音乐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出的一本老书,在各地知青中流传很广。铁生没残疾前,本是喜欢唱歌的,小说里的王雪说他是男低音。但残疾后,我只看到他自我释放的那种憨厚的解嘲般的笑。《没有阳光的角落》里写得最传神的是王雪那“咯咯咯”的笑,“原来人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她“轻轻晃着头找鼻子”。我想,这一定是铁生凝固的少年记忆,因为这笑,这女孩一下便跃然纸上了。这女孩特别不愿意“我们”说“你们和我不一样”,铁生在小说里总是强调“我们”“以攻为守式的防御”,对尊严的保护,是他最早创作的主题——“既然灵魂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何必还在人的躯壳里滞留?”那时他的内心还不足够强大,所以他要求"一切肉体生而平等"。
铁生的早期小说,大家都觉得好,都希望能经自己的手,在正式刊物上发表。当时我在《中国青年》,先递交《午餐半小时》送审,部主任深表遗憾地说:“调子实在太灰暗了。”又递交《没有阳光的角落》,当然还是摇头。那是多青春的一篇小说啊。结果,先是1979年的《当代》,在创刊第二期就发表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后是1980年贵州的《花溪》发表了《午餐半小时》;再是陈浩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季刊》后,发表了《没有阳光的角落》(因为“阴暗”,就把标题改成了《就是这个角落》。1985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第一本小说集时,改为《我们的角落》,还是没有恢复本名)。我经手,1982年才在《中国青年》发表了《绵绵的秋雨》,也被改得面目全非。
《绵绵的秋雨》写一个到了美国的游子回乡,在绵绵秋雨的背景下,面对一个被欺骗的母亲。她儿子在“文革”武斗中被打死了,却一直骗她是烈士。我喜欢这小说里同样被凝固般的夕照下那片面对着儿童游乐场的沉静的柏树林。铁生的小说、散文里,魂牵梦绕着这片树林。我觉得小说里那个母亲就是常痴痴地到地坛找他的,他的母亲。因为这小说与他的第一篇散文《秋天的怀念》几乎是同时写的,那是他篇幅最短,也最感人的文字。
《绵绵的秋雨》里贯穿着一首美国民歌《梅姬,当你和我年轻的时候》,这是《外国民歌200首续编》里的。我从这首歌里能感知到铁生深藏的情意绵绵。这小说里有鸽哨与雍和宫的风铃,以此为伴奏,写到“我”对往事的“恨悔”——14年前因为胆怯,没爬上楼顶,导致了“大勇”的死亡。写这小说是1981年,14年前是1967年,那个武斗中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7年后,1988年我编《东方纪事》时,铁生给了我一篇《文革记愧》,写到他一直不能释怀的“愧”是:1974年因为B拿来了一个手抄本,他读过并抄过后,又传到了C的手里,结果事发,殃及池鱼。他写了他在考虑应对的过程中,如何“一次比一次胆怯”,终因不能担当,而向警察交代了将小说传递给他的B,还写了他内心保护自己谴责的过程。1988写1974,也是14年,看来这事在铁生心里真的盘桓不去。他外表豁达,其实内心对自己很严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约谁的内心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愧,而真将其刻在心里的大约也少之又少。铁生是一个活得太重的人,他宽恕别人,却不宽恕自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