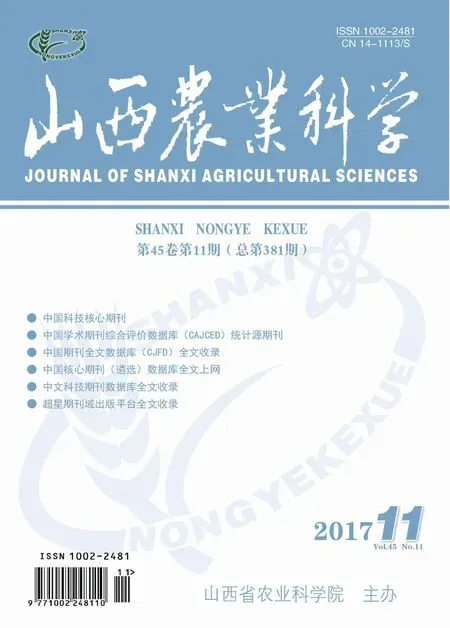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对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2017-11-14秦晓娟
秦晓娟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对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秦晓娟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在明晰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特征的基础上,规范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实证研究1995—2013年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异质性通过农业生产主体的市场化意识、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效率及农业产业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工资性、经营性及转移性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但未影响财产性收入;多重收入的深刻变化导致收入结构变动,因此,应培育农业经营主体市场参与意识及能力、科学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升级农业生产条件、破解土地流转的价值定价难题、激励农业生产参与“互联网+”市场,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促使其发挥增收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生产效率;生产条件;收入结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2个方面。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逐步完善,农业经营主体由改革初期相对同质性的家庭经营主体向现阶段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等在内的多类型新型经营主体逐步转变,新型经营主体与传统经营主体的异质性必然带来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深刻变动,进而引发收入结构变动。与中部其他5个省份相比,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除在2006年之前的一些年份高于安徽和河南2省农村居民外,2007—2015年均处于中部最低水平,且差距呈扩大趋势。因此,选取山西省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解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对山西省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变动的影响机理,探讨山西省农村居民增收对策,为缩小山西省与中部其他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参考。
国外学者,如BECKER等[1-4]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原因提出了一些解释,观点可概括为:随着农业科技进步与生产效率提高,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释放出的劳动力转移至其他产业,带来家庭资源配置行为与收入结构的相应变化;农业部门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农业收入份额下降;随着城镇人口迁入乡村社区,农业区的人口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改变;伴随农业人口接受教育与培训水平的提高,就业选择范围扩大;经济条件改变,促使农村居民家庭采取避免收入大幅波动的措施;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使得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迅速,也便利了农村人口进城就业。
国内学者主要从原因与结果等方面研究农村居民收入结构问题。张凤龙等[5]研究指出,个别省份农业收入比例因政策性因素有所回升只是暂时现象,不能改变收入增长结构的非农化趋势;张车伟等[6]分地区观察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发现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单一化。白凤娇[7]研究认为,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马凌等[8]分析了产业比较优势转换、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城市化水平提高等经济规律对农民工资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
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现有研究成果侧重分析农民收入结构演变与单一影响因素的关系,而未能结合特定历史背景、宏微观经济规律,就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效应的深层、本质原因及规律进行全面系统分析。鉴于此,基于国内外农民收入结构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从生产条件、生产效率及生产产品等层面解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影响机理,寻找农民持续增收根本着力点;进而依据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山西省经营体系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既可以在理论上丰富农民增收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关理论,又为统筹城乡发展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结合国家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相关政策,立足山西省特色农业发展,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创新,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优化、收入水平持续增加提供参考依据。
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对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1.1 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演变特征
1.1.1 不同来源收入构成比例 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构成比例(表1)显示,1995—2015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是农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但二者之和呈下降态势,2015年达到最低值,为79.82%(因调整统计口径,2014年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与2013年之前缺乏可比性,但其差异主要在于转移性收入,故区别分析不同来源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构成比例稳步上升,2015年较1995年上升21.67百分点,从30.39%上升至52.06%,2010年开始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构成比例,成为最主要收入来源;家庭经营纯收入构成比例逐年下降,2015年较2000年下降30.68百分点,从58.44%下降至27.76%,从2010年开始,家庭经营纯收入由第一主要收入来源成为第二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比例的增长及家庭经营纯收入比例的下降映射了农村产业结构的非农化转变和就业结构的演进,反映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升级优化情况。1995—2015年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远低于工资性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且财产性收入占比最小。其中,财产性收入比例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动特征,2015年较1995年下降0.39百分点,2002年占比为最低值(0.71%),2009年占比为最高值(4.83%),反映出财产性收入增收的艰难性。1995—2013年转移性收入占比呈上升态势,2013年较1995年上升7.67百分点,从3.09%上升至10.76%;2014—2015年转移性净收入占比均超过18.50%。

表1 1995—2015年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构成情况[9-10] %
1.1.2 不同来源收入的增长率及其对人均收入的拉动度 山西省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增长率(表2)显示,除1999年以外,1995—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均为正,年均增长率为9.55%;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均为正值,年均增长率为12.69%;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率出现正负波动变化,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20%,9.26%和15.07%。年均增长率最大的为转移性收入,其次为工资性收入,最小的为家庭经营纯收入。
从不同来源收入对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拉动度来看(表2),工资性收入的拉动度均为正向,其他三类来源收入的拉动度有正有负;工资性及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拉动度远大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2008年以来,工资性收入的拉动度大于家庭经营纯收入。

表2 1995—2013年山西省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增长率及其对人均纯收入的拉动情况[9-10]
1.2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对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变的影响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2个基本面下,农业生产主体、生产条件、生产效率及生产产品等较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均发生质变,进而对不同来源收入产生影响。
1.2.1 提升生产主体的市场化参与程度 相较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化参与意识及参与程度高,体现于广义生产过程的各环节。首先,参与生产资料市场,如购买所需的农用机械、化肥、农药、农业信息等;参与劳动力市场,雇佣职业农民进行生产加工,聘请专家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参与金融市场展开借贷活动[11];参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开展规模土地经营。其次,作为农产品供给者,参与农产品需求信息市场,形成合理价格预期及销售预期。1.2.2 促使生产条件社会化、现代化,从而确保生产效率高效化 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重农业生产条件社会化、现代化,表现为生产安排的资本化、市场化运作。首先,劳动力的社会化、职业化。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意味着劳动力生产要素发生质的飞跃,劳动分工专业化程度越来越精细。其次,生产设备的专业化、现代化。农产品的种植、加工生产设备的机械化、专业化程度提升。再次,生产组织社会化、现代化。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使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和服务职能的差异性凸显,进一步促使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合力”效应发挥。最后,生产产品流通社会化、现代化。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农产品的流通渠道的社会化程度提升,物流体系的现代化技术程度不断提高。以上生产安排的资本化、市场化运作使土地、劳动、资金生产率均得以有效提高,从而对农业生产增收带来深刻影响。
1.2.3 提高农产品的产业化、市场化程度 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农产品的市场化竞争力显著加强。其表现为:首先,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加快,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其次,农产品流通成本降低,农产品价格优势显现。再次,农产品的流通时间缩短,增强农产品的变现能力。随着农村“互联网+流通”行动的深入实施,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从而在保障农产品的绿色、健康品质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以更快速度销往更广范围的地区,农产品的市场渗透力加强。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化参与程度、生产条件社会化及现代化程度、农产品市场化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会促使该家庭生产经营收入的提高,同时,根据其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的政策性生产补贴、救灾款等转移性收入也会随之提高;另一方面会使职业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及土地经营权流出方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类经营主体的市场化参与程度、生产条件社会化及现代化程度、农产品市场化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会促使就业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及土地经营权流出方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各类收入的变动势必导致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2 农业经营体系变动对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2.1 农业经营体系变动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指标确定及数据说明
笔者设计以下指标来反映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1)农村土地经营规模(X1),即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值越大表明农业经营者的规模经营程度越高,其市场参与程度越高[12]。(2)农业现代化(X2),即有效灌溉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值越大表明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条件的现代化水平越高,普及范围越广。(3)农业生产效率,包括农业劳动生产效率(X3)和农业土地生产效率(X4),前者即农业生产总值与农业从业人员比值,反映了劳动力参与生产的效率,值越大表明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越高;后者即农业生产总值与总播种面积的比值,反映了土地要素参与生产的效率,值越大表明农业经营土地生产效率越高。(4)农产品的流通效率(X5),即狭义流通业中的批发零售业的增加值与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每单位农业生产总值所能支撑的批发零售业的增加值,值越大表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越高。根据不同收入来源,设置以下指标反映收入结构情况:工资性收入(Y1);家庭经营纯收入(Y2);财产性收入(Y3);转移性收入(Y4)。实证分析取1995—2013年为样本期间(此样本虽然没有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及发挥作用的时间,但鉴于各变量从传统到新型是一个渐进变动过程,故依然能分析出新型经营体系的本质对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效应),所有水平值均为实际值(1994年=100)。
2.2 计量模型
实证计量分析采用Eviews 7.0软件,拟合多元回归方程。

式中,β0,βj为待估参数,u1为残差。各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列于表3,可知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被解释变量序列和解释变量序列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综合考察模型的经济理论意义和统计学检验结果,确定最终模型如表4所示,除变量所在模型协整关系不成立外,其他各模型中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成立,表明模型设定合理有效。

表3 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表4 模型拟合结果
2.3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农业经营体系的变动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化意识、生产条件、生产效率及农业产业化程度等因素对不同来源收入产生不同影响效应。
2.3.1 生产主体市场参与程度因素的影响效应第一,与工资性收入的相关性关系不成立,对家庭经营纯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原因主要是:现阶段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形式的新型农业主体并未从根本上取代传统农业主体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其市场参与程度更多地体现为自身收入的变动,并未对雇佣农民,尤其是大范围的农村居民获得工资性收入产生影响,且其对家庭经营纯收入增加具有抑制作用,暗合现阶段农业经营主体市场意识较为薄弱,已经不能推动家庭经营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必然被市场意识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取代。第二,对转移性收入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证实政策性生产补贴与家庭经营规模间的相关关系成立。
2.3.2 生产条件、生产效率因素的影响效应 第一,生产条件因素仅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增收效应,生产效率因素未体现对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收效应。表明生产条件因素仍然是限制农业生产性收入提高的最主要方面。第二,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因素对工资性及转移性收入具有显著增收效应。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提升外出务工而放弃务农收入的机会成本,促使外出务工者搜寻更高工资性收入机会;同时,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更加节约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外出务工创造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时间资本,从而提升工资性收入。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因素通过政策性生产补贴、生活补贴对转移性收入产生增收效应。第三,农业土地生产效率因素未对各种来源收入产生增收效应。这反映出:一方面,现有生产条件下的农业生产仍在较大范围内处于粗放式的土地耕种状态,土地生产效率未产生本质提高,并未提高外出务工而放弃务农的机会成本,且未对家庭经营纯收入产生实质性提高效应;另一方面,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而言尚未形成稳定性收入,反映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的弱势性。
2.3.3 农业产业化程度因素的影响效应 第一,对工资性收入具有增收效应。农业产业化程度提升有利于增加农业工人就业机会,进而增加工资性收入;有利于加速农产品的市场流通,越易增加价值从而提高务农收入而使务工收入的机会成本上升,致使工资性收入上升。第二,对家庭经营纯收入未产生增收效应。由于农业生产成本投入居高不下,导致家庭经营纯收入增收困难。第三,对转移性收入具有增收效应。农业产业化程度提升及农产品的市场流通越快,促使通过农产品生产及销售获得的政策性生产补贴越多,从而转移性收入越高。
2.3.4 标准化系数分析 第一,农产品市场参与程度、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变量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应依次递减。从侧面说明,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较农业生产效率因素对工资性收入造成的影响效应大。第二,生产条件、生产主体市场参与程度变量对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影响效应依次递减。表明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应注重提高农业生产主体的市场适应性。第三,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农产品市场参与程度、生产主体市场参与程度对转移性收入的影响效应依次递减。表明对农村居民的政策性生产、生活补贴的标准制定应在依据农业生产效率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考虑农产品及生产主体的市场化程度差异,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政策补贴成效。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3.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1995—2013年山西省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相关数据,发现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工资性收入成为最主要收入来源,其构成比例不断上升,对人均收入增长的拉动度最大;家庭经营纯收入成为第二主要收入来源,其构成比例不断下降,对人均收入增长的拉动度呈正负波动性变化;非生产性收入呈扩大趋势,对人均收入增长的拉动度较工资性和家庭经营纯收入小,且呈正负波动性变化。
农业经营体系变动对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农业生产主体的市场化意识、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效率及农业产业化程度等因素对工资性、经营性及转移性收入产生不同影响效应,但并未对财产性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3.2 政策建议
上述结论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应以农业生产主体的市场化意识、农业生产效率、生产条件及农业产业化程度等为着力点,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以使其发挥增收效应。首先,培育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市场参与意识及能力,促使其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成为参与市场活动、积极应对市场风险的生产者。第二,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科学合理配置,发挥职业农民、土地、资本、农业科技信息及新型主体管理经营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最优价值,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第三,改善升级农业经营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业深加工生产线、农产品物流业等的现代化水平,实现工农发展一体化。第四,激励农业生产及农产品流通等各环节参与“互联网+”市场,彰显山西省农产品的文化、绿色、杂粮等多重特性,提升其市场价值。
[1] BECKER GRAY S,MURPHY KEVIN,TAMURA ROBERT.Human capital,fertility,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12-37.
[2] TIMOTHY JAMES HATTON,JEFFREY GALE WILLIAMSON.What explains wage gaps between farm and city?exploring the todaro model with American evidence,1890—1941[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2,40(2):267-294.
[3]MICHAELSOFER.Pluriactivityin the Moshav:familyfarminginIsrael[J].Journal ofRural Studies,2001(17):363-375.
[4] BJORN GUSTAFASSON,LI SHI.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ies in rural China 1988 and 1995[J].Journal of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69:179-204.
[5]张凤龙,臧良.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研究[J].经济纵横,2007(7):2-5.
[6]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分地区对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的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2004(1):2-13.
[7]白凤娇.关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动态分析:以陕西省1995—2011 年数据为样本[J].经济问题,2013(5):66-68.
[8]马凌,朱丽莉,彭小智.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成因与优化对策[J].华东经济管理,2011,25(12):16-20.
[9]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10]山西统计信息网.山西统计年鉴[EB/OL].[2017-08-04].http://www.stats-sx.gov.cn/tjsj/.
[11]秦晓娟.从流通过程看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本质[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13(5):475-481.
[12]秦晓娟,许译文.山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9):9-14.
Eff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on Income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s in Shanxi Province
QINXiaojuan
(College of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gu 030801,China)
Based on clarityofthe characteristics ofrural residents income structure ofShanxi province,the article gives a normativ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new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on rural residents'income structure,and giv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on rural residents'income structure from 1995 to 2013,by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in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through the market consciousness of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ers,the condition and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e,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wage income,household income,and transfer income except the property income.These income changes lead to alterations in income structure,therefore we should cultivate agricultural managers'market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dispo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upgrad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s,driv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participate the"Internet+"market,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to exert great influence in raisingincom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r;new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production efficiency;production conditions;income structure
F328
A
1002-2481(2017)11-1871-06
10.3969/j.issn.1002-2481.2017.11.34
2017-08-04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2015)
秦晓娟(1982-),女,山西长子人,讲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