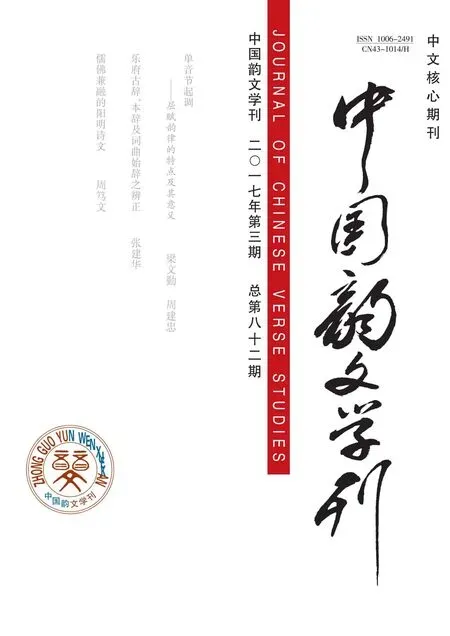说“玉衡指孟冬”
2017-11-14黄瑞云
黄瑞云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2)
说“玉衡指孟冬”
黄瑞云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2)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后期的作品,而非西汉之作。但十九首中有《玉衡指孟冬》一句,前代注家认为这句诗反映的时令用的是汉武帝太初以前的历法,因而证实十九首是西汉的怍品。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玉衡指孟冬”句中,“孟冬”是“孟秋”之误。
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孟冬;孟秋
《古诗十九首》是《文选》著录的第一组成熟的汉代古诗,但具体产生在什么时候,西汉还是东汉,却长期成为疑问。钟嵘《诗品·总论》云:“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他们先笼统地推定古诗出于两汉,而不断定其具体时间。然钟嵘又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刘勰也说:“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尽管他们用存疑的语气,实际上都否定了十九首出于西汉之说。《文选》李善注云:“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叔,疑不能明也。诗云‘出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词兼东都,非尽是乘作明矣。”李善同样采取存疑的态度,但明确指出了“词兼东都”的证据。
任何一种文体,其定型成熟之作,不可能产生在这种文体萌发之时,更不可能产生在这种文体萌发以前。西汉时代还没有十九首这样定型成熟的五言古诗。钟嵘、刘勰都说西汉之时,“吟咏靡闻”“莫见五言”。据十九首的内容和风格,特别是和东汉乐府的渊源,《古诗十九首》只可能是东汉作品,而且是东汉后期之作。
然而梁代徐陵《玉台新咏》竟有枚乘《杂诗九首》,其中却有八首见于《古诗十九首》。枚乘是汉文帝、景帝时人,如果这些诗确系枚乘所作,则与上述结论直接抵触。按,《玉台新咏》所录,每多错误,《杂诗九首》便是错误最为突出的一例。第一,西晋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其中十一首拟《古诗十九首》中的作品。可知《古诗十九首》这组古诗在魏晋时代即已逐步形成。所谓枚乘《杂诗九首》,就有八首在陆机拟作范围之内。陆机所拟的每一首,都标明是拟古诗的某一首,如《拟行行重行行》《拟今日良宵会》等等,并没有说是拟枚乘之作。第二,钟嵘说“自王杨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点明了古诗中没有枚乘之作。刘勰也说汉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中,“辞人遗翰,莫见五言”。“辞人”无疑包括枚乘,同样说明古诗中没有枚乘作品。第三,十九首其八《冉冉孤生竹》,刘勰说是东汉傅毅之诗,《玉台新咏》也归之枚乘杂诗,足见其何等混乱。第四,昭明编《文选》,诗作凡主名清楚者皆标举明白,而《古诗十九首》并无标有枚乘之作。与昭明关系密切的徐陵,有什么理由认为十九首中竟有如此之多的作品是枚乘的杂诗呢!由此可以断定《玉台新咏》所录《杂诗九首》,同《古诗十九首》其他作品一样是佚名作者的古诗,不可能是枚乘之作。至于《玉台新咏》何以会出现这种错误,我们今天已无法弄清楚了。
《古诗十九首》不是西汉作品,应该可以确定。但十九首中《明月皎夜光》篇有“玉衡指孟冬”一句,前人认为这句诗反映的时令用的是汉武帝太初以前的历法。如果这种解释成立,则十九首只能是太初以前的作品,同样与前述结论直接抵触。——由此有必要对“玉衡指孟冬”这句诗进行探讨。
《明月皎夜光》篇全诗如下: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北斗七星中第五星曰衡,即玉衡,第七星曰杓。由第五星至第七星组成斗柄。北斗在它的位置上旋转,每个月斗柄指向不同的方位。夏历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古人又把周天划成十二宫,与月建配合。北斗玉衡(即斗柄,又曰招摇)指向哪一宫即哪一月。如正月建寅,斗柄即指寅。故观察斗柄所指的方位,即知道当时是什么月分。玉衡指孟冬,即斗柄指亥,时为夏历孟冬十月。然诗云:“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全是秋天物候,与“玉衡指孟冬”时令不符。
《玉衡指孟冬》李善注:“《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摇指申。’然上云蟋蟀,下云秋蝉,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汉高祖以十月为岁首,到武帝太初元年才改用夏历,以正月为岁首。李善以为太初之前,十月为岁首,故太初之前的孟冬,即太初之后的七月。按照李善的解释,“玉衡指孟冬”的孟冬实际是夏历七月。之所以称为“孟冬”,因为用的太初之前的历法,也就足证诗作于太初之前,并与“或称枚叔”的年代相符。“孟冬”既是夏历七月,写的是秋天的物候也就正常了。后世注家认定《古诗十九首》出于西汉者,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根据李善对这句诗的解释。
然而李善的解释是错误的。无论十月为岁首还是正月为岁首,只是人为规定岁首的月份不同,并不能改变春夏秋冬四季自然时令的前后。因为春夏秋冬是由立春、雨水等二十四节气即由自然气候的变化决定的,并不受岁首人为地变易的影响。我们来查一下《汉书》中的纪年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试看《高帝纪》: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注引如淳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为岁首。”
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
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
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
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
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
春正月,羽击田荣城阳。
夏四月,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
秋八月,汉王如荥阳。
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
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这里只录了高帝前三年的纪年记事,其他年代纪时方式完全相同。汉高祖以十月为岁首,仅仅是纪年从十月开始起算,不仅没有因改变岁首而改动春夏秋冬的实际时间,连月份也没有改动。纪年中每年岁首都称为“冬十月”,并没有改称“春正月”。而纪年中的“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仍和夏历完全相同。直到汉武帝时代也仍然如此。自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岁首都称为“冬十月”,也不称为“春正月”。武帝从太初开始,改以正月为岁首。然太初元年岁首仍在“冬十月”,真正以正月为岁首在太初二年,从此岁首即称为“春正月”。因此根本不存在“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事实,“今之七月”决不能称为“孟冬”;孟冬仍然在建亥之月,即夏历十月,太初之前如此,太初之后也如此。
李善注所说可能是唐代人的共同看法,因为《汉书·高帝纪》“春正月”颜师古注云:“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这与李善之说相同。也就是说,《高帝纪》中的“元年冬十月、二月、夏四月、五月”之类是后人改的。颜师古注是颜师古的理解,即使颜师古之说有据,原文也只可能是“元年正月、五月、七月”等等,而绝不可能是“元年春正月、夏五月、秋七月”等等。因为月分份序数可以人为地改变,春夏秋冬自然时令是不可改变的;如前所述,四季是由自然节气决定的,无法人为改变。假定当初的十月可能称为正月,也绝不可能称为“春”正月,因为时令仍然是冬天,所谓“月改春移”之说绝对是错误的。正如我们现代用的阳历,二月才立春,但一月二月三月只能称为第一季度,不能称为春季,春季应是阳历二月三月四月。由此可知,诗中“玉衡指孟冬”,孟冬不可能是太初以后的七月,而只可能是十月。李善的解释不正确,也就不能证明诗作于太初之前。
近人对诗中“玉衡指孟冬”写的是秋天物候也有不少曲说。如金克木、马茂元并谓天空的十二宫,与四季配合:“孟冬代表星空中的亥宫,并非实指十月的时令。”“仲秋八月,玉衡夜半指酉,但现在已过了夜半的两三个时辰,玉衡渐渐移向西北,经戌宫指向亥宫了。因此,‘玉衡指孟冬’,是从星空的流转说明秋夜已深。”(见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此说极其错误,决不可信。玉衡在每个月所指的方位是固定的,其角度偏转是逐渐进行的,每月只指一宫,绝不是一夜之间流转数宫。如果不相对固定,一夜之间流转数宫,则用玉衡所指来定时令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者,金马二公认为十二宫除子丑寅卯之类的名称以外,同样有孟春孟夏孟秋孟冬之类的名称,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根据。
几十年前,俞平伯也曾解释此句。旁引陆机拟作“招摇西北指”句,招摇是斗柄的别名。“招摇西北指”与“玉衡指孟冬”意思完全相同。据《淮南子·天文》,斗柄所指,西北是夏历九月十月之交的方位,正西北则是立冬的方位。诗说“玉衡指孟冬”,当作于夏历九月立冬以后。俞氏之意,谓九月自然还有秋令物候;而其时又已立冬,故可称为“孟冬”。(见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
这是为了将诗称“孟冬”而诗中所写是秋令物候两者加以牵合。然而牵合毕竟是牵合,并不能真正解决两者的矛盾。孟春、孟夏、孟秋、孟冬之类的名称,从来只用于它们通常所指的那个月。孟春即正月,孟夏即四月,孟秋即七月,孟冬即十月,并不从哪个具体的节气到来的日子算起。比方,如果九月二十五日立冬,孟冬只指十月,而不从九月二十五日算起。同样的道理,如果十月十一立冬,孟冬也泛指十月,并不因十月前十天尚未立冬就算在孟冬之外。此其一。其二,既是孟冬,哪怕是九月立冬,也不会有秋令物候。《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仲秋之月,“鸿雁来,玄鸟归”。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群燕辞归雁南翔。”这是古人的记载。我们从现实观察也仍然如此。中原地区“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绝不会拖到立冬以后。何况句中明白点出了“秋”字。
还有人说,陶渊明《九日闲居》诗也有“往燕无遗影”之句,与“玄鸟逝安适”句意相近,因此如果九月立冬而仍见燕归并非不可能。此论也是错误的。陶诗“九日”在九月上旬,即使九月立冬也必在九月下旬,两者相隔一个节气。关键还在于,陶诗“往燕无遗影”是说南归的燕子已去得没踪影了,古诗“玄鸟将安适”是问燕子将去向何方,两者有“早已离去”和“将要离去”的差异。怎么能混为一谈呢!何况陶渊明家在江西,与中原地区相距千里。江南地暖,北地风寒,陶渊明家乡的燕子可能比北方离去较晚,因此更不能用陶诗证明北方九月立冬以后尚见燕归。
上述分析,辩证了前人所谓诗中“玉衡指孟冬”实指夏历七月的错误,孟冬只可能是夏历十月;也辩证了今人所谓“孟冬”可能指夏历九月立冬以后因此仍可能有秋天物候的曲说,夏历九月不能称为孟冬。
排除了各种曲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这句诗错了一个字,“玉衡指孟冬”当作“玉衡指孟秋”,“冬”字是“秋”字之误。——就因为一个词的错误,使历代注家判断《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间提前了几百年,并对诗中词句作了不少的曲解。人们或许会问,说“孟冬”是“孟秋”之误,你也没有任何不同版本或异文作为佐证,是否为了支持《古诗十九首》不出于西汉而作的主观判断呢?绝非如此。断定此诗中“孟冬”是“孟秋”之误,有足够的理由:
第一,诗中“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玄鸟适安逝”,全是孟秋物候,与《礼记·月令》谓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完全一致。
第二,既说玉衡所指是“孟冬”,而“秋蝉鸣树间”句中却点明为“秋”令。一首诗中,写同一时令,既说是“冬”,又说是“秋”,两者必有一错。用全诗所写物候判断,只能是“孟冬”系“孟秋”之误,而“秋蝉”绝不会是“冬蝉”之误。
第三,十九首之十七《孟冬寒气至》篇,说其时“寒气至”“北风惨”,确是冬日景象;而《明月皎夜光》篇同样说是“孟冬”,而其时却“秋蝉鸣”“玄鸟逝”,纯是秋天物候。一组诗中,两篇作品,同写“孟冬”,时令物候不应如此绝然不同。如果后一篇写的是“孟秋”,两者各适其所适,就没有矛盾了。
第四,诗中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二句,尽管是用典,且系用作比喻,但必与当时所见天象一致。而且这两句与前文“众星何历历”相呼应,斗箕牛女同时使人感到“历历”明烂,必在天汉横空之际,其时正是孟秋七月。古人诗中凡涉天汉横空咏牵牛织女者,必在七月孟秋,绝不会在孟冬十月。
从诗中所写地上物候,天空星象,内部矛盾,两诗对比,都说明《明月皎夜光》篇写的不是孟冬,而是孟秋。由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断定:“玉衡指孟冬”当作“玉衡指孟秋”;自然也就推翻了用这句诗作为《古诗十九首》出于西汉的根据。
责任编辑 赵成林
2016-08-23
黄瑞云(1932— ),男,湖南娄底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I207.22
A
1006-2491(2017)03-0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