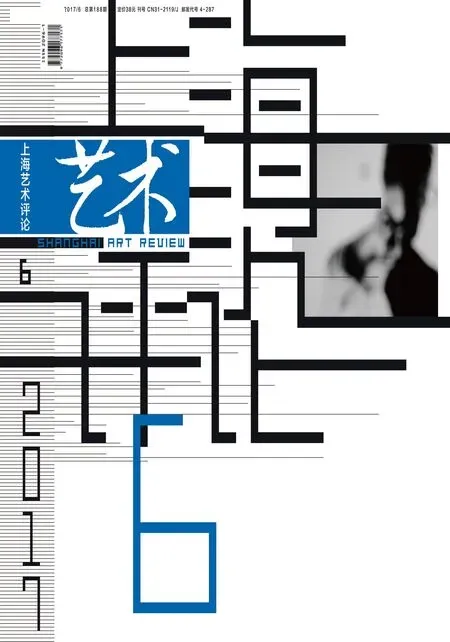《我是医生》:写实呈现与银幕赋魅的正向合力
2017-11-13杜梁
杜 梁
如何达成写实呈现与银幕赋魅这两种驱动力的平衡,仍然是当前国产人物传记片创作中存在的重要的问题。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产人物传记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如《孔子》过度注重商业诉求却忽略人物塑造,又如《中国合伙人》为表现对象过度赋魅。当下国内银幕急需启动对优质人物传记片的召唤,《我是医生》的登场正逢其时。
作为故事片的一个重要分支,人物传记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叙事驱动力的二元性:对真人实事的能动反映以及基于艺术想象的再创作。换言之,人物传记片的创制可以被表述为对人物本身这一容量巨大的“数据库”(真人实事)进行信息提炼和编码(艺术再创作)的过程,受众观影等同解码环节。就我国而言,除了历史、社会和政治语境变化的影响,人物传记片意图实现对银幕英雄的成功塑造,更需达成写实性呈现与想象性赋魅的关系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语境重焕新生的人物传记片,无论是表现对象的选择还是银幕形象的呈现,都受到了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毛泽东曾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一文艺创作路线在建国后迅速得到贯彻实施,表现英雄事迹和模范行为被视作“目前文艺创作上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一时期国产人物传记片选择的表现对象均属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辩证的角度看,当时的人物传记片创作也反过来为建设新中国的创世话语提供了具备象征意义与示范作用的银幕形象符号。《赵一曼》(1950)、《刘胡兰》(1950)、《董存瑞》(1955)、《宋景诗》(1955)、《李时珍》(1956)《聂耳》(1959)、《林则徐》(1959)《白求恩大夫》(1964)、《雷锋》(1964)等文本的主人公,或者是曾在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古人先贤,或者是具备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甚至在斗争中流血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或者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砥砺前行的劳动模范。总之,他们都可以被指认为民族记忆与时代任务的叙事承载者。
改革开放之后,国产人物传记片更为注重对表现对象的主体意识与心理活动的深层挖掘。无论是《孙中山》(1986)、《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周恩来》(1992)、《邓小平》(2003)等文本中的革命开拓者与国家领袖人物,还是《焦裕禄》(1990)、《蒋筑英》(1992)、《孔繁森》(1995)、《郑培民》(2004)、《张思德》(2004)、《杨善洲》(2011)等作品中的革命战士、科学家和干部楷模,这些银幕形象身上蕴含的“神性”光辉逐步消退,而表现对象性格中的人性面向则经由写实造型的方式进入银幕前景。走下“神坛”的主人公们面对民族危难与现实困境时产生的种种内心波动,以及他们面对生老病死、聚散离合时下意识的情绪外露,构成其性格维度中与普通观众的情感图谱相互重叠的部分。
如何达成写实呈现与银幕赋魅这两种驱动力的平衡,仍然是当前国产人物传记片创作中存在的重要的问题。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产人物传记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如《孔子》过度注重商业诉求却忽略人物塑造,又如《中国合伙人》为表现对象过度赋魅。当下国内银幕急需启动对优质人物传记片的召唤,《我是医生》的登场正逢其时。
作为表现对象的吴孟超身上所携带的浓厚的传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物造型过程中写实呈现与银幕赋魅的反向作用力。吴孟超在长逾七十年的从医生涯中,始终坚持以科学的“开路先锋”姿态不断进取,他最早曾灌注我国第一具完整的肝脏血管模型、开创“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发明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法、全球最早实施了肝中叶切除手术、创立了中国肝胆外科的学科体系……这些创举事实上构成了吴孟超的“英雄成长”叙事链条:如果将彻底消除肝胆癌症视为其职业生涯终极目标,那么他的从医之路就是不断发现障碍/病魔——克服障碍/病魔的循环往复,他也得到了属于英雄的奖励——来自国家和社会的认可。鉴于吴孟超以拓荒者姿态在肝胆医学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在200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1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第17606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孟超星”。
电影单片的容量显然难以穷尽吴孟超自身“数据库”中不胜枚举的传奇事迹。《我是医生》并非首个以吴孟超为表现对象的影像文本,此前关于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医者的纪录片、专题片已有很多。早在1964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吴孟超、张晓华和胡宏楷三人组成的医学攻坚小组攻克肝脏外科难关的事迹,拍摄了一部名为《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彩色纪录片。央视《大家》栏目曾分别在2005年和2015年制作了专题纪录片《吴孟超·中国肝胆外科开创者》和《吴孟超的李庄情缘》。2014年,上海电影集团出品了讲述吴孟超寻根之旅和从医之历程的纪录片《报国之路》。这些文本与《我是医生》存在互文关系,并共同构成了解读银幕吴孟超的作品矩阵:一方面,此类纪实影像可以用来验证《我是医生》确实按照写实呈现的方式进行基础的人物造型;另一方面,《我是医生》又深入到前者较少触及的个体日常生活领域,从吴孟超与师友、弟子、亲人的关系出发,进一步呈现人物自身具备的人性魅力。
《我是医生》从寻根记忆、医学开拓和精神传承三个层面展开了对银幕吴孟超的编码过程,若要实现对这一形象的有效解码,就必须建立起《我是医生》与互文文本的“超链接”。首先看吴孟超的双向寻根记忆。《我是医生》通过闪回的方式来追溯吴孟超在马来西亚割橡胶的童年经历,这是其他纪录性影像无法真实再现的记忆起点。由于当时马来西亚未曾设立华人高中,吴孟超开启了重返故国和原乡的首次人生寻根旅途,他也在这一过程中强烈地体味到国家孱弱则侨民饱受歧视的现实无奈。可以说,青年吴孟超的主体认同困惑必须在国家复兴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化解,这也解释了缘何报效国家是他人生奋斗目标的必须选择项。
《我是医生》较为注重对主人公日常工作的写实性呈现。影片开篇即通过一组手术室镜头的蒙太奇呈现出年逾九十的吴孟超无影灯下与“死神”争夺生命的身姿。此间有两处细节值得注意:其一,吴孟超在为病人施行手术时眼镜有滑落之势,他随即示意护士将之取下。对该情形的解释,可以从《吴孟超·中国肝胆外科开创者》中寻找到,按照吴孟超本人的说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累积,他早已能够凭借手感实现肿瘤剥离。其二,对比《向肝胆外科进军》与《我是医生》,从中可见国内手术室空间的现代化转型,当年甚至需要医生通过听诊器来监控病人的生命体征,如今多数医疗器械都可通过电力进行驱动。《我是医生》通过这些日常工作影像的不断聚集形成量变,最终形塑起严谨精诚的医者形象。
最后看以吴孟超为中继力量的三代医者的精神传承。吴孟超自其精神之父裘法祖身上习得医者的自我修养与科学素养,也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陈汉在相互鼓励中共抗病魔,当他因难以根治肝癌而无法纾解胸中苦闷时,仍旧选择通过意识完形的方式与记忆中的师友再度展开对话。对于《我是医生》而言,其他互文文本构成了最为贴近历史真相的记忆来源。吴孟超亲自动手为女儿做手术的前夜,医院走廊的电子屏幕在光影的流动中复现了他第一次尝试切除肝叶时,外科主任将手术刀传递给他的画面,这一极富传承意味的场景的纪实性影像资料,就存在于《向肝胆革命进军》的文本中。
《我是医生》并非是对主人公职业生涯的片段式回顾和总结陈词,而是再次以《向肝胆革命进军》式的人生豪情,刻画吴孟超力图通过青年人才布局来根除癌症的全新征程。赵一涛开展针对肝癌的基础性研究受阻,是《向肝胆革命进军》中吴孟超灌注我国第一具完整的肝脏血管模型的情形给予他精神鼓舞和学术启发。可以说,赵一涛所继承的正是吴孟超对于肝胆外科发展的未来希冀。尽管众多国内外同行均已尝试过种种失败滋味,但吴孟超身上挥之不散的开拓进取的激情未曾因此衰减半分,“我已经90多岁了,还能做多长?不知道。因此我要赶紧建立平台,把这个科学院、研究院建好,把平台建好。再培养人才,有人、有平台,基础研究就能开展下去,20年、30年、40年总能解决问题。到那时,我在天上看。”
银幕吴孟超的传奇色彩,来源于他作为万千病人灵魂与肉体的“摆渡人”的身份。2011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他的颁奖词是,“六十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昔日的肿瘤病人陈梅香在吴老为其施术后创下了生存26年的生命奇迹,如今她拿出10万元购买电影票,让更多民众感受仁心医者的人格魅力。借助写实呈现与银幕赋魅的合力作用,《我是医生》成功诠释了病人和大众对吴孟超的形象认知,并实现了银幕形象向表现对象的归元:“我是医生,我想背着每一位病人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