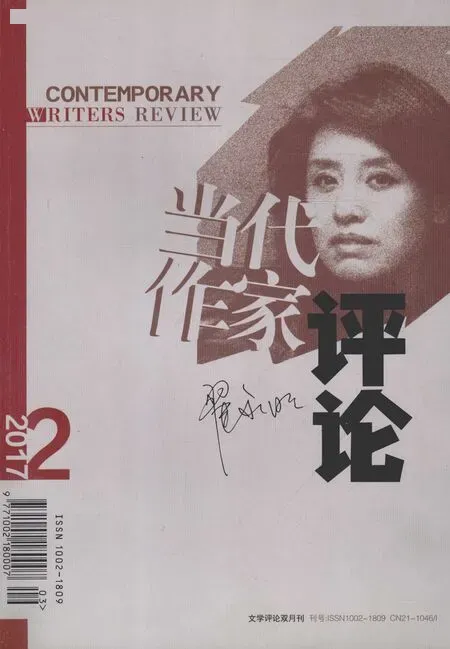作为文学史家的程光炜
2017-11-13张均
张 均

作为文学史家的程光炜
张 均
1998年,程光炜“因文坛‘纠纷’宣布脱离(诗歌)‘江湖’”,而随后的十多年时光也逐渐“淹没”了他作为朦胧诗人和重要诗歌评论家的曾经的形象。这或许是程光炜个人学术生涯中的偶然,但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而言,却毋宁是意外而丰厚的收获。作为文学史家的程光炜,不但和洪子诚等学者一起将“当代文学史研究”从当代批评中剥离、独立出来,而且还以其独到、深邃和切实的方法论思考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勘定了明确的问题、方法与边界。受他的文学史理论的训练和影响,杨庆祥、黄平、杨晓帆等一批出自“人大课堂”的“80后学者”在学术界“异军突起”,“重返80年代”也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继“重写文学史”、“再解读”之后波及甚广、甚深的新的学术思潮。那么,作为当代文学研究“文学史转向”最重要的推动者,程光炜究竟为他的学生和“70后”、“80后”两代青年学人提供了什么?作为有幸参与“人大课堂”的“70后”一代,我愿意从方法论角度将他对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看古物的眼光”。这是郜元宝对“重返80年代”的评价,程光炜也“自觉他说得在理”,“我现在做文章,再看8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文章时,确实是一种看‘古物’的心情和眼光。”何谓“看古物的眼光”,主要不是指对象距现在“已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已经在那里‘古老’了”,而应在于知识考古学眼光、小心翼翼的怀疑论方法。譬如,“80年代”呈现给我们的文学史知识真的是历史原生态么,它所讲述的“经典”作家与文本、“重要”时刻、“转折性”事件以及文学史迁徙地图,是如何从原初物事经种种“层累”而成为今天这番面貌的?这里面的问题毋宁杂乱层叠,存在着将之“作古”、细察其建构“痕迹”的广阔问题空间。由此,程光炜就把“重返”主要定位在“对已经‘形成’的文学史‘共识’的怀疑性研究”,“即是文学史研究之研究。它的目的是以既有的文学经典、批评结论、成规、制度以及研究它们的‘方法’为对象,对那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做一些讨论,借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事后看,这种定位使“重返”必然包含某种研究史冒犯。这突出地体现在对“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疏离之上。在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以“人的文学”、“主体性”等概念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阐释模式发起了持续“讨论”,并最终在“重写文学史”实践中毕其功于一役。然而,随着“重写文学史”体制化,新启蒙主义将自身作为方法而导致的结构性权力问题也日渐显露出来。程光炜的“重返80年代”是学界最系统的有关“重写”过程中排斥、压抑、改写、重塑等问题的“清理”工作,它在两个向度上展开。(1)对“80年代”的自我叙述的清理。有关现代派、新时期文学“起源”、路遥、遇罗锦、蒋子龙、《晚霞消失的时候》等的一系列研究,清理的都是牵连纵横在80年代诸多“重要”文学运动、思潮、现象、文本之下的“事实的肌理脉络”。以沾连在“古物”上的这些“肌理脉络”为历史支撑点,众多“不成问题的问题”被重新问题化,新问题更“胀破”新启蒙主义的边界纷涌而出,如“十七年”与80年代的关系、新时期文学的“脱历史化”、先锋小说与消费的关系、作为“成规”的伤痕,等等。这种“再问题化”使“重写文学史”搭建的“80年代”知识秩序面临崩解的压力。(2)对“80年代”文学史叙述的清理。程光炜认为我们今天所接受的诸多文学史形象,都是以“80年代”“作为方法”投射出来的结果。这其中不免有“奇谈怪论”,如对五四形象的本质论追问:“以‘反封建’(实际是反思‘文革’)的‘启蒙论’为中心,并对‘当代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学观做新的‘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最重要的工作。而这一‘历史化’工作,又是通过套牢‘五四’和‘鲁迅’来实现的”,然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鲁迅、沈从文、徐志摩,事实上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的鲁迅、沈从文和徐志摩,而是根据80年代历史转折需要和当时文学史家(例如钱理群、王富仁、赵园等)的感情、愿望所‘重新建构’起来的作家形象”。这类异见几有“搅乱”现代文学研究之势。有关“十七年”的讨论则较少令人紧张:“在‘改革开放’这一个‘认识装置’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变成被怀疑、被否定的对象”,故应“重新识别被80年代所否定、简化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文学?”以上两个向度的“清理”都贯穿着后现代式的怀疑论,都在努力从“客观”知识中发现叙述性:“这个历史并不是‘那个年代’的,而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依据‘今天语境’和‘文献材料’的结合中想象出来的。”因此,“重返”充满对既有知识和权威的冒犯,总希望在公共“知识”中析离出“80年代”并探看其最初“古物”风貌。
二是事关“古物”的政治经济学的还原方法。“看古物的眼光”对怎么“看”其实有精细而深刻的要求。在这方面,“重返”与“再解读”亦有很大区别。客观而言,主要出自于海外学者的“再解读”在解剖(“看”)文本内在的多重话语纠葛方面是有独到经验的,但程光炜不止一次对此种汉学方法表示不满:“大陆文学被演变成了‘晚清语境’乱世男女情缘的一脉相承,或是更大的西方历史时空里的摩登故事或是骑士传奇。于是‘当代’被编织在历史、空间万千细节中的一个不确定的变数,它的历史性痛苦,它的万千不安的辗转,它的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声至今不息于耳的历史性深沉叹息遭到了后现代主义式的彻底瓦解,变成了‘现代性’故事中的万千碎片。这样的‘当代’,我们已经无法认真地加以辨认。我们的心灵,整个是一个被西方学术话语完全抽空了的虚无感觉。”这番不满潜藏着程光炜作为当代思想者之于现实中国的内在关切。个人的身世经历,知识群体的历史挫痛,万千民众辗转的命运,这些可能并不谐和的经验和观察构成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感和热情。这种“心热”的学术品质海外汉学的确难以兼备。但在“心热”和如何“观看”“古物”之间,程光炜提倡适宜距离:“我的一个看法是,做文学史研究的人,要做到两点,即心热、手冷。”何谓“手冷”?就是我们不必成竹在胸,不必急于给眼前“古物”快速配备上新结论,而是暂时“遗忘”所有判断(包括权威结论和自己的“新见”),目光凝聚于“古物”之上,把它看作陌生之物,慢慢地体认,慢慢地辨识。用程光炜自己的表述是:“(我)小心翼翼地读这些小说,联想作家在创作它们时的各种情境”,“想看看落在上面的历史风尘,找找当年的斑痕,聆听一下作家创作作品时的呼吸,包括作品留下的一些莽撞、粗糙、不管不顾的那些痕迹。”此种之于“风尘”、“斑痕”的辨认,意在还原“古物”所置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权力关系,以及这层层叠叠的权力关系在“古物”流变为“熟悉之物”过程中的竞争与妥协。程光炜在最初提倡“重返”时,即提出了类似还原方法:“有必要采用历史还原的方式,通过细读读出渗透到一部作品中的‘多种声音’,进而对这多重因素、多种声音是如何型塑了‘80年代文学’的历史策略及其逻辑展开学术研究。”不过从后来“人大课堂”的研究看来,缠绕在文本、作家、事件、文学史形象之上的,并不限于观念性声音,还与现实的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介入性力量有关。故而梁鸿将“重返”总结为“重新进入历史,去发现‘80年代’的被建构性与生成性,把铁板一块的‘80年代’变为一个个‘事件’,去寻找它的话语组成,它的阶层性、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这种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文化观察,合“文本细读”与“文学社会学”于一体的历史辨认,构成了“观看”“古物”的主要内涵。在此方面,程光炜的一批“小说细读”论文,如《小镇的娜拉——读王安忆小说〈妙妙〉》《〈塔铺〉的高考——一九七〇年代末农村考生的政治经济学》《香雪们的“一九八〇年代”——从小说〈哦,香雪〉和文学批评中折射的当时农村之一角》《“我”与这个世界——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当代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堪称是近年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翘楚之作。
三是双重互动的“历史分析”框架。如果说把“80年代”“作古”使程光炜与新启蒙主义渐行渐远、政治经济学还原使他不趋从于“再解读”,那么双重互动的“历史分析”框架则使他的问题意识真正“落地”,变成可以在“人大课堂”上为学生提供的实操性的论文撰写方案。那么,这种互动框架在“重返”中是怎样体现的呢?这主要表现在程光炜在论述中不循以作家创作心理或文本精神指向为轴的“旧例”,而是“将它们与一个大时代的氛围联系起来”,进而将缠绕在文本、事件、出版等文学问题周边的多重交叉的“力的关系”作为叙述线索和问题核心。有关《塔铺》《妙妙》、先锋文学、《八十年代访谈录》等的解读,都存在此种别出一格的论述设置。不过,程光炜并未将“时代”理解为使人茫然失措的混沌、抽象之物,而是予以了清晰的分层处理。对此,他有较细致的陈述:“我所指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孔德和埃斯卡皮的两个知识层面上:即孔德抽象化地认为‘社会学能够追寻和发现社会世界中基本的结构和关系’,由此援引为我个人对当代文学史‘基本结构和关系’的历史分析;而在埃斯卡皮相对具象化的层面上,我则主张像他那样对‘文学’首先要通过‘市场’才能成为被社会公众阅读的‘文化产品’,换句话说,‘作家’是在‘读者’、‘大众’和‘市场’的意义上才得以成立的”,“我所说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即是‘抽象化’与‘具象化’能够达到相结合状态的那种研究方法”。或许,这种“抽象化”社会学研究可理解为文本、文学事件等所置身的政治经济之“大历史”观察,“具象化”则可理解为文学范围内的“微历史”观察,恰如杨庆祥所言:“(抽象化)考察文学在总体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效用是最主要的目的”,“具象化的文学社会学指的其实就是文学的周边研究”,“文学史不仅仅是关于文本的历史,同时也是批评家的文学史、编辑的文学史、读者的文学史、书商的文学史”。这意味着,“重返”之于多重“力的关系”的历史分析是在抽象与具体、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展开的。就“大历史”框架而言,出现在程光炜研究中的主要有“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全球化”数种。在怀疑论分析模式下,程光炜视这些框架为“认识装置”,并观察它们在文学周边的“力的关系”中的作用。其中,“改革开放”的“装置”导致了“伤痕文学”的成规和“十七年文学”的“非文学化”,“走向世界”则促成了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的自我合法化,“全球化”则使“《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和《论文学的主体性》所担忧的冷战年代中国当代文学‘自主性’缺失等”“不再是一个紧迫而敏感的‘当代’问题”,相反,“以‘文学’的立场来反抗全球化与大众文化的全面侵略”凸显为新问题,“这样,一度被90年代大众文化所压抑的‘重写文学史’、‘纯文学’、‘五四传统’等新启蒙话语,再次被请回到90年代的‘当代’语境中来,并释放出一度曾经丧失掉的叙述活力”。类似“大历史”视野不时闪现在程光炜的论述中。比较起来,由编辑、读者、“批评圈子”、文学会议乃至琴棋书画等交错而成的“微历史”视野就在程光炜研究中无处不在了。他不但写过《作家与故乡》《作家与阅读》《作家与读者》《作家与编辑》《作家与批评家》等系列论文,更在多数研究中以此“微历史”来结构论述。譬如,在孙犁“复活”现象的周边,程光炜就向硕士生和博士生们清理出层层叠叠的“条件”:“一个现代作家在‘当代’的‘复活’仍然是有条件的,有‘文学规律’和‘人事因素’等因素”,也包括“一个作家的‘年龄’、‘事件’、‘遭遇’、‘传统文化修养’、‘大家庭出身’、‘历史同情’等等”,“而且,这些‘条件’又必须是与‘当代’社会语境密切联系的,是后者精心认定和挑选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伦理因素都在参与对文学史的‘重写’,它将‘历史的同情’赏赐给一部分作家,同时冷落另一部分作家,它是要将前一部分人从他们原属的‘流派’、‘群体’和‘现象’中抽离出来,成为人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新版文学史中‘充满新意’的章节”。这种衬托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微历史”分析,这种“力的关系”的发掘,怎么看都是目前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创新感与历史感的研究方法。
“看古物的眼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还原方法、双重互动的“历史分析”框架,是程光炜在方法论层面上最主要的创造。在此之外,他对跨界写作与历史间距的处理,也颇可为后学取法。前者指的是他仍以才情盈于纸上的评论文字承载历史复杂性思考(学界誉为“史家批评”)、融印象批评与历史分析于一体的文体创造。自由腾挪的论述,密密匝匝的史料,在“人大课堂”上实已形成较为稳定一致的文风。后者指程光炜在处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关系上的谨慎。相对于那类将特殊的自我经验作为全部“当代文学历史起源和所有问题之所在”*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的学者,他更希望“把‘共同经验’与‘个体经验’的关系处理成一个适当的、有分寸的而且是符合理性的关系”,即“在不损害个体经验的基础上照顾共同经验在社会生活中的通约性,与此同时在照顾社会通约性的基础上又保护和维护了个体经验的尖锐性和鲜活性,在一种适当的状态中形成一个新的认识的张力”。*程光炜:《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文艺争鸣》2011年第8期。
以上所述,大约是我对程光炜的“后现代加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的观感。不过它显然不是对程光炜十多年来文学史研究成就的整体评价,而主要是对“70后”、“80后”青年学人在方法论层面上可以取资于这位杰出学者的部分经验的梳理。但可以肯定地说,仅由于方法论层面的创造及相关文学史哲学的思考,程光炜就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的具有学科史意义的学者。不过走笔至此,我忽然想到,程光炜为什么总是“重返”(从“80年代”到“70年代”又到“90年代”)而不是“前行”呢?或许,是由于面对人生“不知所终的旅行”,程光炜始终不愿克服某种“茫然失措的心情”而找到历史胜利者的感觉吧。
(责任编辑 李桂玲)
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