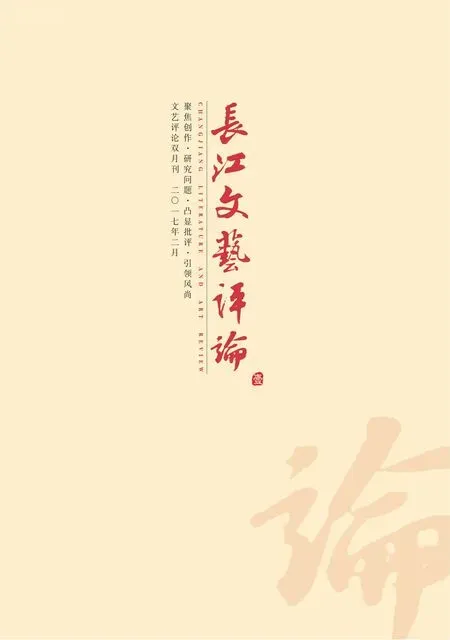学术、思想与力道
——论徐刚的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特质
2017-11-13龙其林
◎龙其林
学术、思想与力道——论徐刚的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特质
◎龙其林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虽然处于一种互生、交杂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时代的作家与批评家也总处于同步生长、相互观照的状态。与上世纪末“80后作家”即引起社会关注不同,“80后”批评家的成长可谓大器晚成,虽然作为个体他们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一直连绵不断,但一直到2013年底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才标志着这一群体的正式亮相。随后“80后”批评家的范围不断扩大,一些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学者陆续加入这一批评阵营,以风格交错、视野迥异的论著将“80后”批评家推向了历史舞台。在“80后”批评家挥斥方遒评点作家作品之际,我们也隐约察觉到了其中天马行空、脱离束缚的洒脱与随意。当代文学批评是美学趣味与直觉以及个性禀赋的试验场,而文学史的退场、趣味的张扬以及感性的飘忽,也使得主观臆测的、不及物的批评隐约其中。
在姗姗来迟的“80后”批评家群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青年批评家徐刚则是其中不事张扬、默默耕耘的一位。他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影视文化批评富于现实批评精神,擅长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综合观照下还原文学的发生语境,在时代思潮、作家心理与集体心理的共振中找寻文学现象的蛛丝马迹。与一些同龄的批评家仅仅关注当下文学现象不同,徐刚的研究还深入到“十七年”文学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斑驳庞杂的影视文化之中,多领域的齐头并进使得他的文学研究、影视文化批评的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相互交错,形成了一种更为立体、多元的观照方式。迄今徐刚已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电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了《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影像的踪迹——当代电影的文化政治阐释》《虚构的仪式:同时代文学片论》等专著多部,先后被评选为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人民文学》“2014年度青年批评家年度表现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三届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等,以扎实、厚重的文学研究、影视文化批评成绩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关注。
一、捍卫批评的学术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常常对当代文学批评持有某种误解或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当代文学批评不是正经的学问,批评者往往依据阅读感受天马行空的任意发挥,根据文本内容进行主题的阐释和故事的分析,虽然感性经验丰富,实则缺乏学理深度与更自觉的研究理念。这些观念虽不一定正确,但至少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在现代文学与其他学科中所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当代文学批评是随心所至的感悟,是才子灵感乍现的产物。依照邓晓芒先生的观点,文学批评可以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四个层次:“第一,批评家对作品的直接感受和感动,这种感受力比一般读者更强,批评家是作品美的传播者和读者的导游;第二,批评家对这种感动的理性分析,包括形式上的分析和人性结构上的分析,这种分析具有超越特殊感动之上的理论的普遍性;第三,批评家对作品中人性的历史维度即‘时代精神’的感悟,他能够立足于当代对文学史中体现的人类精神发展历程有更加深入的洞察;第四,批评家的人文哲学涵养,它将前面三个层次熔为一炉,构成文学批评的力量的最终源泉。”
很显然,不少当代文学批评者没有超出对于文学作品情感因素的直观呈现与就作品谈作品的简单层面,他们在文本细读的旗帜下沉溺于对于作品情感、人物言行的反复咀嚼,试图发现一种贯穿于作品内核的潜在规律。即便一些当代文学的批评者寻找到了理论阐释的武器,并且能够结合当代文本进行娴熟的解构与言说,但依然很难发现一种更为本质而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即一部作品构成其自身的最重要的存在要素。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质疑,某种程度上与当代文学批评自身质地与深度匮乏有着直接关系。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差异在于,“学术论文的规格和属性要求它所论证的观点,它所举证的材料,它所提出的见解必须反映某种真理性或者公理性的内容,必须体现历史的客观形态,必须表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的规律”。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应该是跳出了个人经验主义的浅层,并借助于批评家深厚的人文社科内涵的高度观照,切入时代的本质精神与作品的审美表现、形式分析才能够真正成为有深度、有质地的文学批评。
徐刚的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虽然也常常运用各种理论、方法,甚至还有不少研究对象本身即属于比较热门的题材,但徐刚的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显然并不停留于这一批评的表层,他总是力图在文本细读与多理论视角的基础上,着力发掘特定时期作家创作的群体无意识与文化旨趣。徐刚对当代文学批评侧重形式主义批评、重视文本内部细读的批评方法非常熟悉,也清楚地知道其中存在着的文本经验与时代积淀的隔膜,他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中试图为当代文学批评、影视文化批评赋予缜密的逻辑性、理论的深刻性与文化的普遍性。徐刚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影视文化批评形成了两套话语体系,一方面是对“十七年文学”历史与症候的学理化探究,在扎实的历史文献、系统的资料爬梳与理论的观照中步步推进,有理有据,显示出传统学人对于史料、义理、真知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徐刚又展示出自己对于文学新事物的敏锐触觉,他在对新潮作家作品的言说中积累着对于新时代文化属性的认知。严谨与活泼、规范与逐新这两种治学经历交织在徐刚的研究历程中,并且逐步形成了其自身独具一格的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理念。
徐刚的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具有与同龄人不太相符的老到与冷静,他的研究喜欢重回文学的发生现场,尝试着在立体化的文学语境中探究着时代与文艺、作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果说在硕士期间撰写的《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考察》《“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对文化黄金时代的深情回眸——魏秀仁〈花月痕〉评析》等系列文章中,徐刚在导师王又平教授的指导下形成了严谨的文学研究规范的话,那么到了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后,徐刚在博士导师张颐武教授的启发下又经历了思维认识上的提升,将严肃的学术研究与灵动的文学批评并行不悖地保留下来。正是两位导师不同的治学理念与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的严谨、程式、缜密与文学批评的灵动、轻捷、灵光乍现在他的研究、批评活动中逐渐融合,并逐渐形成了自身兼容学术与批评方法而锻造出的治学新思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徐刚实践着“两条腿走路”的研究与批评方法,他既可以穷尽材料、运用人文社会科学诸多理论探讨了《“十七年”反特谍战片中的城市空间》《1950至19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叙述》以及《被解说的与被建构的:“五四”研究史评析》等严肃命题,又能够发挥自身敏锐的文化触角探究时尚话题与文学现象,撰写了一批引人关注的批评文章,如《革命的激情与主体的幻象——评电影〈色·戒〉》《〈岁月神偷〉与香港怀旧电影》《苍凉而卑微的女性叙事——孙频小说论》《科幻电影的文化阐释与本土启示》等。在徐刚近期出版的《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影像的踪迹——当代电影的文化政治阐释》这两部著作中,其以学术立场切入当下文学现象的身影表现得十分突出。以学术立场进入当下文学批评,要求作者不能够仅仅停留于对于作家作品的情节鉴赏、人物分析以及主题归纳,而应该跳出这些表象,代之以对作家创作与文学想象的历史梳理,以史家的眼光看待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从而给予准确的定位。
《“交叉地带”的叙事镜像——试论“十七年文学”脉络中的路遥小说创作》这篇文章,较为典型地表现了徐刚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与一些同龄的“80后”批评家喜欢分析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行为细节不同,徐刚敏锐地察觉到了路遥作品中那种隐秘的对照解读城市与乡村的心理,即传统与现代相互观照下的精神世界。徐刚借助这一视角所侧重考察的是,“十七年文学”的文学资源如何规训了路遥作品中的城市主题:“路遥小说写的是城乡关系,但这种城乡关系的价值观书写其实极为明显地包含着‘十七年文学’的余脉”,“通过考察路遥小说中‘交叉地带’的叙事所包含的‘十七年文学’脉络,来探讨这位非典型性的20世纪80年代作家与‘十七年文学’传统之间的隐秘关联,进而考察‘十七年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历史方式。”在对近些年逐渐受到读者和传媒欢迎的路遥的作品进行复原时,徐刚发现它与“十七年文学”保持了密切的精神关联,城乡书写的价值取向也是基本一致的:“在‘十七年文学’中,对城市的警惕在其根本意义上是因为城市被指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城市则无疑是一个显性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乡村本位主义的伦理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的悠久传统及‘庄稼人’由来已久的保守和狭隘有关,但归根结底,对乡村的坚守却是对社会主义忠诚的完美体现。”同样是基于这种综合的研究与批评方法,徐刚在对新世纪的作家作品进行内容、主题、趣味、手法的审视中,更喜欢将这些作家、作品历史化,即借助学术研究的理性方式遏制出感性的冲动表达,努力使二者达到一种融合,在理性与感性、细节与趋势之间不断探寻,并由此而形成了其对作家创作经验的独特发现。
在《〈东邪西毒〉:记忆的“修复”与历史的“终结”》中,作者对王家卫导演重新剪辑老电影《东邪西毒》并隆重推出进行了嵌入时代语境的解读,结果发现在电影看似温情脉脉纪念已逝艺人的背景下,实质隐藏的却是后现代的消费社会对于死亡的娱乐敲诈。徐刚将王家卫的电影置于中西电影史和市场化时代的双重背景下进行考察,得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如果将戈达尔、伯格曼的‘作者电影’视为电影作者们拍给哲学家们分析的作品,那么王家卫那些抽象的情绪化的现代主义主题实际上模仿了这种形式,但其明星化的策略、类型化影片的形式,又暴露出他‘作者电影’‘山寨化’的面向。这种商业企图与经典‘作者电影’拒绝交流的艺术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毋宁说王家卫的电影实际上是拍给‘伪哲学家’们思考的作品。”
正是因为有了严谨的学术史视野与扎实的史料功夫,徐刚的当代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才能够跳出思维的单行道,而形成一种具有宏观视野的阐释坐标。不难想象,如果缺乏了学术的底蕴而只讲究主观的感受,这些批评文章即便一时间观点新颖,也难以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上站稳脚跟。严谨文学研究的思维,并未如作者所谦虚地表示的那样“这却使我的工作陷入到了一种刻骨的分裂境地”,反而在长期的文学研究、文学与影视文化批评中熔铸了一种研究新质:理性与感性的完美共存,史料与观点的相互阐发,视野与细读的相得益彰。
二、烛照材料的思想
如果说对于非学院派的批评家而言,凌空蹈虚、历史感缺失是典型症候的话,那么对于长期浸润于学院的研究者而言,如何突破长期学术训练带来的思维的僵化、研究的程式化则是另外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渐渐形成了凸显学术、淡化思想的时代特征。随着经院派研究的盛行,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文章形成了固定的起承转合、词语的使用以及段落的编排。徐刚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中的思想追求有着自觉的追求,他长期实践着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两种治学方式,既追求有学术的思想表达,以严密的逻辑、严谨的学术研究为文学批评奠定坚实的基石,同时又追求着有思想的学术,让文学批评不仅仅是文本故事的推演与细枝末节的考量。徐刚对于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发现的执着探求,在其专著《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时下的学术论文写作往往遵循着固定程式,理论的使用、材料的强化以及语言的单一常常使得许多学术研究著作与论文成为枯燥的材料试验场,精神的细节、思想的发现与人文的超越逐渐在论著之中隐匿。
在《想像城市的方法》中,徐刚以“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表述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了建国之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文化危机,并通过社会主义城市与市民文化这对长期纠葛的矛盾及其关系演变,讨论了革命理想主义与日常生活、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难以彻底消除的矛盾。这部著作选择了几个极富新意的视角进行研究,如“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变奏”、“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消费城市’的空间变革”、“革命伦理与城市日常生活”以及“‘生产城市’的建构及其文化政治”等,进而通过“堕落干部”的进城故事、“‘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上海姑娘’:摩登与革命的辩证法”等具体角度,系统地探讨了“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意义及思想局限。
透过上海在建国之后大量兴建的“工人新村”这一城市聚居区时,徐刚以作家们的文学表述及其寄寓其中的社会主义文化理想为考察点,结合历史资料与政治环境,发现了建国后兴起的这一城市空间所隐藏的象征意义:“‘工人新村’既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身也是一个包容着基层政治组织、经济政策和阶级文化习得等多方面的制度建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制度塑造了一个特殊的人群,即‘住新村的工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日常行为规范的‘独特性’,导向一种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及其与资本主义的文化断裂。在这种社会主义城市想像和实践中,城市的空间便成为了一种物质性力量和意识形态空间化的场所。”在分析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城市题材作品后,徐刚从社会各个阶层对于城市的警惕以及对于身体、消费等事物的忧虑中发现了其中关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其实是依靠一种紧张的意识形态‘超我’结构得以维系的,它难以承受消费主义所裹挟的‘欲望’与‘身体’快感,以及‘无意识’心理结构的冲击。因此,革命的传承并不能依赖一种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必定胜利的自信而实现,而只能通过‘超我’的意识形态结构而达成。”
徐刚所追求的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是,“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其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以及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致的作品阐释力,都显得至关重要。批评远非是要判断或鉴赏某个作品,而是要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进而打开这个隐秘而荒谬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纹路和肌理,虚构的世界里那些宽广博大的人物内心,抑或如深渊般无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对整个丰富而驳杂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阅读历史和社会。”徐刚的文学研究有着对于社会学、文化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广泛涉猎与理论消化,面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时能够形成更为立体式的观照。
在面对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时,徐刚力图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和批评之道,即在还原历史语境、呈现社会经验与表现个体精神世界之间的突破,发现唯有学者和批评家才能发现的文学存在的真相,是对于研究方法和批评效度的极为苛严的检测标准。在陈应松小说《送火神》中,村民们借助一次意外而致“大系哥”这位疯癫的异类于死地,徐刚在这里没有停留在对人性复杂性的喟叹上,而是将思考的触角指向于“缺席的原因”,认为是社会的制度缺失导致了今日乡村的沉沦:“诚然,‘大系哥’无所顾忌的‘放火’给村民带来了生命威胁,但更大的不安其实来自财产的损失,福利院的高额费用,以及其父罗机对于抚养费的吝啬,都是将他推向火海的‘幕后黑手’。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都要归结到整个社会的制度性排斥之上”,“在现实的利益面前,一切淳朴的伦理都化为泡影,一切友爱的传奇亦沦为神话,而乡村的脉脉温情则早已难寻踪迹。”在讨论作为一种现象的“小沈阳”的时候,徐刚在“小沈阳”、二人转、东北三者之间找到了文化现象的社会根源:“实际上,东北的命运折射的是整个中国的命运,东北的‘底层化’过程,也是整个中国‘底层化’的过程,像近些年如火如荼的‘底层文学’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新一波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形成,实际上伴随着中国人精神上的萎缩同步发生的。”
徐刚的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影视文化批评直抵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核,它不是将文学作品及现象视为单纯的个体精神劳动的产物,而是作为特定时期政治氛围、经济状态、文化心理、作家意识等共同合力的结果。正如他在回顾自己的文学研究之路时所说:“最初是电影与文化研究,进而是作家和作品分析,到如今将文学史研究也逐渐‘批评化’。这种‘以论带史’的形式,本意其实并非将冷静客观的‘研究’叙述成观点偏颇的‘批评’,而是要在枯燥繁冗的‘历史’之外,展现‘现实’鲜活的问题视域,在‘历史’的‘重读’之中,寻找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进而成全一种‘有学术的思想’”。徐刚的文学研究与影视文化批评超越了学术研究中常见的匠气、文化批评中狭小的文本细读,显示出宏观审视的思维方式、多角度把握研究对象的驾驭能力。徐刚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影视文化批评显得相得益彰,这与他对于不同研究方法的本质属性的准确把握、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积累的研究经验以及自觉融会不同领域内问学思路具有密切的关系。
三、搏击现实的力道
纵观徐刚的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影视文化批评,不难发现他对于与现实关系密切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有着更多的关注。如果说《时代的精神状况——评格非〈隐身衣〉》《现实的激愤与批判的证词——重评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屈辱而荒谬的灰暗人生——阿乙小说论》等文章直接表现出作者介入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在《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等回溯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史的著作中,也依然能够发现徐刚借历史思考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意图——“解读‘社会主义文学’的‘城市视角’,分析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表述,为分析19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解释的依据”,“是从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和教训的绝佳视角”——依然有着对于现实问题的鲜明指向;甚至,在影视文化繁花似锦的景象中,作者透过《全民目击》《小时代》《天注定》《白日焰火》等热映影视剧中所看到的,依然是冷酷刺目的现实。
现实,在徐刚的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影视文化批评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在徐刚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中,现实主义始终是最根本的指向,这是与他的成长环境、性格、知识、趣味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观察社会现象,还是分析文学作品的内容,现实是他始终无法回避的语境。在徐刚看来,“归根结底,批评或许只是一种态度,它集中呈现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多数的批评者将李健吾‘寻美的批评’奉为圭臬,这也难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固然让人心旷神怡,可这样的时代,纯粹的审美却多少显得有些廉价。批评不是抚慰,它更需要的是一种拆解的能力,一种阐释的方式,一种富有力量的表达,但这一切都要以审慎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展开。批评是批评家认识这个世界,并经由身处的世界来反观自我的方式。通过文本来阐释世界,进而在实践的层面探寻一种新的历史可能。”
学者的学术素养、民间岗位的工作性质以及理想主义情怀,使徐刚在文学研究及影视文化批评过程中注重通过分析作品的生产、传播及接受效果,进而透视出作家创作的社会群体意识、文化经验与时代症候。徐刚的文学研究不局限于经验、细节、感悟,而是通过现代性、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等价值系统来看待人与文学、人与社会、人与时代的关系。他对所有影响个体完整性的行为、思想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努力追求着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理解。在探讨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电影《全民目击》时,徐刚跳出了对于故事情节真实性的简单判断,而是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何以电影最后偏偏是富人通过赎罪实现了大逆转?徐刚在分析中发现,文学作品对拜金主义几乎都持批判态度,而更为商业化的影视剧则往往对金钱、权力充满着膜拜与幻想。徐刚通过分析《全民目击》的内容,对电影中的富豪实现自我救赎的心理进行了颇具现实主义风格的分析:“似乎是为了有意对抗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电影极为突兀地讲述了这个纯洁的有钱人的故事。在此,有钱人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完成的是爱和责任的救赎。对家庭伦理的忠贞,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情感。在此前提下,富人的不择手段、致富的原因、诈骗的嫌疑,都可以忽略不计。由此也可以看出,电影所表达的主要是对财富的崇拜、对财富拥有者毫无抵抗的臣服——这种臣服不仅贯穿在故事讲述者的意识形态之中,其实也贯穿在我们整个社会的情感结构之中。”
现实在徐刚这里不再是文学研究与影视批评中的道具、背景,可以随时根据情况选择取舍;现在在他这里具有更为重要而内在的意义:文学作品表现了怎样的一种现实状况,在冰冷的现实社会里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文学怎样慰藉这些时代大潮中的零余者与渺小个体。徐刚研究与批评中的现实指向,打破了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的界限,他让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在研究文本中相互对话,在相互的诘难、冲突中表现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规训与限制,从而展现出日常平庸生活下世界所隐匿的荒诞本相。批评在徐刚这里有时不再是一种分析的方法,而主要成为一个表现的过程——表现出文学作品内在的精神气质与思想肌理,表现出真实的抑或看似虚构的世界中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经验,表现出繁复的外部世界与内部经验中被遮蔽的声音与存在——唯其如此,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才能表现出专业主义的力道与价值。
在分析格非的小说《隐身衣》时,徐刚才会着力探究那位夸夸其谈的教授所经历的看似日常的生活细节背后的精神症候,从而洞悉物质现象背后的“世界的真相”:“褐石小区的‘花园洋房’里那位夸夸其谈的教授,连同他那似是而非的言论,便定格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堕落的注脚。而以古典音乐为契机,穿插着巴赫、瓦格纳、泰勒斯、马勒或者维奥蒂,与梅艳芳、张学友、刘德华、李宇春的对比,则分明显现出时代精神状况的病态特征”;对于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当大家都在褒奖该片所获得的2013年度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的时候,徐刚却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反思了中国电影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系。在对影片的黑调叙事进行回顾后,作者从电影与现实的关系着手,指出电影不仅是一种销售的产品,而且也是塑造国家形象的良机。基于此,徐刚发现贾樟柯在《天注定》中存在着致命的问题:“尽管电影所显示的影像伦理和社会正义都足以使人钦佩,但这种社会批判的形式却是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在这种现实的重述与建构中,一个阴郁粗鄙,戾气四溢,因问题重重而病入膏肓的中国形象,也颇为尴尬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贾樟柯电影的一贯风格:在追求影像‘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的名义下,以社会记录和批判的方式呈现出压抑消极的中国,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第五代导演自我民族志式的激情与快慰。”徐刚的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状态,以宏大的文化视野与精微的细节捕捉努力还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语境,其对于现实主义批评旨趣的坚守、对文学发生学的探求以及对文学现象条分缕析的能力,向我们昭示着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精神的力道与效果。他的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有着强大的精神底色,直接触及不同时代人们最为本质的生存真相与精神面貌,从而捕捉到文学、文学批评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血肉关联。
在徐刚的学术研究中,洋溢着一股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气质,他如同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将国家、社会与历史看作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其中的精神主线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即表现在徐刚对于研究人文性和承担意识的弘扬。正是基于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使命与社会道义的担当,徐刚通过文学研究这一民间岗位,在犀利、微妙、敏锐的学术工作中,执着地传达着一位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情怀。行文至此,突然想起饶翔在《愿他永远是少年》中对于徐刚的那段精到描述:“他所追求的并非悲壮美学,并非速战速决,而是日常性的苦练、修行,所有的激情潜藏在平静的地表之下,或化作一种日累月积的坚持,一种终其一生的惯性。这或许也是这个年代的作家、批评家所应坚持的状态与所应选择的位置!”
龙其林: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邓晓芒:《论文学批评的力量》,《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朱寿桐:《学术论文的内在品相》,《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3][4][6][10][14][16][17]徐刚:《后革命时代的焦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第141页、第234页、第182页、第168页、第104页。
[5][11][15]徐刚:《影像的踪迹——当代电影的文化政治阐释》,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第207页、第9页。
[7][8][13]徐刚:《想像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26页、第226页。
[9][12]徐刚:《批评的“历史感”与现实关怀》,《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18]饶翔:《愿他永远是少年》,《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