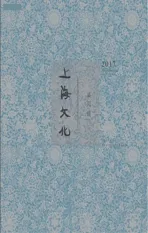从痛苦基石到生命群像赵丽宏《 疼痛》
2017-11-13褚水敖
褚水敖
从痛苦基石到生命群像赵丽宏《 疼痛》
褚水敖
一
在阅读赵丽宏新出版的诗集《疼痛》的过程中,许多清辞丽句,激起我情愫的兴奋,更引发我思索的活跃。诗歌的品质最终是思想的品质,诗化的世界最后是审美的世界。透过作者在这部诗集里精心腾挪的意象种种,凸现在我面前的,是一道道浸染着哲学色彩的精神的波流。正是这精神的波流,引领着生动传神的以“疼痛”为标志的生命群像。
作者把生命放在诗里。而诗人一些深沉的寄托,因为生命旗帜的高扬,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实现。
读毕《疼痛》,最好回味一下这部集子的首尾两首。首尾的放置,可以显示结构的安排。结构主义有一个重要观点:一切美的现象背后,结构在起着作用。这部集子的诗篇,是作者新近几年的作品,唯有最后一首《痛苦是基石》,是他早年的旧作。将一篇旧作作为篇篇新作的压轴,这分明是作者的故意。
《痛苦是基石》把痛苦和欢乐对立起来,同时又把它们归结为统一。痛苦必然存在,痛苦又必须存在,“有了它,才能建筑欢乐的楼阁”。“楼阁”可以理解为生命。因为有生命的痛苦作为基石,欢乐的生命才能造成。痛苦与欢乐,作为生命现象的表现,它们的转换,需要通过“建筑”即生命内容的改变来进行。生命内容的改变本身,也充满了痛苦。“在收割后的田野里拾取遗谷”,需要经受劳累;“在积雪覆盖的峡谷中采撷花朵”,需要战胜寒冷。卒章显其志,在依仗痛苦“建筑”欢乐生命的过程中,生命的崇高感和庄重感油然而生。
很有意思的是,这一生命内容的改变过程,在诗集的第一首《门》里就有了伏笔,或曰暗示。这首诗,以“门”的本来意义的表现情状化为意象徐徐开启,在不知不觉中,“门”已经转换成生命形态,成为意象的提升。于是,呈现出直指人心的生命之门。而诗的结尾“门里的世界,也许是天堂,也许是地狱”,显然指出了生命的命运趋向,暗喻着生命的两种可能,或是欢乐,或是痛苦。伏笔也好,暗示也罢,诗集最后《痛苦是基石》所要传达的作者的精神指向或思想归宿,在诗集的第一篇里就已经开始了。
痛苦是存在,欢乐是追求。必然存在的是痛苦,不断追求的是欢乐。生命在痛苦向欢乐的变化过程中发出夺目的光亮。诗集的第一首是引你入“门”,最后一首是悟出道理。集中除了首尾之外的所有篇章,则环绕着生命所闪现的诸多光泽,五彩缤纷地各显神通。
疼痛是摧心剖肝的。《声带》写出了一种令人讶异的人生遭际,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惊心动魄的苦难画卷:“我的声带”原是那么美好,“曾经纯亮如琴弦”,但是,“在弥漫天地的喧嚣中”,却遭逢“一度涩哑”的痛苦。“被囚禁在无法看见的地方”的“自己的声音”,正是被痛苦煎熬的生命。不过,这种痛苦尽管被笼罩在“死亡的静穆”里,毕竟是明摆着的,是一种明痛。更加难以忍受的,是隐藏在《疼痛》一诗里的那种无迹可寻的暗痛。这种暗痛莫名其妙,“无须利刃割戳,不用棍棒击打”、“看不见一滴血,甚至找不到半丝微痕”,然而“尖利的刺激直锥心肺”、“痛彻每一寸肌肤”。在暗痛里,痛楚因为茫茫难寻和哀哀难诉而臻于极致。
不难看出,作者在不同的诗篇里描绘的明痛与暗痛,实际上是在展示疼痛的类别:物质之痛与精神之痛。在生命的长途中,疼痛有别,有时痛在物质,有时痛在精神,有时则是物质之痛与精神之痛并存。疼痛的样式不一,生命的感受也就五花八门。物质与精神并存之痛,最突出地表现在《一道光》里。“一间没有门窗的屋子里”的黑暗,是物质的黑暗;而当黑暗与“自由和囚禁”相逢,黑暗就成了精神的。与此伴随,“一件没有门窗里”漏进来的光,是物质的光;而当黑暗表现为精神,光也就成“一道虚无的光”,即精神之光。作者还在不少诗篇里,将物质之痛与精神之痛作了有意或无意的比较,后者一定比前者更加难以忍受。前者,犹如《声带》一诗所抒写,还可进行“痛彻心扉的呼喊“;而后者,则犹如《我想忘记》一诗中所喟叹,“我是定格在水声中,一个发不出响声的音符”了。
对于精神之痛,作者在诗篇里,是通过许多错综复杂甚至诡谲奇异的社会生活与人生境遇来显现,这就不光是个人的一己之痛而是关联着社会弊病引起的诸多痛苦。而只要社会生活依旧有危害人类自由和幸福地生存的各种因素存在,当人格上和思想上的真正独立自主和自由解放未能真正实现,人的精神的痛苦总是不可避免。
以上对于《疼痛》中几首诗的剖析,是想就作者在诗集里所驰骋的精神、所寄寓的思想进行追踪。作者如此醉心地沉思“疼痛”,并且把这种执着的沉思蕴含在丰富多彩的意象世界里,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在形象地表达对生命的关注与尊重。这不禁令我浮想联翩。我不由得想起对生命哲学极有建树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一句话:“生命的利益在哪里受到威胁,直觉之灯就会在哪里闪亮。”所谓疼痛,所谓痛苦,无论是物质之痛还是精神之痛,都是生命利益受到威胁的典型表现。赵丽宏在《疼痛》里的笔墨施展,可以说都是他的直觉之灯通过思接意象、神驰意境,在诗的字里行间发出了光亮。这是一种创造,是诗人的杰出智慧在遇到“疼痛”这样的生命方式时的创造。这种创造的核心意义在于对“疼痛”的疗救的用心与用力。《一道光》这首诗,最为明显地体现了用心与用力的程度。“那一道虚无的光”以及“我也变成了一道光”,这“光”的象征意义需要一番猜测,但它所寄寓的作者对“疼痛”的化解力量,却非常鲜明。套用道医界常用的一句话,“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道“虚无的光”的作用,乃是“夫唯痛痛,是以不痛”。达到了“不痛”,也就是在“痛苦”的基石上建成了“欢乐的楼阁”。作者在《疤痕》、《一道光》等少数篇什里,比较含蓄地描写了痛苦向欢乐的转化。除此之外,诗集大部分诗篇没有直接写到欢乐。但细心的读者不难从《疼痛》整部诗集里感受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指向:即百般痛苦之后,必然会达到欢乐。而痛苦作为“基石”的最终意义也在这里。作者正是在清醒而坚定地把握痛苦与欢乐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既将痛苦揭示得深沉透彻,又让痛苦包含向欢乐变化的希望。这既是一种身体遭际的刻划,更是一种人生走向的描绘。这时,积极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便得到体现。而且,也正因为源于对人的生命力量的哲学思考,于是使作者笔下的意象世界不仅外观瑰丽,而且内里深沉。
在这里,引用尼采在《上帝死了》一文中的一段话很有必要:“我们必须像母亲一样地不断地从痛苦中分娩出我们的思想,同这种思想一起分享我们的热血、心灵、激情、快乐、痛苦、良心、命运和不幸。”“分娩出我们的思想”,应该是一部优秀诗作的美学要求。这一要求的实现,在《疼痛》里形象地彰显了。
二
《疼痛》的各种“疼痛”实际所显示的生命状态及其生成原因,远比前文所述的更为错综复杂。“疼痛”诗集上承载着不少值得深究的生命学问。要透彻地揭示这些生命学问的深妙是不容易的;而在我的感觉中,更不容易的是如何准确地看待这部诗集关于这些生命学问的意象实现。换言之,作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以及在什么程度上,通过对于意象世界的开拓,把握着自己的审美倾向,琢磨着自己的艺术追求。
赵丽宏曾经在这部诗集的首发式暨朗诵会上表示,《疼痛》记录了他在年过甲子以后对世界对人生的新的看法。他说:“复杂的世界和曲折的经历,使我有了新的感受、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述方式。”我揣度作者所说的“新的感受”,更多地反映在他的诗集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中,亦即通过对于生命学问的探寻与剖析,所融注的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新的对待与感悟。而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述方式,则体现在这部诗集艺术层面的掌握,主要是在情思发现和艺术建构双向支撑方面的高度发力。
读《疼痛》里的诗篇,和赵丽宏过去创作的大量诗歌相比较,我曾誉之为“变法”。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诗歌创作探索路途上的收获,一种难能可贵的提高;而艺术视角的转换,则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的标志,是艺术视角的把握究竟是向外,还是向内。所谓向外,指的是诗歌的抒情主体虽然也不是没有自我意识,但极其稀薄,主导方向是向外的,包括被动地进行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所谓向内,则是直指内心,怀抱清醒的自我觉悟,以诗的笔触,对人的心灵内在世界进行强而有力的探寻与表现。用诗集中《一道光》来形容:“静穆中,我也变成了一道光”,这就是诗人由外向内的自我之光。自我之光投射在《疼痛》的每一首诗里,有的投射得比较内敛,有的投射得十分率性。比如《脊梁》一诗,在对于脊梁的弯曲与挺直的胸臆倾诉中,“自我”的流露显然率性而为。虽然,“我的脊梁总是挺得很直,但却是当年负重远行,扁担磨碎了肩膀的皮肉,压抑的呻吟直刺云天”。不曾提到十分痛苦,却可以体会到痛苦十分。“拉扯我,拥抱我,把我拽往坟墓的方向”,由脊梁弯曲而必然引起的痛苦,也在这句沉重的诗里显露无遗。即便如此,却依旧是“挺直,挺直,挺直,我的还没有折断的脊梁”。弯曲是相对的,挺直则是绝对的,必然弯曲的是身体,永远挺直的是精神!在这首诗里,与痛苦的弯曲相关连的衰老与坟墓,以及具有引力的大地和鸟在拍动翅膀的天空,对应着挺直的脊梁,鲜明的意象牵动着深沉的情感。而诗的意象与人的情感,都是从诗人的内心深处蓬勃流出,流动成感人的形象,流动成诗的内在素质。这种向内的视角,也从《暗物质》、《疤痕》、《痛苦是基石》等诗里体现出来。伴随着疼痛的感觉,这些优美而沉重的诗句,无不发自沉重而优美的内心:“静穆中,有听不见的嘶喊,炸裂声穿越高墙,却音迹杳然,外套沉寂,包裹沸腾的心,不让任何人谛听”;“是忧心忡忡的眼睛,是无微不至的隐痛,每一处疤痕中,都会生出扑动的羽翼,把我托举成轻盈的鸟,去追求流失的时光,重访曾经年轻的生命”;“学一学打夯人吧,把痛苦当作沉重的基石,夯,夯,把痛苦夯入心底,深深地,深深地。”
说赵丽宏在这部诗集里实现了以向内探索为标志的新的视角转换,这也可以通过他自己诗歌作品的比较来证明。他的诗歌创作早已成果丰盈,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但毋庸讳言,他过去的创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我以为较为明显的不足,是有些诗篇的抒情主体在向内探寻方面还不够突出,有的书写视角还停留在已经描绘的客观世界的表面,对心灵内在世界的深层次开掘尚未呈现高度的自觉。比如他的长诗《沧桑之城》,在形象地展示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他的诗笔在许多方面展示出诗人的难能才情,内中篇章不乏令人激起审美快感的华彩;但是,也有一些篇章还流于一般化的描摹与展开,缺乏一些足以让人心灵为之吸引甚至震撼的诗的摆布或显现。如果用诗的眼光究竟是观望还是凝视作为衡量高低的尺度,赵丽宏过去写作的一些诗歌,还没有完全摆脱观望的痕迹。而《疼痛》则完全不同,已经不仅是观望,还经常是夺人眼球扣人心弦的凝视。
凝视即是向内探索的表现。这也可以用《疼痛》里的《凝视》一诗来加以渲染。这首诗,最可玩味的是一开头的“无形的光”。这“无形的光”,“凝集在某一点”,“没有亮度和声息,却有神奇的能量。”接着,作者写出这道光在“冷峻时”和“灼热时”的状态,最后是“四面八方的聚焦,能穿透铜墙铁壁,让被注视者找不到藏身之处”。凝视的结果,被注视者已无藏身之处,充分说明了凝视的深入和彻底。这是诗人描绘的“无形的光”,但也不妨移用为作者的写作意向,是作者在诗歌艺术上不断向内探索的强光。就此而言,作者无疑是在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诗歌书写进行有效的突破,于是别开生面。
三
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会在一部或多部中外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找到追踪的痕迹。这在艺术表现方式上,可能最为明显。细读《疼痛》,我情不自禁地会想起艾略特的《荒原》。我不是认为《疼痛》的艺术质量已经达到了《荒原》的高度;也不是说,赵丽宏一定对《荒原》这部象征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进行过有意识的借鉴。我只是说,如果拿《疼痛》的美学构图与《荒原》进行比较,可以在审美探寻的实现方面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于是,可能会由此而更加看重《疼痛》的艺术效应。
《疼痛》里的五十余首诗,有的直接抒发“疼痛”,有的是“疼痛”的间接抒发。还有几首看似对“疼痛”未曾涉及,但实际上和“疼痛”存在有机的联系。使这些篇章得以进行诗的飞翔的意象,大都赋予了象征的意义。显而易见,《疼痛》这部诗集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具备,使诗集在内容上的支撑显得结实坚固。而诗集在时代精神的体现上,更多地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而是俯拾皆是地借助于象征主义的功用。注重类型性的象征意味,是现代主义艺术的重要特点。象征意义的普遍存在,现代主义也就格外鲜明。
这一点,诗集里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疼痛》这首诗。此诗一开头即以“无须利刃割戳,不用棍棒击打,那些疼痛的瞬间,如闪电划过长空,尖利的刺激直锥心肺”这样的句子,造成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疼痛的氛围。但这种疼痛,显然不是指向生活中一般意义的疼痛,而是会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引起对于时代伤痛与社会弊病的联想,借用白先勇的一段话,这疼痛会让人联想到“大时代的兴衰,大传统的式微,人世无可挽转的枯荣无常,人生命运无法料测的变幻起伏”之类。同时联想到的还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个人精神之痛。联想一旦产生,“疼痛”的象征作用便脱颖而出。在直接或间接地描写“疼痛”的其他诗篇里,也不时地呈现种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情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诗集以“疼痛”为名,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书名用象征,内中的许多诗篇也用象征,这实际上是在提醒读者,无论是就整体结果还是局部效应,象征的意义在引领或者激发着诗集的审美主旨与思想倾向。因此可以这么说,象征主义在《疼痛》里的布置和释放,不仅在艺术作用上呈现出难能可贵的奇异色彩,而且在作品思想内容的掌握上,也令人滋生一种推波助澜的美好感觉。艾略特作为文学大师,他在《荒原》里的象征主义运用,使作品放射的光彩格外夺目;《疼痛》纵不能与《荒原》比肩,但就象征主义的出色存在这一点而言,喻之为异曲同工是并不过分的。
除了象征主义的出色存在之外,《疼痛》的另一艺术特色是陌生化效果的产生。陌生化效果,是所有艺术重要的追求目标,诗歌也不例外。所谓陌生化,我的理解是艺术创造上一种特殊的美学追寻。作品的面目见所未见,或当初曾见而久久不见,一见之后怦然心动,虽然陌生,却是心中所想。陌生化的极致是道学所崇尚的“无中生有”。因为陌生——包括构思陌生,手法陌生,语言陌生等等,自然会涌动新鲜感、奇特感、刺激感,使作品的审美效果达到引人入胜、夺人眼球的地步。就诗歌而论,陌生化效果可以表现为多方面,还可以表现为多层次。一诗在前,构思的独特,章法的奇峻,诗句的异样,这综合的陌生,能使审美结果别有天地,而将诗篇推入清新别致、高标独特的优美境界。诗集《疼痛》从总体上看待,作为题材,并非完全陌生;然而在主旨的开掘、意象的驰骋、语言的采纳等方面,不时呈现出许多新颖别致,于是,陌生化的感觉就总是存在。这犹如集中《访问梦境的故人》一诗所描述:“我想见见你们,梦中的门吱呀一声打开,进来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有的甚至从未谋面”。就诗句和语言而言,《疼痛》中的陌生化则屡见叠出。例如《想起死亡》里的“想起死亡,心里涌起一丝神秘的甜蜜”,“想到死亡,竟然有一种期盼”;《凝视》里的“冷峻时,如同结冰的风,可以使血液凝成霜雪;灼热时,可以使寒酸的表情,熔化成岩浆,烧灼成火焰”;《访问梦境中的故人》里的“我从不害怕,死者成为梦境的访客,他们常常不请自来,让我一时分不清生和死的界限”,等等。
《疼痛》这部诗集陌生化效果的产生,我也同样窥见了艾略特《荒原》的影子。《荒原》的艺术特色五彩缤纷,但其中的陌生化效果,是《荒原》一经面世即引起轰动的重要原因。《荒原》的陌生化效果是如何实现的呢?艾略特曾将自己诗歌创作手法的运用归结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评论界则有人认为他的诗歌作品得益于新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或新或旧,无不以艺术想象的特别奇峻作为重要特征。而诗歌作品的陌生化,其成因,主要也依赖于奇峻的艺术想象的存在。艾略特在他的论文《玄学派诗人》中,曾提及“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诗人如果以陌生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他诗中“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必须为常人毫不熟悉。诗思海阔天空,让意象的进行呈现诗人完全独特的秩序和逻辑,陌生化就可能萌生于这种别具一格的想象中。细观赵丽宏的《疼痛》,也可以从诗集中面目全新、不胜枚举的陌生化艺术的展现,判定他在写作这些诗篇时的想象特征。他也必然让“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另辟蹊径,甚至天马行空。“独立之意识,自由之精神”,这句常被引用的话,同样可以移用为赵丽宏在创作这些诗篇的过程中如何在达到艺术的陌生化中别具匠心。
四
《疼痛》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缺。比如内中个别篇章无论是谋篇还是表述,尚有平平之嫌;还有个别篇章即使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较突出,但如果从严看待,其实也可以有更深的主旨开掘与更美的意象飞腾。不过白璧微瑕,《疼痛》终究不失为能使读者记忆并且长久传诵的上乘之作。这部诗集,对于当前的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创作,不论是宏观立意还是微观操作,我认为都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诗是心灵的载体。作为诗人,要想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必须使自己具备强大的心灵。有了强大的心灵,就会有坚定的精神立场,就会有理念、形象、感情三者统一的审美理想,这才可能在诗歌创作的宏观立意上臻于必要的高度与深度。以此为前导,继而在微观操作包括语言文字的打磨方面用力,就不愁诗作优美境界的实现。从《疼痛》所显示的成果不难看出,作者在宏观立意与微观操作上是齐头并进的。比如在掌握诗情与诗意的时间维向、空间维向还有人性维向等方面,作者在许多诗篇里都下了一番功夫,再加上艺术上的精雕细刻 诗集才会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熠熠光彩。
作者放在《疼痛》里的生命现象,在中外古今的无数文字也包括诗歌里常可遇见。但既然在当代生活里,生命问题不但没有淡化而且愈见突出,对它的关注就十分必要。而由不断充当时代号角的诗歌来关注,更是责无旁贷的事。
“疼痛”乃是生命关怀的焦点,通过不是向外而是向内的视角看待“疼痛”,不仅是诗人贴切当代生活、对生命现象十分敏感的表现,而且也是诗人的独立精神、理想追求和担当意识的充分展示。
以“疼痛“为核心内容的生命关注,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史的遥远岁月。早在群经之首的《周易》里,已记载了对于宇宙发生与人类生命存在的一些见地。其中《彖传》所说的”内难而能正其志“,道明的是当初文王、箕子在遇到艰难痛苦时,仍能坚持正义、牢守志向。对生命真谛的认知必须有向内的视角;同时,生命真谛的内涵,不能在一般情况下得以感受,只有在艰难痛苦的情形下,这种生命真谛才能充分发挥。从遥远的历史开始,直至当下,人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生命中必然存在的艰难困苦,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守望生命的尊严,永远是人类生存的重大课题。用诗歌来形象地探索这一重大课题,让这一探索过程成为意象世界的瑰丽呈现;使读者在欣赏这种难能可贵的瑰丽的时候,不仅激起艺术的感动,而且得到思想的启示:我认为这正是《疼痛》的深层价值。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