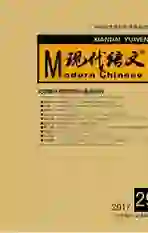灵魂与时代齐舞
2017-10-17雷明刘春
雷明+刘春
《土地的誓言》和《故都的秋》两篇散文在写作动机、写作背景和写作主旨上是很接近的。由于教材分布的不同以及学习目标上的差异,教者往往忽视两篇课文的可比性及其背后蕴藏的教学价值。解读此类文本,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表达的目的,更应重点剖析表达背后的原因,追寻表达后的结果,唯有如此才能彰显人作为人的特殊感情、人作为人的内心困惑、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
《土地的誓言》与《故都的秋》两篇文章在诸多方面值得观照(如表1所示)。将两篇文章进行纵深分析、比较阅读,可获益良多。
一、作者的伤时忧世
以“九一八”事变为分水岭,《土地的誓言》写于十年之后,《故都的秋》成于三年之前。总的社会背景均是民生凋敝、硝烟弥漫。作为知识分子,端木蕻良与郁达夫在时代沉浮之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也使得他们在文学的夜空中熠熠生辉,令人瞩目。
先看端木蕻良。作为东北流亡作家群的成员之一,他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将个人感情与东北广袤的土地交织在一起,将人民的屈辱、日寇的暴行真实而深刻地表达出来。土地作为端木蕻良文化生命的渊薮,他以此为根,以此为源,竭尽所能地呼喊着祖国母亲,正如端木蕻良自己所说,“性格的本质上有一种繁华的热情”[1]。在他眼中,所有的家乡事物均与自己血脉相连,“在离开东北的漫长岁月里,家乡一直是端木蕻良不可忘记的精神发源地,将自己比喻成黑土地上的一株植物(‘蕻良”谐音‘红粱),而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滋润和养育作家的沃土”[2],也正如作者在《土地的誓言》中表白的那样,“对于广大的关东原野,我心里怀着炽痛的热爱”。因此,在“九一八”十周年之际,作者怀着如火的热情造就出了这一篇喷薄汹涌的文章。
再看郁达夫。《故都的秋》写于1934年8月,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郁达夫携家带口,长途奔波,举家搬迁,而暂时的安定并没有让作者轻松许多,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让他无法忘情于世。而此刻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愈发落寞悲凉了。唇亡齿寒,他不能不悲悯,而秋,正是他将中国历史文化洗涤澄净后的独特象征。因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对故都的秋色如此眷恋,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留住北国之秋。作者希冀通过自己的描述以证明这故都的秋独具中国韵味,触目伤怀,情实不能自已。“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个动乱的年代,个体正如片片秋叶漂泊无常。作者也终于四十九岁在异国他乡被日本宪兵杀害;无疑,这又为晚秋增深了一丝凉意。
景虽悲凉,却是故乡之景;城虽衰败,却是故乡之城;民虽衰弱,却是国之同胞。两个被迫离开家乡的人,振奋而起,大声疾呼,仿佛使人谛听得到心脏的跳动。也正是因为这种种困境和难题,才更加显示出个人选择的弥足珍贵,由此可见,在面对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两颗伤时忧世的赤子之心同样赤诚。
二、表达的和而不同
“一切语言都起源于接近人的需要。”[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语言风格,是由他独特的言语方式所决定的。
《土地的誓言》中的文字直接、奔放,读起来有呼之欲出之感,作者通过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相结合的方式赋予土地以性灵,构建出诗般的充满生命与情感的意境。文字给人电影般的动感:
“当我躺在土地上的时候,当我仰望天上的星星,手里握着一把泥土的时候,或者当我回想起儿时的往事的时候,我想起那参天碧绿的白桦林,标直漂亮的白桦树在原野上呻吟;我看见奔流似的马群,深夜嗥鸣的蒙古狗,我听见皮鞭滚落在山涧里的脆响;我想起红布似的高粱,金黄的豆粒,黑色的土地,红玉的脸庞,黑玉的眼睛,斑斓的山雕,奔驰的鹿群,带着松香气味的煤块,带着赤色的足金;我想起幽远的车铃,晴天里马儿带着串铃在溜直的大道上跑着,狐仙姑深夜的谰语,原野上怪诞的狂风。”
在这些文字中,作者调动了各种语言手段,诸如物象的叠加,综合声音、色彩、线条等特有语汇以及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起到了表情达意的作用,同时也扩展了文字的表现力,为散文创造了情绪,创造了氛围。因而,散文呈现出一幅情景交融、激烈浓郁的动态画面效果。
《故都的秋》中的语言含蓄、深沉,凸显平民色彩。如文本第三段中:
“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
读起来姿态洒脱,随性而为,有一种惬意闲适的感觉。但如细细品味这“破”、这“坐”,除了从容闲静以外,还或多或少有一种落寞的孤独之感。另外作者也多次运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如从整体上对北国的秋与南国的秋的对比,其中更是细致到南北方雨的对比,“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诸如此类,不再赘述。
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曾经谈道:“达夫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中映着霞绮。……他把诗人的灵感赋予了每一朵浪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巉岩、每一株小草,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味,再把风俗人情穿插其间,浓淡疏密,无笔不美,灵动浑成,功力惊人。”[4]大师之言,恳切之至!因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故都最普通不过的景物由作者笔下流出竟会如此唯美,牵牛、长草、落蕊、弱蝉、枣子构成了一幅写意的长卷,可谓别具一格,不落窠臼。
梁启超曾说:“境者,心造也。”[5]作者所见之境均是自身内在的生命灵性,是“作者高度个性化的言语对象和言语内容”[6]。因此,也就明晰了两篇文章在表达上不同之处,《土地的誓言》表现出作者内心不可遏制的激情,一气呵成;《故都的秋》则寓情于景,自然、平和,如潺潺流转于青石的溪水,传神而富有意蕴。
三、上下求索的生命存在
“人既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又是一种个体的存在,生命的存在。”[7]在对个人生存的大環境与小环境的把握之间,个体会对外界做出自己的感知、认识、判断和改变。
对于故都的秋天,作者更像是在欣赏一幅水墨画,他满怀敬意地观赏着原创作者的着色布局,但当看到逝去的落蕊,听到弱蝉的残声,又从容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看到各色的牵牛,成熟的枣子,也止于无言之中默默品味。漂泊和流浪在异域他乡,对个人的考验不仅仅是时空的迁移与转换,还需要经历从精神到物质上对其他文化的接受、适应、进而融合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时代的交替之中,作者要孤独地完成自我改造、自我转型以及自我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国家而言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文学是人学”,世界是人的世界。端木蕻良自幼生长在一片充满野性和神奇的大地上,东北沦陷,作者失去了生养他的土地,成为流亡者中的一员,对于都市的陌生,對于家乡的忧思,对于祖国的期盼,使作者发出“土地,原野,我的家乡,你必须被解放!你必须站立!”的呼喊。正如他自己所说,“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的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深厚和真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土地使我有一种力量,也使我有一种悲伤”[8],这种悲伤也促使作者对民族的命运以及人生的遭际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那个时代,最让知识分子感到尴尬的莫过于对自身价值和自身存在的认同,自觉而主动地进行自我拷问、自我批判,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精神进化的必由之路,在那一声声的呼喊背后,作者也获得了心灵世界的安宁与通达。
《土地的誓言》和《故都的秋》在写作理由上是相似的,但在表达上存在一些差异,可谓各有所长。黑格尔说:“环境的互相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坚强。只有在这种发展中,理念和理想的威力才能保持住,因为在否定中能保持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9]就在这巨大的矛盾之中,二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叙述了自我内在的悲凉。个体生命在外界强大压力的作用下,暂时地屈服着。可是这种强制的手段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存使命,只是让他们在独立人格的存在意义中多了一丝犹豫与彷徨。面对现实世界的重压,作为个体的人,在当下该如何选择?个人发展的方向性又当如何?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诘问:到底存不存在一种真正的解决方式,以便把自我与时代结合,进而获得一个人继续前行的力量?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硝烟弥漫的时代里,总有一抹图景令人魂牵梦绕,也许是关东的原野,也许是古都的秋色。动情呼喊也好,委婉叙述也罢;亦或寓情于景,或含泪倾诉。真情表达的文字,抒发的不仅是内心的苦楚,更是增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表达终将被时代所永久记忆,而决非是旋生旋灭的拍岸浪花。正因如此,这一支跨越时空的灵魂与时代的齐舞,才别开生面,荡气回肠。
参考文献:
[1]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李闻闻,李文任.浅析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J].大众文艺,2014,(18).
[3](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M].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刘海粟.漫论郁达夫[J].散文选刊,1986,(3).
[5]鞠守勇.信仰的高度:名家说禅[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6]王荣生.中小学散文教学的问题及对策[J].课程·教材·教法,2011,(9).
[7]洪治刚.伦理与情感的双重纠缠[J].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4,(3).
[8]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9](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