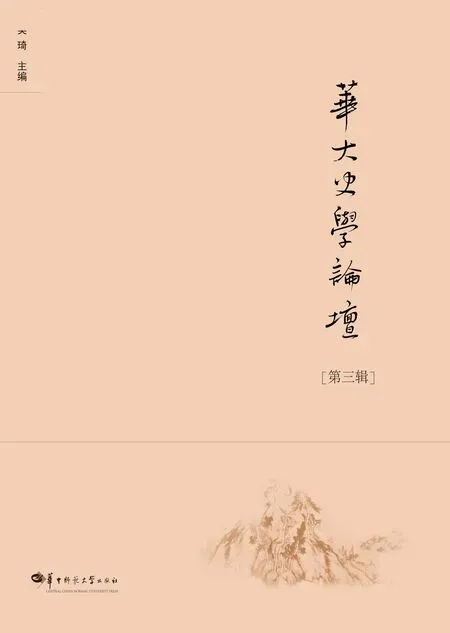龙沙谶之下的晚明文人书写风潮
2017-10-15何璇
何 璇
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净明道中的龙沙谶突然在江南文人之中开始流行[注]涉及净明道的研究,主要有秋月观映著:《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丁培仁译;后有郭武:《净明忠孝全书研究——以宋元社会为背景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许蔚:《断裂与建构:净明道的历史与文献》,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张洪泽:《净明道在江南的传播及其影响——以道派关系史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47-58页。净明道和文士的交涉之相关研究,有张艺曦:《明中晚期江右儒学士人与净明道的交涉──兼论〈净明忠孝全书〉的影响》,《明代研究》2013年6月第20期;张艺曦:《诗文、制艺与经世:以李鼎为例》,《明代研究》2015年第25期。关于文人和宗教的研究,有合山究:《明清の文人とオカルト趣味》,见荒井健编:《中华文人の生活》,东京:平凡社,1994年;柳存仁:《明儒与道教》,见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王阳明与道教》,见《和风堂文集》。徐兆安:《英雄与神仙:十六世纪中国士人的经世功业、文辞习气与道教经验》,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关于仙传书写的研究主要有徐兆安:《十六世纪文坛中的宗教修养——屠隆与王世贞的来往(1577—1590)》,《汉学研究》第30卷第1期;徐兆安:《验证与博闻:万历朝文人王世贞、屠隆与胡应麟的神仙书写与道教文献评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第53期。关于昙阳子的研究有贺晏然:《昙阳子信仰的建立兼论晚明文人宗教的特点》,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Ann Waltner,“T’an-yang-tzu and Wang Shih-chen:Visionary and Bureaucrat in the Late Ming”,Late Imperial China,Vol.8,No. 1,June,1987,pp.105-133;Ann Waltner,The World of A Late Ming Mystic:T’an-Yang-Tzu and Her Follower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徐美洁:《昙阳子的“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象》,《青岛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2月第27卷第4期;魏宏远:《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关于龙沙谶的研究有张艺曦:《飞升出世的期待——明中晚期士人与龙沙谶》,《新史学》2011年第22卷第1期。关于小说传播和道教小说的研究主要有Robert E.Hegel,“Distinguishing Levels of Audience for Ming-Ch’ing Vernacular Literature:A Case Study”,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Evelyn S.Rawski ed.,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C Berkeley Press,1985,pp.112-142;李丰楙:《许逊与萨守坚:邓志谟道教小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7年;王岗:《作为圣传的小说:以编刊艺文传道》,见盖建民编:《开拓者的足迹:卿希泰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李丰楙:《暴力叙述与谪凡神话:中国叙事学的结构问题》,《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7年第17卷第3期;李丰楙:《出身与修行:明代小说谪凡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宗教意识——以〈水浒传〉、〈西游记〉为主》,《国文学志》2003年第7期;李丰楙:《许逊的显化与圣迹——一个非常化祖师形象的历史刻画》,见李丰楙、廖肇亨主编:《圣传与诗禅——中国文学与宗教论集》,台北:台湾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7年。,传说净明道祖师许逊斩蛟时曾预言,一千二百四十年之后,会有地仙八百人现世,平定蛟乱。一时间,不少人参与其中,纷纷坚信自己将在应谶的那一年登仙,故而弃家入山者有之,著书立说者有之,入道修行者有之,求仙拜神者有之。然而,几次推断中的应谶时间都过去了,却没有谁白日飞升,大概不少人都和笃信这一切却什么也没有等到的屠隆一样,死前仍然“扶床凝望”,最终“怅怏而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45页。。
根据张艺曦的研究,龙沙谶以及《灵剑子》中的松沙谶,都源自许逊斩蛟的故事。许逊斩蛟之后,有蛟子破腹而出,但蛟子无罪,不可斩杀,许逊遂许下谶语:“以松坛为记,松枝低覆于坛拂地,合当五百年矣,吾当自下观之,若不伤害于民,吾之灵剑亦不能诛也。今来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相次已去,前后有八百人,皆于此得道,而获升仙,当此之时,自有后贤以降伏之。”同一文本后面提到了“龙沙”,吴猛问许逊以什么为记,许逊说:“豫章大江中心,忽生沙洲,渐长延下,掩过沙井口,与龙沙相对,遮掩是也。”而后宋理宗年间《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卷上“小蛇化”,则成了龙沙谶的完整形态,首次出现了“一千二百四十年”和“地仙八百人”之说。松沙谶的时间是五百年,而在龙沙谶中,则改为了一千二百四十年,之后遂成为龙沙谶的定型*张艺曦:《飞升出世的期待——明中晚期士人和龙沙谶》,《新史学》2011年第1期,第1-57页。。
白玉蟾(1194—1229)的《修真十书·玉隆集》中,也有龙沙谶的定型内容:
弟子施岑、甘战等引剑挥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长数丈,甘君欲战之,真曰:彼未为害,不可妄诛。小蛇惧而奔行六七里,闻鼓噪声,犹返听而顾盼其母。群弟子请追而戮之,真君曰:此蛇五百年后若为民害,当复出诛之。以吾坛前松柏为验,其枝覆拂地,乃其时也。又预谶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其师出于豫章,大扬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过沙井口者,是其时也。此时小蛇若为害,彼八百人自当诛之,苟不害于物,亦不可诛也。[注]《正统道藏》第四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1页,1a-b。
白玉蟾的文本可以视作对《灵剑子》和《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的融合,其间既有五百年之预言,又有一千二百四十年之预言,张艺曦认为,《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编纂于宋理宗年间,已经远超《灵剑子》原文中的五百年之期,故改预言的期限为一千二百四十年,然而白玉蟾年代在宋理宗之后,故而其中在提到五百年的时候,并没有八百地仙的说法,只提到若蛇为害,则弟子共同诛杀;而八百地仙出世的时间,则和《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一致。
到了1283年,刘玉在西山会见洞真天师胡惠超,胡惠超向他传授所得的许逊的谶语,也就是龙沙谶的内容:许逊升天一千二百四十年后,五陵之内有八百弟子出现,在豫章的河西岸宣教,而此刻龙沙已生,正是兴盛净明大道的时候。胡惠超的说法与前文所引的龙沙谶大体相同,但加上了此为净明道大兴的时候。除此之外,又预言刘玉将成为八百弟子之师。刘玉并从郭处获得乩笔所受的道法。然而考察围绕刘玉的相关文献,其中似乎并没有与八百弟子或八百地仙相关的其他内容,也许是因为刘玉受道的时机离谶言中一千二百四十年的期限尚有很长时间有关。
简单梳理过以上文本,虽然时间有差别,但地点则一致,强调的都是“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都在今江西一带。但当我们看向明代万历年间兴起的文人求仙风潮时,却不难发现,这种风气的中心位于江南地区,八百地仙不再出于“五陵之内”而出自江南。
参与万历年间这场登仙运动的主体,并非道士或者庶民,而是文人,其中不乏颇负盛名者,比如“后七子”领袖王世贞(1526—1590),又如“明末五子”之一的屠隆(1544—1605)。为什么这些接受儒家教育的文人会汲汲于这样一个飞升出世的谶言,并从各方面积极实践呢?[注]本文所说的“文人”,指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教育下的知识者,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通常引领当时的文化风气。虽然明清时期道教不断吸收民间俗信的内容,但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对道教的关注却从未减少,而龙沙谶的兴起更是带来了一种“狂欢”,文人们寻找着各种蛛丝马迹,去论证八百地仙之说不诬,或是采用扶乩等神异手段,试图传达他界的讯息,充实自己的信仰。而这种风气之下的书写和出版,也呈现出了一些共同的趋势。
一、以应谶异人为核心的文人信仰群体
虽然龙沙谶历经流传,在内容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一千二百四十年的应谶之期却确定了下来——正是明代的万历年间。而在此时的江南,许多文人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对应谶成仙的期待,甚至坚信自己即在八百弟子的名单之列。如冯梦祯曾记载:
夜,同叔永斋中雅谈,及神仙事,言龙沙之谶,应在十六七年,次八百人者,余得列焉,而邓先生为首,坤仪次之,右武、和甫俱与数,四之一俱士大夫。[注]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屠隆在写给友人陈继儒的一封书信中,也反映了类似的现象:
许旌阳《石凾记》中龙沙期,政在此时。而海内开明疏畅之士,亦往往好谭性命,从事大道。[注]屠隆:《栖真馆集》卷15,《答陈仲醇》,见汪宏超主编:《屠隆集》第五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7页。
冯梦祯的记载透露出的讯息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龙沙谶已成为当时文人之间谈论的话题之一,在讲论神仙之事时会自然带出。二是龙沙谶的应验时间,为万历十六、十七年左右。三是他们所认识的不少人,也在飞升之列。四是飞升的八百弟子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士大夫。从屠隆的表述中,可见当时的“开明疏畅之士”的群体中,已然因龙沙谶期限将至,而掀起了一股修真求道的热潮。
然而冯梦祯和屠隆的记录当中并没有透露这些讯息的来源,我们并不能完全确认,究竟是冯梦祯所接触到的这份也许已经在坊间流传许久的名单上士大夫众多,导致文人阶层对此事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是由于文人阶层对于龙沙谶信仰的迷恋与执着抑或是士大夫们“好谭性命,从事大道”,才导致八百弟子名单上出现了众多士大夫的名字。但不论如何,文士热衷于此,期待飞升成仙,是无可否认的。
勾稽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产生、仙籍名录出现与当时活动在江南的一批异人有密切关系。这些异人往往不是国家管理下的僧道,而带有很强的民间俗信色彩。他们往往居于信仰群体的中心,或者是在不同的文人交游群体中起着穿针引线、互相勾连的作用。如昙阳子、衡山道、彭又朔等人,都在这一时期有着重要的地位。
昙阳子(1558—1580),原名王焘贞,为王锡爵之次女,曾被许配与徐景韶为妻。而在王焘贞十七岁即将出嫁之前,徐景韶却不幸亡故,王焘贞自此立志修行,自号昙阳子,称自己为昙鸾菩萨化身。从她立志修行到最终坐化的短短几年之内,在她身边聚集了大量信徒,其中不少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比如王世贞、屠隆、沈懋学、冯梦祯等,甚至其父王锡爵和叔父王鼎爵,都成了其座下弟子。
考察文献,昙阳子本人并未涉及龙沙谶,但其座下弟子,却不乏热衷龙沙谶者。让昙阳子的弟子将她和龙沙谶联系起来的,则是她的一首诗:
左髻昙阳子,他时王害风。五陵为教主,古月一孤峰。两头尖未至,九环会壁红。[注]尤求:《昙阳仙师像》(沪1-1097),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此诗语言奇异晦涩,难以理解。“王害风”当为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的外号,此处昙阳子将自己同王重阳相提并论,当有以祖师自居之意。而“五陵为教主,古月一孤峰”一句,则直接与龙沙谶预言中的“五陵之内”相吻合,昙阳子成了五陵教主,便似乎应验了龙沙谶中的师者身份。这首诗让她笃信龙沙谶的信徒们找到了应谶的依据。屠隆就曾说:“而先师昙阳子诗所谓五陵教主,世多不能悉。”[注]王世贞:《读书后》卷8,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289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页。又将昙阳子、龙沙谶和衡山二道的预言合而为一[注]屠隆:《栖真馆集》卷15,《与王元美司美》,见汪宏超主编:《屠隆集》第五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87页。。
昙阳子被信徒奉为应谶之人,似乎带来了龙沙谶预言即将成真的第一个证明。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于万历七年末接触昙阳子,八年春奉昙阳子为师,又介绍在青浦任职的屠隆进入昙阳子信仰群体。昙阳子万历八年九月九日化去,此时离龙沙谶预言的升仙之期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以王世贞为代表的文人信徒,纷纷为其著书立传,张煌神异。比如仅王世贞一人,就著有《昙阳大师传》、《昙阳先师授道印上人手迹印》、《纯节祠记》等文,而王世贞实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地位超然,所著述之书无不洛阳纸贵。一时形成文人争相著述之势,以彰显昙阳子之神异灵验。除王世贞之外,王世懋、徐渭、屠隆这些名重一时的江南名士,都有相应文本记载昙阳子之事。王锡爵更是组织人将有关其女事迹的作品编辑成册,并刻印在坊间流传。在昙阳子化去之后,更是不断有文人通过冥通、扶乩等手段与昙阳子联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围绕在昙阳子身边的文人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屠隆本是王世贞的门生,早年追随王世贞的文学主张,而屠隆、沈懋学、冯梦祯三人,更是万历五年(1577年)的同榜进士,而屠隆接触到昙阳子信仰,正是因为王世贞的关系。而根据徐美洁的研究,这些士人都是张居正的反对者[注]徐美洁:《昙阳子的“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象》,《青岛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7卷第4期。。事实上,围绕着昙阳子一事,在当时政坛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徐学谟、张居正察觉此事,对这一派士人展开了口诛笔伐,甚至通过言官对其进行弹劾。魏宏远将此事定位为由昙阳子引发的政治事件。王世贞、王锡爵一派试图通过构建新的信仰,通过推动昙阳子信仰来提高自己的世俗地位。而张居正一派则通过斥责此事为“妖妄”,进而打击对方的政治势力[注]魏宏远:《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不论如何,昙阳子升化一事的影响之大,牵连人数之广,都是极为罕见的。以昙阳子为中心的错综复杂的混合了师生、同年、亲戚、政治等关系的信仰网络,其中涉及之人,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将信将疑还是各抒己见,都无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昙阳子之外,衡山二道一系的弟子以及彭又朔等人,也在轰轰烈烈的龙沙谶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传衡山二道——王初阳和薛玄阳掌握了飞升冲举的金丹秘诀,故而其派系在晚明大受士人欢迎。王世贞曾和衡山一系的道人有过接触,并将他们带入了龙沙谶信仰者的交游网络。衡山系道人同样也被他们视作龙沙谶的应谶之人。不同于昙阳子的是,衡山弟子会直言龙沙谶之事,甚至起到了代言人和宣传者的作用。比如周光岳声称自己亲眼见过载有八百弟子的仙籍名单,上面载有屠隆、管志道、邹元标等人的名字[注]屠隆:《鸿苞》卷40,《与邓汝德少宰》,见汪宏超主编:《屠隆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6页。。自己标榜“得道”已从侧面表明了其学说的权威性,而对龙沙谶应谶情况详尽而确切的描述,又让这些追随者们更加相信自己在八百地仙之列,时日一到,便将飞升登仙。
彭又朔是一位具有方士色彩的人物,钱谦益(1582—1664)的《列朝诗集小传》有彭幼朔的小传,根据张艺曦考证,此两者应为同一人[注]张艺曦:《飞升出世的期待——明中晚期士人与龙沙谶》,《新史学》2011年第1期,第36页。。钱谦益将其形容为仙翁,称他“以服气法授人,兼传汞银法”,并记载了自己同彭又朔的来往经历[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08页。。彭又朔如同衡山系道人一样,在南京宣讲龙沙谶,并得到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与彭又朔类似的人物在当时也有不少。这些异人携龙沙谶之说自重,通过结交士人,与之来往,成功进入了他们的网络,获得了为数不少的支持者,让龙沙谶之说在昙阳子化去后的几十年间仍经久不衰。
传说中的龙沙谶应谶之期的前数十年时间,以这些应谶之异人为中心,文人们组成了一种信仰群体。人们结识并追随这些异人,往往是通过师长或侪辈的引荐,而他们之间自身的种种联系,使得这一群体愈发紧密。而这些信仰者们,往往是文坛作手,他们为昙阳子撰写的诗文,通过有组织的编辑出版,对相关信仰进行了传播,一方面,昙阳子信仰是他们交游网络的中心之一;而另一方面,他们的交游网络又为信仰的扩散提供了有效的渠道。之后,以衡山系道人和彭又朔为代表的异人,也进一步凝聚了这种信仰群体。
二、编纂仙传与道经的风潮
仙传的编写,在古代中国一直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从中古早期的《列仙传》、《神仙传》开始,到五代道士杜光庭所作的《墉城集仙录》,都体现了仙传传统的延绵不绝。而明清之际,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涌现出了不少神仙集传,其中部分神仙集传的撰写者也是龙沙谶事件的关系者。同时,这些文人也热衷于收藏、评点道经。
当时出版面世的几部仙传中,与龙沙谶信仰及周边事件、人物直接相关的,大略有以下数种:

作者编者书名出版时间传世版本屠隆列仙传补见《鸿苞》,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续表
有趣的是,这四种仙传恰好可分为两类,屠隆和陈继儒都是与昙阳子事件和龙沙谶信仰直接相关的文人,而杨尔曾和汪云鹏都是万历年间著名的书商。
徐兆安指出,屠隆的《鸿苞》虽然看似散乱无迹,但实则表明了他反对正史对玄门的压迫,以道教本位看待并书写历史的立场[注]徐兆安:《万历朝文人王世贞、屠隆与胡应麟的神仙书写与道教文献评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第53期,第268页。。《列仙传补》是《历代真仙通鉴》的补充,将明代仙真的事迹增补入内,既是一部既有仙传的续书,也是他个人宗教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体现。《列仙传补》中收录了大量明代出现的异人,而非国家认证的正统僧道,有一些是因行为邪僻恶劣深受士人抨击的,比如赤肚子,甚至不乏被朝廷斥为妖人的乱党,如李福达[注]李福达为明代弥勒教领袖,曾公开宣扬弥勒信仰来鼓吹民众作乱,正德初年发动宗教叛乱,嘉靖年间的叛乱也是其传人所为。见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28页。。这样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当时历史背景和屠隆个人经历的语境下,则变得不难解释。屠隆是昙阳子的虔诚信徒,昙阳子自修道以后,随着影响的逐渐增大,直至声势如日中天,对她的攻讦和抨击就不曾停止,这些攻击除了来自坊间或同为文士的侪辈之外,更有来自代表正统权威的当权者张居正和其派系的官员士大夫,如《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八》记载王锡爵受到张居正一党弹劾时,昙阳子之事也赫然在列:
王锡爵感时行援,引之私情,而攻李植玄宫有水之议,其女为妖蛇所污,计为掩饰,作《昙阳子传》,自称曰奉道弟子。[注]台湾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实录(附校勘记)》,南港:台湾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2—1968年,第1326页。
《明实录》的记载,明显将昙阳子归入“妖妄”一流,称她是被妖蛇(即昙阳子之灵蛇)所污,为昙阳子所作之传记,也是为遮掩不文之事,并对其“奉道弟子”的身份在字里行间表示了怀疑。
基于当时庙堂之上这样的议论,屠隆的《列仙传补》,大肆搜列民间方士异人,当有在这种语境之下为昙阳子张目之意。而为昙阳子张目,则恐怕隐含了他对龙沙谶的坚信不疑,辑录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仙家,也是为坚信自己和侪辈在八百地仙之内做好铺垫,为昙阳子张目的同时也是为自己张目,彰显龙沙谶的正统性和真实性。
陈继儒和大力宣扬昙阳子信仰的王世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在王世贞家为子弟教席,在他的文集中,也时常可以找到一些有关王世贞的侧面记载。他撰写《香案牍》,本质上是对《历代真仙体道通鉴》进行改写,认为《历代真仙体道通鉴》的文字粗鄙,需要润色删改。看起来,这一行为似乎彰显了身为文人的自觉,润色字词,删改语句,增强古书的文学性,仿佛体现的是文人审美的趣味。但对元代道士所撰的《历代真仙体道通鉴》的文笔不满,并对其进行删改润色,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陈继儒自己的宗教倾向,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出于文学修养,而实质上起到推动作用的仍然是作者本身的宗教意识。
在这两部属于昙阳子周边的文人所撰的仙传面世以后,由书商主导的《列仙全传》和《仙媛纪事》也刊行并开始进入世人的视野,而这两本神仙集传都与昙阳子信仰有莫大关联。汪云鹏的《列仙全传》和杨尔曾的《仙媛纪事》都全文收录了王世贞的《昙阳大师传》,而这两部书面世的年份,距离昙阳子化去之时已过去了约二十年之久。基于王世贞的盛名和昙阳子事件的轰动性,加上《昙阳大师传》被刻意印行推广的行为,文坛士林中对此事的议论和反馈从未停止。在文本流传上,虽然有关昙阳子事迹的记述不止一个版本,但有关她的传记,几乎全脱化自《昙阳大师传》。本章的目的之一,即是厘清这二十来年王世贞《昙阳大师传》的流传情况,以及衍生出的诸多文本,以为后续讨论之基础。
同时,《仙媛纪事》的编纂者杨尔曾,有着亦士亦商的身份,他是万历年间重要的书商,有苏州、杭州两间书坊,苏州的名为草玄居,杭州的名为夷白堂,《仙媛纪事》便是在苏州草玄居刊刻出版的。杨尔曾本身是道教徒,对于神仙传记的出版当有浓厚兴趣,《韩湘子全传》也是他所编辑出版的。从他对刊印图书题材和内容的选择来看,他对道教有着强烈的兴趣。《仙媛纪事》更是由昙阳子的追随者冯梦祯作叙,叙中说杨尔曾:
爰暂辍丹铅之暇,考索仙宫之箓,起自殷时,迄于昭代,得女仙如干名……[注]明万历刊本《新镌仙媛纪事》卷首叙,见王秋桂、李丰楙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
可见杨尔曾自身有着道教实践活动,《韩湘子全传》记录了道教重要神仙“八仙”之一的韩湘子的事迹,而《仙媛纪事》更是有不少取材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道教相关书籍的内容。根据梁诗烨对杨尔曾编创小说的研究,他不但是出版商,更是身兼了一部分作者的职责,他所参与编纂出版的作品,都会加入自己的创作和改写,除了书商身份之外,他也是一位具有相当创作才能的文人[注]梁诗烨:《杨尔曾及其编创小说研究》,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0年。。
汪云鹏所编的《列仙全传》托名王世贞,固然有藉助文坛巨公的名气,为所刊印图书增加销量的做法,但是考察汪云鹏所刊刻的其他书本,并没有类似的托名情况,可见他并非仅仅是为了藉助名人效应而谋求利益,更有另一种可能是王世贞早年对昙阳子信仰进行著述与推动,《列仙全传》这样一本宗教色彩浓厚的书籍托名于他,更能彰显权威性。
然而抛开以上所有的外部原因来看,书商刊刻书籍,本质是为了牟利,在古代的图书出版过程中,跟风现象也时常可见。王世贞的《昙阳大师传》面世已久,《仙媛纪事》和《列仙全传》却全文收录该篇,可见事件的火热程度,二十年后依然不减,在图书出版业,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商机。而《仙媛纪事》全书记载女仙事迹,让我们不由思索这二十年间昙阳子事件的余绪对各界的影响。
同时,在江南文人之中,也存在着一股整理、评点道经的风气。其中,活跃在万历年间的李鼎是一位重要人物。李鼎的文名虽然并不如王世贞、屠隆等人一般显扬,但他与明末文坛“前七子”相关人物都有往来,也是当时文人圈子中的重要人物了,亦有文集行于世。李鼎亦是龙沙谶的坚定支持者,李鼎在《净明忠孝经传正讹》之疏中明确提到了龙沙谶:
都仙一千二百四十年之谶适当万历在宥之壬子,距今一年而溢耳。海内奉道弟子延领西望而不得其朕也。盖日怦怦焉。[注]李鼎:《李长卿集》,明万历李嗣宗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从中可见李鼎在净明道正信的经典中,立场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龙沙谶的坚信不疑,之后,他甚至不惜抛却家业,入山等待飞升。李鼎既对净明道虔诚信仰,又是上文所言及的彭又朔的信徒,并对所传的八百地仙之师刘玉极为推崇。[注]许蔚论及此事,认为李鼎是站在儒家士大夫立场上,故而极其推崇刘玉。见许蔚:《断裂与构建:净明道的历史与文献》,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112页。
李鼎曾经作《净明忠孝经传正讹》,他通过考证论辩,重新编订了净明道自许逊而下的道脉传承。他对龙沙谶的贡献,是重新推定了龙沙谶的应谶之期,即前文所引的“万历在宥之壬子”,壬子即万历四十年。李鼎怀着对自己学说的自信,入山以待登仙,最后也自然以失望告终。
李鼎的事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儒道交涉的视角。他曾经以儒家立场,小心翼翼地为飞升冲举之事正名:
冲举之事,传神仙者往往而书,正史不载,意深远矣。铁柱虽镇地脉,则自旌阳公特创,为有目者所共睹,焉可诬也?盖宇宙在手,万化生身,造无而有,则为铁柱;化有而无,则为拔宅。玉真子以为役神物,移置海岛,则物而不化矣。总之以净明忠孝为本,何必异于圣学哉。列子曰:“仲尼能为而能不为者也。”可以释千古之疑网矣。[注]李鼎:《李长卿集》,明万历李嗣宗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他认为正史不载飞升冲举之事,自有其深远含义,论述了飞升拔宅的正当性,强调“净明忠孝为本”,认为净明道的信仰无异于圣人之学。这段论述中,他站在儒家本位的立场之上,提供了一种儒道交涉的视角。
在李鼎这样直接编撰道教经典的文人之外,昙阳子的追随者们也热衷评点、整理道经。王世贞的《弇州山人续稿》一书中,可见不少他对道经的考证,甚至一一指出道经中的神通妙化故事的不可信之处,加以辨伪。他有《书道经后》一系列文章,对他所阅读的《黄庭经》、《阴符经》、《清静经》等诸多道经进行了阐发,并且加以考证论辩[注]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可谓是当时江南文人阅读、批评道藏风潮的代表。屠隆和王世贞在对宗教的见解上有过争论。徐兆安认为,屠隆和王世贞对宗教信仰的不同表述和争论,实质则是二人在文坛的角力[注]徐兆安:《十六世纪文坛中的宗教修养——屠隆与王世贞的来往(1577—1590)》,《汉学研究》2012年3月,第205-238页。。
这种现象也不能仅仅用“文人趣味”来解释之——虽然阐发精要、考索本事、证实证伪的确是古代文人的本色当行。这一行为的背后,有着不可忽视的外界影响,对于飞升的期待,和自身所见所闻的种种异人灵迹,推动了他们著书立说的本能。而时人对于昙阳子的抨击,对于龙沙谶的讨论乃至怀疑,都促使他们去彰显一种“正统性”,而对道经的阅读、评点、考据,表面看似乎推翻了既有道教信仰中的不少元素,但却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为自己的立场树立了一种新的正统。
三、“归位”语境下的小说书写潮流
在终末论的思潮下,众仙归位的观念,自六朝开始的道教传统中,便一直有一席之地。如《真诰》、《真灵位业图》与《周氏冥通记》这些六朝道教经典中所构建的神仙体系,便体现了上清派的神仙归位思想。许翙、周子良、陶弘景都有被命定为仙官的事迹与记载。而这一类型的叙事模式,在后世笔记中也屡见不鲜。查考龙沙谶的书写,则可发现,有很强的终末论色彩与随之而来的神仙归位。其中关系值得深究。
龙沙谶广泛传播的同时,明代中后期涌现的大量宗教意味浓厚的、以神仙斗法为题材的小说作品,被鲁迅概括为“神魔小说”[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而后世学者在论及这类作品时,往往直接采用这一概念[注]专书如茍波:《道教与神魔小说》,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冯汝常:《中国神魔小说文体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至于以“神魔小说”直接入题的单篇论文,更是不可胜数,此处便不枚举了。。然而,即使从题材分类的最初出发点来看,“神魔小说”这一概念也未必准确。比如被视为神魔小说代表的《封神演义》,其中的对立势力,在人间政治层面则为武王之周和纣王之商,在宗教体系层面则为元始天尊之阐教与通天教主之截教,其中仙、神、魔的分野,并不以互相对抗的势力区分。故而,在面对这些文本时,应当先抛开文学史上根深蒂固的成见,从当时的社会风气、宗教背景来审视。
而事实上,明代风行的白话章回小说,不论题材如何,内容上都无法脱离世俗世界中宗教信仰的影响。《西游记》、《南游记》、《东游记》、《北游记》、《封神演义》等这些与宗教直接相关的小说不论,即使是历史题材小说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都不难看出其中反映的当世宗教的意涵。这些小说,通常也是由书坊主刊印,书坊主依靠对市场风向的把握,组织作者对特定题材进行写作,甚至亲身参与创作,这也是市面上会大规模同时出现类似题材的小说的原因,这也导致许多小说的作者在当代已无法确定。
白话小说虽然一度被归入俗文学一类,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针对的读者主要是只有基础文化修养的普罗大众,但就写作而言,能完成谋篇布局、统筹材料等工作,写出传世之作的作者们,绝不可能如其读者群一样,是文化修养平平的普通人,至少应具备中等偏上的文化水平。
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白话小说的流行可以反映两方面的信息:就其出版的特点来看,能显示当时社会上普遍的思潮和流行,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当时人对宗教的认识,以及大众所秉持的宗教观念;而在写作者的层面,写作者通常具有文人的身份,即使是为了市场风向而“量身定制”的小说,也不可避免会带上作者本人思维的印记。故而,从这两点来讲,书坊间的白话章回体小说,不失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宗教氛围、文人思潮和流行风尚的一个绝佳透视点。
在本文的研究议题下,《封神演义》卷末的那张封神榜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在关于龙沙谶的各种讲论或叙述中,我们可知当时龙沙谶的追随者们相信有一张记载了八百弟子的名单,这一名单时常在文人的记载中显现一鳞半爪,而谈论此事的文人,经常流露出一种“榜上有名”的心态,认为自己是命中注定要飞升成仙的。这样“榜上有名”的宿命感,在《封神演义》中时常可见,如第一回:
却说二位殿下殷郊、殷洪来参谒父王——那殷郊后来是“封神榜”上“值年太岁”;殷洪是“五谷神”:皆有名神将。正行礼间,顶上两道红光冲天。[注]许仲琳:《封神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6页。
殷郊、殷洪第一次出场,便特地点明了他们在封神榜上有其位次,日后会分别封神。类似的例子还有第七回:
纣王曰:“二卿,今日升殿,异事非常。”比干曰:“有何异事?”王曰:“分宫楼有一刺客,执剑刺朕,不知何人所使?”黄飞虎听言大惊,忙问曰:“昨日是那一员官宿殿?”内有一人,乃是“封神榜”上有名,官拜总兵,姓鲁名雄,出班拜伏……[注]许仲琳:《封神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9页。
鲁雄在出场时,作者也讲出了他在封神榜上留有姓名之身份。而封神榜这一名单的来历,也在第十五回姜子牙下山时,由作者以旁白的形式道出:
话说昆仑山玉虚宫掌阐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门下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厄,杀罚临身,故此闭宫止讲;又因昊天上帝命仙首十二称臣;故此三教并谈,乃阐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编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又分八部:上四部雷、火、瘟、斗,下四部群星列宿、三山五岳、布雨兴云、善恶之神。此时成汤合灭,周室当兴;又逢神仙犯戒,元始封神,姜子牙享将相之福,恰逢其数,非是偶然。所以“五百年有王者起,其间必有名世者”,正此之故。[注]许仲琳:《封神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38页。
这一段详述了封神榜的来历和构成,其中颇多与龙沙谶预言相通的部分。首先,龙沙谶和封神榜都起源于不祥之灾厄,龙沙谶有蛟患,后来更是发展成了“末世说”一般的存在,而封神榜则来自元始天尊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厄,即小说中常常提到的“杀戒”。此外,二者都由较高等级的神仙编定,如王世贞曾记载昙阳子是参与遴选成仙之人,封神榜亦是由三教掌门共同商议。其次,榜上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龙沙谶无疑是平定蛟患,而封神榜则是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各显神通。最后,龙沙谶和封神榜的体系里,都有一位类似“师者”的角色,龙沙谶的刘玉甚至后来的昙阳子,封神榜的姜子牙,都有意识地引导榜上之人各归其位,而“五百年有王者起”,也让人直接联想到龙沙谶最早原型松沙谶的“合当五百年矣……”
《封神演义》的作者已不可考,主流的说法有许仲琳、陆西星等,而不论如何,目前所知《封神演义》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年间金阊舒载阳刊本,该本成书于明代中晚期,当是事实。舒载阳为苏州书商,地域上也属于江南。《封神演义》的刊行,和龙沙谶的流行在时间、空间上都高度重合,加上内容上的呼应之处,《封神演义》可以被视为龙沙谶传说的“置换变形”[注]置换变形(displacement),由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提出,指小说在运用神话结构时,需要将其进行变形和移位,以让读者觉得真实,见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其书的面世,当是受到江南地区龙沙谶盛行的影响,反映了文人热切追求的群仙归位的意识。
一则有关《封神演义》作者的有趣材料,也为《封神演义》和龙沙谶的关系提供了别样的注脚:
俗传王弇州作《金瓶梅》,为朝廷所知,令进呈御览。弇州惧,一夜而成《封神演义》,以此代彼,因之头白。[注]蒋瑞藻:《小说枝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82页。
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说此说源自不具名笔记。王世贞一夜写成《封神演义》的故事显然荒谬不堪,不足为信,但是,即使是荒谬的坊间传言,也要把虔诚相信着昙阳子和龙沙谶的王世贞和《封神演义》扯上关系,也足以窥见当时人对这种成仙风气的反应。
另一部充满着这种“榜上有名”思想的小说则是《水浒传》,《水浒传》看似与神魔斗法毫无关系,但整个故事的最大线索,却是从开头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到七十一回梁山聚义,石碣现世,梁山诸人发现自己上应天星这一过程。水浒故事中所谓的“聚义”,其实也是散落人间的一百零八星宿聚集的过程。
《水浒传》中所谓的魔王,看似和龙沙谶叙事中的“地仙”相去甚远,但如同《封神演义》表现的那样,《水浒传》中也时时体现了这种“榜上有名”的思想,如第五十七回:
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自然意气相投,就梁山泊做了头领。[注]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756页。
因为韩滔身在七十二地煞的名单之内,纵然他本人并不知情,也注定要留在梁山与其他星宿相聚。这和《封神演义》中时时体现出的因在封神榜上有名某人便命中注定要下山参与殷周大战一般。
虽然我们很难找到当时在江南文人中流传的八百地仙名单的原貌,但《藏外道书》所收录的一份名为《瀛洲仙籍》的材料也能作为登仙之人名单的一种代表,让我们窥见一斑[注]胡道静,等主编:《藏外道书》,成都:巴蜀书社,1992,第664-667页。。《瀛洲仙籍》正文前署名为元和子的《瀛洲仙籍序》中说:
厥后许君证道升霄,依谌母之所嘱,留八百仙之姓名,刻于兰公堂石碑之上。曰八百登瀛洲,故有此瀛洲籍也……真君埋碑去后,迄今国初洪武,水冲碑现,八百仙名俱昭然揭露。[注]胡道静,等主编:《藏外道书》,成都:巴蜀书社,1992,第664页。
八百地仙名单的揭露过程,直让阅读者联想到了《水浒传》中,刻有天罡地煞姓名的石碑是如何发现的:
当日公孙胜与那四十八员道众,都在忠义堂上做醮,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满散。宋江要求上天报应,特教公孙胜专拜青词,奏闻天帝,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时分,公孙胜在虚皇坛第一层,众道士在第二层,宋江等众头领在第三层,众小头目并将校都在坛下。众皆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是夜三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干方天门上。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又唤做“天门开”,又唤做“天眼开”。里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栳之形,直滚下虚皇坛来。那团火绕坛滚了一遭,竟钻入正南地下去了。此时天眼已合,众道士下坛来。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根寻火块。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只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注]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924-925页。
梁山一百零八人聚齐之后,宋江请道士做罗天大醮,第七日天降火块,启示宋江等人掘开地面,挖出了刻有天书的石碑,上面刻着梁山诸人的姓名。此后宋江对诸人的一番感叹,也令人联想到了前面对《封神演义》的论述:
宋江与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一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注]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928页。
“上应星魁”和“一会之人”充分说明了梁山一百单八将聚义的宿命性,而对一百零八人的星宿次序,宋江强调要各守其位,也是龙沙谶、封神榜一贯的“归位思想”体现。虽在《水浒传》中所占笔墨不多,但却成为故事线索的天罡地煞归位的情节,亦是龙沙谶叙事文本互涉的体现。
明代经由书商推动,在江南大量涌现的白话章回小说,虽然所叙之事大部分虚构无凭,但其中贯彻的龙沙谶情节,并不是巧合。一方面,身为作者的文人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而将流行的信仰形诸笔端;另一方面,书商为了迎合市场,推出和当时人心态相吻合的图书商品。《封神演义》出现在万历年间,而《水浒传》嘉靖年代便已经出版,除这两本书外,与之类似的小说还有很多[注]在后来的章回小说中,这样文末出现“仙榜”,主人公们完成任务后一起登仙的模式屡见不鲜,如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也有一张百花仙子的才女仙榜,故事中的女孩子们都是下凡的花神,考上才女后各自归位。这或许可以视为龙沙谶对章回小说影响的余绪。。这种叙事传统多年不衰,广受欢迎,也足见得当时普遍存在的追求升仙、等待归位的社会风气流传甚广。
通过探讨以上由“龙沙谶”在文人和书写中引发的浪潮,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对宗教与文学纷繁复杂的关系做一探讨。除了“宗教与文学”之外,“文学中的宗教”、“宗教中的文学”、“作为宗教的文学”、“作为文学的宗教”等等,也都存在于浩瀚的文本中,此外,文人和宗教的关系也值得深入探讨。王世贞写作的《昙阳大师传》在坊间广为流传,并且成为坊间诸多仙传的底本,不仅仅因为他文坛领袖的身份,亦是昙阳子的神异事迹在当时的风行所致,这种互相交织、互相推动的作用,形成了宗教与文学间的迷离图景。而《昙阳大师传》中,也可以见到在书写范式上对《南岳魏夫人传》的效法,这显然也不能用“王世贞的写作受到道教影响”的理由来敷衍。
当时江南兴起的出版业,也不失为一个别样的视角。万历年间,书坊主热衷于出版神仙集传、神怪小说甚至道教经典,一些书坊主自身也参与编辑写作,如果说是商人逐利的本能所致,那么当时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对此类出版物的欢迎?如果是书坊主自身的立场所致,那么在这个纷繁的信仰网络中,他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此外,出版业的兴盛,对宗教的发展又起到了何种推动作用?
无疑这些书写的元素也如同这场宗教活动中的文人们一样,构成了一张密不可分的网络。而这些主演们之外的舞台,也似乎弥漫着相似的气息。龙沙谶的风潮,也直接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在王阳明平宸濠之乱被附会为龙沙谶斩蛟后,有关斩蛟之事的附会也日益兴盛,如陈继儒所作《斩蛟记》将丰臣秀吉附会为许逊斩蛟故事中逃脱的蛟子,此时出来作乱[注]陈继儒:《斩蛟记》,见薛洪绩、王汝梅主编:《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229页。。在龙沙谶体现出的道教终末论与众仙归位的思潮影响之下,当时风行的白话章回体小说也处处显示出相似的情怀。龙沙谶地仙出世、榜上有名、平定祸乱、终而归位的情节,亦是《水浒传》、《封神演义》等由书坊主主导的白话章回小说的叙事主线,而这些小说也正成书于龙沙谶风行的时间段内,亦出版于龙沙谶流行的地域,这样的重合,显然也是由文人圈子扩散开来的宗教风气的一环。同时,在既有观念中,《水浒传》这种反映啸聚山林、武装暴动的小说,往往很难和宗教产生联系,这也为“宗教文学”这一概念,提供了新的反思角度[注]李丰楙教授已然注意到了《水浒传》和道教的关系,他将《水浒传》的叙事与道教谪凡观念结合,提出水浒英雄们在人间的过程,实为“暴力修行”。见李丰楙:《出身与修行:明代小说谪凡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宗教意识——以〈水浒传〉、〈西游记〉为主》,《国文学志》2003年第7期,第85-113页;李丰楙:《暴力叙述与谪凡神话:中国叙事学的结构问题》,《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7年9月第17卷第3期,第147-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