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中的情感和性别
——陶思瑾案与民国女性同性爱话语
2017-10-10李世鹏
李世鹏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公众舆论中的情感和性别
——陶思瑾案与民国女性同性爱话语
李世鹏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0)
民国;同性爱;话语;媒体
民国女性青年中盛行着“同性爱”之风,时人对于这一现象也一直保持着关注。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于杭州的陶思瑾杀死同性恋人刘梦莹的惨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在媒体的炒作下,同性爱成为了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国族危亡的背景之下,血案的发生使得社会主流舆论对同性爱的态度逐渐呈现出总体负面化的趋势。通过陶思瑾案后的社会讨论,可以见到公众舆论对于性别与情感的想象和介入。在传媒的推动之下,私人情感问题成为了社会问题,从而被公共化。
KeyWords:Republic of China;homosexuality;discourse;media
Abstract:“Homosexuality”(同性爱) was popular among women and became a public concer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In the early 1930s,the case within which Tao Sijin From Hangzhou killed her same-sex lover Liu Mengying was widely reported and debated across the country.Homosexuality,sensationalized by the media,became an issue that caused wide controversies.In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crisis,this murder helped create a general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homosexuality in the mainstream of public.By examining the public discussions about Tao’s case,we can see public’s imagination about,and intervention in,gender and emotion,through publicizing personal emotions and turning it into a gender issue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The media helped transform a personal emotional affair into a social issue publicly discussed.
民国时期的女性,特别是女学生中盛行“同性爱”。“一女子和另一女子发生爱的关系,在摩登的女学生中间,原是普遍的现象。”[1](PP 113-114)“五四”以后,青年学生的同性恋爱更成为很普遍的事情[2](P 32)。有人说“在我们当女学校的寄宿生时,常时会听到些某人与某人,爱到了不能再爱”[3],实际上大多经历过当时校园生活的女性都有此类经历或见闻。在女性同性情欲流行的同时,民国时期的人们开始将同性情感与性行为作为一种性取向加以认知,并围绕同性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民国时期占据舆论主要篇幅的是对于女性同性爱的讨论,专门探讨男性同性爱的相对较少),进而形成评判同性爱的现代话语*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话语”研究,可参见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女性同性爱在民国时期的流行,与社会的整体风气相关。一方面,“自由恋爱”思想此时得以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从观念到实践,青年男女仍难逃各种羁绊。(吕芳上:《革命与恋爱——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情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载于邓小南、王政、游鉴明编:《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9页)女学生自身的心理禁锢难以一时消解,很多人羞于接近异性。社会也处于半新不旧的状态,即使女青年们“理智上明白了结婚不能像过去一代那样马马虎虎,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去摆布”,然而“那时中国的社会,还在半新不旧的过渡时期,男女的社交,还没有达到很公开的地步,要自由选择对象,还没有很多的自由场合”(珍妮:《同性恋爱》,《新妇女月刊》1946年第5期)。现实生活中的男女社交并未完全公开化,加之“父母管束严紧,不会交际,异性是很少见面的”,女校“封闭的空间”又隔绝了两性间的日常接触,因此,在被限制的空间之中,处于青春期的女子们多数只能接触同性,“一切的安慰,便就近向同性的身上追求了”,与此同时,校园中女性之间互相撮合的“拉朋友”游戏也催生了女子间的爱恋。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学生们“不得已,在可能范围中,舍远求近,弃异性而专攻同性恋爱之途径。初则姐姐妹妹,亲热有逾同胞,继则情焰高烧,陷入特殊无聊恨海,终则竟超越情理之常,来一下卿卿我我,双宿双飞,若妇若夫,如胶如漆”(玉壶:《冰心演讲同性爱记》,《玲珑》1936年第6卷第28期)。关于此点,笔者另有专文探讨。。
在中国古代,同性间的性行为和情感虽然为社会所认知,但对它们的描述十分宽泛,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被用以形容这种关系,同性间的情欲常被称作“风”或“癖”等,并没有“同性爱”“同性恋”等词汇。同样地,在民国“女同性爱”概念产生以前,中国古代虽也有女性同性情欲的展现,但并不存在一种“可以与‘男色’相提并论的一般化范畴,来指称一种独特的女性间关系”[4](P 19)。同时由于古代女性地位较低,其同性情欲的展现也相对隐晦*在严格的家庭和男女等级中,例如女婢之间、妻妾之间的同性情感关系很多时候被默许存在,但中国古代女子的同性情欲通常藏于闺阁,不见诸公众视野,今人仅能通过一些隐晦的明清文学大致窥见这一群体的样态。。女性同性情欲的形象大多也是通过男性的视角描绘出来的,男性书写者基本对女性间的情欲世界“抱以同情宽容的态度”*参见曾春娥:《中国女同性恋历史》,《中国性科学》2005年第14卷第4期,第37页。同时,女性同性情感较之男性获得了更大的宽容空间,更在于在古代中国“女性”往往是被忽视的,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忽视并不意味着“女性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它仅能意味着没有被男人看作是威胁”。见桑梓兰:《浮现中的女同性恋:现代中国的女同性爱欲》,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24页。。概言之,同性情感关系是作为一种情欲选择而不是性别取向被人们所认知。
目前对于民国女性同性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性别理论和新闻史方面。文学研究者对近现代同性恋史的研究目前相对较为充分。庐隐、凌叔华、石评梅等一批“五四”作家对同性爱的大量描写,使得对“同性爱”的关注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话题*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简瑛瑛:《何处是(女)儿家?试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同性情谊与书写》,《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7年第5期;王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同性恋书写的变迁》,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陈娇华、闵怡红:《试论20世纪中国女作家笔下的女同性恋书写》,《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刘小菠:《论中国文学作品对同性恋的表现》,《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郭海鹰:《从性别视角看中国女作家的女同性恋书写悖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Wendy Larson,“Female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Relations:The Early Stories of Lu Yin and Bing Xin”,Politics,Ideology,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Eds.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Wendy Larson,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eng Hsiao-yen,“The New Woman:May Fourth Women’s Struggle,Self-Liberation”,《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5年第6期。。除了文学研究以外,还有一些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人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及民国社会对同性爱的讨论*近年有相关的博士论文出现,如复旦大学的陆新蕾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了新闻媒介与同性爱自民国以来的互动,但其论说侧重于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与表达,何楠博士在对《玲珑》杂志的研究中也将同性爱作为30年代女性生活的一部分来解析。参见陆新蕾:《从话语再现到身份抗争:大众媒介与中国同性恋社群的互动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何楠:《〈玲珑〉杂志中的30年代都市女性生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而历史学者对于民国同性爱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季家珍、冯客、李海燕等在其研究中均提示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但未进行专门的解读*参见[美]季家珍著,杨可译:《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Dikötter,F.,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Haiyan Lee,Revolution of the Heart: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190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 2007;Paul J.Bailey,“‘Unharnessed Fillis’:Discourse on the‘Modern’Female Stude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罗久蓉、吕妙芬主编:《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年,第350页;王东杰:《一个女学生日记中的感情世界(1931-1934)》(《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7年第15期)中亦涉及女学生间的亲昵关系。。简要总结当前的主流观点,从事新闻史或女性史的研究者均得出与康文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大众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经历了“由松到紧”或“由极具争议性到较一致的谴责”的变化*参见Kang Wenqing,Obsession:Male Same-Sex Relations in China,1900-1950,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
在民国同性爱历史过程中,1932年发生在杭州的陶思瑾杀人案是最为轰动的新闻事件,女学生陶思瑾杀死其同性恋人刘梦莹,各路媒体大量跟进和报导,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杀人案和同性爱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者重建了陶思瑾杀人案的案情发展,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案后的舆论,并指出陶思瑾、刘梦莹血案之于社会对同性爱态度的影响*如韩珊:《跨语言改写:重读民国时期“同性爱”话语的翻译与演变》,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陈静梅、桑梓兰等学者在其对民国同性爱问题的研究中也注意到陶思瑾案。可参见陈静梅:《现代中国同性恋爱话语译介及小说文本解读》,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桑梓兰、王晴锋译:《浮现中的女同性恋:现代中国的女同性爱欲》,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前揭何楠、陆新蕾等的研究中也有所论述。承四川大学徐阳同学提供相关资料,谨致谢忱。。
本文将从私人情感与性别议题的公共化角度出发,主要关注媒体及社会舆论对于民国时期同性爱话语的影响,通过梳理媒体对陶案的炒作和公众舆论对于陶案的评论,观察民国时期的公共舆论如何想象、参与同性爱议题,并将同性爱置于社会问题与国族话语之中,最终塑造对同性爱的主流话语,借由这一案例揭示出传媒与近代中国私人情感公共化的关系。
一、制造新闻:陶思瑾案的发生与媒体的参与
1932年2月11日,著名作家许钦文的家中发生一桩凶杀案,女学生陶思瑾受伤,另一位女学生刘梦莹死亡。案情发展几经波折,初则因陶思瑾与刘梦莹皆昏迷不醒,因此媒体将杀人嫌疑指向屋主许钦文。但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陶思瑾假装昏迷的行径被发现,又经办案人员调查发现陶、刘的同性恋人关系,最终,陶思瑾承认她杀害同学刘梦莹的事实。
案卷调查报告指出,陶、刘是浙江艺术专科学校的连床舍友,二人在亲昵中逐渐发生恋爱关系,并誓不结婚。但陶、刘二人爱久生疑,“刘梦莹见陶思瑾与该校绘图系女教师刘文如亲近异常,颇疑其亦有同性恋爱关系,屡嘱思瑾与刘文如绝交,并以杀害刘文如或陶思瑾及宣布恋爱历史等词为恐吓。因之两人情感,已由此日疏”[5]。许钦文是陶思瑾亡兄陶元庆的挚友,他平日对作为陶元庆妹妹的陶思瑾也多有关照,许氏在西湖边购置房产陈列陶元庆画作,陶、刘二人亦常来此居住。1932年,刘梦莹因上海战事爆发,逃难至许钦文处,与此同时陶思瑾亦自绍兴来杭州送刘文如回四川。陶思瑾见刘梦莹后即前往艺专留宿,原本计划八号回绍兴的陶思瑾在刘梦莹的挽留下在杭州多住三日,二月十一日,徐钦文出门后,陶思瑾与刘梦莹发生激烈争吵,陶思瑾愤而砍杀刘梦莹*据结案陈词载:“陶思瑾又欲回里,复因刘梦莹之留未去,午后许钦文送其女友郭德辉至江干北仙桥学校……家中仅有刘梦莹陶思瑾及女佣陈竹姑三人……刘梦莹浴罢,又向陶思瑾诘问,是否为看刘文如而来,并谓再不回头,将来定要发生悲剧。陶思瑾说其不必如此固执,遂即走至浴室外间取电炉烧茶。刘梦莹复跟踪而至,哓哓不休。陶思瑾一时愤急触动杀机……取菜刀一柄,向刘梦莹猛砍。刘梦莹亦取木棍一根抵御,格斗于陈列室之四周,血淋遍地,刘梦莹负伤弃棍,奔至大门,正欲开门逃出,又为陶思瑾追及,砍倒地上,并割断其颈部气管即时身死,陶亦昏卧于地。”《陶刘情杀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申报》1934年3月17日,第10版。。最后陶思瑾被判无期徒刑,许钦文不仅失去工作,还因窝藏有共产党员嫌疑的刘梦莹而锒铛入狱。案件在杭州地方法院判决以后,又被提至最高法院,一年多后才由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关于本案的过程,可参见:《女学生同性恋爱之恶果》,《时报》1932年3月24日,第3版;《杀人的小姐:狱中访问记》,《时报》1932年5月9日,第5版;《昨日杭州法院提审陶思瑾》,《时报》1932年5月10日,第5版;《陶思瑾仅免一死》,《时报》1932年5月21日,第6版;《陶刘情杀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申报》1934年3月17日,第3版。。
陶思瑾案案情复杂且旷日持久,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此案发生后,全国各报纸都登载“刘陶惨案”的消息[6](P 133),各大报纷纷跟进案情的发展,甚至派出私家调查队往杭州调查,或以表格等形式征求社会对本案的意见[7]。娱乐小报则竭力发掘“同性爱”“三角恋”“血案”等吸人眼球的方面,将其塑造为一则桃色血案。与此同时,众多评论家亦于报刊上刊文讨论此案,各种言论尽皆有之。《申报》说陶案“两月迄今,杭城各报每长篇登载,芳影惨骸,则时一披露”[8],其受关注程度可见一斑。
当案件提交至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法官接受媒体采访谈及此案:“世人以为同性爱之畸形现象,引起研讨之兴味,社会绘声绘色,报纸大登特登,个人对此,殊不谓然。”[9]他所言并非夸大,当时此案在全国引起极大的舆论。这固然因“同性爱之畸形现象”是一个能够引起社会争议和讨论的话题,但他所说的“殊不谓然”应作何解?这里需要做一些辨析。
一个几乎被以往研究者忽视的细节是陶案发生的时间。陶案案发的大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机关枪震撼淞沪的时候”[10](PP 4-5),本来所有媒体均将视线对准中日淞沪战事,爱好社会新闻者如《时报》此时版面也全为战况报道占据,在华东战事危急的情况下,一则带着情色色彩的凶杀新闻本不会引起如此大轰动,但是陶案的发生却极为特殊:
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在黑云飞卷、大雷大雨下的人们,好像紧张了好久的心胸,至此又得疏松一下……好多当时热血充塞住了周身的朋友,到现在竟然反而绝口不谈国事,“在满腔仇恨向谁诉”的无聊时候,会调转眼光来,全神贯注到“食色天性也”的问题上面。因同性恋爱而弄出人命来的“陶刘案”,其所以又能轰动一时,绝不因国难问题而稍减社会上注意的原由,亦不外乎在此烦闷的无可如何之中,要想换受一点新奇的刺激而已[11](PP 7-10)。
战事的紧张稍解,亟需一些可供放松的“资料”,陶案的发生正当其时,其故事中具备的学生、恋爱、杀人等因素,正与社会普遍的“愁闷”心态相合,使得陶案具备了成为社会谈资和轰动话题的可能性。
此外,新闻媒介在陶案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海报纸最繁荣的时期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详细论述可参见熊月之编:《上海通史》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3-224页。,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国民党的权力渗透使公共领域、政治舆论空间受到摧残的同时[12](PP 85-86),公众舆论中的社会新闻和娱乐八卦等却得到快速发展。而当时欧美国家盛行的“黄色新闻浪潮”也正波及中国*这一时期黄色新闻的特点是诸如《晶报》一类的小报大量流行,它们侧重于以文化娱乐新闻、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和新闻图片来产生社会轰动效应。,对“性”的大力宣扬和鼓动成为潮流,“黄色新闻的色情因素,就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13](P 291),在其影响之下,各类报刊上充斥着对奇人怪事、情色逸闻、凶杀暴力和畸形恋情等的报道,媒体炒作也越发常见。同时,读者也对此类新闻很感兴趣,当时有人已经指出:“白话文运动虽已十五年,而一般大众还是没有可资阅读的书物……由这种低级趣味,于是小报盛行,黄色新闻主义支配了整个的新闻界。”[14]
显然,陶刘的同性情杀案符合了媒体追逐的标准。案件甫一发生,大报小报便蜂拥而上,在他们看来,此事“既香艳,又风流”[15](P 2)。初始时,案件被描述成作家与两名女学生的三角情杀,随着案情的明朗,案件又被改写为陶、刘同性相恋,许钦文从中作梗(甚至诱奸)。媒体总之是以“三角恋”与“同性恋”加上“情杀”作为报道的最大卖点。以《时报》为例,该报由黄伯惠接手后,便走模仿赫斯特的黄色新闻道路,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文体报道,制造轰动效应*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申报》《新闻报》也大加刊布广告,加大文化娱乐方面的版面,宣扬物欲和享乐。。1927年之后,《时报》经常有一个半版面专门刊载黄色新闻,内容包括凶杀、离婚、赌博以及同性恋等等[16](P 142)。在陶案案发以后,《时报》便全方位参与到陶案的报道之中。
“知名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小报名人是围绕着大众传播和舞台表演的真实性而组织起来的文化饰品,媒体对陶案的疯狂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许钦文是杭州有名的作家,颇受鲁迅推崇,在《北新》等杂志上长期刊有作品。陶思瑾之兄陶元庆亦是与鲁迅长期合作的美术家、浙江省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与他们关涉的凶杀案,自然不会被媒体轻易放过。案件甫一发生,《文艺新闻》即以“儒林新史:许钦文的奇情案”为标题报道此事[17],许氏自身的知名度与后来被披露的“引诱”情节,都是案件得以广播的重要原因。
有了上述各种因素和契机,媒体在案件的塑造中不遗余力。1932-1934年,陶、刘、许三人的照片频繁见诸报端。《申报》《时报》等沪上大报全程跟进,包括每一次审理、当事人的申诉均被报道,社会名流和普通百姓的评议也屡见不鲜,案件审理期间几乎每天都能在各种报刊上觅得相关报道*在1932年5月28日判决以后,29日的《时报》甚至使用一整版另加一个版块的巨大篇幅报道案件审理始末和法院的调查结果、判词等,殊为罕见。见《时报》1932年5月29日第3版、第4版。。
在媒体的初步报道阶段,最集中的是对陶、刘、许三人关系的梳理。陶刘二人的同性恋爱被确认以后,许多论者对许钦文与两女生共处一室的行为展开批评。随着陶刘二人日记的披露,许钦文又被指曾对二位女生有调戏、引诱之举。《星期评论》上署名为丽娟的作者对许钦文展开强烈抨击,认为许钦文的心地和行为极其龌龊,“法院判他一年监禁,这种便宜货,可谓无处可塌”[18](PP 7-8)。但相反,文艺界有倾向许氏的声音,如《现代》杂志就以“许钦文被累入狱”为标题进行报道,其立场不问可知。而在案件进入到进一步的讨论阶段之后,许钦文则淡出了焦点,仅因为“窝藏共党嫌疑”而获得关注。案件的重心变成了陶、刘二位同性恋人。
林郁沁(Eugenia Lean)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传播技术的出现……媒体炒作越来越常见,并且具有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力。这样轰动性的案子(施剑翘案)与以往的任何案子都有所不同,它们的影响里不再仅仅局限于面对面接触的狭小社群,其在影响范围和传播速度上远远超越了过去的状况。区域性时间能够迅速转变为广泛流传的传奇并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城市及近郊社群公众的同情。”[19](PP 26-27)的确如此,远在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成都的《新新新闻》、青岛的《民报》等均大力报道。陶案案发不到两个月,上海的各大剧院甚至都排演出以陶刘惨案为主题的戏剧(见图1至图4*分别见于《申报》1932年4月5日,《申报》1932年4月13日和《申报》1932年6月11日。),各戏院纷纷派出专员赴杭州调查、跟进陶案,即使当事人亲属对此进行起诉也未停止相关戏剧的上演*时刘梦莹之姊刘庆荇起诉剧院并登报通告(见《申报》6月6日,第5版),杭州艺专亦以“有碍社会风化,呈请禁演”(《时报》1932年4月27日,第5版)。但剧院回复:“本剧场此次排演陶思瑾与刘梦莹一剧,曾将剧本呈准当局许可开演,兹据报载,刘庆荇因本场开演此剧,已延律师向法院起诉,本场为求公判起见,特再续演,务请各界注意是幸”,并照演不误。,演出时间更长达半个月之久,观者不绝。这一点放在今日也令人称奇。陶案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街头巷议的材料*陶思瑾案被大量引用,有论者论及“争”一题时也要引陶案为例:“认为两个男子追逐一个女子,或是两个女子追逐一个男子,也免不了有(争锋)之一幕,而且据说这争的成份最强,为的是醋意太深。所以,虽然弱又子如陶思瑾者,为了想占有文学家许钦文先生,遂以菜刀劈落刘梦莹女士的五寸艳颈,惹得自己如今还在吃司官。”(匡:《争》,《申报》1933年4月29日,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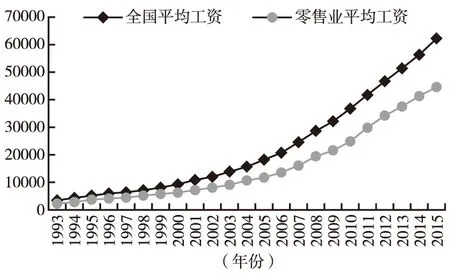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图4
经过媒体炒作以后,社会各界莫不关心此案。“杭州全市居民,街头巷尾,无不以此为话题,纷纷议论,大小各报天没亮就被抢购一空”,当时在杭州读书的琦君回忆说:“我也天没亮就起床,站在门口等报纸送来,赶着上学前先读为快,并且可以带到学校去传观……到了学校,全班同学叽叽喳喳讲的都是陶刘案。有的骂陶思堇(瑾)狠毒,有的骂许钦文感情不专,有的惋惜刘梦蓉(莹)死得悲惨,七嘴八舌,连第一节最认真的英文科都没心思听了。美国老师慕先生要我们背书,都结结巴巴背不出来。老师倒不生气,用美国腔的杭州话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心不丁(定),是因为有一个滔(陶)小姐傻(杀)了她的朋友溜(刘)小姐……那一周的作文题,老师出的就是《对陶刘案的感想》。这可有的好发挥了,每个人都振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上几大张。本子发下来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陶刘惨案风靡一时’笑嘻嘻地问我们这句句子如何。”[21](PP 151-154)可见,当时的杭州,不论是成年的老师或年幼的学生,国人或外国人,均对此案保持着高度关注,此案甚至还成为学生的作文题。同时,在媒体各种报道的影响下,众人对于陶思瑾杀人案也持各异的态度。四月一日上午开庭时“观审民众,已纷至沓来,一拥而入合议庭,倏忽满座。后来者遂拥挤于庭隙廊下,至正午来者愈多,法官座后左右,均为旁听男女所挤住,及十二时半,警官学校学生第二队三十九人,由教官率领入庭。均盘膝坐于律师案前,军政部航空学校一部分学生,则集于法座后,至一时,来者犹络绎不绝。致将庭前大门玻璃挤破”。另有一部分人在庭外拥挤,一部分人在候审室拥挤,各校学生达到两千多人,“恍如一盛大游园会”。下午两点,更为拥挤,当事人、证人、法官无立足之地,无奈延期至二号审讯。二号开庭,闭门审理,等待法官开始审理时,才准进入,但“玻璃亦被挤破数块”*具体内容可参见《陶思瑾与刘梦莹》,时事新闻社,1932年。,案件轰动程度由此可见(拥挤场景可见图5)。

图5陶案审理时的拥挤状况
如《民众导报》所言,“陶刘案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因为资产阶级报纸的宣传,所以弄得任何人都知道”[22]。“资产阶级报纸”这一表述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大众媒体的参与,使陶思瑾案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二、渲染同情:媒体、当事人与观众的互动
不过,陶思瑾案的轰动并不是媒体单方面的作用,这一过程不啻为一次“合唱”与“交响”。在这一新闻中,当事人、公众均被调动,新闻内外的人被汇聚在一起,共同参与到这一事件之中。
在媒体制造新闻的过程中,当事人自身往往也通过媒体发出声音,表达诉求,二者的互动是颇为有趣的一面。案件审理过程中,许钦文就主动投书至《时报》,刊出小说《爱的突变》,记载一对女学生同性相恋的故事,但实际上却在讲述陶案始末(陶、刘皆为化名)[23]。许氏所以急切,应当是希图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中通过媒体争取自己的话语权,毕竟当时媒体已经将其塑造为沾花惹草的不良文人甚至案件嫌疑犯,这给最终的定罪和他自己的声名都造成了极差的影响。

图6 许钦文《爱的突变》之广告与原文[24]
而另一主角陶思瑾亦如此。《时报》记者曾先后三次至狱中探访陶思瑾,一次采访其狱友*《陶思瑾狱中唱小曲》,《时报》1932年4月30日,第5版。记者的结论是陶思瑾“似有病”。,两次采访陶思瑾本人,采访中她都言语从容,待人和善,乐意将她与刘梦莹之间的故事分享于记者,她一再指出刘梦莹性格多疑,妨碍其正常交际,且愈难相处,杀人也是刘梦莹先动手,自己纯属“出于抵抗”[25][26]。她也与许钦文一样,利用文学的特长在媒体上进行表达。比如杭州法院判决前她向记者吟诗道:
啊!当这凄清恐怖的深夜里
我尚不知我已失掉了自由的人儿了
可是当我已经觉醒了的时候
我底心头用上了无限的悲愁
无限的悲愁只为了热情的奔流
为挚爱崇敬的导师!
为保护我信仰的导师!
毕生卒命也只可承受
……
啊!但是哟!上帝须知道
我受着了真理的驱使
为了信义和忠义
却受了无限的烦恼
依然为真理的爱火燃烧
虽然我受尽了社会残酷的待遇
和受尽了人们无理的狞笑
可是我也不半点儿号叫
因为我底心是何等的伟大、纯洁
和我底行为是何等正大光明
而忘却了我已成了今日的囚徒
……
但是我想起了我的残体已成了他人的管束
永远不能再见天日的光明
我满腔的衷情何处是我申诉的地方?
我唯有滴出我心头的泪血!
远远地遥祝着你!!你!!你!![27]
她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陷入情网导致犯罪而不自知的女子,凄惨和悲愤溢于言表,但同时又竭力声明自己是为“恋爱的伟大”而死。在判处死刑后,她效仿许钦文写作小说,描写“与刘梦莹恋爱经过”以及“惨剧的真相”[28](P 143)。案件在最高法院侦查时,她又作诗刊于报上:
桃色底青春
变成了银灰色的死路
爱神你何等的狡猾呵!
你是青年的仇敌
你是少女的对头
谁是我的爱人,引我的灵魂,去游墟墓?
天呵,我正在等待着!
等待到呕干了血,流完了泪,消灭了智慧
那就是恢复了我底自由[29](P 12)!
陶思瑾不再认为“恋爱”伟大,但她再次控诉“爱神”,认为是“爱”害了自己和诸多的少女,如果说这一文学化的表达还比较含蓄的话,她的另一篇文章表现得便十分明显:
现代的刺激是何等地大,燃烧着热血的青年们的心呀暴露了,彼此不觉得斗战了,这是个人平日受着时代的反应和病态的现象,而不觉地构成了此悲剧。天知道我是如何的痛悔呀,何以发生了此悲剧?我感觉到我俩都是被时代的牺牲者呵!当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悲愁地想起了我那亲爱的尸体呀……[30]
她极力控诉作为悲剧源头的“时代的反应”,表达自己的懊悔与愁苦,彰显自己作为“时代牺牲者”的不幸。
媒体也加入陶思瑾悲剧的渲染之中。在记者的笔下,陶思瑾的个人形象是可怜而不幸的,她时而与母亲痛哭[31],时而与姐姐相拥而泣[32],又或是向刘文如投书道“我为你而死,为你而牺牲……我的友啊,你可为还不幸者的命运同忆吗,你会为我哭过么,我如果能得有你的一点甘美的同情之泪,我已狠甘心地去死了”[33],以求得其同情。《益世报》记者探监后,形容陶“近日颇消瘦,殊有‘人比黄花’之感”[34]。《时报》记者记载她“依然是那么憔悴可怜,虽然气候这样闷热,但她的音容是那么异常冰寒”[26]。而这些报道又不断被其他媒体所转载,一时间陶思瑾的悲剧形象广为传播。
陶思瑾是否有利用媒体的目的,我们难以知晓,但通过媒体进行的自我表达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悲剧形象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陶思瑾在狱中收到的慰问信“案头盈尺,京沪鄂蜀平粤,均有邮传”。有的女校学生专程赴监狱,为见陶思瑾一眼,基督教组织中华妇女节制会还派遣专员赴浙江探望陶思瑾[35]。
此外,许多人对陶思瑾以及死去的刘梦莹抱有同情的态度。阅过《时报》刊出的二人日记,名为“止水”的论者就感慨“她们生动流利的文字,与夫求之两性间亦不可多得的浓情,却使我留下了怜惜敬爱的热泪……对于陶刘的文字,我是没有方法抑止我对她们的钦佩。我觉得陶刘二人在现在新旧思想混乱的时间中,她们是个冒险家,她们是个为时代牺牲者;但,同时,她们的思想是太背离了‘常情’,她们的行为是太隔别了现代社会的‘组织’。不必她们为了三角恋爱,为了打翻醋罐头而造成这个惨剧;她们是终于要弄到一个悲哀的结局的……”。而见到陶思瑾在判刑前夜所作的诗后,他更“想象得起她(指陶思瑾)现在是十分的憔悴,他的内心是一定绞搾得血丝都没有一滴;或者她的灵魂早已脱离了她的躯壳”[36](PP 7-10)。这很明显就是受到《时报》等媒体的影响,进而对陶思瑾抱有同情、惋惜了。
更有激动者如王敖溪,还在《社会月报》上刊出《我哭陶思瑾》一诗:
我哭陶思瑾,更哭刘梦莹。嗟汝二仙女,何为下蓬瀛。天宫本寂寞,颜色徒倾城。无处觅裴航,祗自羡云英。不敢问萧史,最怕听箫声。谁云神仙好,依然苦不平。金母与木公,独作鸾凤鸣。何如人间好,自由爱众生。料得黄金屋,乐于白玉京。哪知堕人世,烦恼苦相萦。爱情不自由,世道难变更。也知有宋玉,相对可目成。不幸遇登徒,人便说淫行。虽自惜颜色,宁不惜声名。惟有憔悴死,人始称坚贞。多少好儿女,为此而牺牲。人间与天上,都原不平衡。避为此浊世,只有我怜卿……两心清如水,宛如湖水请。为爱湖本清,夜夜看月明……[37](PP 36-37)
作者强烈主张恋爱的自由,夸赞陶刘之恋爱,他将二人比作仙女,而爱恋十分纯美,一如“清水”,但可“哭”之处正在于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天上”抑或“人间”,实际上都没有她们的安生之处,“都原不平衡”,“爱情不自由,世道难变更”更是他代陶思瑾控诉社会的宣言。
当时上海各报上都有主张为陶辩护的言说,甚至对陶思瑾杀人的量刑展开辩护,很多人认为情杀不应处死刑,“还有把陶比作莎乐美,好像莎乐美的杀人是情有可原的”[38](P 2)。因为感于陶刘的“爱情”,《时事新报》的黄天鹏(天庐)便成为主张“情杀减刑论”的一员,因为“陶杀人的动机是为爱情而起,就这一点纯情的动机而论,就是预谋杀人而且残忍,也应该减罪判决”,要“卸去你们冷酷无情法律的眼镜”“创造个爱情的新社会来”。沈孝祥则主张陶思瑾杀人是受神经衰弱影响,“爱之愈深,杀之愈惨,一念嘶杀,铸成大错,非陶思瑾预料所及,实属情有可原而法有可恕者”[39](P 17),惨案发生是她自己所无法控制的。
邹韬奋对天庐等人的观点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爱人只应该爱,不应该杀,因爱她而要杀她,这种爱何用我们提倡?下毒手惨杀他人,固是‘冷酷无情’,下毒手惨杀爱人,便不算‘冷酷无情’而算得仁爱多情吗?我也觉得不懂……提倡惨杀爱人和‘创造个爱情的新社会’有什么相干呢?”[40](PP 639-642)朱惺公不尽同意黄、邹二人的观点,他与前述止水的看法类似,认为“陶思瑾的杀人,实就是受了畸形社会矛盾思想下而产生的结果”,“政治的不良,社会的不安定,以及一切畸形的发展,都可以使人类逐渐脱离了理智的思想,而恢复他原有的野蛮性上去。这一点,我们可以大胆去咒诅现代不良的秩序,而压迫到人类走向这条路上去”[41](P 59)。实际上,牺牲于爱、牺牲于时代确实是陶案中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念。
“五四”以后至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恋爱”已成为堪称伟大的词汇,对于青年男女而言,恋爱无疑具有一种“神圣性”。当媒体塑造陶、刘的爱情牺牲者形象时,很容易调动起众多鼓吹“恋爱”者的同情。当“恋爱”“同性爱”“血案”等词汇被新闻勾连在一起,社会大众对于这一案件的讨论便进一步得以展开。20世纪30年代,媒体乐于追求轰动效应和鼓动感伤主义以迎合大众[19](PP 26-27),从陶思瑾案的塑造中可以看到,从最开始荒诞的“三角恋同性爱”叙事开始,随着案情明朗并进入长时间的审理阶段,媒体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开始将陶思瑾描述成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是为“恋爱”(准确来讲是“同性爱”)而死的女子。
三、走向负面:陶案后社会批评的展开
然而,在媒体、公众的慨叹和同情之外,同时在舆论中占据更大篇幅的却是批评的声音,这些批评也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一些左派的论者对此案尤为不满,《社会与教育》的编者认为减罪说是无聊至极,“最无聊的是那些上海的洋场才子,报屁股作家,不惜以宝贵的篇幅,记载讨论,说起来还是因为上海还有许多买办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要求这样的材料作谈资以消遣呢”[42](P 2)。在作者看来,陶案这类新闻本身就毫无价值可言。
实际上很多报刊之所以要大肆报道陶思瑾案,其目的除了吸引眼球外,恐怕也有使社会讨论同性爱的目的。《时事新报》的天庐说:“《时事新报》不惜巨大的篇幅,来刊载刘案法院判决的全文,这里有一种重大的意义。而谋所以解决这个难题……这不只是班维持风化者所谓世道人心的大忧,应提出这个悲惨而严重的问题,请教育家特别注意,求得一个解决的教育方案。”[43]而以今日之眼光回看,这种目的似乎已然达成。陶案以后,《玲珑》杂志上一位名为任培初的作者这样写道:
我的思想很幼稚,以前对于同性爱一说,仅认为和腾云驾雾的剑仙一般的都是小说家笔下空谈罢了。自从杭州陶思瑾刘梦莹两女士同性恋爱血案发生之后,我才知道同性恋确有其事[44]。
对他而言,正是陶案使“同性爱”从一个缥缈的概念变为现实,他的感受并非特例,事实上普罗大众确实是在这次血案以后才真正“发现”并开始认为要“正视”同性爱。陶案后社会的讨论极为丰富,同性爱由一个相对隐秘的事情变为社会各界均要发表意见的问题。而当陶案将同性爱这样一个话题引入社会讨论中以后,就等同于拉开了更大讨论的“闸门”,同性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大众观念的审视。
有的作者虽然不特别批判同性爱,但却也并不赞同。名为“英”的论者认为“现在的女学校里,同性恋爱是普遍的现象了,我觉得同性恋爱,是值得歌颂的神圣的爱,不过有人说少用一分热情,可以省却一分烦恼的,我以为同性恋爱,也未尝不是这样”[45](P 529)。也有人认为“两性间发生爱情,本来是一种自然定律”,“一位少女在未有跟男性结交的经验时,常会引起于同性爱的憧憬。自然在她们开始了解异性爱的甜蜜时,同性爱便归幻灭”[46](P 1377)。
时事新闻社出版有《陶思瑾与刘梦莹》一书,其序言中写道:“这虽是受了情爱的迷恋……所以个性有时竟会呈着变态,而自己还不知不觉得自以为是了。尤其是二十来岁的少女们,在这个社会,受了新时代的洗礼,更有多大的影响,像刘陶两位就是这时代的牺牲者,她俩这种变态的同性恋爱,达到这样狂热的高度,甚至由爱而恨,由恨而妒,由妒而仇,这些过去所表现给我们听的事实,也就是受着心理变态的影响,才会演成这一幕悲惨的活剧。”“为人类进化,而虑到这种行为或为进化的荆棘,不得不加以制裁……中国人在新道德未建设旧道德未崩坠之间,这种过程是免不掉的,何况这重大而似乎存疑的案件,那能逃出例外呢。”[47](P 3)此处就是对“同性爱”这一具体的形式产生质疑,“变态的同性恋爱”乃是“不得不加以制裁”的。
一方面,当时很多人大肆宣扬同性爱可能造成的生理损害和疾病。任培初称,“做医生的朋友说,同性恋爱是生理上所不许的,是不合法的。日子久了,便要发生神经衰弱。窒道麻痹。指肠出血。子宫破裂、头痛、头晕、双目失明,四肢寒冷、萎黄病、肝火、黄疸病、脑充血等病症。不上三年便要香消玉殒”[48]。这类言论正与当时社会很多人的认知契合,论者“爱卿”也认为“凡是稍懂得生理学的人都晓得独身和同性爱是对于身体和精神均有妨害的……同性爱的恶果把人变成忧郁、反常,同时对于身体更有很大的影响”[49](P 1253)。
另一方面,也有人不断强调同性爱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同性爱的弊害,不但在精神上造成衰弱的病态,即在生理上更蒙受极大的影响……同性爱的易于招致妒嫉,斗争或情杀……错综复杂,极易生出乱子来的。”[50](PP 2426-2428)这就将同性爱由个人的生理问题推向了社会秩序的讨论之中。鉴于陶思瑾杀人案,“丙辰”说“近年女学大兴,女子的同性爱愈演愈烈,陶思瑾案可为代表,因女子用情较专,一结为‘朋友’,即预备‘终身不渝’,故一有变故,小则斗殴,大则残杀。中国女子教育问题中,同性恋爱问题应居首要地位”[51]。这些观点极力阐述了同性爱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陶案则无疑成为一个有力的例证。
主流意见开始形成,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同性爱既妨害身体健康亦不利于社会安全的论调。主要编者多为女性的《玲珑》杂志刊出多篇文章讨论同性恋爱,其态度不可谓不强硬:
同性爱在法律上道德上和生理上的地位,是种犯罪的行为。这丑恶的行为,一般叫做“性的倒错”,是一种变态的色情,往往带有危险性的。刘陶案就是这危险的产物。所以正热于同性恋的姊妹们,看了上述的可怖的惨剧,应该立刻觉悟,赶紧解决了同性的关系,而树立起两性的爱,那不仅能免去无限烦恼而且是促进人生的光明的幸福的生活[52](PP 113-114)。
作者直接批评“同性爱”是一种“丑恶”“变态”“危险”“犯罪”,后果“可怖”,必须由两性生活来弥补这“危险的行为”,并呼吁广大女性以陶案为鉴,了结同性爱。
在陶案旷日持久的审讯期间,一些其他的关于同性爱的危害的“证据”也不断被媒体所介绍。兢存翻译日本学说称“有对于自己所爱的同性失恋时,因而生出嫉妒,或迫于情死的,在此时期之行为,完全和异性间的恋爱相同,至其甚者,竟有发生情杀”[53](PP 115-117)。“变态”说和“性的倒错”也是此时最为常见的评述,此时对于同性爱,呈现出一种“恐慌”。如陆孝先在《申报》上刊文,指出同性恋爱是“一个变态的行为”“一种幻觉”“一时的麻醉”,陶思瑾与刘梦莹案件的发生则是“恋爱灵肉的不调和”[54]。
到1934年,同性恋爱被认为“是最令人注意的一个问题了”[55](P 24)。当时有人评论同性爱时就说:“同性爱的结果,不但使身体精神发生病态,且因此不能营异性间正常的结婚生活……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陶刘惨杀案……一般人都说是同性恋爱的结果。”[56]可见,这也成为大众的一个认知。时人更有认为同性爱“已经离疯人不远了”[57]一类的论述。
在陶思瑾案以后,从对案情的注目开始,逐渐演变出一场社会对于同性爱的大讨论,“同性爱”浮现出来,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对“同性爱”的评论也一时纷纭。不论是社会对案件本身和当事人展开评论,抑或是由此说开去而讨论同性恋爱问题,均是私人情感世界公共化的表现。由于命案的发生,情感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
陶案发生以后,《陶思瑾与刘梦莹:他们都为恋爱而死》一文就针对“理智与恋爱”展开议论:
同性恋爱,已是一件无可讳言的公开秘密了!因为同性恋爱发生吵闹的事情,在学校中也不一而足,我承认恋爱与理智及行为,是绝对的会冲突的,不论同性与异性,所谓爱深憎生,爱之深而不觉恨之甚了!那末陶刘之惨剧,也就发生于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不能控自己的缘故,恋爱是单纯的,无条件的,因为爱就能为了爱,像沙乐美残忍的故事,其出发点也只为了绯红色的恋爱的背景,女士们,我们见了陶刘二人为了恋爱而召惨果,你也该知所警惕,你要以你的理智控制住了你的感情[58](P 586)。
这里的作者虽然认可恋爱,但是趋于理性,并从理智恋爱的角度对女性提出诸多劝告,并不以恋爱为神圣并因此采激动、同情乃至崇拜的态度。这类的反思是极其普遍的。如署名“婉”的作者就由陶刘的分裂来反思恋爱中的“嫉妒”,警示后来人要妥善处理这一点:
此次惨剧,为互相妒忌怀疑而起……大凡恋爱到了极峰的时候,便有危机潜伏。就是怀疑与嫉忌,如果怀疑与嫉忌,一经解释,而相各坦然,那恋爱的基础,便更巩固了一层,如果不能坦白的相互了解,那便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惨剧了,不论男与女的恋爱,就是同性爱也是如是的。我以为恋爱的背景,是有着时代、环境、生理各方面的关系,所以恋爱是受自然支配的作为,不是强制的。如果认定了这个原理,世界上就可以减失许多失恋的痛苦,或不致于有意想不到的惨祸了[59](PP 418-419)。
《申报》读者的来稿则由媒体渲染的“恋爱”与陶思瑾案的反思质疑恋爱自身。他认为:
爱的感化,可以使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改善而为贤人君子;反过来讲:爱的损伤,可以令一个贤人君子激怒做出杀人流血的勾当。因此这个新名词“恋爱”不光是含有社会性,而且含有改造性,在现代已经成为极严重的问题。历史内,电影里,小说中,不知道表演过多少回。最近如陶思瑾女士和黎妹妹的情杀案件就是一个例子。固然恋爱是不容第三者的插口。他们有他们的内幕,我作者是没有权限可以干涉:但我本身是社会的一份子,不得不想些办法来改良一下:怎样增进人群的幸福而减少恋爱的痛苦呢[60]?
作者认为恋爱需要改造是当然的,因为恋爱本身并不十分美好,甚至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作者看来,“恋爱”似乎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恋爱势必又与“社会”发生龃龉,故而“人群的幸福”与恋爱之间便存在一种紧张。陶案等的发生更启示社会,应该采取对恋爱的改良行动,以避免恋爱对社会造成困扰,从而保护人群的幸福。这番言论和上述几则材料都折射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近代中国努力打破“传统社会”对恋爱的束缚,走向“解放”之后,在此期间很多人却又“折回”,期待社会对于过分自由的恋爱进行规劝,希望形成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恋爱模式。
在规劝和警觉之外,还有众多的言论将陶案的发生直接归咎于“恋爱”,并对青年的恋爱进行批判。在青年组织讨论会讨论陶思瑾、刘梦莹案件时,“徒然”刊文痛批青年对陶思瑾案的关注。他认为:
目前中国与社会更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有多少,而无暇及此。然而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理偏像和陶思瑾同病似的,指导社会的报纸发疯似的大载特载,留欧做教授以爱情来美化人生的艺术家们大讨论特讨论……青年在国难中不摒弃恋爱,谁也不敢反对。反成为问题的,是明朝真个有警之后,果能有离开酥胸执戈上沙场的勇气否?若说能有的罢,则“警”已经去年就有,不待明朝了,何以我们的青年界还不执戈上沙场,而只是搭沪杭车赴监狱见情杀案主角的一面呢?……生在这个年头儿的中国青年,不能学人家的样,把恋爱为人生最高目的,把享乐当饭吃,把讨论情杀案当做研究社会问题,我们即使没有执戈上沙场的勇气,也应回到我们的家乡去看看胼手胝足的父兄们还像个人样子不像[61](PP 633-634)。
相似的批评也见于名为“宸”对北平一则桃色案和陶刘惨案的评论中:
是的,我们承认近年来许多青年男女负上“爱神的箭”的创伤而殀亡,其间大有客观的原因在,然而许多青年男女忘避现实的躲入“爱”的小天地,纠缠得来成为人生的唯一真义,不能不说这是自寻苦恼,作茧自缚了。
有了恋爱至上主义,自然才有近年来无数殉爱自杀与情杀的事件发生。这种现象发现于承平之时,已经表现一种社会意识不健全的变态,然而却盛行于中国这所谓“国难当前”“民族危机”的现代,未免就十分的不调和。在现在,男女间的“爱”真的如像流行的“恋爱经”所谓,爱是生命,爱是人生,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那样么?实在只有使人浩叹[62]。
在社会、国家的危机面前,个人的爱情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中国青年被期许的不是去恋爱,不能“把恋爱为人生最高目的”,而要让步于国族的时代使命。
任白涛刊发多篇文章,从“性病”传播的角度反对同性爱,他认为“同性爱……郁勃的性的暴威奔放恣肆的结果,那可恐的性病即花柳病遂蔓延起来。……资本主义文化的进步,这个美丽的陷阱,益发地增加起来,而能不能巧妙地躲避这个陷阱,便是青年的向上与堕落的断定,也就是那个国家的发展或衰亡的重要的关键”[63](PP 51-58)。“士杰”关于同性爱的评论则更为直白:“我们人类,既然生在这世界上,得称为人,就负有依从生物界的法则,保存自身,同时保存种族的生命……繁殖子孙的天职,这当然是我们人类生来的本能。”[64](PP 194-196)实际上,早在20年代中期“性道德”问题的讨论之时,周建人就已经明确提出:“性的行为的结果,是关系于未来民族的,故一方面更须顾到民族的利益,这是今日科学的性道德的基础。”[65](PP 8-12)在这种逻辑之下,李宝儿抨击同性爱“陷民族于冷酷阴险,消沉不振之结果”:
故其社会随处表示一无组织不能独立之社会,其民族,亦必反映一无团结而指日可灭之民族,此于其两性爱情不热烈之一说,我人可预断彼社会必陷于某种现象也,现代欧美各国,不特知爱情于社会民族之要……爱情之罪恶,不可与欧美同论,是则吾人固自愿以摧残自己民族精神,而陷中国民族之沦亡乎,抑自视为末等国,及半开化民族,乃自愧难与欧美文明各国,作相提并论乎[66]。
由此,同性爱被加上了亡国灭种、摧毁民族精神的罪名,而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这种罪名无疑将使同性爱面对着强大的压力。
随着陶思瑾案件后续影响的扩大,对这一事件严重性的预估也被拔高。在陶案后的讨论中,对于大众尤其是社会精英而言,陶案不仅仅是一个“杀人案”、桃色新闻,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关涉“同性爱”乃至“恋爱”合理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30年代以后的国族建设中,女性被赋予“养育”和“持家”的“使命”。独身的女子、不生育的女子成为被挞伐的对象。而同性爱既无法生育繁衍,便成为众多论者攻击的对象。1932年任培初批评同性爱时说“假使常此闹下去。同化了全国的女同胞之后。那末岂不是要绝种吗”[67](P 247)。其关心的问题就在于同性爱与生殖的关系,女性若流行同性之爱,则国家将面临绝种的危机。
同时,同性爱作为一种恋爱方式也与国族危亡的大主题相龃龉,立场激进的《民众导报》说:
陶刘案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她们是现代中国一部分醉生梦死的青年的典型。老实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不容我们有去过那些花前月夜的恋爱生活的余地。我们要做的事情□多着,谁要□赖,谁只有步向他的灭落去。所以刘之被陶杀,固然是该死,陶之被判死刑,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几年来中国劳苦青年不知被害了多少,这种堕落的无用的女性,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怜悯[68]。
在很多人看来,恋爱不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国家民族的危亡才是青年应该为之努力的所在。
20世纪30年代以后,五四的回音渐弱,“个人”让位于“集体”、小我服从于大我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当国家、民族的危机愈加突出之时,私人情感也面临着社会的评议和规训。在社会的集体想象中,受到普遍提倡的是强国保种、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男女结合的恋爱模式。而同性爱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加之陶思瑾案带来的负面影响,招致普遍的抨击与批评。社会对同性爱的话语与民国时期的民族、国家等话语交织缠绕,难解难分。
四、观念转变:民国同性爱话语演变中的陶思瑾案
对于事件的研究还应该放诸更宏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理解陶思瑾案,也应该对民国时期的同性爱话语整体发展的历史做一些分疏。
陶思瑾案案发之前,民国社会对于女性同性爱问题的相关讨论相对不多,且较为多元。冯客认为,民初的话语对同性恋性欲基本上提出三种解释:第一是把同性恋说成是青少年期的暂时迷失,第二是视之为一种疾病,第三是视之为一种颠倒[69](PP 64-65)。但1910-1920年对于同性爱的讨论并不常见,目前可见到的是1912年“善哉”于《妇女时报》发表的《妇女同性之爱情》一文指出,同性爱是一种权宜之计,“陷于同性之爱情者,并非全出于情欲之颠倒。其中因无与男子相接之机会,而为满足其情欲计”[70](PP 36-38)。
“同性爱”作为一个话题被广泛讨论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20年代,大量关于同性爱的外来学说涌入中国,总体上看来,西方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学说对时人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种不同的见解在国内激起的浪花亦姿态各异,既有同性爱称为“罪恶之色情”“变态之色情”[71](P 355)者,也有对其表示赞赏者。“五四”以后,一批中国学者热心于译介欧洲学者的同性恋学说,Homosexuality一词在中国被翻译为“同性恋”“同性爱”或“同性恋爱”,在定义产生的同时,西方对于同性爱的整套观念开始被译介。“性的倒错”“性的变态”是冠于同性恋头上最多的词汇。
如“慨士”将生物的繁殖等理论引用到同性爱的分析中,认为同性爱是一种不自然的性爱,所以称为“性的颠倒”,“这种比友爱更亲密的爱,虽然不能说他怎样的坏,但不自然是的确的”[72](PP 727-729)。“慨士”作为一个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者,本身具有一种“科学”的自觉。同时,在中国传流及实践的西方学说,并不全然是西方定义下的科学知识,也有经由中国本土知识人本身所选择、诠释之后的再阐释[73]。李宗武认为,同性爱的双方是将彼此视为异性,是一种性的吸引,同性爱又可分为先天和后天两种,而后天的多来自于异性交际的隔膜与断绝。“同性爱不是性爱的自然发达,是一种变态心理,是精神的病的现象,是性的畸形的发达”。并且,在李宗武看来,久而久之,生理上也要起变化。它会妨碍个人的幸福,更会害及种族的持续与繁殖[74](P 1)。
除了上述的社会观察以外,身处校园中的学生对此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尚为学生的吴文藻就批评同性爱,他受弗洛伊德和Tansley的心理学学说影响甚深,主张同性爱是一种非正常的变态行为,反对其他主张和赞赏同性爱的学说,“借学说为护符以满足性欲的要求为目的是一种卑鄙龌龊的心态。有害身心,莫此为甚”。但他又认为不可过多地猜测和揣度同学间友谊的关系,友爱精神是应该被提倡的[75](P 186)。同属清华的吴景超也反对同性之爱而赞同友谊之爱,他更赞同霭理士的学说,在他看来同性爱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人皆有之,只是个体的强弱以及后天的各种刺激造成了区别罢了。不过可以注意的一点是,如吴景超自己所言“我并不抬出道德两个字来诅咒那些过同性恋爱生活的人”[76](PP 14-18),他并未以道德来批判同性恋爱,他和吴文藻一样,都是受西学影响极深的学生,故而更多的是从他们接受的学理和现实情境来反对同性恋爱。
不过,同样主张重视同性恋爱的教育引导问题,另一批人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他们认为同性恋爱可以在现代教育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受卡本特等的学说[77]影响,沈泽民呼吁宽容对待同性爱,要“大胆地回想”,因为“我们都是学校生活底过来人”。郑婴认为,“同性爱之间,并不是一定犯道德上与生理上之罪恶的,也有受真情之流的洗礼而营崇高的(Pure Love)精神生活的,将同性爱当作爱情之一种”[78](P 3)。卡本特的《爱的成年》(其内容多为对同性爱的辩护)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读物,先后几次被不同译者翻译、出版[79](P 79)。郭真将卡本特的思想加以阐释与传播,在《恋爱论》一书中引介卡氏观点,认为恋爱不但存在异性之间,同性爱也有伟大的社会价值[80](P 64)。
更多的人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探讨,没有过多的情感偏向。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同性爱是生理的关系,很难研究的,而且又是秘密的,往往不肯实说,如果的确是生理的关系,那是同吃饭一样,不能预防的了。”[81](P 38)同性爱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还是与生理学相关,与性、精神等方面有所关联,至于对待同性爱究竟该采什么态度,当时并没有十分一致的见解。
除了上述的争论,在1932年以前,很多人认为同性爱是一种人生必经的阶段。田泉就认为同性恋爱“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发生的现象,是为环境所促成的”,“总之社会制度不达到十分完善的境域,这变态的现象,是万难拔蒂连根的”。田泉进而分析道:“我们性的过程可以概分为四种:第一为自我恋时期,第二为母恋时期,第三为同性恋时期,第四为异性恋时期”,“同性恋时期是我们必经的过程之一。如能顺序走过,不特无害,而且有益。要是停着不前走,害处就发生了”[82]。
概言之,在20年代,通过近代“同性爱”概念的译介,时人已习惯用这样一个现代的概念和随之而来的一整套知识来解释同性情感和性行为。同时随着女性同性爱现象的普及,社会关于同性爱的讨论也更加充分,社会对于同性爱的话语呈现出多元的面貌。
然而1932年的陶思瑾案使得社会各界均认识到同性爱问题,并促使社会对这一现象进行重新评估。案发以后社会观感不一,引起众多论争,但仔细考察其舆论,却可以看到其后主流社会话语呈现出一种渐趋一致的势头——话语负面化。杨开原说“所谓颠倒症,就是同性间所发生的一种变态的性欲”,“女同性恋,陷入此种关系的结果,有不少因而情死的。殊不容吾人过分漠视”[83](PP 11-13)。很明显杨氏之言便是受陶案影响而发。前已述及,在此期间内,认为“同性恋乃是种罪恶”,“非但为不正当的性欲,且有伤于身体”[84](P 1047)的观念占据了舆论的很大篇幅,认为同性恋爱“有误青年人的前途、学业”[85]的论断也为很多人采信。
1932年以后,陶案的热度渐渐消退,但同性爱问题相关话语的整体负面化偏向已然不可逆转。在陶案的阴影之下,社会言说虽不再围绕血案展开,但舆论讨论中有一种渐趋强势的解释倾向——病理化。
当同性爱已经作为一个危及社会的严重问题被确认之后,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也变为如何寻求同性爱的解决之道。《性科学》《健康生活》等杂志热心于译介西方学者对于同性爱的诊疗方法,提出“与以和异性交际的机会”“用催眠术或精神分析疗法”“由本人自发地反复练习正常的性欲发动,逐渐矫正”等方法[86](PP 3-7)。虞车提出“将一个正常男子的睾丸移植到一个同性恋男子身上”“催眠的暗示方法”“联想治疗法”[87](PP 97-102)。医学家丁瓒表示,“这种病态的发生是源于体质上的变易[异],特别是与性格能有关的内分泌腺的失常,在这等个案中,非经医药的治疗,是很难改正那些变态行为的”[88](PP 11-12)。
不过,张保善认为同性爱用医疗很难医治,必须要设法与异性接触,此外别无他法[89](PP 134-136)。“妙妙”也认为环境是重要因素,因此男女结婚、男女同校是防止同性爱的好办法[90](P 21),傅韵涵亦持此说[91](PP 58-60)。赞成主张通过教育的手段防治同性爱的言论十分多见,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性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同性爱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性教育的实施。张铁笙认为学校的介入,如减少学生的独处时间、分配住处,学校进行直接干涉等是一种“消极的防止办法”,而积极的办法是尽量公开向学生讲述性的知识,帮助学生解决性的烦闷,提高学生对事业及前途的兴趣[92](PP 17-20)。
在1935年以后的讨论里,同性爱的防止成为一桩重要的问题,众多的医生、心理学家都参与其中出谋划策,直到40年代晚期,众多的医学者仍在延续对同性爱治疗方法的探讨*如丁瓒说:“其实真正说起同性爱,不单是指缺乏异性爱的兴趣,并且在这等病态患者们有时甚至是异性爱无能的。严重一点的,这种病态的发生是源于体质上的变易(异),特别是与性格能有关的内分泌腺的失常,在这等个案中,非经医药的治疗,是很难改正那些变态行为的。”参见丁瓒:《谈谈同性爱》,《卫生旬刊》1948年第81期,第11-12页,第17页。。
从本节的论述可见,一方面,陶思瑾案确实对民国时期的同性爱话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血案的发生导致舆论对同性爱负面印象加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同性爱话语置于整个民国时期的历史之中进行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同性爱话语的变迁本身即呈现出一个整体走向负面的“大势”,陶思瑾案件的发生只是观念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和加速器而已。可以看到的是,对同性爱的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几年,特别是陶案发生以后,已经有了明显的转折,这种转折,是长时段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血案、传媒、“科学知识”等共同作用的结果。1936年以后,社会对于同性爱的关注呈减少之势,对同性爱的讨论不可阻挡地走向整体负面化,其中虽还留有讨论的空间,但为同性爱摇旗呐喊的声音几乎已消失不见,或以之为暂时的选择,或以疾病视之,而这些观念实际上与医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观念紧密相连。
五、余论:陶思瑾案与近代私人情感的公共化
顾德曼(Bryna Goodman)和林郁沁都曾讨论过民国时凶杀案与舆论的互动,顾氏通过自杀案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报纸如何通过组织公众对现代情感进行讨论并构建出“现代主体性”以及通过讨论创造了有理性的公众。后者则详细考察了在施剑翘刺杀案中,大众媒体和其他主体是如何利用戏剧化炒作和渲染激起公众同情,并进而揭示出公众同情的批评性和被政治力量操纵这两种社会批判功能*见[美]顾德曼:《向公众呼吁:1920年代中国报纸对情感的展示和评判》,《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6年第14期;[美]林郁沁著:《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本文所探究的陶思瑾案亦属于一个被“公众化”的事件,而推动其成为公众事件的正是大众媒体,但本文想揭示的是作为社会组成的“公众”与“传媒”以及其他因素是如何互动并在互动中塑造陶思瑾案的。
事实上,民国时期关于同性爱的案件并不鲜见。1929年同样在杭州发生过女学生赵梦南因同性爱而自杀的悲剧[93],1931年有女学生孙景贤、蔡蕙芳一同跳海殉情[94],1948年在成都也发生了同性恋爱的女学生自杀事件[95]……同为血案,这些事件获得的关注度却远不能与陶案相比,仅在陶思瑾案后,舆论才被充分地调动,这其中的原因不得不使我们思考。时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战事日紧的30年代,淞沪战役的暂停使得陶思瑾案成为了休战期内的轰动新闻,而报刊和其他媒体的参与,则是更为直接的推手。
在民国的大众社会中,媒体和公众互动,前者使陶思瑾案成为一个轰动事件,后者则是在参与或接受中获得了对同性爱的认知。
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新知识、新名词,“虽然大多发轫于精英阶层,但莫不是通过各种媒介,经由各种长于传播到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进而产生效果”[96](P 7)。同性爱这一概念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知识便是通过媒体传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大众媒体的崛起、消费文化的盛行,促使商业媒体要以煽情渲染和伦理炒作来博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媒体以犯罪、情杀主题的陶思瑾案作为招揽观者的素材,之后它们成功吸引了广泛的注目。20年代呈现于报章之上的同性爱讨论尚少,且主要是学理性争论,但在陶思瑾事件后,各类小报、娱乐杂志、健康杂志等蜂拥而上,媒介被充分调动,同性爱的相关讨论随之兴起。报纸特有的公共性使其通过公开报道和刊载评论,将陶思瑾案以及同性爱这一话题置于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之中,引起了大众热议,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同时,对于普通读者和观众而言,呈现在媒体上的对同性爱、对陶思瑾案的评论等,也在构建着普通人关于“同性爱”的认知,使媒体的讨论变为一场公开讨论*不过,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其中,讨论的范围是有所界定的。参见[英]格雷姆·伯顿著,史安斌主译:《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4-336页。,社会大众藉此“体验他们未曾经历过的现实生活”*斯图亚特·霍尔语,见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6页。。更多的受众由此知道了“同性爱”,并在观念上潜移默化地接受媒体的见解和表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并不是没有对“同性爱”的负面意见,只是它们仍然停留在一种民间的、非正式的层面,而同性爱本身也是一种相对私密的事情。
当公众的注意力被调动以后,女性同性爱从舆论中原本相对隐匿的位置“浮现”,陶思瑾案后出现的对同性爱的舆论获得了塑造更广泛、更深远、更持久的观念的可能性。此前,女同性爱可能是处在人们目光边缘的位置,此时,大量的“理性讨论”接踵而至,最终形成一种“公共意见”,而公共意见又通过大众文化的媒介被传播到更多的人那里。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偏偏是在陶思瑾案件以后,对同性爱的观念发生了一种渐趋塑型的变化。
在这里笔者还要指出的是,陶思瑾案使得同性爱成为一则社会皆知的话题,这是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私人事务的公共化紧密相关的。实际上除了陶思瑾案以外,民国时期的众多情感纠纷都已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和大众的目光之下。同性爱成为社会讨论的话题是不可避免之事,陶案只是使其扩大化。“当矛盾和不确定性在制定新关系和新空间的道德和行为准则过程中发展时,‘公众’——一群新的想象中的公众,就成为现代爱情的新的认可和评判权威。宣称代表政治公众新资讯灵通的报纸,就成为这个新公共领域的一部分。”[97](P 188)在陶案中,借由更多的大众媒体的传播和被营造出的“轰动性”,这种公众的意见就成为一种强势的力量,他们对同性爱的讨论和意见在这个无形的过程中被强势地推向了更多的地方。
虽然受西方影响,对于私领域、隐私等的关注也在近代中国出现,但私领域范畴在中国社会的确立和展开却并不充分,“私领域”“隐私”等观念并未被全社会所普遍认知*黄克武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的私领域观念由西方引进,但保障私领域的想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因为“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而饱经挫折。参见黄克武:《近代中国私领域观念的崛起与限制》,载于《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而当大众传媒将私人的情感世界作为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提供给公众的时候,这一情感世界就已经不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
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讨论呈现出极其多元的状态。然而,随着民放国家危机的日益突出和更多社会现实问题的纠结,宏大话语的力量便愈发突出,最终通过公众之口,经由公领域的讨论,形成一种社会的集体意见,介入私人情感世界并影响着它。“大众媒介……可以营造顺服的气氛,方法不是压制所有的异端观点,而是把落在共识之外的见解,当做是邪说异端来呈现。”[98]同性爱与同性恋便是在国族话语渐趋强势、社会规训愈发强化的过程中走向了负面化,它的负面化作为私人情感公共化的一个面向,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潮流一致。王汎森曾指出近代中国的“主义”宰制人们私人生活并使私人领域政治化的现象[99]。实质上,近代中国的私人领域,在这里主要是私人情感,不仅是被政治化了,也是被公共化了,而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只是近代中国私领域整体公共化中的一个部分。
[1]同性爱的血案[J].玲珑,1932,(53).
[2]朱夷白.同性间的纠缠[J].文华,1930,(14).
[3]更媞.关于同性恋[N].民国日报,1931-12-27.
[4]桑梓兰著,王晴锋译.浮现中的女同性恋:现代中国的女同性爱欲[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
[5]陶刘情杀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N].申报,1934-03-17.
[6]盛棣卿.西湖艺专纪事[A].浙江文史资料(第70辑)[M].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2.
[7]梦残花落[N].申报,1932-05-04.
[8]絜非.西湖春讯[N].申报,1932-05-04.
[9]陶思瑾案难邀宽典[N].申报,1932-10-01.
[10]娜.关于陶刘惨案[J].女朋友1932,1(13).
[11]止水.陶思瑾刘梦莹的观感[N].斗报,1932,2(8).
[12]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史林,2003(2).
[13]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4]樊仲云.关于大众语的建设[N].申报,1934-06-30.
[15]时事短评[J].社会与教育,1932,4(12).
[16]邵绿.从“参考”到“表达”:黄伯惠时期《时报》的黄色新闻与上海的都市化[J].国际新闻界,2013(4).
[17]儒林新史:许钦文的奇情案[J].文艺新闻,1932,(48).
[18]丽娟.许钦文的辞令[J].星期评论,1932,1(8).
[19][美]林郁沁著,陈湘静译.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0]广告[N].申报,1932-05-22.
[21]琦君.友情与爱情——一件惨案的追忆[A].妈妈银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22]该死的陶刘[N].民众导报,1932,(21).
[23]徐钦文.爱的突变[N].时报,1932-06-11。
[24]广告[N].申报,1932-06-08;广告[N].时报,1932-06-11.
[25]杀人的小姐狱中访问记[N].时报,1932-05-09.
[26]刘陶案宣判:还是那么憔悴再度狱中访问[N].时报,1932-05-21.
[27]这是她所谓包含了一切的诗[N].时报,1932-05-21.
[28]陶思瑾狱中从事创作[J].橄榄月刊,1932,(26).
[29]女画家陶思瑾狱中悲吟的诗[N].法治周报,1933,(51).
[30]丰子恺.陶刘惨案[A].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31]陶思瑾在看守所,陶母往看,母女相见依依[N].大公报,1932-08-18.
[32]陶思璧探妹相对痛泣[N].大公报,1932-07-13.
[33]其言也哀 陶思瑾函刘文如求一些同情之泪[N].大公报,1932-09-04.
[34]杭州狱中之杀人小姐陶思瑾各方慰问之书案头盈尺[N].益世报,1932-11-30.
[35]妇女节制会扩大宣传[N].申报,1932-11-06.
[36]止水.陶思瑾刘梦莹的观感[N].斗报,1932,2(8).
[37]王敖溪.我哭陶思瑾[N].社会月报,1935,(9).
[38]时事短评[J].社会与教育,1932,4(12).
[39]沈孝祥.同性惨杀案陶思瑾处死刑探讨[J].实业界专刊,1932,(3).
[40]韬奋、思君.未讨论过的一个问题[J].生活,1932,7(34).
[41]朱惺公.陶案的犯罪心理剖解[A].惺公评论集[M].机杼出版社,1933.
[42]时事短评[J].社会与教育,1932,4(12).
[43]天庐.同性恋爱[A].逍遥夜谈选[M],上海:广益书局,1934.
[44]任培初.同性爱之不良结果[J].玲珑,1932,2(56).
[45]英.同性爱的痛苦[J].妇女生活,1932,1(21).
[46]叶莹.同性爱不敌异性爱两女生双双服毒[J].玲珑,1932,2(79).
[47]樊迪民.总之是一个?[A].陶思瑾与刘梦莹[M].时事新闻社,1932.
[48]任培初.同性爱之不良结果[J].玲珑,1932,2(56).
[49]爱卿.独身主义与同性爱[J].玲珑,1932,2(77).
[50]萍.同性爱之原因与弊害[J].玲珑,1934,4(38).
[51]丙辰.略论同性爱[N].大公报,1932-12-20.
[52]同性爱的血案[J].玲珑,1932,2(53).
[53]雨宫保卫著,兢存译.女子同性爱的解剖[J].健康生活,1934,1(3).
[54]陆孝先.灵肉一元论[N].申报,1935-02-24.
[55]火花女士.“同性爱”的新估价[J].群言,1934,11(7-8).
[56]友白.关于同性爱[N].申报,1934-11-04.
[57]温和.独生子[N].申报,1940-02-29.
[58]陶思瑾与刘梦莹:他们都为恋爱而死[J].妇女生活,1932,(23).
[59]婉.“爱”的背景是这样可怕[J].妇女生活,1932,1(17).
[60]一个读者.恋爱痛苦与神经关系[N].申报,1932-09-12.
[61]徒然.望远镜与显微镜[J].生活,1932,7(34).
[62]宸.北平桃色讼案开审[N].申报,1935-04-29.
[63]任白涛.现代青年的性病问题[J].青年界,1933,4(2).
[64]士杰.处女的同性爱与保护者之注意[J].健康生活,1935,3(4).
[65]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J].妇女杂志,1925,11(1).
[66]李宝儿.论悲剧之动机与背景:提出仇杀情杀之问题[N].时报,1932-05-21.
[67]任培初.同性爱之不良结果[J].玲珑,1932,2(56).
[68]该死的陶刘[N].民众导报,1932,(21).
[69]Dikötter,F..Sex,CultureandModernityinChina:MedicalScienceandtheConstructionofSexualIdentitiesintheEarlyRepublicanPeriod[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
[70]善哉.妇女同性之爱情[N].妇女时报,1912,(7).
[71]恋爱的研究[M].上海:大众书局,出版时间与作者不详.
[72]慨士.同性爱和婚姻问题[J].妇女杂志,1925,11(5).
[73]Benjamin Elman.OnTheirOwnTerms:ScienceinChina,1550-1900[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74]李宗武.同性爱之讨论[N].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5(12).
[75]吴文藻.评清华学生生活[J].清华周刊,1922,(纪念号).
[76]吴景超.从“清华生活”中所见的同性恋爱[J].清华周刊,1923(284).
[77]卡宾塔著、沈泽民译.同性爱与教育[A].性教育与学校课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78]郑婴.恋爱教育之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79]陈静梅.现代中国同性恋爱话语译介及小说文本解读[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80]郭真.恋爱论ABC[M].上海:世界书局,1929.
[81]文砥.妇女问题的研究[M].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
[82]田泉.同性恋问题的讨论[N].大公报,1931-02-21.
[83]杨开原.性的颠倒症:同性爱[J].性科学,1936,2(4).
[84]S.C.H.同性爱的女子[J].玲珑,1935,6(14).
[85]怀似.现代妇女同性爱的批判[J].现代青年,1936,3(3).
[86][德]满和穆著,长虹译.变态性欲与其疗法[J].性科学,1936,2(1).
[87]虞车.谈同性恋爱[J].茶话,1947,(16).
[88]丁瓒.谈谈同性爱[J].卫生旬刊,1948,(81).
[89]张保善.变态性欲与其预防及治疗法[J].健康生活,1938,13(5).
[90]妙妙.同性爱的构成与防止[J].现代青年,1936,3(3).
[91]傅韵涵.同性恋爱及其防止[J].妇女杂志,1941,2(8).
[92]张铁笙.如何防止青年的同性爱[J].现代青年,1936,(3).
[93]赵梦南为同性恋爱而死[N].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9,(188).
[94]蔡蕙芳为婚姻而死[N].申报,1931-12-22.
[95]蓉市学界悲剧同性爱护士小姐殉情命危[N].申报,1948-01-22.
[96]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97][美]顾德曼.向公众呼吁:1920年代中国报纸对情感的展示和评判[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6,(14).
[98]R.Milib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M].Quarter Books,1969.
[99]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A].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责任编辑:绘山
EmotionandGenderinPublicOpinions:TaoSijinMurderCaseandFemaleHomosexualDiscourseintheRepublicofChina
LI Shi-peng
(DepartmentofHistoryand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200,SichuanProrince,China)
D442.9
A
1004-2563(2017)05-0060-19
李世鹏(1996-),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