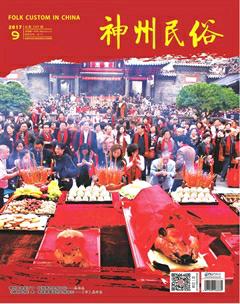天堂“草湖”巴里坤
2017-09-29文图牛顺莉
文图/牛顺莉
天堂“草湖”巴里坤
文图/牛顺莉
巴里坤是距离草原最近的城市,近到你的双脚行走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你的鼻翼里依然呼吸着草原清爽的气息,近到你左侧行走着一位时尚的现代女子,右侧同时行走着一位脚蹬马靴的哈萨克族汉子,青草的气息,从天,到地,从无形有形之所在,从你不时的期盼里以及意料外涌现。

草原中的巴里坤
作为新疆著名的草原,1650米的海拔让巴里坤享有了“天堂草原”的美誉。但巴里坤人管草原不叫“草原”,而叫“草湖”,把南山(即东天山)脚下的草原称为“大草湖”,把县城与乡村之间的草原叫“小草湖”。大草湖和小草湖都是草,外地人来赏美景,巴里坤人看到的却是草料。
巴里坤草原由许许多多夏草场、春秋草场、冬草场、刈割草场组成,总面积191.08万公顷,可承载牲畜100多万头(只)。巴里坤古称蒲类,是汉朝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类国。自古以来,巴里坤就是游牧民族驰骋角逐之地。远在七八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狩猎和游牧。约公元前4世纪,乌孙人在哈密建立王庭,巴里坤草原是其游牧草场。公元前2世纪,乌孙人在匈奴人的逼迫下西迁,巴里坤草原又成为匈奴人的游牧地,“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汉朝时巴里坤草原是蒲类国的归地,“……有牛、马、骆驼、羊群,能作弓矢,国出好马”(《后汉书》卷八十八)。唐、宋、元、明、清诸朝,巴里坤草原都是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可以说,千百年来,巴里坤都是兵马布阵、商贾云集之地,东西方文化以及中原与西部文化在这里交融荟萃。于是,巴里坤得到了最丰厚的颐养,虽然那些史前遗址,汉唐文化已成过眼云烟,却也为这片土地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依然会在风起之时划过耳际,令人生出许多遐想……
巴里坤,是一座搅拌着青草气息的古城。

八月正是打草时
每年的八月开始,巴里坤就进入打草时节。打草是巴里坤人秋收的序曲,紧张而有序,集中展示了草原浓郁的生活情趣。
打草就是收割牧草,主要是为牧养的牲畜,准备充足的过冬“口粮”。这里的牧民要收割,农民也要收割。天然的优质牧草,是育肥牲畜的极好食料。这里的农民家家育有羊、牛,有养几只的,有养几十只的,他们养的牲畜主要用来自家宰杀冬肉。
草湖是打草的主战场。打草主要由打、搂、捆、拉这几部分程序组成。
打草前,农妇们要为自家打草的男人们准备吃的,蒸花卷和蒸饼,烧锅盔和干粮。有的人家还要提前宰好羊,怕活儿重,自家男人吃不好,打不动草,落别人家后面。
统一的打草时间到了,人们纷纷下草湖,开始搭帐篷,有的人家把随行的毛驴车翘起,辕口处搭上帆布或塑料布,建成简易的“房”,有的用数根椽子搭起,建成像马脊梁一样的“房”,还有的直接在干燥处铺上干草,拉开被子而眠。
打草,主要是男人的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草湖归集体所有,打草由生产队统一组织,扛着钐镰向草湖深处走去的都是青壮男人。劈柴引火,烧水做饭、负责后勤的都是女人。各家的娃娃都是在草湖里玩耍,或平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或一个接一个在草地上翻跟头,比谁的体力强,或提着自编的笼子,追捉飞蹦的蚂蚱、蝈蝈。承包责任制后,女人和娃娃也加入了打草的行列,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前两个月才能完成的打草,现在三、四天时间就完成了。
打草需用钐镰。钐镰是一种用金属制造的把儿很长的大镰刀,镰刀有一米长,镰刀把也近两米长。钐镰和刀把是用一个附板再加两个铁环固定在一起。钐镰把中间装了一个“A”型的拐把,打草人可一手握刀把,一手握拐把。钐镰大小可分六号、七号、八号刀即大、中、小三种,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及自身能力选用。
打草,需要力气,更需要技巧。打草者需两腿叉开,平端双臂,猛地一扭腰肢,抡圆的杉镰紧贴着草皮掠过,三四米宽的青草齐刷刷躺倒在刀尖经过处,整整齐齐的码在草趟子里。草茬低得贴近草皮,这样出草多,来年草长得均匀、平整,好打。如果是生手,一刀很难打透,再加上近一米长的钐镰又不听使唤,不是闷头朝草地里扎,就是贴着草半腰飞过,割倒的青草乱蓬蓬的,散得到处都是。兴趣最浓的打草者要算刚学会的,尽管浑身被汗水湿透,也不肯放下钐镰休息一会。看着身后倒下的片片成果,连单调的“刷---刷---”打草声,在他们听来都是无比美妙的天籁仙乐。
钐镰需要经常磨,磨钐镰时,打草人停住脚步,弯腰抓起一把草,顺着钐镰从刀根擦向刀尖,抹去刀上的草渣,顺手拿起腰里系着的磨刀石,前后左右,有节奏地磨着。要想钐镰刀刃锋利,男人必须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砸钐镰。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打草能手的重要标准。砸钐镰时,把刀刃平放在铁砧上,用平嘴小铁锤砸,从刀根顺着刀尖砸过去,要适度的频频敲打,不能用力不一,把刀刃砸开、砸薄、又不能把刀刃砸裂。休息时,草原上就会响起“叮叮咣咣”的声响,像一首首敲打乐曲。

打草、搂草
全家老少齐收草
夏末秋初的天很热,割倒的青草很快就晒得半干,匍匐在地上,这就要进入搂草模式,即收草。把散在草湖四处晒干的青草,用耙子收集在一起。以前收草,都是女人们的活,现在全家老少一起干。一家人排成两列,挥动耙子,左右夹击,合拢的草堆像一条条青龙伏卧草湖。

草合拢以后,开始捆草。捆草的绳叫葽子,用芨芨草拧制而成。打捆时,用木耙子将草搂成堆,弄成工整紧密的草扎儿,捆草人则将成把的葽子挂在腰间,到搂好的草扎跟前,一弯腰掀起草扎儿塞进葽子,一扳,从一端抽出咬抓子,以膝盖垫在草扎上压紧,拧上咬抓儿,待起身时拎起草捆顺势将其一扔一滚,两边松散的草便给抖掉,一个干净利落的草捆便出来了,五十个草捆子码成一个草垛。夕阳下,余辉洒满草湖,那散布在草湖的草垛,像绿色的烽火台,神秘而庄重。
捆草间隙,男女散坐在草堆上,说笑打骂,偶尔会有男人们玩笑开过了,惹得女人们群起而攻之,甚至将其掀翻在草地上,并把干草塞满裤裆,扎得他一个劲求饶,女人们则满意地嘻笑着一哄而散。
现在,机器代替了人工捆草,这热闹的场景已不复存在。
拉草的运输工具,以前用毛驴车、马车,人们在车上绑上棱木,就是数根比车厢长的细椽子,首尾连接着固定在车厢上,这样做的目的是面积大,拉的草多。如今,小四轮、大拖拉机、大卡车成了主力军。一辆辆小四轮、大卡车,装得方方正正、平平稳稳,车装好草后,车头大都被青草掩盖,行走起来,酷似一座草山在移动。运草的队伍排成行,连成串,高坐于其上的驭手和乘坐者,闻着草香,带着疲惫,载着收获往家赶。往日长鞭甩出的脆响,已被今日机器的轰鸣声代替,但他们红润的脸膛仍旧,带着希望,带着满足,带着舒适和惬意。
成群的马、牛、羊、毛驴散落在草原上,尽情的吃着、咀嚼着,满嘴的青春味流溢、飘散,从一个村庄逍遥到另一个村庄,回缓、温情。

巴里坤草原,挂在乡村的前面,傍依在县城的身后,横卧在天山脚下,如盈盈的女子,娇喘、矜持,散发出令人陶醉的幽香。一抬头,一回首,眼被美吸引,心被美浸染。往前走,往后行,都如在画中行走,不经然间,你就成为草原微小的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