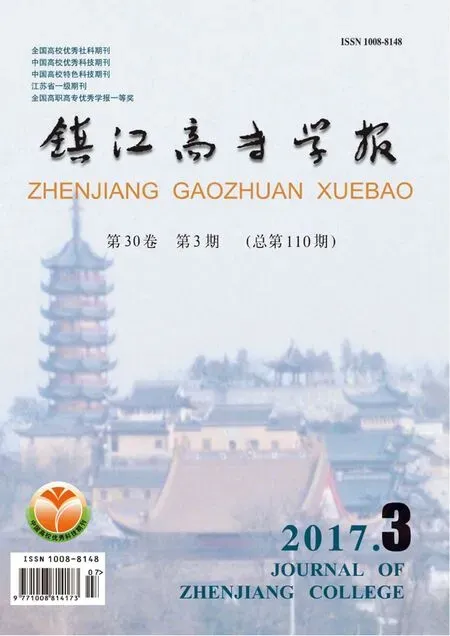原型理论视角下《简·爱》的另类解析
2017-09-20朱燕秋
朱燕秋
(贵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原型理论视角下《简·爱》的另类解析
朱燕秋
(贵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借鉴荣格的原型理论观,对《简·爱》进行文本的细读和分析,我们认为简爱体现了作者夏洛特的人格面具,疯女人伯莎体现了她的心理阴影,罗切斯特代表了她心中和现实中整合为一的阿尼姆斯。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变化,就是夏洛特“自身”现实化得以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又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观点:女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不仅要解构男权中心主义,也要消解女性主义,以此来构建两性和谐关系。
原型;人格面具;心理阴影;阿尼姆斯;女性主义
泰纳提出的“三因素”说(种族、环境和时代)主要着眼于文化对文学的制约。当旧有的文化不能表现正在革新中的社会风尚与时代精神,甚至成为发展障碍时,文学家便会率先对其进行批判与扬弃,催生新的文学模式。夏洛蒂·勃朗特就属于这样的作家。荣格曾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1]237就《简·爱》而言,可以说不是夏洛特创造了《简·爱》,而是《简·爱》创造和体现了一个人格丰满的夏洛特。
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体系中,人格结构理论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而他的“自身现实化”观点又是人格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每个人的人格中最重要的原型有四种:人格面具(persona)、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阴影(shadow),以及“自身”(the self)。“人格面具”指为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可而愿意在公开场合展现的人格特征,处于人格的表层。“阴影”指心灵中最阴暗隐秘的内容,不受一般道德束缚,位于人格最深层。“阿尼玛是男性心灵中的女性原型,阿尼姆斯是女性心灵中的男性原型。”[1]144“自身”是人格结构理论中最重要的中心原型,它表明人的精神具有一种先天的走向完整的倾向,它是人格的开端和最终目的,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顶点,即“自我”实现,其它原型都由它产生、组织、协调,以达到人格的平衡和统一。同时,“自身”现实化的实现又有赖于其它原型的变化。在荣格的原型理论观照下,我们可以将简爱理解为作者夏洛特本人的人格面具,将伯沙理解为她内心的阴影,罗切斯特则可以理解为被现实化的阿尼姆斯,这三者之间相互的协调和变化,折射出夏洛特“自身”现实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体现了夏洛特的女性主义观点:女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不仅是为了解构男权中心主义,也是为了消解女性主义,以此构建两性的和谐关系。
1 人格面具:简爱——环境和时代的产物
“任何文学的历史,只有把这种文学和创造这种文学的人民的社会和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才能被人理解,才能加以研究。”[2]要理解夏洛特的人格面具,就得回顾当时的创作背景。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特别是已婚女子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活动范围基本被局限在家庭和社交场合。女性作家为了能够出版自己的作品,不得不采用男性笔名。而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此时的女性已开始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敢于为自己的创造力和才华展示争取空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夏洛特在创作时,希望通过对简爱的塑造传达出一个怎样的人格面具呢?为了能够更简单明了地说明这一点,笔者特拟出如下表格:

表1 夏洛特与简爱相似点
由此表可以看出,无论是幼年失去母亲和好姐妹,长大后成为家庭教师,还是在不知道罗切斯特先生已婚的情况下爱上他,在知道伯莎的存在后离开桑菲尔德山庄,都可以说是夏洛特为了在作品中达到“自身”的现实化,把简爱塑造成了自己的人格面具:无畏生活的苦难,敢于独立思考,拥有文化自觉意识,勇于追求和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的人,夏洛特已不再是一个狭隘的个体,而是一个承载并造就人类文化和人类无意识的“集体的人”。因此,简爱的形象也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主义者的集体无意识。
但是,人格面具与真正的人格并非完全一致。荣格认为,人虽然可以依靠面具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上,可是,人格面具掩盖了真我,使人格成为一种假象。要理解一个人真正的人格,必然离不开分析他的心理阴影。
2 心理阴影:伯莎——消解了男权中心与女性主义
在男权中心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史上绝大多数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来想象和操控,从男性视角来刻画。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形象的塑造史几乎也是女性被男性通过文字进行文学文本虐待来构建男权中心的历史。在这一历程中,男性的中心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通过历代作家的描写和读者的阅读得以不断延续。如小说中罗切斯特对伯沙进行一种不在场的描述,从他们结婚到伯沙变得疯癫,伯沙都只是一个被描述的缺席的“他者”,一个没有话语权为自己辩护的若隐若现的“他者”。然而当女性主义出现,男性的中心统治地位受到挑战时,很多人认为男权中心主义会被女性主义所颠覆、消解、取代。其实不然,在《简·爱》里我们就发现,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除了要解构男权中心,也要消解女性主义。
长期以来,女性都处于一种压抑的第二性社会历史中,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夏洛特有意识地运用“缓和手段”使现实生活中的“压抑”在作品中得以宣泄出来,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代表夏洛特心理阴影原型的疯女人——伯莎的肩上。简爱离开桑菲尔德庄园,意即让作者的人格面具退场,让被压抑的心理阴影伯莎登场。小说在第三十六章提起伯莎,罗切斯特先生的老管家这样描述:
“She was kept in very close confinement...; people even for some years was not absolutely certain of her existence...They said Mr. Edward had brought her from abroad , and some believed she had been his mistress .”[3]451
“过去她一直被严加看管着……;许多年了,外人都不能十分确定她的存在……有人说她是爱德华先生从国外带回来的,也有人认为她是爱德华先生的情妇。”(笔者译)
伯莎活在这样一种自身身份不为人所知,也不为人所接受的黑暗中,失去了在场的话语权。而这种黑暗源于她丈夫对她的禁锢。所以,当伯莎第一次在半夜三更出现的时候,她走进了罗切斯特的房间,点燃了他的床单。第二次出现时,在一众宾客中,她唯独咬伤了她的兄弟。原因何在?因为她的家人对她的婚姻负有直接责任。所以,燃烧的火焰既可以理解为被锁在黑暗中的妻子对丈夫的警告,也可理解为作为女性,已经燃起了要消解男权中心的女性主义之火。夏洛特在此借伯莎对当时处于父权、夫权传统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无声的猛烈抨击。第三次出现的时候, 伯莎在夜里偷看并撕毁了简爱的婚纱。笔者认为这一举动不是出于嫉恨,也不是报复,而是她不希望下一个穿上婚纱的无辜而又无知(不了解真相)的简爱也如她一般遭受婚姻的痛苦,步她的后尘。但是,在整个桑菲尔德庄园,唯一拥有话语权的人是罗切斯特先生,因此,伯莎第四次出现,被罗切斯特昭告给大家,认定她就是一个“疯女人”时,她也无权为自己辩护或反驳。当无法和男性进行理性与平等对话的时候,女性只能选择通过疯癫似的吼叫来表达自己的在场和意图。疯癫正是她们反抗和摆脱男性霸权、争取自由的方式,是她们从被剥夺话语权的缺席的“他者”到拥有话语权在场的“自我”的实现途径。
“she was on the roof , where she was standing, waving her arms, above the battlements , and shouting out till they could hear her a mile off: ...we could see it streaming against the flames as she stood . ”[3]453
“她站在城垛上、挥动着胳膊,大喊大叫,一英里外都听得见……我们看到她站着时头发映着火光在飘动。”(笔者译)
唯有通过疯癫,伯沙才能够出场,才能够拥有话语权,才能够从缺席的“他者”转变成在场的“自我”。当伯莎放火烧毁了只有罗切斯特先生才有话语权的庄园时,也就此消解了小说里男性霸权的文化场域。罗切斯特只是受伤,并没有在大火中丧生,这显示了女性主义的目标并非是要消灭男权中心主义。可是,伯莎却在大火中丧生了,这表明女性要想获得平等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同时,随着伯莎的离去,女性主义也由此被消解。因为当简爱回归,女性得到应有的尊重,两性能够和谐平等地相处之时,自然就不需再提及女性主义。
3 阿尼姆斯与“自身”现实化:夏洛特——重塑自我
一切人格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自我实现。文学家通过语言来“虚无”世界的本质,把自己从现实世界里解放出来,进行新的“自我塑造”,以期达到“自身”的现实化。“自我塑造”是一个自我与他者(一切外力)相互妥协、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过程。作家的自我塑造往往通过对某种主流文化、统治霸权的否定与叛逆来实现,夏洛特的自我重塑即是如此。
夏洛特能够在小说中实现“自身”现实化,重塑自我,有赖于她对人格面具、阴影和阿尼姆斯所进行的协调与整合。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都属于集体无意识,只有在与具体的情境发生关联时才会被激活,既具有创造力又具有破坏力,往往通过“自身”的协调将其积极的力量整合到整体人格中去。阿尼姆斯是女性心目中的男性形象,通常表现为智力发达、有艺术气质、英勇无惧等,也结合了权利和控制力等。女人在遇到像自己阿尼姆斯的男性时,会感到极强的吸引力。现实生活中,埃热先生符合阿尼姆斯特征,是夏洛特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男性,正如罗切斯特是简爱的理想爱人一样。但若把理想与现实中的男性形象对等,则两性关系必然破灭。因此,男女关系要得以维系,就必须要调整理想与现实中的男性形象。小说中,当遭遇火灾之后,罗切斯特原先智慧、富有、绅士的完美形象被转化,实现了理想形象向现实的过渡与统一。
荣格的原型理论还认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每个人的身上都潜藏着一个异性形象,每个人的无意识中都有着一定的异性人格成分。阿尼姆斯原型就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中会被激发出来的女人心理中男性气质的一面。火灾之后,伯莎死去,阴影消失,象征着女性受压抑、束缚的“第二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简爱回归,人格面具再次登场,有情人终成眷属,两性之间构建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男女相处模式。这意味着女性在爱情和婚姻的世界里终于拥有了自我选择的决定权和话语权。然而,在那时的社会背景中,“如果一个女人想在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做一个创造者,那么她不仅需要把身体里的‘男性气质’激活,还必须时刻体会她的女性天性带给她的气质。”[4]通过对伯莎和简爱的塑造,夏洛特在小说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伯莎和简爱分别体现了女性心理中阿尼姆斯原型的破坏力和创造力。一方面,小说中真正消解了男权中心的不是简爱,而是疯女人伯莎。夏洛特赋予伯莎的“智慧”就在于她的疯癫:疯女人不用像正常女性一样活在男性霸权话语的社会约束之中,她完全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不畏惧性别暴力,且敢于反抗。当伯莎放火烧毁桑菲尔德庄园时,她身体里极具破坏力的“男性气质”被激活。表面上看,纵火是一种“疯癫”的行为,实际上,这正是无数智性正常的女性被压抑的阿尼姆斯原型中的“男性气质”。从男性视角来说,虽然伯莎的行为绝对是破坏性的,但是从女性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反观,伯莎因为“疯癫”而具有的纵火勇气,以及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来解构男权中心的“智慧”,却是具有时代性创造意义的。另一方面, 当拥有了一定财富且身体健康的简爱决定留在桑菲尔德庄园时,她心理中积极的、具有创造力的“男性气质”也已经被激活。之前的简爱柔弱、贫穷、矮小、被动,需要罗切斯特的庇护,而此时的她仿佛与罗切斯特互换了形象,她以勇敢的强者形象给予轮椅上的罗切斯特以关爱和照顾,成为罗切斯特的“眼睛”和“拐杖”。无意识中,一种新的男女和谐相处模式得以创建。至此,夏洛特让疯癫的伯莎呐喊与破坏,让理智的简爱思考与创建,使罗彻斯特的完美理想形象在小说中被转化。通过改变并协调人格面具、阴影和阿尼姆斯三者之间的关系,夏洛特成功地完成了“自身”的现实化,实现自我重塑。
4 结束语
西方有一句谚语:理论来了又走了,但文本永存(Theories come and go, but the text stays)。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构成了作品的存在。文学作品至少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作者通过文本表达的,文本自带的意义;二是读者在阅读时,通过对文本中的“语言”进行话语解构和建构,“解码”和再“编码”、构想与整合后得出的重建意义(reconstruction meaning)。这种重建意义由于融入了不同的理论维度而不完全等同于文本自带的意义,会随着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文明的变迁而变化。本文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为视角,结合小说的创作环境和时代背景,通过分析认为:罗切斯特是夏洛特理想与现实生活中阿尼姆斯的统一体;理智的简爱、疯狂的伯莎分别代表着夏洛特的人格面具和心理阴影以及阿尼姆斯原型中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共同体现了一个显性的和一个隐性的夏洛特,是
夏洛特对自己的双重书写,也是她在用两个女人的身份同时与男权社会进行对话。由此,夏洛特不仅在小说中成功地完成了自我人格的构建,实现了“自身”的现实化,而且还鲜明地表达了她希望解构男权中心、消解女性主义,使两性能够和谐共存的“平衡”思想。
在对文本内的语言和文字进行阐释的过程中,能指可能永远追不上所指。只要有文本阐释,就一定会存在意义的“黑洞”。本文对《简·爱》的分析仍存在很多的“空白点”和“未知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理论的更新,随着思想范式的转变,人们凭借已知去认识未知,进行新的探索,发现原先被遮蔽了的认识的盲点,夏洛特和《简·爱》必将会在更加多元的理论解析中绽放新的生命。
[1]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M].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1.
[3] BRONTE C. Jane eyre [M].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3.
[4] HARDING E. The way of all women [M]. New York: C. G. Jung Foundation,1970:81.
〔责任编辑: 刘 蓓〕
AdifferentanalysisofJaneEyreundertheperspectiveofprototypetheory
ZHU Yanq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Jung’s prototype theory, and by means of close reading and analysis,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Jane is the embodiment of Charlotte Bront’s persona, Bertha,the crazy woman, is that of her psychologjcal shadow, and that Mr. Rochester symbolizes the combined animus both in her inner heart and reality. The coordination and change of persona, shadow and animus is the realization process of Charlotte Bront’s self actualization. This process shows Charlotte Bronte’s perspective on feminism that feminist’s ultimate goal is not only to deconstruct male chauvinism, but also to eliminate feminism, and to establish a kind of harmonious bisexual relationship.
prototype; persona; psychological shadow; animus; feminism
2017-03-02
朱燕秋(1980—),女,贵州毕节人,副教授 ,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I106.4
: A
:1008-8148(2017)03-0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