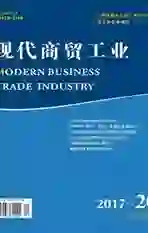数据产权界定:一个文献综述
2017-09-13吴俊熠
吴俊熠
摘 要:近年来,数据在电子商务、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日益广泛,对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必须在市场中参与配置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涉及了数据交易问题。数据交易的本质,就是对数据的产权,即数据的拥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利的转让。首先将数据划分为底层数据和大数据。然后按照经济层面和法律层面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数据产权界定的文献。最后将数据产业链上的数据参与者划分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并按照底层数据和大数据两层面进行总结阐述。
关键词:数据;数据产业链;产权界定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20.031
数据伴随着人类记录工具的出现而产生,近年来凭借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数据处理技术的提高以及数据应用领域的扩大,体量大种类多的大数据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其实大数据并不是新生事物,只是在大数据时代下运用信息技术处理的数据,其根本来源是元数据。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在其说明中就指出其交易对象是大数据资产——不是底层数据,是清洗、分析、建模之后的数据结果。为了便于梳理文献和明确产权界定,本文将数据划分为底层数据和大数据。
当数据被作为资源和要素时,就必须探讨数据的产权问题。目前数据产权界定的状况并不理想。一方面,对于越有价值的事物,人们越是倾向于清晰地界定其产权。当前数据的学术和商业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挖掘,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人们迫切要求明确产权。另一方面,产权界定需要考虑的是其带来的好处和确定产权导致的交易成本两者的相对大小。考虑到数据是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使得作为数据的交易费用较高,从而加大了产权界定的成本。因此当前国际上对数据产权的界定尚无统一说法,而数据产权的界定对数据流通交易和分析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1 数据产权界定综述
王忠(2015)通过比较界定产权导致的交易成本和带来的好处得出当前不界定数据产权是现有条件下自发演进的状态。然而随着数据交易机制的完善,数据质量评价指标的完善和更可操作性以及充分的市场竞争等带来的数据交易费用的降低,同时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对生产发挥的效用日益增加,那么就有必要分析数据交易中的产权问题,从而为优化交易机制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参考。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一个事物的多种属性意味着有多个产权。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资源主要具有财产属性和法律属性,下文将按照数据属性进行数据产权界定的分类归纳。
1.1 法律层面
宋志红(2016)根据核心利益的不同将大数据产业参与者划分为三方:国家、以企业为主体的数据业者以及个人等数据主体,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对其本国的数据具有数据主权,数据业者对其收集整理后的数据有知识产权,公民对其个人数据享有控制权(个人数据权),并就个人数据权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说明。王融(2015)根据不同的场景来研究个人数据的产权问题,指出以个人数据为交易对象时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归数据主体本人;企业对数据做匿名化处理后的数据拥有有限的所有权。邹沛东(2016)基于不同类型数据有不同的权利类型将其划分为数据主权和数据权。并具体指出数据主权是国家对政权地域内的数据有管理、控制的权利;数据权又分个人信息类的人格权,分析处理后的数据由加工者拥有的知识产权,社会经济组织拥有的商业秘密权。黄立芳(2014)从数据产权的角度将大数据分为公有数据和专有数据两部分,前者任何人都可以无偿进行收集和使用,而后者是经过处理所得到新的数据属于一种智力创造成果,数据开发主体拥有所有权,并称之为数据产权。
1.2 经济层面
王融(2015)在文章中指出当前关于大数据产权的两种观点中产业界的观点:云平台不得侵害客户数据且云客户对其数据享有绝对所有权(即自由使用、分享、交换、转移、删除这些数据)。王忠(2015)指出对于经过二次加工后的数据,其产权属于二次数据供给者。
2 数据产权界定小结
由以上对数据产权从法律层面和经济层面的文献归纳中可以看出,尽管没有统一一致的看法,但是大多都分门别类对数据产权进行阐述。从现实情况看,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种类繁多,属性多样,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界定产权难免偏颇。因此,对数据进行分类是界定其所有权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基于数据产业链的分析将数据产业链上的众多数据参与者划分为三方:国家、包括企业在内的数据业者、作为数据原始来源方的个人等数据主体,并把数据按照底层数据和大数据两方面从上述三方主体进行综合归纳对数据产权进行界定。
2.1 底层数据
底层数据是由被记录主体直接产生的未经数据服务提供商处理的数据,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底层数据才是真正的命脉。本文按照底层数据的来源主体进行分类并提出底层数据的产权归被记录主体。
2.1.1 个人
被记录者为个人时所得到的数据,其产权归个人所有。跟据记录个人数据的主体不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类是国家机关从执行公务中获得的数据。这里又可以根据获得数据的内容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块。其中间接数据属于这里的底层数据,是指国家机关在办公中获得的相对人的资产经营数据或行为记录数据,这类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由相对人所有。第二类是平台获得的关于个体交易或行为的数据。在当前信息化背景下,虚拟经济的出现和兴盛使得平台变成了电子、虚拟化平台,信息变成了数据,因此数据的存储、复制、加工变得越来越容易,也因此产生了信息增值问题。本文认为平台记录数据的产权应當归属交易双方,而不属于第三方平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讨论的数据是平台获取的个体原始未加工的数据信息,属于底层数据范畴。而经过了二次加工的个体数据产生的产权问题将在下文大数据板块中的公司数据中讨论。
2.1.2 企业endprint
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企业所掌握的数据,如果属于其自身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且能产生经济价值的,这部分数据就属于商业秘密,企业对其享有权利。
2.2 大数据
根据对大数据产业链的分析可以得出,数据源需要通过数据服务提供商的收集、存储、加工、处理才能到最后的应用。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数据服务提供商的劳动。因此本文认为大数据的产权归数据服务提供商所有。根据数据服务提供商的不同,这里主要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主体。
2.2.1 国家
国家掌握的大数据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关对大自然认知的数据。这类数据涉及公共利益,且由政府或科研机构掌握,国家有义务将此类数据向社会共享。如果数据需求方将数据用于商业目的,可有偿提供。这类数据和国资相似,它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表现出全民所有、国家经营管理的特点。第二类是国家机关在执行公务获得数据中的直接数据。直接数据是指国家机关针对相对人作出的履职数据,包括主体识别、登记、许可、处罚、判决等,即政务、法务数据。这类数据应归属国家所有,国家机关可以出于一定用途进行处置,但是相对人具有数据被应用的知情权。
2.2.2 企业
企业通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从而实现数据商业价值或社会管理价值的过程中,因为包含了其智力劳动,数据业者对此类具有原创性的数据形态具有(知识)产权。具体而言,个人在使用企业等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各项服务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均已被电子化,并被保存下来。服务提供商基于这些数据进行二次加工。二次数据主要通过企业进行深加工后获得,并打包成数据集合或数据服务提供给下游企业,所有数据二次加工后的产权属于二次数据供给者。
参考文献
[1]王忠.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交易许可机制研究[J].理论月刊,2015,(06):131-135.
[2]王融.关于大数据交易核心法律问题——数据所有权的探讨[J].大数据,2015,(02):49-55.
[3]邹沛东,曹红丽.大数据权利属性浅析[J].法制与社会,2016,(09):256-257.
[4]宋志红.大数据对传统法治的挑战与立法回应[J].经济研究参考,2016,(10):26-34.
[5]黃立芳.大数据时代呼唤数据产权[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12):50-5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