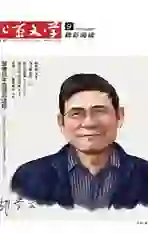遁入岁月的宅院(散文)
2017-09-11钟月
钟月
一
天气渐暖,多风少雨的春季来了,正是土木工程的时节,家里盘算着翻盖居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屋顶的石板松动了,有些漏雨;屋里,长年的烟熏火燎,约有二尺粗的房柁和半尺多粗的房檩已没了木色,花架发黑还折了不少,固定石板的泥土之所以没有掉下来,完全依仗于荆条编的笆拍子。也难怪,歇山脊式的房顶本为雨水流下去顺畅,可这顶子却成了家里的一块场院,晒过草,晒过豆子,还晒过唐山地震那年阴雨绵绵、生产队分的发霉的麦子。
几乎是四年没有攀爬了,顺着围墙,我上房下房依然如履平地,熟门熟路,可见房顶的利用率之高。再不翻盖,恐怕哪一天石板也会从屋里掉下来砸到炕上。
我又一次登上房顶,想再看看我无数次登临过的地方。那高高的房脊斜斜的流水面上仿佛还晒着什么东西,好像处处都印着风吹日晒雨淋也无法抹去的足迹,印着我童年的天真、快乐和心酸。真不想这么潦草地告别啊,可又有什么办法?畢竟它老了,再不能为我们全家遮风挡雨,原地翻新或许是它涅槃重生的最好选择。放眼四望,北面东面鳞次栉比的房子都已翻新了,只有这两间还留着原始气派的韵味,高高的房脊向东西伸展着,从两端翘起,高傲地兀立,很有些老骥伏枥的感觉。突兀的屋脊两侧,东西和南北对称着,镇着石板的三溜青瓦已残破不堪。初春,小草已在瓦下的泥土里蠢蠢欲动,就要钻出来。我们虽住了十几年,但这房子原比父亲的年龄还大,听老人们一次次偶然说起,我的印象中逐渐形成了一条小河,今天多股水,明天又多一道泉,慢慢涌入,慢慢丰沛,终于,一座坐北朝南大宅院的景象渐次还原出来,栩栩如生了。
二
那曾是一座完整的四合院。整座宅院坐落在村南一处把角的地块,方方正正,南面、西面临街,东面是一条小胡同,北面是另一家的过道。正北一字排开的五间正房,木装修,玻璃窗,高地基,衬得全屋都很敞亮;房前左右两侧各是两大间的东西厢房;南面是一拉溜的五间南房,中间的一间是门厅,青石地面,矗立在方方墩墩门槛上的两扇朱漆大门镌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训。
传到我们这一代,借着文革的东风,连名字里都有了个“忠”字,名如其人,我的儿子也一样。不过,那“诗书”就不敢说了,我的叔辈们连初中都没上下来,大概没有人知道“诗书”为何物?至于他们的子孙,也没听说哪个考上大学了。
大院东侧约两三亩的空场是菜地和牲口棚,几挂大车和十几匹牲口晚间就停放在那里。一间小南房(因在大院东侧,我们一直称它小东屋)是晚间照料牲口的佣人值夜用的。据说,菜地里住着狐仙,月上中天时,常常自带食料帮着佣人喂牲口。正应了那句话,马无夜草不肥,家里的牲口在整夜整夜的饲养中膘肥体壮,像主人家的日子一样昂扬向上,精气神十足。连整夜吃豆子的牲口拉出的粪便都肥肥的,不用堆沤便直接撒到菜地里,催得那菜田总是绿油油的,生机勃勃。
据说,祖上是在脊骨山开灰窑的,那些大车便将石灰运到各村各户或琉璃河码头后远走天津。
太爷爷时代应该是这个家最鼎盛的时期了,虽说不上钟鸣鼎食,也是远近有名的大户,建了这所足以让子孙后代安逸舒适的气派宅院,青堂瓦舍,使佃唤婢,风光了几近二十年。两个少爷也就是我的爷辈们读到中学时家道中落,但二人的学识在别人眼里也已是先生一级的人物了。虽同出一门,但性格取向迥异,老大花钱如流水,老二于家里或学校尚知节俭。二人秉性不同便决定了二人的命运。太爷过世前按老大的意愿多给了他一些钱财,加上东厢房后面原是牲口棚的大片院子及南面的五间房,五间正房和两侧厢房则给了老二。太爷爷一死,灰窑也不开了,大宅院也画地为牢,院当中东西向垒起的一道又高又厚的大墙将大院分为南北两院。那大墙的古板、陈旧、敦实,宛若金刚,不容置疑。小时候,没少在大墙下玩耍,总觉它别扭,今日剜个坑,明日掏个洞,可它就是倒不了。大墙隔开的不仅是院子,还有亲情,墙南北的两家后来连话都没了。
默默无语的院落,高高耸立的大墙,几十年里,容纳了太多的沉重、浮躁和辛酸,容纳了太多的冷漠、隔膜和怨恨。
二爷爷因善于打理,家境不错,虽遭了丧妻之痛续娶一房、前后窝差距悬殊外,因为有文化,人又厚道,解放后一直在乡里任职,直至改革开放前后退休。而居家过日子就不是我亲爷爷的所长了。年纪不大,却早已在京华这片温柔之乡里瘫软融化了,一桩桩风流韵事几十年后还传到了我们孙辈的耳朵里,他是一家之主,没有人敢指责他的荒腔走板。习惯了大把花钱,父亲留下的钱财很快就光了。他又没有生财之道,就开始想着法子变卖家产,大车没了,牲口没了,东面的几亩菜田也没了,最后,连那两扇气派的“忠厚”“诗书”的大门也难逃厄运,卖给了一个贾姓的邻居,“久”和“长”不复存在。
我会走路了,曾在这安装“忠厚”“诗书”大门的门洞里走过了幼年。小小的我眼中,门槛又厚又高,每一次都要扶着门槛才能过去。门也是那样高大、厚重,推挪不动,望不到顶,在日复一日年轮的风雨中,朱漆虽然剥落,显出了木本色,但它依然坚守着这个已经衰颓的院落,傲然挺立,坚韧不屈。直到被主人卸下,轰隆隆倒地,劈成数瓣,成了人家家具的木料。
上世纪80年代,初进残破的房山云居寺时,就听说了一句“只要大门不倒,寺院必有重生之日”的预言,果然,云居寺重生了,香烟袅袅,香客如织。可我家的大门倾倒了,于是,家已不是家。入不敷出的日子接踵而来,百无所依,爷爷只好在自己的五间房子上打主意,最后把门厅西面的两间房子(也就是我们一家后来住的那两间)以十五担玉米的价格一次性租给了别人,一租就是二十年。大门没了,留个空门厅又有何用?随着子女的增多,他干脆把它堵死改成了一间内屋,供儿女们居住。又在房子东面和过去佣人住的小东屋西新开了一处南向的狭长的走道。
否及泰来,败成了“无产阶级”,也未必是坏事。
一座熙熙攘攘的大宅院到解放前夕,只剩一个七零八落的空架子,没地,也没有财产,划定成分,响当当的贫农,连下中农都不是。所以,到文革时,也就没给子孙留下个狗崽子的黑帽子。挥洒之间,竟钻进了根红苗正的圈子里,历次运动下来,就少了无数揪斗和屈辱。塞翁失马,不是坏事,这马丢得是时候。endprint
太爷辈建造的这所大宅院幻想着子孙们繁衍生息,兴旺发达,不绝如缕。可刚传一代就已经一分为二、东鳞西爪了,真能响应俗语所说的“富不过三代”。只有他老人家那辈儿红红火火,生前和死后进出在同一个气派的门厅。如今,门洞成了居室,儿孙们再没有进出的福分了。
两位秉性迥异的爷辈已匆匆去了,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又该说些什么?真不知这勤俭与自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养成?更不敢说富足与贫穷留下的是福还是祸。
三
我父亲的母亲、我的亲奶奶是爷爷的第一任妻子,在父亲一岁时染病,年轻轻就走了。邻里的另一个女人过门后,一拉溜又生出了六个子女,小的比我还要小,前后的子女就有了天壤之别。父亲成了个野孩子,曾经被丢弃、被毒打、被往坑塘里赶,也算是命大,多少次死里逃生,总算活下来了。十一二岁时就独自住在当年佣人住过的、又堆了许多杂物的不足十平的小东屋里。直到1959年初从密云水库的工地上悄悄当了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光荣的义务兵。如今,每月也能从国家领到40元的优恤钱了。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带着母亲从支边的西藏回到家乡,无处可住,只得住进了当年的小东屋里。随着我们兄妹几人的陆续降生,小屋根本住不下,他们下狠心用当年在西藏工作时攒下的一点钱,又变卖了一些“贵重”物品,朝朋友借了些,凑足80元钱赎回了被老爷子赁给外人的那两间靠西侧的房子,我们一家才算有了一处稍显宽裕的住处。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明白,对于年收入百八十元的农民来说,上世纪60年代那有如天文数字一样的80元钱是怎样凑上的。
那是个清晨,夜色已经褪尽,浓浓的朝雾再也阻挡不住东升的日头,我们在渐退的朝雾中搬到了新家,实在也没什么可搬的。今后,向东30米走人家的院门出入已明显不行。于是,父母着手对旧房进行改造,在与屋门相对的南面又凿了一个南门,堵死冬天阴风呼啸的北窗后,新辟了两扇南窗。南房改成北房,在房东北拉上院墙与东院隔开,斩除门前丛生的荆棘杂草,一个没有墙垣的南向小院就这样形成了。虽然贫穷,总算是另立门户挑梁单过,一家六口人的日子便在艰难中向前爬行了。
屋里的陈设再简陋不过。西侧是占了多半间屋子的一张大炕,炕上一个破旧的纸箱子;北侧是烧柴的大灶台,中间是地炉和炉坑;南侧是两个墙柜和一张旧桌子;东面基本是空的,堆放杂物,东北角用铁丝在墙上固定了三块木板,放醋瓶、酱油瓶、刷牙缸之类的东西,东南角放了一个储水用的、每年冬天都要结冰的大水缸。有一年冬天,一只花蛇大概在屋顶待烦了,居然就从墙角的顶棚上溜下来,落在水缸的锅拍上。亏了有一个高粱秆编的大锅拍,要不,父母费力从六百多米外的井台挑来的一大缸水都要洗蛇了。
四
春天来了,我们在院中栽下了一棵脆枣树,在院南侧栽了一棵杨树和一棵槐树。大概是我們的日子太苦,富贵的槐树没有站住;杨树却长成了参天大树;枣树一天天长大,第三年就开始挂枣了,虽然没几个,却也成了饥饿年代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梦。像是急着要报答似的,连续几年,它结的枣一年比一年多,清甜的脆枣慰藉着我们的肠胃,也温暖着我们的心。可好景不长,大约七八年后的一个春天,它长出的叶子竟是黄的,也没有开花,入夏以后,叶子也一直卷着,舒展不开,我们才得出结论,“树疯了”——再不能结枣了!妈妈说是弟弟把它当成了饭笸箩,只要见了枣,就没命地摇,是给摇疯的。而我却以为,枣树的年纪不大,几年间就结了那么多枣,是过劳,生生累疯的。
随着我们兄妹四人年龄的增长,父母又将房北至北院那座大墙的空地压上两小间房子,摆了一张自制的弹簧大床分担大炕的压力。前院的院墙也垒上了,又用树条编了一个柴门,小院子严严实实。不大的房子配上不大的院子,我们这个6口之家一住就是15年。正是从这间老房子起步,我开始阅读中国历史。
上世纪70年代末,先是北院二爷爷家翻盖了旧房,一正两厢前后脚完成;接着是东院的老爷子家,三间旧南屋(含原来的门厅)翻盖成三间背北朝南的房子,前面都是一水的半墙半桩修玻璃。新房子虽没有旧房子气派了,毕竟是新的,透着新奇。只有我们家还守着古董般的旧房子直住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
当年那深宅大院仅存的、我们家那两间五十多岁的老房子一点一点被拆除了,竟这样潦潦草草,我的心在一点点收紧,再想做一次老宅的宅男而不能了。我想为这半百的老宅做一个祭奠般的告别,却已来不及。后来便幻想着会有一次隆重的弥补,可世间的一切又如何弥补呢!屋顶的石板一块块被拆下,顺着两根自制的滑竿滑下去,石板没了,房顶似乎只剩了头皮,光秃秃的很难看。接着,这难看也没有了,揭掉了破朽的荆条笆,露出许多夭折的花架和结实的檩条。拆除檩条最惊心动魄,两人从两头将房檩高高地抛起后扔在地上,以验证它的结实程度,不折不朽就可以继续使用。结果,十几根檩条没一根被摔断,连那房柁去了污垢后又继续使用了二十多年。代之而起的是两间新北房和作为配房的两小间东房。
繁华尽,风云灭。老宅所留的最后两间石板房烟消云散了,那是一个时代的最后终结,确切地说,是那个年代存世物的最后终结。其实, 自那座宽厚的横亘东西的大墙垒起,老宅的兴旺就结束了。
总把新桃换旧符。是规律,也是无奈。
世事沧桑,物非人非,原来的四合院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了。而记录这座大院历史的,只剩下爷辈们分家时又高又厚的、那座东西向的大墙,快一百岁了,仍巍然耸立在那里。
(标题书法:陈小平)
责任编辑 师力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