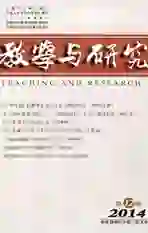生活的彰显或消逝?
2017-09-01徐志宏
徐志宏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生活;文化价值;异化劳动;实在界的荒芜
[摘要]“自媒体”是当代人生活经验的形象表征,要理解当下生活世界发生着的根本变化,极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本质的哲学思考。本文选取了颇具启示性的三大经验现象(“随身听”、“微信日常化”和“草根选秀”),借助海德格尔“文化价值”、马克思“异化劳动”以及齐泽克“实在界之荒芜”的视角加以审视,试图揭示“自媒体时代”生活之当代遭遇:首先被制作成文化,然后经历异化的深化,最后则在“彰显”的同时悄然“消逝”。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2-0032-07
仿佛是一夜之間,世界迈入了“互联网时代”;之后,用了更短的时间,又升级为“自媒体时代”。什么是“自媒体”?2003年7月,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发布了有关“We Media”(“自媒体”)的研究报告,对“We Media”下了一个严谨的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换言之,就是每个人都能用来发布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事件的载体。如今国内最常见的自媒体有博客、微博、微信、论坛/BBS等网络社区。
自媒体的出现意味深长。曾经以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等形式示人的传统媒体,曾经与平民百姓相距甚远、高不可攀乃至神秘神圣的媒体组织,曾经由“权威”自上而下发布或灌输给民众的媒体资讯,如今落向了民众个人,落向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换个角度讲,完全可以将自媒体时代理解为这样一个时代:个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了(或正在变成)“新闻发布”。几千年来一直沉默于幽暗区域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忽然被“照亮”了,登上了历史前台。对此,传媒工具的加速革新当然功不可没。如果说借助于个人计算机(PC),人们连接了互联网;那么,借助于智能手机,人们就成为了自媒体。如果说互联网让世界变成“平”的;那么,自媒体则让世界变成“我”的,当然,同时也让“我”变成世界的。
现代技术创新所具有的加速特点使自媒体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令理论越来越难以把握、驾驭甚至只是跟上它的变化。这一点,从各领域学者面对扑面而来的新奇案例所作的仓促应对中可以见到;而远不在少数的理论工作者,则不无恼怒地选择了避而不见。
笔者认为,首先,“自媒体时代”的名称并非哗众取宠,它的威力也不是个人只要拒绝使用智能手机就可抵挡的。其次,对于“自媒体时代”的种种生活经验的思考却远未达到哲学本质的深度。再次,海德格尔曾批判性提出的“文化价值”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可为本质性地理解“自媒体时代”的生活经验提供颇具启发性的视角;而齐泽克的诠释则完全可作为对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相关思想的当代补充和延伸。
一、当代人的“自媒体”生活经验
让我们先从生活世界的经验现象开始。为更好地深入“自媒体时代”生活之本质,笔者选取了以下三种紧密关联的经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经验一:“随身听”现象——为生活配上背景音乐。
“随身听”最早是日本索尼公司1979年发明的(“walkman"),是一种个人可随身携带的音乐播放器的通称,音乐载体从磁带、CD,变成现在的“数字”形式。这一事物早在“自媒体”出现之前就极为流行。但它成为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远非因其“可随身携带”以及形式上的越来越便利,倒是首先在于它的那副耳机和它播放的内容即音乐。在“苹果”牌随身听的广告中,那个戴着耳机随音乐扭动的黑色人影和长长的白色耳机线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可以成为某种意象性的存在。
耳机,隔绝个人与世界:戴上耳机,就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听到音乐,其他人无法听到,而我也不再听到外部世界的声音。所以,这副耳机为我营造了一个绝对个人的世界。用声音的方式,我过滤并隔离了世界,为自己建构起专属一己的世界。更要紧的是,这个声音非同寻常:它是音乐。生活世界是没有音乐的,只有自然界的声音,还有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噪音。而音乐则是人的创造,更准确地说,它是艺术家的创造,属于广义的“戏剧”,是“文化”的一个显眼的符号。
由于“随身听”的发明,人们忽然痴迷于听音乐了,而且是让音乐只为我一个人所听,只萦绕在我一个人的耳畔,这意味着什么?通常以为这无非表明了一种个人兴趣——对音乐的爱好罢了;甚至只不过是为了用一种美妙的乐音来隔绝外在噪音的干扰。这种解释显然不无道理,但若仅限于此则未免肤浅。为了更为深入探讨,在此我们不能忽略这种个人音乐的“随身携带性”。也就是说,因其便利性,我们完全不必再“专门地”只是在做“听音乐”这件事,或者,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如传统意义上的剧院,或家中)听音乐;相反,人们通常是边做其他事边听着音乐,或者,在从某地到某地的途中听音乐。这意味着,原本没有音乐的“生活”,现在有了音乐,而且它是生活的“背景音乐”。而“背景音乐”原来只存在于“戏剧”之中。由此可见,“随身听”使“生活”变得离“戏剧”更近了。在此意义上,痴迷于“随身听”意味深长,意味着我们正在改造我们的生活:为生活配乐,将其难以忍受的“粗糙”、“寂寞”乃至“丑陋”制作成“戏剧”或艺术品,即文化本身。由于音乐本身的神奇魅力,这一切只要借助于一副耳机就能实现,这便是“随身听”能如此盛行不衰以致成为公认的文化现象的原因。
经验二:“微信日常化”现象——将生活做成“作品”发布。
“微信”当下大有后来者居上,取代“微博”与“博客”之势。它正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成为日常生活极其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申请一个“微信”号码,进而拥有“朋友圈”,在圈中发布任何信息。和在“随身听”现象中人们主要以音乐改造生活不同,这一现象更关乎文字与图像,目前看来也更易令用户上瘾。智能手机越来越齐全的功能为其流行提供了极大便利。现在的智能手机除了摄影、摄像和自拍功能,还能下载各种美图软件,为用户即刻间制作出具有心仪的风格和效果的照片。有了令人迷醉的图像,再配上文字说明;或者,将生活的点滴落于文字,再配以契合的图像,就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生活的作品——发布到“朋友圈”了。朋友们见到我们精心制作的“生活作品”,通常会纷纷“点赞”和评论;而那一刻,我们就收获了莫大的价值感。endprint
就像生活世界本无音乐一样,文字和图像原来也是艺术家的创造,属于高尚而遥远的文化元素。在传统媒体时代,在纸质媒体还占绝对主流的时期,人们经常幻想当自己的文字被铅印出来,出现在报端或书本之际,自己会有多么激动。为什么?因为公开发表的文字与图像仿佛具有神奇功效,能令人晕眩,如同舞台上的聚光灯一般,令人产生不朽的错觉。
今天,当代人都正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变成一个“自媒体”。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沉浸在那种晕眩之中,不朽的错觉更真实了。所以,人们很快就迷上了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边生活,一边拍摄、描述,一边将此图文并茂的“生活”之艺術品上传、公布。由此,我们沉迷于改造和制作生活,并欣喜于让生活五彩纷呈地“彰显”。
经验三:“草根选秀”现象——“我”就是偶像!
在自媒体时代,“秀”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词。这个“秀”,除了是对英语“show”一词的音译;也含有其在汉语中“突出、出色、美好”的意思;更有英语“show”的“展现”乃至“炫耀”之意。所以,现在电视比赛都叫做“选秀”。这特别表达了一种当代主流的个人价值观——“我”就是偶像!如果我优秀,那么,我一定要将此优秀给“秀”出来,或“彰显”出来,让所有人都看到。
在诸多选秀节目中,各种“草根选秀”节目正在主宰电视荧屏。从最早的歌唱类选秀(如今依然还是最多,这与音乐的特性相关,这一点耐人寻味),到舞蹈类、演讲类、知识类、竞技类等项目选秀,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这类比赛节目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的舞台为所有平民草根而设。由大量这类选秀节目在电视屏幕上的公开播放营造出了一个颇为鼓舞民心的时代讯息:在今天,只要你有一技之长(甚至没有一技之长也行),只要你敢于参赛,敢于在电视上露面,那么,你总能找到那个适合你的舞台(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而是真实的舞台),甚至一夜成名,变成明星。
此外,在这个“草根舞台”上,最令人瞩目的还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关乎“梦想”,就是那个也许已成经典的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问题如今属于所有种类比赛中的评委必问之题。但是,由于它的必问性乃至“逼问性”,使“梦想”这个原本还是个人性或偶然性的东西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和必然性;并且,这种对“理所当然”的营造霸道地遮蔽了这个问题可疑的合法性。最终,它源源不断地向着舞台上以及电视机前的每个人传递着这样一条“绝对命令”:你必须有梦想!人怎么可以没有梦想呢?!就此而言,这个“草根舞台”完全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梦想舞台”——一个可以一窥现代人“梦想”及梦想方式的场所。其间隐匿的强制性完全被遮蔽在五光十色的魅惑之中。
第二件事关乎“故事”,即每个选手必须要有“故事”方可能获胜。除了舞台上的精彩表现,还必须有能够像“故事”那般打动评委和观众的生活——它应该或者是悲惨的,或者是励志的,或者是离奇的……当这个要求越来越成为参赛者和评委彼此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时,人们就不难理解如下“怪”事了:生活的不如意遭遇成了最大的资本;生活的平淡、顺利成了先天的缺陷,需要找到独特视角的诠释方能示人;人人都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故事化”处理,甚至杜撰造假。这件事跟被逼问的“梦想”问题一样,令每个人都开始重新思考、理解并“处理”自己的生活。
从“自媒体时代”的这些生活经验中可以清楚地发现,生活以及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与欲望正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生活正在被迅速戏剧化,从而被日益“彰显”为某种快速消费的文化作品。
二、“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
上述三种当代现象或经验都具有不同于以往生活的、独具特色的核心因素:背景音乐;“我”的文字,“我”的画面;属于“我”的舞台,舞台上的聚光灯和麦克风,舞台下的镜头,“我”的“梦想”,“我”的“故事”——这些因素都曾是远离粗糙生活(尤其是平民生活)的文化元素,而今却统统成了生活本身的可能性。甚至,这种可能性闪耀得如此之近,如此诱人,从而成为完全现实的生活目标,令生活的非“文化”维度(生活的原始属性)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
我们时代的这一现象,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的笔下,已有所预示。海德格尔把它表述为:“一切行为和活动被理解为文化”,“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此事如此重大,以至于海德格尔在当时就已将其界定为“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那么,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将一切活动都理解和贯彻为文化呢?海德格尔认为,根本原因是这片“大地”上的“精神”遗落了,于是“精神”被歪曲为“智能”和“文化”;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存在”的遗忘,被遗忘的“存在”则要求在“价值”中得到弥补。最终,文化被理解为一种最具精神意味的价值,亦即最高价值。在这里,海德格尔敏锐地揭示出现代发生的两个根本变化:一是对“价值”的追求成为至关紧要之事,亦即人必须是一种有“价值”的存在者,必须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过程;二是文化成为一种最高的价值表现形式。所以,此种文化又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文化价值”。
本文所选取的经验现象印证了这一点。在“随身听”音乐的衬托下进行的活动,哪怕只是默默地走路,默默地坐在公交车上、地铁车厢里,都具有文化的色彩——音乐激荡起心灵的波动,令它产生各种细致入微的情感,这种情感与生活中的情绪反应不同,相当于把此情此景转换为电影镜头之后产生的观感,所以本质上属于文化创造的范畴。“随身听”的魅力恰在于它运用音乐对情感的影响力,使人脱离生活并把生活对象化,将原本粗陋的生活在想象的内空间当中转变成唯美的电影镜头,而戴着耳机默默行动的“我”,则是镜头中的主角。这是一个小人物主角(也许惟有小人物才特别渴望当主角),但是,只要通过想象的镜头成为主角,生活即刻就被赋予一种“文化价值”。也许,音乐的瞬时流逝性注定了由“随身听”营造的文化价值的虚幻性,但那虚幻是被真实感受到的情境。与之对照,智能手机和选秀舞台之所以有着更大魅惑力,很可能在于其真实可见(而非想象中)的镜头。这镜头曾经为摄影师所专用,也曾是画家手中的画笔;而镜头中、画布上,曾经是明星和贵族被设计好的造型。如今,镜头在“我”手,镜头对准的是“我”的“生活”。如此被记录的生活,具有文化价值,令人觉得平凡普通的小人物生活也美丽起来,可欣赏了,值得过了。endprint
可见,在对生活的文化性改造和制作中,既表现了人们对文化的价值性理解,更蕴含着人们对自我价值的渴求。据此,我们可将“自媒体”生活理解为对“追求自我,实现价值”的渴求。
以前,人们在彼岸的“超感性世界”(天国或理念的世界)寄托价值与意义,此世的生活因而只有有限的意义,总体上属于蒙昧幽暗的区域,仅被理解为工具或过渡。但自近代以来,科学实证主义和资本主义确立了此岸世界的绝对权威,价值和意义落到了每一个作为个体的“我”和“我”此世的“生活”之上。这意味着现代人只剩一个“此世”的维度,但他不能仅仅是“生活着”;他要把生活和生命理解为自觉的生产、创造过程,以此来实现其最高的自我价值。海德格尔认为,根据这一逻辑,才会出现资本主义永远停不下来的创新和“生产主义”。所以,他最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恰恰主张人的本质是自我的生产。
那么,以“自媒体”形式呈现的、当代人对生活的“彰显”或文化改造,究竟是不是暗合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呢?
三、“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马克思反对依赖于任何他者来理解人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乃是由人自身的生产(或劳动)所创造的。而今天的人们借助科技手段越来越习惯于将生活“制作”成“文化作品”,以此赋予生活以意义,这是不是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人之本质的“创造”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来回顾一下马克思语境中的劳动、生产与创造。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因为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人是其劳动造就的。他曾明言:“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而且,他所说的活动并非抽象的、不痛不痒的任何活动,而是特属于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的活动,是一种革命性的实践。
理解這种劳动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对照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之所以受到马克思的猛烈批判,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颠倒了劳动对于人的本质意义——人的本质本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而异化劳动却因完全偏离和扭曲了真正的劳动,导致生产出完全扭曲和异化的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变成“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马克思在这一论断中所揭示的乃是问题之实质:工人(劳动者)的生活被鲜明地分成两块内容,一块是异化劳动(劳动本该属人,却令人感同牲畜,避之如避瘟疫般唯恐不及),另一块是难得的休闲时光(吃喝、性,本是自然,却是唯一令人觉得像人的活动)。无论如何,这两块生活内容的边界是清晰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工人心目中善与恶的属性也是明确的。但马克思作此论断的意图显然不是要将二者颠倒过来,将吃喝、性、休闲定义为生活的手段,而将劳动定义为生活的目的。毋宁说,他的批判含有两个维度:其一,生活分裂;其二,性质颠倒。当然,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无非由异化劳动生产出来。所以,他始终只强调劳动或生产并非要宣扬一种“生产主义”,而是要从源头上消除生活的分裂,以及被分裂的两部分本质上同样的异化。
依据马克思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对当代生活有更好的领会。从表面上看,人们工作、劳动时的状况和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以至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显得似乎已然过时。但是,若就生活依然被分裂为互相矛盾的工作-休闲,而所谓文化价值的追求依然只能在“休闲”上做文章(使之成为对毫无价值感可言的工作部分的弥补和逃避)的话,情况又如何呢?存在着本质的变化吗?如果今天的世界本质上还不得不被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所统摄的话,那么,我们所推崇的创造和文化价值究竟是真的完成着人的本质,还是“异化”的当代变型与纵深化发展呢?答案不言自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洞见是一致的:马克思预见的异化之极致,便是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学的完成。换言之,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文化价值”让我们懂得生活的“彰显”其实就是将生活制作成文化,其本质却是形而上学的完成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则使我们明白这种对生活的“彰显”其实只是将异化引向极致。而形而上学的完成和异化的极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四、“最大的输家是生活本身”
形而上学的完成和异化的极致,在所谓“当代最危险的哲学家”齐泽克看来,意味着生活本身成了“最大的输家”。当代众多哲学家认为尼采的一大功绩在于他发现了人的“身体”,宣告“一切从身体出发”,“重估一切价值”(内含有提高“身体”之价值的逻辑),较之马克思的“感性”更具体,较之笛卡尔的“我思”则更尘世化,是“我”之伸张的进一步完成。但是,齐泽克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大张旗鼓地张扬生活,反对一切超验性事业(transcendent causes),那么最大的输家则是生活本身”。所以,尼采的伸张构成了一个“尼采式的悖论”。
齐泽克所谓“大张旗鼓地张扬生活”,就是本文聚焦的“自媒体”式生活——令生活尽量地暴露在以“镜头”为象征的第三只眼的注视下,从而将生活尽可能地美化成文化制品,使“生活本身”具有价值,使作为生活主人的“我”具有价值。这种价值感,进而甚至令人产生“不朽”的幻觉和对“不朽”的欲望。随时随地地发布微信,草根舞台上的明星梦……这个时代的科技发展看来无不是为世界变成“我”的和“我”变成世界的而服务的。曾经只为极少数“英雄”享有的“不朽”待遇,今日正在向每一个“我”召唤!人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从牛顿的苹果夷平了彼岸与此岸的等级,到乔布斯的“苹果”夷平了人与人的等级,科技为人类带来了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的福音。
既然如此,为什么断言“最大的输家则是生活本身”呢?“生活本身”究竟有什么可被输掉的呢?
这就不得不涉及“生活是什么”这个问题了。但我们还是首先来看生活被价值所“照亮”的形而上学乃至消费主义内涵——它意味着“概念化”(形而上学的方式)和“商品化”(消费主义的方式)向着生活无孔不入地覆盖和渗透。生活被再现为文化,必须以生活的概念化和商品化为中介方能完成;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实体世界的消融。离开了实体世界的牵引,价值就滑向符号了,在消费世界中,它则表现为不断变换的时尚。变成文化的生活只有“风格”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原始部落穷困而自然的生活和大都市繁荣却抑郁的生活之间,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什么都行,什么都好,导致了追逐的无止境,变幻的无止境,以及确实的价值判断的不可能。所以,从追求“价值”和“文化”出发,最终竟变成“价值”是不可能的(因其不确定),只能把“追求”本身理解为绝对价值——亦即永不停顿,不断创造,不断出新。endprint
齐泽克借用电影《黑客帝国》(Matrix)的台词“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当代历事,即生活世界这个实在界正在日渐荒芜,乃至消逝。现在,我们可以大致地说说“生活”是什么——它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大地”,马克思的“感性活动”,齐泽克的“实在界”。这些术语共同表达的核心维度则是前概念的生活世界。
西方哲学在当代有一个重大的转向,就是朝着这个维度的转向——马克思坚持改造世界的实践,尼采强调回到身体,胡塞尔主张生活世界,其实都是为了挽救在形而上学上走人末途的哲学。然而,吊诡的是,所有这些来自实在界的拯救者(实践、身体、生活世界),都被概念化、符号化、价值化,一言以蔽之,又被形而上学吞噬了。
“自媒体”和“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生活世界、个人的隐私世界非但没能成为“超感性世界”破灭后施行“拯救”的那个场所;反而,因为某种神秘力量的推动,生活与个人也在一种“向自然回归”的假象中一并被形而上学化了。人们一次一次地“投身于”某种“真正的生活”(自然风景区的度假,关爱身体,修养心灵……),又一次一次地发现它只是被制造出来的概念和消费品。最后,人们只能陷入困惑与绝望:什么是“真实”?有没有“真实”?我在追求的那个独一无二的“我”,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吗?更令人沮丧的是这样的疑问:真的是“我自己”在追求吗?
这件事意味著,在哲学尚未走出困境之际,生活世界却已走上形而上学之路:追求不朽的文化价值。因此,这个高扬生活、彰显生活的时代,骨子里竟是前所未有大规模的形而上学时代,人人形而上学的时代,从而也是形而上学彻底完成、从而导致生活悄然消逝的时代。
借助于海德格尔、马克思与齐泽克的视角,我们在自媒体生活“追求自我、实现价值”的表象下看到了隐藏的危险:生活世界和自然界一样,正在疾速消失。由符号的无限性而引发的怀疑主义,原来只是哲学和哲学家才有机会染上的病症,现在,每个人都存在罹患此病的风险了。唯因如此,由美国好莱坞塑造的人物阿甘——一个脑子傻傻的,却不断投身于“做”的人——才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全民偶像。而且,生活世界的消逝(即形而上学化)速度,由于网络、技术和资本的推动,是以往哲学望尘莫及、难以想象的。
那么,还有出路吗?或者更乐观一点问:出路何在?马克思曾把希望寄托在异化与异化扬弃的辩证统一上。海德格尔给出的建议是反价值而思,即反形而上学而思,从而守护存在。而齐泽克则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集体性(collectiVity),即共同地、完全地投身于实践,取消那造成无限倒退的“第三只眼”的注视。
这大致就是当代哲学去形而上学化的一条可能路径:从追求形而上学的真理,到厌倦形而上学,回到生活,回到大地,回到身体,回到沉重、劳累以及气喘吁吁的生动知觉,乃至回到沉默。这时,也只有这时,自媒体时代各种价值展示与文化现象所激发的众生喧哗才会变得愈发令人沉思:生活不同寻常的“彰显”会不会恰恰意味着生活本身的“消逝”?
[责任编辑 孔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