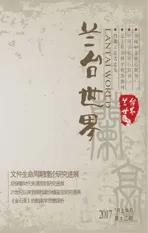后保管时代来源原则研究进展
2017-08-08张晨文
陈 洁 张晨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后保管时代来源原则研究进展
陈 洁 张晨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来源原则是档案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在后保管时代,来源原则面临新的挑战,具有新的内涵。文献调查表明,中外学者对后保管时代来源原则的研究聚集于:对来源原则中的“来源”进行重新定义、对不同来源档案整体分类研究、国家档案全宗在新时期的适用性、来源原则在档案鉴定中的综合应用、来源原则在保证电子文件凭证性方面的应用以及来源原则在档案信息系统中的应用。学者们积极探索、乐于交流,但是借鉴有余、创新不足,重视理论、疏于实践。
后保管时代 来源原则 全宗 档案
来源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从最初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到德国的登记室原则、荷兰的来源原则,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才成为比较系统的档案学特色理论。德国档案学家布伦内克所提出的自由来源原则,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所提出的双重来源原则,苏联的全宗理论等对传统的来源原则作出了修正和发展,丰富了来源原则的内涵。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档案工作全面进入后保管时代。“后保管”(post-custodial)这一术语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74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第38届年会上,协会主席F·杰拉尔德·汉姆(F.Gerald Ham)的《档案边缘》一文中提出“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文件数量剧增、信息缺失、文件易逝和技术进步,档案工作者应改变旧观念,投入智力资源,进行合作,积极主动地参与文件鉴定和档案接收,使档案工作不再是随着编史工作风气变化的‘风向标’,档案不再只反映狭隘的研究兴趣,而能真正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边缘’)”[1],后保管的思想初次萌发。1981年,F·杰拉尔德·汉姆在《后保管时代的档案战略》一文中指出,社会记录、存储和使用信息的方式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及其对档案的影响,这些变化使得档案工作进入后保管时代[2]。当时电子文件的数量开始大幅增长,使用计算机技术处理档案文件也越来越普及。于是在档案文件的管理过程中,档案信息与其载体的关联性被大大削弱了,档案工作人员往往更注重档案文件内容,对文件间的来源联系的重视性相对也就有所减少,因此许多人对来源原则在新时期的实用性提出了质疑。针对来源原则所面临的应用困境,1986年,美国电子文件管理专家理查德·莱特(Richard Lytleand)和戴维·比尔曼(David Bearman)以《来源原则的力量》一文一反既往档案界对来源原则的批判论调,并重申了来源原则的意义[3]。
后来,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 Cook)更深入地阐述了“后保管时代”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并在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所做的《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主报告中,将其与电子文件联系起来,强调了文件来源的重要性[4]。在此次大会上,意大利档案学者A·穆勒表示,尽管来源原则不是万能公式,并不能解决档案管理中的所有问题,但却能为我们指明努力的方向[5]。自此,国内外对来源原则的重新发掘和讨论达到新的高峰。
一、文献统计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来源原则理论在后保管时代的研究概况,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 和 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Abstracts(LISA)数据库进行检索,统计了不同年度研究来源原则的论文数量。在中国知网中以“来源原则”为检索词在主题字段中进行检索,再以“全宗”为检索词在篇名字段中进行检索,将学科范围限定为档案及博物馆。综合检索结果,剔除不相关和重复的论文,共检索到1250篇论文,所检索出的论文数量按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在LISA中以“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为检索词,同样进行人工筛选,最后得到71篇论文,所检索出的论文数量按年度分布如图2所示。
总体而言,档案学界对来源原则的研究开始较早,不同时期研究热度不同,但在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前后,国内外相关文章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近年来逐渐趋于稳定。在对来源原则的研究中,多篇文章都将其与电子文件、档案管理以及档案学其他基础理论等概念联系起来。经过对论文具体内容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后保管时代关于来源原则研究的主要主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来源原则在理论层面上的分析,二是对来源原则在应用层面上的分析,如表1所示。
二、主要研究成果
1.概念来源与广义来源。最初,来源原则中的“来源”一词是指档案的形成者。后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活动的复杂性使得机关单位间联系日益紧密,同一项工作往往涉及多个组织和部门,传统“实体来源”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于是“概念来源”应运而生。首次提出“概念来源”的是特里·库克,他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指出,来源一词不应限定在实体机构上,而应当还包括文件形成的目的、过程、活动、形成者职能及其他抽象来源等,这类来源存在变动性、复杂性,甚至虚拟性,不同于“实体来源”,而应当归属于“概念来源”[4]。同一时期,何嘉荪也提出“广义来源”的思想,他认为来源原则的实质便是要坚持维护档案形成全过程中的有机联系,这一联系指的是“来源于同一社会活动过程之间的联系”,它既包含狭义的来源联系,又与狭义的事由联系相吻合和统一[6]。

图1: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文章数量的年度分布

图2:LISA数据库中文章数量的年度分布

表1:后保管时代来源原则的研究主题
将中外学者对来源的重新定义对比来看,不难发现不论是“概念来源”还是“广义来源”,都并没有脱离来源原则的基本精神,而是扩大了传统“来源”的外延,两种观点不谋而合。稍有不同的是前者更为抽象,强调来源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而后者则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更为紧密,定义的界限更为清楚,实用性更强。“来源”的重新定义对于打破传统来源观给现代档案管理实践构建的壁垒有着重要意义,有利于我们在后保管时代建设出全新的档案管理体系。
2.主客体全宗理论。全宗是指一个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形成的具有有机联系的档案整体[7],是对来源原则的具象延伸。后保管时代的到来模糊了档案来源,于是何嘉荪、冯惠玲基于来源原则,从人类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多样化来源的档案进行规范划分和针对性管理的相关理论,统称为主客体全宗理论。社会实践的主体指的是从事社会活动的主导者,即主动开展实践活动的法人或自然人,而对应的客体则是指人类活动的对象,既可以是自然物体、社会事务,也可以是人或者组织[8]。因此,以实践主体为核心而形成的档案全宗为主体全宗,以实践客体为核心所形成的档案全宗为客体全宗。为便于理解,两位学者将主体全宗的形成和组建核心称为立档单位,客体全宗的核心则称为立档单元。他们还指出具备立档单位和立档单元条件并不就等于构成一个全宗,还需要把“便于保管利用”作为衡量标准[9]。唐振华认为,档案汇集、联合全宗等作为传统全宗的补充形式,汇集的档案间必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联系或逻辑联系,即可理解为客体全宗[10]。
虽然国外未有主客体全宗的概念,但是也已有类似的理论。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藏主要分为“文件组合”(Record Group)和“合集”(Collections)[11],文件组合指的是政府部门或独立组织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材料组合,而合集则主要指以特定的人、事务或组织等对象为分类基础而形成的档案整体。所以,我们可以将文件组合看做主体全宗,而将合集看做客体全宗。主客体全宗、文件组合和合集的要义基本相通,美国国家档案馆也明确指出文件组合和合集的组织都基于来源原则的核心内涵[12]。
基于此类定义,潘连根从哲学的层面上对主客体全宗发散出了新的思考。哲学中的主体概念可以分为人类主体、社会主体、集团主体和个人主体,但并非每一个主体均可成为全宗的构成者,人类主体作为最宽泛的主体概念,并不适用与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档案管理活动。其他三者对应到主体全宗上,分别为社会主体全宗、集团主体全宗和个人主体全宗。在社会主义国家,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益趋于一致,国家可以对个人和集体的档案进行统一管理,形成国家档案全宗。而客体概念可以分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三者分别属于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精神文化实践的改造对象,在实践中形成以客体为核心的档案整体则为对应客体全宗[13]。档案学理论与哲学思想融合后形成主客体全宗的具体分类,便于档案工作中更好地把握不同档案整体间的区别和联系,因档制宜。
主客体全宗理论实际上是对来源原则的具体延伸,与“概念来源”和“广义来源”相比,它将来源原则落实到了具体工作实践中,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3.国家档案全宗。“国家档案全宗”最初指的是国家全部档案,核心思想是把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档案来源,国家所有的一切档案均为国家档案全宗的组成部分。国家档案全宗引进于苏联,曾在我国档案学界内得到较高的评价。但进入后保管时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表述国家全部档案时使用的是“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档案”,并未提及国家档案全宗,俄罗斯也在苏联解体后弃用国家档案全宗这一概念,并改用为俄罗斯联邦全宗[14],因此引发学者们对国家档案全宗的深度思考。
不同学者对国家档案全宗这一概念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争论的焦点是国家档案全宗是否等于国家全部档案,在新的时期是否已过时,不再适用于档案实践工作。具体而言,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定国家档案全宗不应该再存在。例如,张辑哲认为,全宗原本是内涵外延均很确定的科学概念,而国家档案全宗这一概念的使用则打破了全宗的外延界限,违反了基本的科学规则,故认为国家全部档案不能称为全宗[15]。黄存勋也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代,继续使用国家档案全宗这一概念不利于档案行政改革,也不利于档案学的创新与发展,早已不合时宜[16]。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胡燕[17]等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家档案全宗在新时期有其局限性,对其进行补充修正仍适用于现代档案工作。吴宝康提出对于国家档案全宗这一概念需要辩证看待,定义也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的国家档案全宗指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广义上则指在我国国土上的所有单位以及我国所辖的国外单位,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无论是哪种所有制形式(外资企业除外),都属于国家档案全宗[18]。丁华东提出“主权国家档案全宗”的概念,作为国家档案全宗的拓展,既继承了其基本内涵,又能解决学界争论的主要问题[19]。另外,黄新苏、冯兢、翟素萍、杨晓南等也支持国家全宗概念需要发展和完善,但不能完全摒弃[20]。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国家档案全宗的基本内涵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没有必要再去完善和修改。持这一观点的王茂跃先后著文数篇,对多种观点进行分析和驳论,最后提出,虽然我国档案所有权已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但是国家档案全宗概念的适用范围并非一成不变,只要党和国家机关仍存在档案,国家档案全宗便可一直存在下去[21]。
然而随着档案实践工作的发展,国家档案全宗淡出档案理论界是大势所趋,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档案资源。傅华将其定义为过去和现在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产生的具有国家和社会保存价值的档案,即需要由国家管理的全部档案资源[22],学界研究的关注点也进而转移到档案资源的信息性、资源性和集成性上。这是对国家档案全宗的部分继承和延伸创新。虽然国家档案资源并未直接指明其来源,其含义却仍体现了国家档案内部存在的有机联系,也更适用于后保管时代档案资源管理工作实践。
4.来源鉴定。档案价值鉴定一直就是档案工作的难点。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而当其与来源原则联系起来后,才真正步入正轨。来源鉴定作为来源原则在档案鉴定领域的推广应用,伴随着来源原则的创新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也在不断完善,先后出现“年龄鉴定论”“职能鉴定论”“利用决定论”“社会分析法”等观点。
进入后保管时代后,各类型的档案数量日益增多,档案价值鉴定标准的确立尤显迫切。随着来源原则的重新发现,应用来源原则新内涵的鉴定方法体系也日益丰富起来,来源鉴定成为后保管时代最具有实际意义的档案价值鉴定手段,被国内外档案界积极研究和倡导。最先是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提出“新宏观鉴定”,它是以职能鉴定论为基础,以新来源原则为指导,鉴定方法是以文件前后关系为基础,处于以来源为中心的框架之中,而并非处于以内容为基础的历史文献框架中[4],来源鉴定也因此变得更为抽象和复杂。后来,特里·库克在探讨档案鉴定的前世今生时,再次指出需要根据不同来源来确定档案的价值,并且需要兼顾来源的广泛性,有选择地保留下某些特定群体形成的档案文件[23]。而关于来源鉴定的具体特点,贺佳指出,来源鉴定的首要特点便是宏观性,鉴定对象从单份文件变为文件来源,提升了档案鉴定的可操作性、标准性和全面性;其他两个特点是系统性和超前性,为提升档案鉴定工作效率和水平提供了保障[24]。
档案从产生到销毁需要经过多重鉴定,来源鉴定也就在实践工作中被应用到了档案鉴定的多个环节。晋平指出,在归档鉴定中需要坚持“内宽外严”,以我为主,确保机构内所藏档案能全面反映本机构的历史原貌和自身特色;并且对归档文件的鉴定需要在文件运行阶段就开始,体现来源鉴定的超前性。对于已确定归档的文件,在判定其保管期限时则要联系立档单位的内部结构和职能活动,坚持主次分明、“内长外短”的准则。接着在选择进馆档案时,也要格外注意档案全宗的完整性,同时要坚持“内外有别”,精炼馆藏。最后在进行期满鉴定时,以全宗为鉴定单位,将待销毁档案按内外来源分类造册,“重内轻外”[25]。
5.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的数量在后保管时代呈现指数型的增长。不同于传统纸质文件,电子文件的形成往往涉及多个机构、部门和人员,整个管理过程中也具有很强的动态性,传统来源观已无法指导现代电子文件的管理,取而代之的新来源观承担起了关键的指导作用。电子文件管理的方方面面均离不开来源原则,在此以确保电子文件的凭证作用为例来具体阐述。
一直以来,文件构成三要素论在档案学界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它将文件的构成要素定为内容、背景和结构。李曙光认为,文件的背景信息也就是文件的来源信息,包含文件的形成者、形成目的、形成过程等综合背景信息[26]。传统纸质载体文件本身就包含了其背景信息,而电子文件信息是由二进制编码的电磁信号构成,其内容信息和其背景信息往往是分离开的,而且电子文件信息还可以轻易地被复制到任何适应的载体上。因此在电子文件管理过程中,一旦背景信息被损坏或丢失,那么该电子文件便失去了凭证性。美国天主教大学简·张(Jane Zhang)也探讨了来源原则在保证电子文件内容真实再现方面的重要意义[27]。至此,就可以理解背景为何会被设定为构成文件的要素,而何嘉荪等学者又为何会称此举为“承继传统档案学基本理论精华的创举”[28]。来源原则应用于保护电子文件凭证作用的意义不言而喻。后保管时代,电子文件管理活动中对元数据的研究和应用也正是基于利用来源信息保证电子文件凭证性这一原理所进行的。
6.档案信息系统。随着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机构建立起档案信息系统,档案管理自动化的时代正在到来。早在1994年,加拿大兰伯特·J(Lambert,J)就指出,档案管理自动化的趋势并不会淘汰来源原则,反而会对来源原则有更深刻的解读和更广泛的应用[29]。如今,细究各类系统工作运行原理,可发现无一不是基于来源原则的核心内涵。接下来以档案信息自动分类编目体系、档案信息检索系统为例,阐述档案信息系统对于来源原则的应用。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离不开前期的档案分类与编目。在档案信息系统中,首先需要将来源一致的档案信息嵌入到计算机档案模糊分类系统里面,之后才能依据主题词、关键词等进行标引和分类。然后在建立档案信息配置管理数据库时,还需要将各种相关的数据参数加以配置,如发文单位、责任者等。接下来要实现档案信息自动分类的功能则需基于来源原则,构建出合适的分类模型和编目参数,这样进入系统的档案信息便能通过比对匹配的方式确定类别、保管期限和档案号,最终完成档案信息规范的分类和编目[30]。特里·库克指出以来源为基础的信息检索相比起以内容为基础的检索,更注重文件形成的形式、功能和有机联系[4]。基于这种认识,加拿大开发了一套全国著录标注系统,这套系统以来源为中心,勾画了所有文件实体从总到分的多层次关系以及众多形成者的关系[26]。
对于已经进入档案信息系统内部的档案信息资源,则需要更多地考虑检索利用的问题。目前,档案信息资源的检索主要依赖档案信息数据库和检索系统,用户需要以档案信息检索系统为接口,输入检索目标的相关信息,如特定的关键字,然后档案信息检索系统才能根据要求到数据库中调取匹配用户需求的档案信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档案信息检索系统要如何保证输出的结果是符合用户要求的呢?又要如何对输出结果进行相关性的排序呢?这便要求档案信息检索系统能够基于来源原则,对已经科学序化和整理好的档案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判定,准确地计算出档案信息之间、档案信息与检索条件间的联系程度,兼顾查全率和查准率,从而保证最后检索的结果在具有有机联系的同时,也与用户需求相契合。典型应用范例有PLAIN(The Progetto Lombardo Archivi in Internet)项目。据意大利赛沃佳·毛里求斯(Savoja Maurizio)等介绍,这一项目由帕维亚大学和米兰档案馆合作进行,项目中产生的系统可以使用多种工具完成档案信息的集成检索,对于档案的收集者和创建者也设立了独立的检索列表,充分应用了来源原则[31]。美国网络档案信息检索系统ARC(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也很好地实现了以多种途径对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属各机构文件的查询检索。这些机构均有自己独立的网站,通过ARC实现了内容上的整合,用户可针对不同来源进行多样化的信息检索。虽然于2013年,ARC下线并被Online Public Access所取代[32],但它作为来源原则的典型应用,在网站档案信息检索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评价与展望
后保管时代的来临给来源原则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生机。来源原则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变化,也曾遭质疑和被否认,但由于其原始内涵的科学性和包容性,终究还是承受住实践工作发展造成的冲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在后保管时代对于来源原则的研究有三个特点。
1.积极探索,乐于交流。一直以来,中外档案界都在积极推动来源原则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进入后保管时代后,国内外档案学者对来源原则的理论和应用又进行了很多新的探索。总体而言,无论是从继承性方面,还是从创新性方面,表现都可圈可点。与此同时,原本一直以来沟通甚少的国内外档案界,随着后保管时代带来的社会实践变迁也开始有了更多联系,中国档案学界逐渐重视起国际上主要的档案学理论和思想。1996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此次大会上,中外档案学者进行了深度交流;此后,国内对来源原则的探索除了原有理论之外又有了新的方向。
2.借鉴有余,创新不足。国内档案学者积极地对外来理论进行研究和讨论,研究视野得到拓展。我国档案工作实践适应后保管时代,学习和借鉴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颇有裨益。与此同时,国内原创性的来源原则相关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然而在国际上却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力。究其缘由,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研究中过多地去追求理论的国际性,容易跟风去研究国外热点,关注于对已有理论的阐释,创新性不够,更鲜有突破性的应用实例,再加之在相关的国际会议论坛上听音较多、发声较少,自然不会引起足够的关注。
3.重视理论,疏于实践。国内外档案界对于来源原则的研究都兼顾了理论层面和应用层面,但是二者相较而言,理论研究要远远多于应用研究,直接结果就是理论水平要远远超出实践水平。这一问题在国内外都存在,在国内尤为明显。国外的应用研究多集中于电子文件自动化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网页归档等,而国内的应用研究重心另外也涉及来源鉴定、电子文件的来源凭证等。总体而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相对实际需求而言还是有很多不足,研究成果也存在可操作性差的问题。
笔者认为,后保管时代国内档案界研究的重点可以放在对新理论的创新性应用上,融合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和国外优秀经验,结合国内档案实践工作的特色和发展趋势,寻找出合适的创新点再加以突破。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档案界的对话,让中国的档案学理论有更多的话语权。最后借用丁华东的一句话:“有实力才会有魅力,从‘传声筒’到‘发声器’是学者的责任,更是学术共同体的责任。任重而道远!”[33]308-315
[1]杰拉尔德·汉姆,刘越南译.档案边缘[J].山西档案,1999(1).
[2]F.Gerald Ham.Archival strategies for the post-custodial era[J]. AMERICAN ARCHIVIST,1981,44(3).
[3]Bearman,David A;Lytle,Richard H.The power of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J].Archivaria 1986(21).
[4]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143-176.
[5]A·穆勒.来源原则:仍是本专业的基本原则吗.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93-205.
[6]何嘉荪.历史联系就是广义的来源联系[J].档案学研究,1998(2).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第5部分档案整理:DA/T1-2000[S/OL].[2017-3-11]http://www .saac.gov.cn/xxgk/site2/20150604/00e04ce0897016da317b01.pdf
[8]何嘉荪,冯惠玲.关于更新全宗概念的设想:全宗理论新探之三[J].档案学通讯,1988(6).
[9]何嘉荪,冯惠玲.划分全宗的原则:全宗理论新探之四[J].档案学通讯,1989(1).
[10]唐振华.档案全宗理论的发展探微[J].档案天地,2006(1).
[11]张翠平.客体全宗在综合档案馆的应用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14.
[12]Record Group Concept.[EB/OL][2017-03-11]https://www. archives.gov/research/guide-fed-records/index-numeric/concept.html
[13]潘连根.关于主客体全宗的哲学思考[J].档案学研究,1997(3).
[14]肖秋会.前苏联国家档案全宗的历史发展及演变[J].中国档案,2016(9).
[15]张辑哲.“国家档案全宗”概念质疑[J].档案工作,1992(8).
[16]黄存勋.国家档案全宗与档案行政改革问题初探:兼与王茂跃先生商榷[J].北京档案,1999(3).
[17]胡燕.关于全宗理论的再思考:兼与王茂跃先生等商榷[J].北京档案,2000(8).
[18]吴宝康.坚持和发展国家档案全宗概念[J].学校档案,1989(1).
[19]丁华东.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档案全宗理论[J].档案学通讯,1999(2).
[20]黄新苏,冯兢,翟素萍,杨晓南.也谈国家档案全宗概念的发展和完善论[J].兰台世界,2005(10).
[21]王茂跃.关于国家档案全宗概念的再思考[J].浙江档案,2003(4).
[22]傅华,冯惠玲.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5(5).
[23]Cook,Terry.‘We Are What We Keep;We Keep What We Are’:Archival Appraisal Past,Present and Future[J].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2011,32(2).
[24]贺佳.来源原则在档案鉴定中的应用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08.
[25]晋平.档案价值鉴定的来源原则及其应用[J].档案学通讯,2000(2).
[26]李曙光.论电子文件时代档案管理的核心原则——来源原则[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研究生论丛),2003(S1).
[27]Jane Zhang.Archiv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Digital Age[J].Journal of Archival Organization,2012,10(1).
[28]何嘉荪,史习人,章燕华.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简评文件构成要素论[J].档案学研究,2010(1).
[29]Lambert,J.Informatisation etprovenance.Computerization and provenance[J].Archives(Quebec),1994,26(1/2).
[30]齐菁.基于档案来源原则建立档案信息自动分类编目体系的思考[J].办公室业务,2012(3).
[31]Savoja,Maurizio;Weston,Paul Gabriele.Progetto Lombardo Archivi in INternet-PLAIN (Lombardy Project for Archives on the Internet):identification,retrieval,and display of creators of archives and of archival fonds[J].Cataloging&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004,39(1/2).
[32]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 is Retiring on August 15th.[EB/OL] [2017-03-11].https://narations.blogs.archives.gov/2013/07/15/archi val-research-catalog-is-retiring-on-august-15th
[33]丁华东,饶露.传声筒、话语权与中国特色[C].上海市第四届“‘3+1’档案论坛”论文集,2010.
Research Review on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in Post-custody Age
Chen Jie,Zhang Chenw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is one of the core theories of archival science.In post-custody age,it has faced new challenges and got new connotative meanings.Literature surveys show that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mainly focused their studies on the redefinition of provenance,the classification of archives from different provenances,the applicability of national archives fonds in the new era,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to archival appraisal,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 to ensuring the evidential quality of electronic records and to the archives information system.The scholars made active explorations and became more communicative.However,they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on reference with insufficient innovation.They put a high value on theories,but neglected practice.
post-custody age;the principle of provenance;fonds;archives
G270
A
2017-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