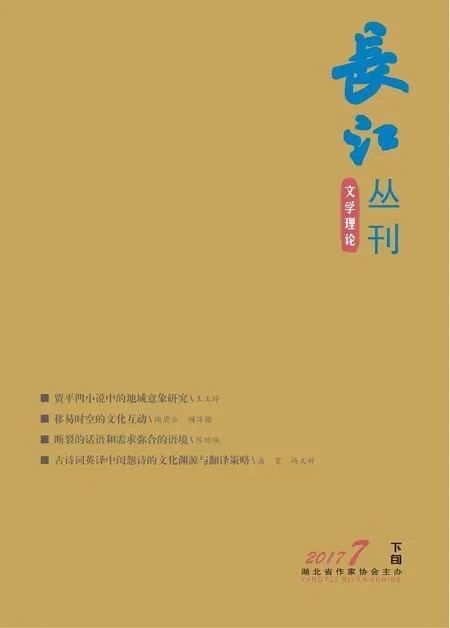鱼腥风
2017-08-07曹军庆
曹军庆
本期推介
鱼腥风
曹军庆
都说邱正义娶了一个石女,跟石头似的没缝隙,百毒不侵。刘秀梅一脸正气,不苟言笑,是县农机局机关里出了名的宅女。人们议论刘秀梅不是没有原因,她让人别扭。和她在一起会让你不自在,即使不在一起,一想到她也会让你牙疼似的吸气。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人,当然头疼。她不串门子,不扯是非,也没个相好。身上没有一点瑕疵的人,不说是怪物,至少也太奇怪了。这种人无法让人信赖,你会没理由地想要防着她,有那么一点点害怕她。她跟大家隔着,无法跟周围人打成一片。日子往下过着,她疏离了大家,大家也疏离了她。
人和人之间总还是要有点烟火气息,你不能过日子把烟火气息给过没了,把吃喝拉撒的生活过得像纸上的文字,像人们写下的阳春白雪的诗句。比如说吧,就说说刘秀梅机关里的那些事吧。那些事主要集中在男女方面,男女方面的事哪儿都有,明里暗里特别多。县城里有好些个局,各个局大小也算是机关。但是县城里的局机关不比大城市,也比不了上级机关,上面的事情不去说它,也说不明白,通常越是上面的事越要隐晦得多。县城不同,县城里哪怕身在局机关也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机关内部的人和外面、和老百姓、甚至和不三不四的人都有很深的瓜葛。谁有了相好,谁和谁在搞名堂,大家心里一清二楚。地方小,哪怕一点小事就会像蒲公英一样满城风传。人们热衷于八卦,热衷于把一些是是非非传来传去。在传递这些是非的过程中,既可以指证他者身上长出的脓疮,也可以扯扯衣摆遮盖住自己身上的溃烂处。这其实就是一个局,所有人都在局里,唯有刘秀梅不在局里面,她是个冷美人,事实上也是个局外人。
刘秀梅机关里的一把手是刘局长,刘局长的相好是个老师。老师颇有几分姿色,热爱音乐,因此她在教学之余开了一间歌厅。每天局里来了客人,酒醉饭饱之后刘局都要留下客人高歌一曲。这成了局里的惯例,办公室主任小李经常跟人介绍说,我们刘局擅长男高音,他唱得和戴玉强一样好。这时刘局就会摆一摆手,很内敛地说哪是!我那是瞎唱。话虽这么说,刘局还是一脸灿烂地笑。两个副局长一个姓何,一个姓王。何副局长的相好在开餐馆,局里要撑得住门面,来来往往的客人自然多。刘局长有句名言,他在局党组会上说,你家做得好,才会有人来。你家做不好,请人来人还不来呢。整日里你门口熙熙攘攘那才叫兴旺,机关和家里是一个理,如果你冷清得鬼都打不死一个那还叫个什么鬼局呀。何副局长分管机关,来了客人多半往他相好那里带。反正在别处是吃,在她那也是个吃。王副局长也有相好,他的相好开了个洗脚城。这下全了,基本上是一条龙服务。先吃饭,吃完饭去吼两嗓子,折腾累了再去洗洗脚捶捶背。一条龙都集中在班子成员身上,没别人事。都有规矩,能给相好好处人家才会跟着你。好处的多少跟权力大小有关,各负其责各安其位,心里都有数。
说完了几个局长,再说说小李。办公室主任小李也不是省油的灯,据说他的相好专卖文具用品。局里购买办公用品以及地方土特产啦礼品什么的都得找她。听说财务室的会计小黄和刘局也有一腿,都这么说,谁也没见到过。唯一的证据是每次歌厅的人来结账小黄都会拖拖拉拉,或者给来人脸色看。有时刘局长还要亲自做工作,关上财务室的门和小黄说上好一会儿。打开门小黄钱是付了,脸上却依稀有了泪痕。小黄把老师当作情敌,和她过不去。刘局身份不同,可以有几个相好,比较好理解。这些人还好说一点,嘴巴伸出栅栏外嚼几口青草好歹也还说得过去。有意思的是司机小马居然也有。小马的相好是中百超市的收银员,局里有时要开一些假发票充账,都是小马在跑。一来二去,就和收银员好上了。
在幸福县,刘秀梅所在的局是一个很边缘的小局。农机局,一听这名字你就明白,没多少职能,也没多少油水。可怎么说也还是一个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不缺吃不缺喝。大家的日子一样过得滋润,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相好,唯独刘秀梅没有。现在要在县城里混,稍有点身份的人,有点位置的人如果没有相好是说不过去的。人们会觉得你不是真的有身份,也不是真的有位置。时局在变,现在的时局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以前谁有相好,会被人戳脊梁骨。现在反过来了,谁没有相好尽管在表面上还是会被人尊敬,但是在别人心里人家会给你白眼,人家会贬低你。
刘秀梅长得漂亮,气质好。按理说红颜祸水红杏出墙,她的长相大概算得上是县城里最有风险的长相。说真的,打她主意的人也多。单就局里来说,刘局何局王局都先后暗示过她,或是曾经赤裸裸地追过她。但是刘秀梅不为所动,她要么是不明白,要么是即使明白了也从不回应。她身正不怕影子斜,谁也没能得逞。这种情况使得刘秀梅在农机局里无法进步。她在局机关里待了十大几年,连个科长也没混上。想想的确很微妙。刘秀梅在业务科宣传科稽查科全都干过,后来居然沦落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也不是做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只能做做后勤搞搞勤杂。比她晚来好多年的小李一步步升任办公室主任,成了她的领导。局长们在嘴上恭维刘秀梅,表彰她,说她为人实在,形象好,堪称单位里的形象大使。但在心里边呢,却又没人真把她当个事。刘秀梅被扔在角落里,变成农机局里可有可无的人。人们谈论谁是谁的相好,谈到刘秀梅这儿不得不戛然而止,你确实不知道能说她什么。
刘秀梅孤身一人,这真是很奇怪的一种说法,充满了悖论。因为刘秀梅有同事,也有丈夫和女儿,尽管事实是这样,她却仍然被所有人视作形单影只。她每天按时回家,不在外面吃饭,不参加应酬。她骑自行车,因为腿长的缘故,刘秀梅从不使用车把手上面的刹车。她只要两条长腿夹着车在地上一叉,就能稳稳地把车停住。刘秀梅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女儿小贝身上。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刘秀梅一直在陪读。她给小贝做饭,陪小贝写作业。这么多年来,小贝写过的每一道作业题,刘秀梅都陪她经历过。辅导她做,或是亲眼看着她做。
很多人在议论刘秀梅。对刘秀梅的议论在一开始更多是怜悯。人们认为刘秀梅的生活太刻板了,太无趣了。她除了上班就是孩子小贝。没有别的。没有像我们那样多姿多彩的风流,没有像我们那样在饭铺吃饭喝酒,也没有在酒店开房。但是时间长了,那种私底下的议论却在转向。好像刘秀梅不需要怜悯,相反需要怜悯的却是正在议论她的那些人。这种想法或是这样一种现实激怒了大家。于是刘秀梅成了众矢之的。她不仅被议论,同时也被排挤,被诽谤。在幸福县城里刘秀梅是著名的异己者,这位著名的异己者不同于正常人,她没有相好。问题是这些情况刘秀梅自己并不知道。她不知道她在被人议论,也不知道无意间她已经在危害别人了。和以往一样,刘秀梅目不斜视地走在大街上,她的作息时间和每天所做的事一成不变,一个年头又一个年头。
像刘秀梅这样活着,就是在危害别人。她像是扎在幸福县城里的的一根刺。很多人想要拔掉她,想要拔掉她的人多半是男人。或者换一种说法,刘秀梅就像是飘浮在人们头顶的一只鲜艳的气球,有那么多人梦想着能亲手刺破它。也或者说吧,刘秀梅就像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能从刘秀梅这里照见自己,因为不言自明的原因,每个在这里照见了自己的人都想捣碎这面镜子。
当然喽,刘秀梅又是一个天真的人。这很好理解,因为天真,刘秀梅又特别特别容易被欺骗。要欺骗她你不用费多少脑子。刘秀梅的丈夫邱正义也搞相好。他在发改局工作。跟刘秀梅的农机局比起来,发改局是大局。到处都要报项目,求他的人自然就多了。邱正义经常在宾馆酒店开房,有一次他还把相好带回家。那天他喝高了,跟相好说他要打个时间差。相好知道他老婆是个宅女,每天按时回来,因此有些害怕。邱正义坚持要这么弄,玩的就是心跳。他说我们掐着表来,这样更刺激。吃过中饭,远远地瞅着刘秀梅出门上班去了,他们便悄悄地溜回去。
在刘秀梅家里,两人折腾得很尽兴。四点多钟的时候相好先走了,邱正义留在后面收拾屋子。这时,刘秀梅却提前回来了。她在机关里哪怕没什么事做,也从不迟到早退。这天因为担心厨房里炖着汤,便提前了一个小时溜号。她进了小区,依稀看见一个女人从她屋里出门。这女人有些眼熟,又不能确定。两人擦肩而过,刘秀梅嗅到一股热乎乎的气息轻拂面庞。她想这女人脸好烫啊一定是刚喝过酒,或是刚哭过。但是她并没有多想,没有计较为什么会有个女人从她家里出来。或者她不认为她是从她屋里出来的,仅仅只是从她门口路过?刘秀梅推门进屋,她看见邱正义正在叠被子。
“你回来早了,”邱正义说,“还没下班呢。”
刘秀梅说,“我回来看看厨房里的汤。”她进了厨房,不一会又出来了,“汤水果真给得太少,锅底都快炖糊了。”
“亏你回来得及时,真糊了小贝就没得吃了。”
“你怎么会在家睡觉呢?”
邱正义说,“我酒喝高了,头疼,躲家里睡了半天。”
相好此时正好打电话来询问穿帮了没,她说我好像看到了你老婆,吓死人了啊。邱正义捂着话筒支支吾吾。接完电话,他却对刘秀梅谎称是单位打来的电话,要他赶紧过去处理事情。刘秀梅心平气和地说那你快去吧。一场危机算是无声无息地化解了,但是邱正义却从此落下病根,他觉得刘秀梅太容易蒙混过关了,要么她城府太深,要么她根本不在意自己。谁的老婆会像她这样蔑视自己的丈夫呢?他在刘秀梅面前变得缩头缩脑,打不起精神。她就是一垛棉花,就是一袋子面粉,你一拳打进去没用。你打一拳棉花试试,砸一拳面粉试试。
邱正义有个同学叫邓国恩,邓国恩是个花花公子,是幸福县城著名的骗子。说这个人是骗子,但他并不骗钱,也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只骗女人。其实也不是骗,按邓国恩的说法都是成年人,那叫“两厢情愿”。凡是被他骗过的女人,在事情过去了之后他都会讲出来。他愿意讲述他从前的风流韵事,别人也愿意听。因为邓国恩同时还是个诗人。他也有职业,他在当老师,和农机局一把手刘局的相好是同事。他和她在同一所学校教书。邓国恩曾经吹嘘说他早就搞过了刘局的相好,搞过之后又把她甩了,相好不得已又太绝望这才又投靠了刘局。虽然他的话没有人去追究,谁也不会花时间去追根溯源,但是听他这么说你就明白了,邓国恩是个胆大妄为的人。
邓国恩写诗,他是幸福县不太多的几个诗人中的一个。可是他公开说,他写诗无非是接近女性的借口。从什么时候起,他打定主意想勾搭刘秀梅。邓国恩擅长死缠烂打,如果能够得手,那将是县城里极有影响的一件事情。人们将看到,这个骄傲的女人终于沦陷在邓国恩手上了。
有一天,刘秀梅在中百超市购物,巧遇到了邓国恩。当时邱正义也在,他很少见地陪在刘秀梅身边。看到邓国恩,邱正义适时地为他们做了介绍。他说邓国恩是他同学,也是他朋友。刘秀梅瞟了一下,眼睛转到货物架上,她正在选购她平时习惯用的醋和酱油。邱正义又补了句,说邓国恩还是个诗人。
刘秀梅抿着嘴笑了一下说,“现在还有诗人?”
“有,”邓国恩赶紧说,“找机会我送你一本诗集。”
刘秀梅未置可否,只是微笑。她把醋和酱油从货物架上取下来,搁在购物篮里。
次日,邓国恩来到县农机局找刘秀梅。刘秀梅显然已经不记得他了,她的笑容略显僵硬冷淡,完全把他当成了陌生人。邓国恩心里有了一份凉意,但还是强打精神。他告诉刘秀梅昨天晚上在超市里他们见过面,邱正义当时还做过介绍。邓国恩尽量说得很有耐心,不过他小心地没有说到诗人和诗集这上面来。因为他还不太清楚,刘秀梅是否对诗这种东西有兴趣。经过邓国恩的点拨,刘秀梅一下子就记起来了。她跟他道歉,说看着面熟,可就是一下子有点蒙。接着,她问他这时过来有事吗,是不是送诗集来了?看来她还记得诗集,这不是坏事。没带诗集,邓国恩说这回来得匆忙,下回再带过来。那么你还有别的事吗?邓国恩心里想没事就不能来?当然他不能把这话说出口。他说这次来是为了乡下表哥的事,表哥想买一台联合收割机,他先过来打前站,咨询一下。刘秀梅说买联合收割机是好事,她可以带他到业务科去,建议他跟业务人员具体谈。但是邓国恩不愿意去业务科,他说现在哪里都一样,若是没有熟人根本就办不了事。所以他只想和刘秀梅谈。有关联合收割机的品牌、产地、性能和价格,邓国恩一一都问到了。刘秀梅回答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她拿来了纸质的资料,说你带回去看吧。
邓国恩一出农机局,就把手上的资料扔进了垃圾桶。见鬼去吧,联合收割机只是一个由头,是他接近刘秀梅的道具。事实上他没乡下表哥,也没人要买联合收割机。刚才那一通煞有介事的交谈,究其实竟然是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事由,邓国恩想想就觉得好笑。但刘秀梅却是认真的,邓国恩回忆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能确认她毫无防备。她不知道正在谈论的联合收割机,只是一个谎言和玩笑。看上去刘秀梅是那么的不老练和缺心眼,邓国恩因此对拿下这个女人渐渐有了信心。
接下来的几天,邓国恩每天都来农机局。他不厌其烦地询问联合收割机的各种情况,弄得他自己都成了联合收割机这方面的专家。实在没什么再好问了,人不能太死乞白赖吧,邓国恩只好给这事挽了一个结。他找理由说表哥的钱不够,买不了联合收割机,看来只能来年再买。刘秀梅表示她能理解,来年再买也行。这些天来老是麻烦刘秀梅,邓国恩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想请她出来聚一下,吃个饭或是喝个茶。也就是表示一下心意。为了不打草惊蛇,邓国恩试探性地说,他打算多叫几个朋友。但刘秀梅还是一口就拒绝了。她说她要回家给小贝做饭,小贝上大学之前,她不会在外面参加任何应酬。
看来请吃饭这一类太老套了,的确不起作用。邓国恩于是便把他的诗集送给了刘秀梅。他没钱印书,也没有谁资助他印书,他的诗集是个打印本。用A4纸打印出来,封面上的纸稍厚一点,也硬一点,颜色比内页稍暗。诗集的书名叫《鬼话》。
“为什么给你的诗集起这么一个书名?”
邓国恩说,“因为里面都是情诗。”
这下刘秀梅更好奇了,“既然是情诗,怎么就变成鬼话了?”
“我相信人不会有这种情感。”
“你的意思是,鬼才会有爱情。”刘秀梅特意看了邓国恩一眼。
“我这么认为。”
“真是鬼话。”
送过诗集,邓国恩又和刘秀梅交换了电话号码。彼此扫了对方的微信。刘秀梅还算配合,她把她的手机递给他,由着邓国恩去操作。看上去和普通人的交往没什么两样,不过就是礼节性的,但邓国恩在此埋下了伏笔。
邓国恩开始给刘秀梅发微信。他在微信里给她发送图片,有微笑的图片,握手的图片。继而又发拥抱的图片,发亲吻。刘秀梅都没理他。邓国恩有经验,他把微信当做药,对人对症要下不同的药。起初他给刘秀梅下温和的药,问候一下,闲扯一下。如果她回复了,再加大药力,给她下猛药。计划是这样子的,事情的发展也有正常的轨迹,但结果却很不尽如人意。或者说出现的结果,让邓国恩瞠目结舌。
对问候的微信,刘秀梅只要看到了,都会及时回复。邓国恩以为有了呼应,渐渐用上了猛药。可是刘秀梅不再回复了,有意思的是她居然还把这些微信直接给邱正义看。
刘秀梅把手机递给邱正义,“看看你结交的朋友。”
“怎么了,”邱正义说,“有问题吗?”
“你看看就知道了,看你朋友给我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微信。”
微信是邓国恩发来的,让邱正义意外的是刘秀梅这么坦然,真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啊。她没有震怒,也没有气急败坏,好像只是在怪罪邱正义交友不慎。
邓国恩在微信里说,“好想你。”
“我想你但是我不知道你想不想我。”
“我昨夜梦见你了。梦见你在我床上跳舞。你踩着我的脸舞蹈。舞着舞着,你的双脚陡然间变成了乳房。”
“你的头发缠着我。我在你网里。再也出不来了。”
到底是诗人。这类鬼话对一般的女人大概会有杀伤力吧。但刘秀梅偏就是一块石头,刀枪不入。
邱正义把手机还给刘秀梅,“这家伙在写诗。”
“真是鬼话诗,你呀这种朋友不交也罢。”
说着,刘秀梅随手把手机扔在桌上。
邱正义打了邓国恩电话,他骂他混蛋。邓国恩问他为什么要骂他?为什么骂你,难道你自己做的好事你自己不知道吗?邓国恩就问他是不是我给刘秀梅发的微信让你看到了?邱正义承认他看到了,既然我看到了我不能不骂你,对吧?邓国恩反过来又骂邱正义,妈的你也太无聊了吧,哪个男人会去翻看自个老婆的手机?我没看,邱正义说,是她自己给我看的。邓国恩一下子就无语了,太失败了,他恨不得抽自己几耳刮子。
两年后小贝高考。高考结束,刘秀梅突然感到很虚无。身体虚无,世事也虚无。小贝肯定是要走了,她考得相当不错,理应进一所名牌大学。刘秀梅就像是身体里有一根骨头抽离了她。这么多年来,表面看是刘秀梅在照顾小贝,她是小贝的依靠。其实完全相反,事实是小贝在照顾她,小贝才是她的依靠,是她的避风港。如果没了小贝,刘秀梅根本不知道这些年她是否还能熬过来。她宅在家里,因为小贝没风险。陪读是一个多么正当的借口啊,是一个多么好的理由啊,它让她能够无所顾忌地龟缩在女儿身边。这些事情别人不会知道,小贝也不知道。没人相信刘秀梅会是一个虚弱的人。在那么多猥琐的人中间,她就像是一只天鹅,可她仍然虚弱。
现在小贝要走了,刘秀梅暗地里哭了一场。她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死去活来。她明白,小贝一走,她再也没了可以依赖的人,没了可以打发时光并得以躲藏自己的地方。
但是小贝很懂事,她感激她的母亲,感激她这些年为她所付出的心血。她抱着刘秀梅,在她耳边悄声说,“以后就好了,反正你也不喜欢打麻将,你尽可以到外面去旅游。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吧。”
“好啊,”刘秀梅说,“我要玩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事有凑巧,这段时间农机局刚好需要派一个人到省城学习,时间为半个月。局里排来排去抽不出人手。刘局灵机一动想到了刘秀梅。尽管之前她肯定不会答应这类事,但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小贝高考结束,刘秀梅会有空闲,说不定她会答应下来的。
于是刘局找来刘秀梅问她意见。为了打动她,刘局特意告诉她这次学习的地点在武汉磨山。考虑到刘秀梅喜静不喜闹,刘局说,“东湖磨山,风景非常好。”
没让刘局多做工作,刘秀梅就答应了。她听小贝的话,也想调理一下自己。
刘秀梅在武汉读过大学,东湖是她热爱的地方。之前她所上的大学,也就坐落在东湖边上。
所谓学习,带有很明显的休养性质。作息时间安排很松,上午有人讲课,也不是每天都讲。下午多半是讨论,或自由活动。这天下午,也就是刘秀梅来学习的第二天,讨论还不到五点钟就结束了。学习的人分散开去。有人回到自己房间,有人邀约着到外面吃饭去了。刘秀梅没地方可去,她不认识人,也没人约她。她就一个人在东湖边溜达,天气炎热,刘秀梅穿着白色短裙,两条腿修长笔直,看上去楚楚动人。
这会儿,刘秀梅倚靠着一座小桥的栏杆,栏杆也是白色。她望着湖面细微的波浪,嗅着从湖上吹来的风,风里有一股淡淡的鱼腥味。鱼的腥味混杂在风里真好闻啊。这气息不仅对皮肤、对鼻腔也有轻柔的抚慰。沉醉在鱼腥风里,刘秀梅眼圈微红。
有一辆车在缓慢地滑动,车窗开着,驾车人无所事事地望着这边。驾车的这个人不像是在欣赏风景,也不像是要去哪里。然后,车就停在不远处的树下面。从车上走下来的人竟然是邓国恩。
“不敢相信,真是你啊。”邓国恩说,“我还以为是哪个大学生呢,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见面了。”
刘秀梅皱了皱眉头,“我们认识吗?”
“我们认识吗?”邓国恩重复了一句她的问话,在她眼面前竖起一根手指头晃了晃,“你是真不记人吗?我是邓国恩,邓国恩啊。”
“对了,你是邓国恩,《鬼话》的作者。”
“这么说,你还记得《鬼话》。”
“记得。”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学习的,”刘秀梅冷淡地说,“你呢,怎么也在这?”
邓国恩在学校里不好好教书,整天就记着写诗。他和外面的人一起混,有时候还和学生勾肩搭背,没大没小地互称哥儿们。没有规矩,也不顾脸面羞耻,教育局本来就对他有看法,视他为教师队伍里的老鼠屎。恰巧呢,他班上又出事了。有个学生在宿舍里照镜子,他说怎么我脸上老长痘痘啊?同宿舍的室友这时靠过来说哪有痘痘啊?在哪儿?他说在这你帮我看看,说着他就在镜子里指给他的室友看。据他的室友后来说,他手指着镜子,人却一下子倒在他怀里了。他的室友以为他在恶作剧,试图推开他,但是他已经没了呼吸。医院里也检查不出什么,这孩子猝死在学校宿舍里了。学生家长一开始没打算扯皮,他们沉浸在悲伤里。他们认命,在认命的悲愤里诅咒自己的未来。可是邓国恩在劝解他们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学校即使没有责任,也应该承担部分人道主义义务。教育局认为邓国恩这样跟学生家长说话太不合适宜,有吃里扒外之嫌。你给了人家杆子人家当然会往上爬。学生家长以此为由,找学校敲了一笔钱。事情处理完了,教育局老找邓国恩的茬。停他的课,停他的职。邓国恩干得没意思,寻思着不如离开。教育局允许他出去,保留他的教师编制,不发工资。邓国恩就这样到了武汉,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
这里面的曲折原委邓国恩不想告诉刘秀梅,邓国恩本就是个二流子男人,在幸福县城他就曾勾搭过她,却以失败告终。这事搁在别人身上,断不会再有第二次。但是邓国恩不一样,在武汉巧遇刘秀梅,邓国恩忽然有了再次勾搭她的想法。
“见到你我觉得羞愧。”邓国恩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却这么绕着弯子说话。
“你羞愧什么呢?”刘秀梅觉得奇怪。
“羞愧我给你发的那些微信,微信里的那些言词不适合我们。”
“那些啊,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不过的确比较轻佻,当时我没想到你会那样。”
“你还保留着这种印象,可见。”邓国恩没有把话说完,不知道他要说可见什么。
“腐朽的土壤里,也有活着的种子。”刘秀梅却把话岔开了,她朗诵了两句诗,问道,“这是你写的诗吧?”
“你读过我的诗?”
“读过,就是那本《鬼话》。”
邓国恩突然间满脸通红,“可那不是诗,那都是一些子不着边际的鬼话。你别信,我自己都不相信。”
“真是奇怪,看你脸红的样子,好像你对自己写的诗歌也很羞愧。”刘秀梅说,“你发给我的微信和你写的诗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字,老实说你的文字是分裂的文字。”
“同样是羞愧,可我宁愿你阅读我的微信。”
“那么,《鬼话》呢?”
“《鬼话》太矫揉造作了,无病呻吟。”
“你这么看啊。”
“对呀,鬼话连篇。”
“但是我相信。”
刘秀梅望着水面,几乎像是自言自语。
邓国恩在揣摩刘秀梅所说的话,同时他也在调整思路。他说,“你认为我发给你的微信言词轻佻,其实不是。我那时是真的爱上了你,并深陷其中。在超市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无力自拔了。那都是我的真心话,却被你斥为无聊。自从被你回绝后,顺便说一句,你回绝我的方式也真够毒辣。你告诫邱正义,让他不要再结交我这样的朋友,他臭骂了我一顿。遭你回绝后,我觉得再没脸待在幸福县,就辞了教职,来到武汉。”
他说了假话。在超市不是他第一次见到刘秀梅。他很早就知道她,也认识她,只是她不认识他罢了。在超市邱正义正式为他们做了介绍。那也是邓国恩自己凑来的,他看到有邱正义在场,便迎上去打了招呼。
刘秀梅的脸慢慢转向邓国恩,“我没让邱正义骂你,我就是不太理解你的微信,拿给他看就是了。”她显得若有所思,“但是就算这样,你也没必要辞去教职呀,我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你不能因为我而失去了你的工作。”
所谓辞去教职,也是邓国恩在说假话。既然编到这里了,那就继续往下编吧。邓国恩说被刘秀梅拒绝之后,他很痛苦,甚至都活不下去了。县城太小,他不想再见到她,却又老是有意无意间碰到她。你那么美丽,看到你一次我就会伤一次。邓国恩读过日本小说《春琴抄》,书中的男主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他说我也想刺瞎我的眼睛。书中的男主是害怕看到女主毁容了的脸才刺瞎他的眼睛,我不一样,我是因为害怕看到你美丽的容貌才想着刺瞎我自己的眼睛。既然不能和你在一起,我有一双能看到你的眼睛又有什么用。邓国恩说他计划剜掉自己的眼睛,但他下不了手。于是他想能不能利用药物让自己失明?他在网上查找,到乡下去寻医问药。再这样下去,我可能真就不行了。邓国恩说他选择了逃离,离开幸福县城,逃到武汉去,至少他为自己保留了一双眼睛。
“有什么不好明白的呢,”邓国恩急赤白脸地说,“我是因为真真地爱着你,所以才会逃离。”
刘秀梅的脸扭曲着,“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不是。”
“我怎么确认?”刘秀梅扭曲着的脸变得苍白,如果邓国恩这时能握住她的手,他将会发现她的双手冰凉如雪。
“如果是,就让我立马死在你面前。”邓国恩举起一只手,他在发誓。
“别发毒誓。”刘秀梅说她害怕誓言,害怕发下的毒誓瞬间变成现实。她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和她初恋的男友在这磨山顶上待过一夜。她和他在那个夜里,男人和女人的事大体上都做了,就是没做爱。不是不想做,是怕,怕怀孕。他带着一条毛巾,他们躺在山坡上。刘秀梅要他发誓说爱她。他就发了,他说我若不是真心爱你,就让我得绝症死掉。刘秀梅觉得这样的誓言才让人放心,便不停地要他重复。他因此就在她耳边不停地重复,他说我若不是真心爱你,就让我得绝症死掉。不久,他果真死于一场绝症。
“是癌症吗?”邓国恩问她。
“是的,癌症。”
“这么说,你初恋男友并不是真心爱你。”
“我不这样看,我还是信他。”
“我也信他,但是我还活着。”
“爱情和癌症差不多,一旦得上即是终身,永难治愈。”
刘秀梅比之前活泛多了,脸上现出红晕。
谎言就像一条河流,只要说开了头,就会无休无止地往前流淌。越往前,水流越多,河面也越宽阔。邓国恩现在准确找到了刘秀梅的弱点、命脉、入口。他说他因为爱她,因为逃离才来到武汉。到了武汉,本以为心病会断了念想,没想到思念愈重。他通过各种途径小心地打探她的消息,因此得知她来了武汉,在武汉学习。今天他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放下手上很重要的工作,借了同事的车来到磨山。他不敢去她学习的宾馆找她,只想在东湖边绕着走,试一下运气看能不能碰上她。他的运气太好了,真就碰上了。还有,他写的那些诗其实全是他的内心。因为害怕嘲笑,害怕被人指认为精神不正常,这才故意掩人耳目,自己把它叫作鬼话。现在在她面前,他敢说那不是鬼话,那就是人话。爱情不仅仅是鬼界的事情,也能是人间的事情。
邓国恩住着出租屋,刘秀梅帮他清理屋子,帮他洗衣服。她说你看会电视,我做完家务就来。邓国恩说没电视。刘秀梅说那你在电脑上看会电影吧。洗完衣服,刘秀梅进来时,发现邓国恩已光着身子躺在床上。他说,“我在等你。”
这是他们的第一夜。做完爱,床单上有一摊梅花般大小的血迹。邓国恩问刘秀梅来月经了吗?刘秀梅说没有,大约十天前月经才回去。那么是不是有创口,好像也不是,她没觉着疼痛。既然都不是,这血是从哪儿来的呢?你是处女?哪是!刘秀梅笑着打他的手,“我女儿都高考了。”
邓国恩很在意第一夜流出的血。有象征意义,有仪式感。可是第二夜却没有,什么都没有,第三夜也没有。他坚持要在这里和刘秀梅举行一个简易的秘密婚礼。就在出租屋里,就他们两个人。不要证婚人,谁也不要。我们彼此对拜一下就行了。
刘秀梅答应了他,他们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相互对拜。
“现在我们都犯了重婚罪。”刘秀梅抚摸着邓国恩,伤感地说。
“重婚罪也要。”
“你能给我生个孩子吗?”邓国恩问道。
刘秀梅说,“我愿意。”
“可是生不了。”
“想想都觉着好。”
这几天,邓国恩把他和刘秀梅的事用微信传回了幸福县。他给他的朋友发了私信,他的朋友又把他的私信转给了他自己的朋友。朋友又转给朋友。邓国恩的朋友在微信中说,邓国恩已经在武汉攻陷了刘秀梅。她这只鲜艳的气球终于被戳穿了。半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刘秀梅回到了幸福县,她一下车忽然发现气氛不对。所有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目光都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飞过来,然后潮乎乎地粘在她身体上。许多人在窃窃私语,声音不是太大,又故意让她听到片言只语。
到了家,邱正义迎上来,二话不说猛地抽了刘秀梅一嘴巴。血线从她嘴角淌下。
“你也有今天。你在武汉做的破事,全县人民都知道。你让我丢尽了脸。”邱正义说,“你现在不会再装了吧。装了这么多年,你不累我还嫌累得慌啊。”
“你打我,”刘秀梅说,“以前你从没打过我。”
“打你怎么了,你和大家是一样的人。”
“我没装,从来就没装过。”刘秀梅头晕目眩,她无比虚弱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不一样!我要离婚。”
邱正义不愿离婚,刘秀梅坚持要离。他们还是离了,离了婚的刘秀梅常在河边散步。人们不久就忘记了她,她不再是县城里的名人,新的名人总在不断涌现。很少再有人关注她。刘秀梅一边散步,一边低头沉思。有时候,她会走到很晚。八月份的一天夜里,刘秀梅又走到了深夜。她站在河边,驻足观望黑漆漆的河面。这时,一条黑影飘过来,站在她身后。
“我知道是你。”刘秀梅说。
确实是邓国恩,他说,“我对你说过的所有那些话,全都是谎言。我还给你编故事,那些故事也全是假的。”
“可是我信你。”
“你为什么要信我?”
“不知道。”刘秀梅的身体往下软。
邓国恩扶着她,像是要从下面托住。“有一天我发现,我对你撒过的谎不是谎言,它其实就是誓言。我不收回我的谎言,因为那是我在对你发誓。”
“我信你。”
刘秀梅还是这么说,她的身子骨里有了些力气。
“现在我也离婚了,”邓国恩坚定地说,“我回来娶你。”
“你不用娶我,我们早就结婚了。”
“是啊,我们已经结过婚了。”
幸福县城的这条河叫府河,他们在八月的府河边拥抱着。刘秀梅靠在邓国恩怀里说,“我常在河边散步,喜欢这风里的鱼腥味。”
邓国恩嗅了嗅,果然有。
“你知道为什么河里的风会有鱼腥味吗?”
“为什么?”邓国恩说。
“因为这河里的水和东湖里的水一样,里面也有鱼。”

曹军庆,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出篇有长篇小说《魔气》《影子大厦》,中短篇小说集《雨水》《越狱》《24小说》等;在文学刊物发表小说三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