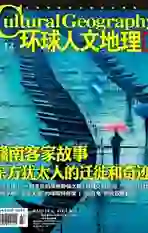陌生的城市与“恋地情结”
2017-08-02唐晓峰
唐晓峰
现在,我国的城市有两个特点,一是盖楼多,另一个是搬家多。因为这两个特点,城市变得陌生了。大批旧房拆了,新楼盖起来,城市的景观大变。城市居民一个接一个离开旧居,搬入新房,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大的变化。
看电影《没事儿偷着乐》,看到最后,张大民一家從胡同的狭窄小房搬进单元楼,虽然为他们一家高兴,但也在心中暗暗猜想,电影里面展现的那种滋味丰富的邻里生活还会延续吗?电影结束了,心里却留下一桩“悬案”。
常听社会学家说,城市环境会造就一种特别的“人类”,他们有四种特点:一是理智性强,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对待事情;二是精于计算,对于利弊得失要考虑再三;三是厌倦享乐;四是人情淡漠。过去我总认为这些情况不适合北京城,老北京的胡同生活不是这样冷淡疏远,但看到现在城市的变化,我渐渐感到社会学家说得有道理。电影里张大民一家最后是搬进单元楼了,但我们不难推测,大民“贫嘴”的生活环境也就没了。原来的胡同院里,邻居之间常见常聊,好说的人可以施展,但在单元楼里面,大家都比较“独”,对话很少,想象张大民在单元楼里一定憋死了。
电影里没有讲张大民是否还留恋他原来生活的那个胡同小院,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推测,张大民一定会留恋一番的。我自己也有从陈旧故居搬进新式楼房的经历,最近,因故居院子要被彻底拆除,老邻居们故院重游,拍照留影,对曾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尽情感怀了一回。所谓“老邻居”,其实都是在这个院中长大的孩子,后来天各一方,从事各色职业,也有颇具知名度的明星,大家听说老院子要拆,都赶来要见它最后一面,回来的人数之多、之全,都超出事前的预料。一个“地方”的毁灭,竟有这么大的感召力!
美国一位有名的华人地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人文地理术语,叫“恋地情结”(Topophilia),我想这个术语的提出很有必要,因为“恋地”是普遍存在的,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这种情结。以故地为题作诗、作歌的大有其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些诗歌都道出“恋地情结”,这些“恋地”诗歌,作者有情,闻者动容,一点也不比“恋人”的诗歌差。
不过,“恋地”是要有条件的。要“恋”的地方都是“特征性场所”(人文地理的另一术语),在这些特征性场所都有特定的景观,恋地与恋景观是并存的。如果把原来的景观拆个精光,换一个大样,恋地之情会变得空洞而无所依托,也就不会长久。我后来路过老院子那个地方,旧平房已被推倒,大树也被砍伐,面目全非,看上去俨然是个陌生的地方,想到日后会有新式高楼在这里耸立,那更是个与我无关的景观,对这个地方的“感觉”也就从我心中消退了。
我们居住很久的城市就这样一块一块地变得陌生起来,我们的生活,交往的群体也在同步地改变。竟然有学者说:“迷路的经历就成了我们对现代城市认知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城市中的“迷路”,从本质上说是城市生活的迅速改变,人们几乎产生了全方位的“陌生”感。我们在北京城里看到,不少老字号也搬了家,换了地方,还换了门面,“老”的感觉全然没有了。如果到处都没有了“老”的感觉,则产生了一种效果,即一个本地人站在了与外地人类似的地位。
在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中,人们必然要重建自己的地方认同感,选择新的城市空间位置和新的景观特征,渐渐形成新的“恋地情结”。当然,由于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态已经改变,人们在重新选择地方认同时可能与过去的观念完全两样。眼下,似乎没有人能够清高到完全不顾“经济形象”地去选择位置,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恋地情结”,都是要恋富贵之地,所以,才出现了如“富贵山庄”、“尊贵家园”之类的地方。这类地方正在形成新的“特征性场所”,为了追求这种“特征性场所”,人们不顾超度消费,与此同时,房地产商们则在“偷着乐”。陌生,使许多人产生盲目,却为商人带来大量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