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一期、云冈二期大像窟洞窟形制中国化之比较
2017-07-31范鸿武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范鸿武(扬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云冈一期、云冈二期大像窟洞窟形制中国化之比较
范鸿武(扬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云冈一期与云冈二期大像窟都是石窟洞窟形制的中国化,但是,这两期大像窟洞窟形制的中国化具有明显的差异。云冈一期大像窟具有鲜卑文化特点,云冈二期大像窟具有汉文化特点。
云冈一期;云冈二期;大像窟;洞窟形制;中国化
虽然从广义上说,云冈一期与云冈二期大像窟都是石窟洞窟形制的中国化,但是云冈一期与云冈二期的大像窟在洞窟形制上的中国化,两者的文化差异和建筑空间的不同是明显的。
中外专家和研究者已经在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根据已知的文献、记录,利用考古标型学、年代学等方法,将云冈石窟艺术形成的三个显著变化的发展阶段分作三期①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文物出版社出版,199:120., 分别称为云冈一期、云冈二期、云冈三期。
云冈一期是指北魏文成、献文帝时期(公元四六O年—四七O年),云冈二期是指孝文帝都平城时期(公元四七一年—四九四年),云冈三期是指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公元四九五年—五二四年)。比较研究这两期的大像窟,它们的洞窟形制之中国化,各有不同的特点。云冈一期洞窟形制具有鲜卑化之特点,呈现强烈的鲜卑民族建筑特色,而云冈二期洞窟形制具有明显的汉化之特点,呈现汉民族建筑特色。
一、云冈一期大像窟昙曜五窟在洞窟形制上的鲜卑化
云冈一期昙曜五窟(16~20窟)都是大像窟形制,是由北魏高僧昙曜法师主持设计开凿的。曾经在河西凉州修行、弘扬佛法的高僧昙曜主持设计开凿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这五座洞窟形制相同,平面为马蹄形,窟顶呈穹隆状;每窟一门一明窗,明窗在上,门在下;外壁雕满千佛。各窟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和现在佛),主佛居中而设,身躯高大(都在13米以上),或坐或立,姿态各异,神情有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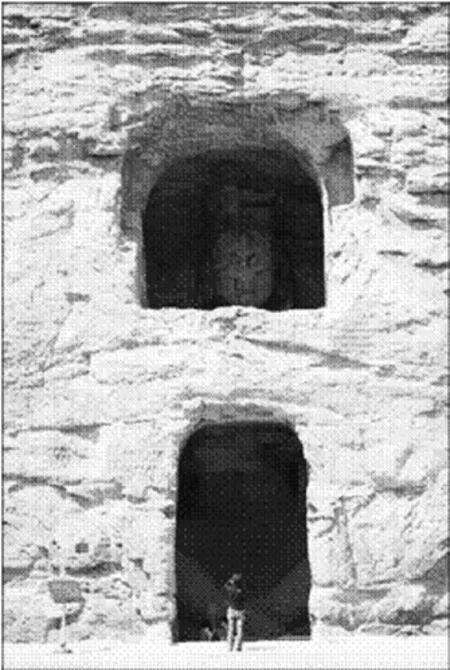
图1 第17窟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从窟内空间形态来看,佛像体量高大,占据了窟内的绝大部分空间,有一种高大魁梧、顶天立地的雄伟气魄。窟内留给信徒参拜的空间很狭小,信徒进入洞窟之后,只有高高仰视才能见佛的全貌。人与佛像之间体量的反差和参拜空间的狭小,使信徒产生一种敬畏之心理,神圣崇拜的宗教情感自然产生(图1)。
云冈一期昙曜五窟的共同特征极其明显,它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模式——大像窟。
大像窟是石窟寺形制的一种,也成为大佛窟。由于其主体造像高大,占据窟内较大空间而得名。大像窟的宗教功能是作为礼拜和禅观的场所。这种类型的石窟是460~470年间平城地区开凿石窟的流行式样,是应雕琢巨像特定需要而开凿的特殊形制——大像窟。云冈石窟大像窟是北魏460~470年间平城地区开凿石窟的新式样2,与公元1世纪大月氏贵霜王朝时期开凿的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和后来的新疆地区龟兹石窟大像窟的洞窟形制都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云冈一期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是非常特殊的建筑形式,与原创于印度的石窟寺形制不同。印度的支提窟兴起于公元前1、2世纪,普遍认为与中国早期石窟寺的形制有着渊源关系。印度的支提窟由覆钵式塔将石窟窟室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室较大,是用来礼佛的场所。后室置塔,由信徒自右绕塔巡礼。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与印度的支提窟形制不同。昙曜五窟这种窟形不仅在印度、西域、凉州一带没有,即使最早的龟兹大像窟也与云冈一期的形制完全不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也与云冈一期昙曜五窟的形制不同。
关于云冈一期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的独创性,宿白先生曾指出:“这种式样的石窟,就已知的资料,自南亚、中亚以迄我国新疆、甘肃地区,都没有发现相似的先例……它应是五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作出的新模式”。[1]所以,中国的石窟研究者有理由认为昙曜五窟是北魏时期独创的窟形。它的这种特殊结构也正是云冈北魏早期雕刻艺术的显著特点。
显然,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没有沿用既有的建筑形式,我们在中外各地的石窟中找不到与之相似的洞窟形制。所以可以推断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在当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是一个新的建筑形式。在当时的社会具体条件下,云冈早期洞窟形制参考的建筑形式应当是当时游牧民族最普遍、最广泛的建筑形式——游牧民族的毡帐,游牧民族的毡帐就是穹庐。云冈早期洞窟形制的原型是穹庐,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是采用帐篷式的游牧民族穹庐。
“毡帐是鲜卑族日常生活的居所,鲜卑人对其有着深厚的情感。北魏定都平城后已逐渐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众多的鲜卑人从移动的毡帐走向定居生活,但传统的毡帐对于固守本民族文化的鲜卑人而言,还是不能忘却的。石窟形制是一种文化载体形式,它所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风貌,其发展变化一方面是石窟艺术自身发展变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形制的变化也反映了北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与宗教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鲜卑人对自己本民族固有传统习俗的追忆”。[2]
关于游牧民族的毡帐(穹庐),历史上,鲜卑族人和突厥人都是游牧民族,都多以毡帐为屋。“野外用的毡帐构造简单,而设于较固定的地点供起居之用的毡帐却有很华丽的。唐太和公主嫁回鹘时,‘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毡幄于楼下,以居公主’”。[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突厥“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饰之,烂眩人目。”[3]
总之,我国历史文献证明历史上确实存在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穹庐)这种有圆拱形帐顶、顶呈穹隆状的建筑形式。虽然西域地区人居住的毡帐和鲜卑民族居住的毡帐在形式上可能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作为游牧民族基本生活空间的毡帐,其基本形式应当是一致的。
云冈石窟所处的地区当时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区,鲜卑民族和其他的胡人是平城的主要民族成分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决定其建筑形式的建筑形式是可以移动、可以拆迁的穹庐。穹庐,作为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是游牧民族基本的生活空间,其基本形式就是平面呈圆形、顶呈穹隆状、圆拱形帐顶、前部开门,并且在适当的部位开天窗或者亮窗。
从昙曜五窟形制和内部结构来看,平面为马蹄形窟顶呈穹隆状,向上弧转收小的壁面与窟顶交接处转折自然,无明显的分界形成了“球状”的圆拱,昙曜五窟的形制和内部结构与鲜卑拓跋游牧民族的帐篷形式有相似之处,模仿鲜卑拓跋游牧民族居住的帐篷是有根据的。从佛教造像的角度来看,云冈昙曜五窟造像仿自鲜卑拓跋民族之论点已经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赞同。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云冈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和结构是模仿鲜卑拓跋民族居住的基本建筑形式——穹庐。
总之,云冈一期昙曜五窟洞窟形制具有鲜卑化之特点,呈现出强烈的鲜卑民族建筑——穹庐的特色。
二、云冈二期大像窟与云冈一期大像窟昙曜五窟在洞窟形制上的不同之处
当我们比较研究云冈二期大像窟与云冈一期大像窟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时,我们会发现——云冈二期的大像窟继承了云冈一期昙曜五窟的流行式样(窟形与结构),窟形与结构继承下来了,但在石窟的壁面布局和窟室空间感上作了明显的创新。
云冈二期第五窟,是迁洛前开凿的。第五窟是大像窟,马蹄形平面,穹隆状窟顶仍保存了早期昙曜五窟窟形的式样,除了具有云冈一期昙曜五窟大像窟本身的特征外,其洞窟形制与云冈一期大像窟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有以下四点:
其一、第五窟主佛像前的面积空间加大,主像明显的有向后移的趋势,以扩展洞窟的空间,洞窟内的空间扩大了许多,它并无昙曜五窟那种给人以局促的印象之感。
其二、与昙曜五窟明显不同,第五窟并在北壁下部凿有低矮的隧道式的礼拜道,形成了一个符合佛教仪轨“右绕”的甬道式空间。
其三、同时,壁面采用地面汉式殿堂的上下分层、左右列段的重层布局方式,这和昙曜五窟壁面最初设计的千佛图像形式完全不同,却与中期其他类型洞窟的壁面布局一致,这种壁面的表现形式是云冈石窟开凿者模仿北魏当时地面汉民族的木构佛殿建筑之结果,这种壁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孝文帝时期云冈石窟艺术的显著特点(图2)。

图2 云冈石窟第五窟
其四、在北壁下部开凿出礼拜道,这更方便适宜参拜。这些应该是开凿者有意识地模仿北魏当时地面木构佛殿建筑之迹象。大像窟这种洞窟形制之变化,正是佛教与佛教建筑向着汉化、本土化发展的表现。
三、云冈二期大像窟在洞窟形制上的汉化
云冈二期大像窟,与云冈一期昙曜五窟相比,洞窟形制,力求走向汉化。北魏云冈二期是云冈渊源西方的佛教石窟东方化转折的关键点,洞窟形制汉化的倾向更加明显。
云冈二期工程突出了皇家“改梵为夏”的造像宗旨,使石窟的形制和佛的形象发生了明显变化。石窟在雕琢形式和布局上,吸收了中国古代汉民族的传统建筑风格和样式。北魏中期是云冈渊源于西来样式的佛教石窟东方化转折的关键点。因为这个时期的云冈石窟,无论洞窟的建筑构造形式还是造像的艺术风格,都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汉化,这与北魏孝文帝时期一系列汉化政策措施相一致,它是孝文帝时期汉化之风在佛教文化上的反映和体现。由于早期昙曜五窟造窟活动积累了经验并经历了探索,从北魏孝文帝开始,云冈雕塑艺术逐渐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此时汉化政策已积极进行,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因素闯进了石窟,来自印度、中亚、西域、中原和南方的佛教思潮和艺术风格已被北魏各族的艺术家和工匠吸收、改造,石窟艺术民族化已趋成。所以,孝文帝时期,云冈佛教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云冈二期第五窟大像窟充分体现了这种变化。
云冈二期大像窟在洞窟形制上的汉化是明显的。云冈一期与云冈二期的大像窟在洞窟形制上的中国化是有非常明显的文化差异和建筑空间的不同。云冈二期洞窟形制具有明显的汉化之特点,呈现汉民族建筑特色。
结 论
云冈一期大像窟昙曜五窟具有鲜卑化的特色,体现了鲜卑民族的文化特点,云冈一期洞窟形制和结构是直接模仿鲜卑拓跋民族居住的帐篷式的基本建筑形式——穹庐,独作椭圆形、杏仁形,这五窟显然出自昙曜和尚及其工匠独创的智慧、独特的设计,其洞窟形制是当时北魏拓跋鲜卑独一无二的创新,鲜卑化的特点很明显。而云冈二期大像窟在洞窟形制上彻底汉化了,体现了汉化的特色,鲜卑民族居住的帐篷式基本建筑形式——穹庐之基本特点已经消失,汉文化特点非常鲜明地体现于其中。
大像窟洞窟形制的中国化,在云冈一期大像窟呈现为鲜卑化,在云冈二期大像窟大像窟呈现为汉化。云冈一期的鲜卑化和云冈二期的汉化,都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表现。
[1]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M].文物出版社出版,1996:122.
[2]李雪芹.试论云冈第7、8窟雕刻中的鲜卑因素[G]//云冈石窟研究院编.2005年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192.
[3]孙机.我国早期单层佛塔建筑中的粟特因素[G]//《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下卷).文物出版社,2002:428.
(责任编辑:吕少卿)
J309
A
1008-9675(2017)03-0094-03
2017-02-14
范鸿武(1968-),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佛教造像艺术,环境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