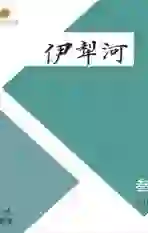那一片海子水蓝蓝
2017-07-26刘渊
刘渊
尕秀家住在洛布海子边上,下地不怎么方便,可是用水方便。穿过一条芦苇簇拥的小道,再下几道土坎,就是蓝汪汪的一大片水域。
尕秀来海子里挑水。身上那件豆绿色衬衫,又合体又鲜亮。她把一只木桶伸进水里,来回地荡了荡,灌满了水,一提劲就掂了起来。两只水桶打满了,她挑起就走。肩上的胡杨扁担一闪一闪的,胸前鼓鼓的两团肉一颤一颤的,翘翘的屁股蛋子还一晃一晃的,走路的样子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晌午了,尕秀得挑水做饭了。
李队长李大嘴从湖边割羊草回来,正好碰上了尕秀,立刻两眼放光,他的目光一飘一飘地落到尕秀脸上,笑嘻嘻地说,尕秀挑水做饭啦?做啥好饭?尕秀见是李大嘴,没好气地说,啥好饭,有一碗玉米糊糊喝就不错了。尕秀并没有停下脚步。李大嘴左右扫了一眼,没有看到尕秀她妈,便紧走几步,抓住尕秀肩上的扁担,梦呓般地说,我来帮你挑。
尕秀见到李大嘴本来就有气,自然不会让李大嘴帮她挑水,鼻子里哼了一声,没理他,还是自个走自个的路。
可李大嘴不让尕秀走。李大嘴摘下尕秀肩上的扁担,一把从身后搂住了她的腰。一个20岁的大姑娘,哪能让一个男人随便搂,尕秀身子一缩,一使劲,就从李大嘴怀里挣了出来。不但挣了出来,还虎起脸,高声大气地叫道,想干啥?我要喊人了。看到尕秀真生气了,李大嘴干干涩涩地说,啥也不干,只想帮你挑水呢。尕秀朝地上“呸”地唾了一口,横着眼说,李队长,请放规矩点,不要仗势欺人!
没占到一点便宜的李大嘴,嘴里嘟囔着,鼻子哼了一声,只好气咻咻地一摇一晃地走了。不过,嘴里不干不净地甩下了一句话:你不让咱弄,来顺那小子也休想碰。
尕秀家门前的海子,不叫湖,也不叫芦苇荡,叫洛布海子。
洛布海子这地方不是个好地方。地处塔里木河下游,白花花一片,全是盐碱地。周边除了莽莽苍苍的原始胡杨林,就是连天接地的芦苇丛。说它不是好地方,也不全对。洛布海子方圆百里,那些星罗棋布的小海子,像是无数撒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明珠,给这儿添了不少活气。海子大的水天茫茫,一望无际;小的其实也不小,起码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那时,塔里木河来水很多,海子里的水也多,清得见底,蓝得醉人,算得上是一道风景。
有了很多水的海子,引来了许多水鸟,野鸭、鹭鸶漫空欢舞鸣叫;芦苇也发疯地长,长得四五米高,大拇指一般粗,茂密如南方的水竹林。
海子里除了生長芦苇,还生长很多鱼,草鱼、鲢鱼、裂腹鱼、大头鱼……多的是。从四面八方流浪到这里的盲流们,只要在塔里木河边有地种,有林子可以放羊,有一汪水可以打鱼,即使在这地老天荒的地方,也生活得有滋有味。
至少,尕秀一家人挺满足。尕秀老家在甘肃民勤,那地方十年九旱,日子过得很苦。尕秀她爸早死了,尕秀是跟她妈一起逃荒逃到洛布海子的。这儿起码不缺水,还有地种,她没有理由不满足。尕秀跟她妈除了干队上的活,也跟其他人家一样,在塔里木河边私自开了两三亩地,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还养了三只山羊,在新疆的日子,怎么也比在老家强多了。
说起来,人也有点像草木一样,有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就长得格外欢实。原先粗皮黑瘦的尕秀,仅仅来这儿才两年工夫,就出落成了一个花儿般烂漫的大姑娘。
乡亲们都夸尕秀长得美,说尕秀是洛布海子的一枝红柳花。
这天晚上,李队长李大嘴门前的那棵胡杨树上挂起了一盏马灯,灯光白花花的,照得四野透亮。月儿早已爬上了洛布海子上空,洒下碎银似的月光,湖边更亮了。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1972年春天,全国都在瞎折腾的年月,队上没有多少正经事要开会。队上总共才六七十户人家,有啥事,队长招呼一声就行了,用不着开会。可今晚这个会不能不开。李大嘴咧着一张大嘴说,大队要让队上出八个壮劳力去加坝固堤,这可是大事。接着又加重语气说,加固堤坝很重要,要是加固不好,坝垮了,全公社的庄稼就泡汤了。
紧接着,李大嘴就念了上坝社员的名字。
在这个名单中,就有来顺的名字。
来顺一听到念到自己的名字,开始还有点高兴。这高兴不是没有理由。来顺打小在老家沱江边上长大,是只“水耗子”,水性好得没得说。他认为,上坝工分高不说,还能填饱肚子。可当他再一想,就有点不高兴了。因为他跟尕秀好了大半年了,热乎劲正在兴头上,一天不见都想得慌,这样他就不想上坝了。来顺跟尕秀是自由恋上的,二十出头的富农“狗崽子”,能谈上这么一个漂亮妹子,他说自己不知道是哪辈子烧了高香了。
来顺一想起尕秀,心里的热乎劲就往上蹿,还有一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东西在心头漫延着,他把这一切归结为缘分。
第二天下了工,来顺来找李大嘴。李大嘴正在房前和宋大头下象棋,见来顺朝他走来,拿眼角瞟了一眼,又埋头只顾下他的棋。来顺走到李大嘴跟前,有些迟迟疑疑,不过,只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干干涩涩地开了腔。
队长,我没法去固坝。
为啥没法去?怕苦?还是怕累?
那倒不是,我一个单身汉,家没人看。
哈,单身汉就没法去?家里到底有啥舍不下?
倒没啥舍不下,不过,家总得有人看吧。
李大嘴鼻子里哼了一声,不同意。真的,来顺家里除了队上分的那点儿玉米和土豆,就几件破衣烂衫,谁会要?李大嘴翻着眼皮说,革命工作,得服从需要,这事就这么定了,不换!
来顺本来就是个言语不多的人,李大嘴一大串硬邦邦的话,戗得来顺没话说。他一张脸灰灰地愁苦着,呆愣了一会儿,只得气鼓鼓地走了。
尕秀来到来顺住的土坏房,问李大嘴答没答应换人。
来顺还在生闷气,一想到李大嘴的那副样子,恨恨地说,那狗杂种说不给换。
尕秀坐到来顺身边,扑闪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瞅着来顺,用湿润的声音说,我猜想他肯定不给换呢。
没想到尕秀会这样说,来顺愣着眼问,你咋知道?
这不明摆着的吗?尕秀眼睛水汪汪地望着来顺,红着脸说,李大嘴见我俩好,他肚子胀呗。
李大嘴三十好几了,已是有老婆的人。他也是前些年投靠他舅舅来到洛布海子落户的。后来,李大嘴靠他当支书的舅舅,当上了生产队长,就开始嫌弃他那个白麻子老婆了,天天吵着要跟他白麻子老婆离婚。可白麻子老婆就是不离。之前,李大嘴就跟队上别的女人乱来,后来,见尕秀出落得像一枝花,李大嘴就打起了尕秀的主意,有事没事就爱跟尕秀套近乎,逮着机会,不是捏一把尕秀的奶子,就是摸一把尕秀的屁股,尽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尕秀讨厌李大嘴,狠狠地骂过李大嘴几回,可李大嘴还是死皮赖脸地老纠缠尕秀。尕秀早想把这事跟来顺说说,可这种事,一个大姑娘怎么好说出口呢。
来顺看出尕秀的心事,一脸疑惑地问,有啥事你说啊。尕秀低着眉头说,没啥事。嘴上虽然这么说,可眼睛却泄露了心头的秘密。看到来顺一副着急的样子,尕秀不由眼圈一下红了,随着眼窝滚出来泪水。
尕秀哽着声,终于把李大嘴一次次纠缠她的事对来顺说了。
来顺在心里号叫了一声,这条狗呀——啥话都说不出来了。
天刚麻麻亮,队上去固坝的汉子们的行李和粮食统统装上了马车。赶车的宋大头,手里捏着的鞭杆上,系着红布条扎成的红缨缨,像一团熊熊的火在燃烧。一甩鞭杆,鞭声就像放鞭炮一样,叭叭地响,又清脆,又响亮。
婆娘们都来给自己的男人送行,有的煎了葱花饼,有的蒸了白面馍,都跟自家的男人说着悄悄话,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没有人来给来顺送行,来顺显得孤零零的。不是没有人来送行,起码尕秀会来,是他来顺不让尕秀来。
马车就要走了,忽然有人喊:等一等!大伙儿回头一看,是尕秀。尕秀额头上沁出一层细细的汗珠,怀里抱着个蓝布包,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尕秀走到来顺跟前,把蓝布包塞给来顺,颤着声说,把这几个甜面饼带上。
见到尕秀一副痴痴迷迷的样子,汉子们的目光里流出几丝妒嫉几丝羡慕。宋大头说,尕秀你给来顺送甜面饼,也不送我一个?尕秀横了一眼说,下辈子吧,这辈子你怕是没门了。
不知谁说了一句,宋大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哇?傻想去吧。
车上的汉子们轰的一声全笑了。
站在一旁的李大嘴,见到这个情景,黑着一张脸说,别闲扯淡啦。转身拿眼睛瞟了一眼尕秀说,固坝就个把月,有啥不舍的?随后扭头对宋大头叫道,走!
固坝的男人出发了。马车跑在海子边的土路上,扬起一溜黄黄的土尘;马铃叮叮当当地响着,转过弯就不见人影了,但还能听到悠远的当当声。
铃铛声远了,远了,带走了尕秀的一腔痴情一份念想。
尕秀早早地就下地干活了。每天,她都要赶早在自家地里干一会儿。
尕秀是个勤快人,除了干队上的农活,还得抽空忙自己地里的活。
那年月,队上的土地都姓“公”,大伙儿干活磨洋工,分的粮食总是填不饱肚皮。于是,洛布海子周边的人,私下里都在塔里木河边开了一些荒地,种麦子、种玉米、种土豆。队上的人大都是盲流,为了填饱肚子,谁也不会打“小报告”。
这儿开荒种地,不像内地那样精耕细种。每年夏天,塔里木河洪水下来后,漫过洪水的河滩地,随便种点庄稼都能长。一年里河水漫过几回,庄稼就有收成了。当然收不了多少,每畝也就收个百十来斤。就这,盲流们也感到比在老家强多了。
尕秀妈来给尕秀送饭。没有什么好饭,稀的是玉米糊糊,干的是玉米饼,再就是几块咸萝卜干。家家都差不多,谁也不觉得这日子有多苦。
嚼一口玉米饼,喝一口玉米糊糊,尕秀吃得呼噜噜响。尕秀妈看着丫头吃得这么香,喜滋滋地说,等今年秋后庄稼收了,我看就把你跟来顺的婚事办了。
尕秀瞅了一眼她妈,嗲着声说,妈,你想赶我走哇!
尕秀妈盯着尕秀说,你也老大不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该嫁人了。
尕秀想探探她妈的口气,悠长着声音说,来顺那么穷,我咋个嫁哇?
尕秀妈笑眯眯地说,来顺眼下是没啥家底,可来顺人好、心眼好,往后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尕秀也是这么想的。尕秀听她妈这么一说,心里溢满了温情,就像海子里吹来一阵阵轻风,掀起层层幸福的浪花。
来顺虽说是盲流,可人家识文断字。
来顺个头高高的,像胡杨树一样挺拔。
来顺挺壮实,胸前那两疙瘩肌肉,像紫铜一样闪着亮光。
来顺憨厚本分,不多言、不多语,做起事来却挺有主见。
来顺还是一个勤快人,帮人干事,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一想到来顺,尕秀就有些走神了。尕秀妈看见丫头没有说话,当妈的知道女儿心里想的是啥,她在心里说,女儿是该嫁人了。
李大嘴门前那棵胡杨树上的大喇叭又喊话了,叫队上的人全都去开会。
尕秀不知道开啥会,走到队长家院子一看,黑压压的一群人,围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被捆绑着,头被按得很低很低。
李大嘴揪住那人的头发,往上一提,让所有的人都看清那张脸。一看那张脸,尕秀的心顿时像被雷击了一样,浑身颤抖着,天哪,这个男人正是她的来顺。
听人悄悄说,来顺从固坝工地偷跑没跑掉,是被弄回来批斗的。
来顺那张黑红的脸,看上去还是那么有棱有角,不但有棱有角,还分明显出几分傲气。
这当儿,有几个人冲了上去,像是一群恶狼扑向一只羔羊。等到狼群散去,再看那只羔羊,已经被撕扯得没了样子。来顺脸上布满了血印子,鼻子里流出的血,把胸前染红了一大片,比血色黄昏的落霞还要嫣红。
尕秀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但这时的尕秀已不是那个柔弱的尕秀了。不知哪来的勇气,她分开拥挤的人群,一下冲到了来顺跟前。她想用身子护住来顺。还想用身子撑住来顺。但尕秀不但没有办到,自己反而还挨了几巴掌。
尕秀一时感到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身子摇晃了几下,一下晕倒了。
来顺在家养伤的日子,尕秀每天都来给来顺送饭。尕秀打心里不怕李大嘴。她知道,李大嘴收拾来顺,无非就是为了把她弄到手。她不相信,李大嘴能把她咋样。
来顺的家实在不像个家,房子就一问土坯房,胡杨树的椽子,铺上一层芦苇,再糊上一层草泥就成了。房子里就一个炕、一床被子。再就是一张桌子和几条凳子。不过,这不算什么,洛布海子的人家几乎都一样。漂泊流浪的人,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能有这么个家也算不错了。
尕秀看着来顺吃饭,每次总要劝来顺,让他多吃点。
轻轻地抚摸来顺脸上的伤痕,尕秀问来顺,还疼不?来顺说,不疼。尕秀说,李大嘴咋这么毒啊?来顺说,公报私仇呗。尕秀说,这条恶狼,说不定日后还会整你呢,来顺说,我不犯法,看他能把我咋样!尕秀一边给来顺敷药,一边说,不行的话,我们跑吧,离开这个鬼地方,远走高飞。来顺说,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跑到哪里都不会好过,听天由命吧。尕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来顺,嘴里叫了一声来顺哥——就死死地把来顺抱住了。尕秀心碎了,泪水不听话地滚了出来,怎么忍也忍不住。尕秀是在为心爱的人伤心落泪啊。有人說,世上表达感情的方式多种多样,流泪或许是最真实的一种表达方式。
想方设法想把来顺的身子养好。尕秀划上“卡盆”(独木舟)到海子里去打鱼。
来顺房前的那片海子不大,不会有大鱼。尕秀想,只要打上一点儿小鱼,给来顺哥补补身子也好。
尕秀是头一次单独下海子打鱼。以前,她只是坐来顺的卡盆下过几回海子,但尕秀硬是学会了划卡盆,学会了下网。
整个海子静静的,水也是蓝莹莹的。天光、云影撒落在清清浅浅的水面上,幻化出五光十色的斑斓。
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尕秀划着卡盆收网时,发现一条网被水草挂住了。尕秀弯下腰,想伸手去拔开水草,可能是用力过大,失去平衡,卡盆一歪,翻了,尕秀一下掉进了水里。
好在海子水不深,只是刚淹到胸口。尕秀费了好大的劲,才重新把卡盆翻了过来,跳上了卡盆。尕妹心里空荡荡的,她捂着眼睛,突然忍不住嘤嘤地抽泣起来。
这一回,尕秀只收了一两斤小白条鱼。虽说鱼不多,但至少可以熬两回鱼汤喝了。
来顺身上的伤,养了一段时间,已经好多了,精气神也足了。
这天晚上,尕秀跟来顺俩人来到海子后面的沙窝里谈心。
静静的沙梁、低语的清风、空潆的月色,这样的夜晚,太适合谈情说爱了。沙地上,沙子温温的,很软。坐在上面,像坐在毡毯上一样舒服。
紧挨着尕秀坐着的来顺,轻轻地理着尕秀一头柔柔的头发。来顺觉得那头发不是头发,是一匹绸子。不,绸子也没有这么黑亮、这么滑溜。
尕秀感到一种特别的温存。这种温存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甜蜜。从来顺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气味,也觉得好闻。不是酸酸的汗臭味,也不是呛人的莫合烟味,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男人独有的一种味道。
尕秀跟来顺好了将近一年了,还是头一次和来顺在夜里这样亲密地接触,心头像有一群兔子在蹦哒。头靠在来顺的肩上,紧紧地贴着来顺,心里溢满了少女的柔情。
就这么相互依偎着,似乎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抱着尕秀的来顺,抱着抱着,就有些心动了。心一动,手也跟着在尕秀胸前动起来。尕秀是个大姑娘,两个奶子鼓鼓的挺有弹性。来顺一边揉着,一边贴着尕秀的耳根,动情地说,你真好,让我抱到天亮吧。
是么?尕秀唱歌似的说,你想抱,那你就早点娶我吧。娶了我,我天天都让你抱。来顺低着声说,可我现在太穷。尕秀说,我们都有一双手,都年轻,只要舍得出力,日子就不会穷。接着又说,等结了婚,我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还给你……
来顺没想到尕秀会这么说。尕秀说的话,正是他来顺心里想的,立时心里像有一头小鹿在冲撞着。这种时候,只要是一个男人,没有不冲动的。来顺一冲动,扳过尕秀的脸,发疯地吻。一边吻,一边说,我真的好想你,想得我心尖尖都疼。
尕秀清楚来顺这会儿想什么,不知咋的,尕秀也胆大起来。尕秀一大胆,就成了一团燃烧的火,就成了一汪漫滩的水。来顺也好像不是来顺了。来顺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头强健的马鹿,正在啃噬着一片青青的芳草地……
来顺的伤刚刚痊愈,李大嘴就通知他上筑坝工地去。说不去,就不给分粮,就要下户口。胳膊拧不过大腿,来顺不想走,也只得走。
心里舍不下尕秀。尕秀跑来,哽着声问来顺,你咋还要走?
来顺苦着脸说,整我呗。
尕秀带着哭腔说,你走了,我咋办?
来顺叹着气说,你要留点心,李大嘴可不是好东西。
尕秀点点头,背过身去,眼里有两滴晶莹的东西滚了出来。
洛布海子四周,全是绵延无尽的原始胡杨林。这片胡杨林到底有多大,连当地的维吾尔族老乡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好大好大。胡杨树特别适宜在沙漠边缘生长,又有塔里木河的滋润,长得可欢实啦。胡杨林里有野兔、野鸡、黄羊、野猪,还有马鹿什么的,林子是它们的快乐家园。
尕秀赶上毛驴车,去胡杨林里拾柴火。林子里柴火很多,枯倒的胡杨树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大的搬不动,小的又嫌不经烧,尕秀专捡胳膊粗的,用脚一踩,“咔嘣”一声,枯枝便断了,只管往毛驴车上搬就是了。
尕秀拾了不多一会儿,就拾了大半车了,不想拾了。她一个女人,没有多大力气;再说,沙漠里没有路,拾多了也拉不回去。她想休息一会儿,就在一棵树桩上坐了下来。
尕秀拾柴禾,好像没有别的人知道。其实,她去林子里拾柴禾,除了她妈,还有一个人看见。
看见她的这个人,就是李大嘴。
从李大嘴再一次逼着来顺去固坝后,他的心里就想尽快干成一件事。这件事他已寻摸好久了。不是什么大事,可也不是什么小事,这件事干成了,李大嘴他就交桃花运了。
李大嘴看见尕秀赶着毛驴去了林子,心里像有一头小鹿在冲撞,早想干的一件事,今天终于逮着机会了。
李大嘴对这片林子太熟悉了,毫不费力地就寻到了尕秀。当他像一个猎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尕秀身后时,尕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他。李大嘴冷不丁地喊了一声“尕秀”。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喊,虽然声音不大,却似旱天里的一声炸雷,差一点把尕秀的魂都吓飞了,尕秀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李大嘴说,看把你吓成这样。尕秀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直愣愣地望着李大嘴,满脸惊恐地问,你要干啥?
李大嘴说,不干啥,就是想跟你亲热亲热。
尕秀说,你以为你是队长,你就可以随便欺侮人?
李大嘴说,来顺能亲热,我就不能亲热?
尕秀说,你嘴巴放干净点,不要满嘴喷粪。
李大嘴说,我把老婆离了,就跟你结婚。
尕秀说,嫁人也不嫁你,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这种时候,李大嘴是没法控制住自己的,一瞬间,他就成了一头野兽一条恶狼,猛地向身单力薄的尕秀扑去……
有人说,一个女人要是不让男人干,这个男人怎么也干不成。
其实,这种事要看发生在什么地方,要知道这事儿是发生在胡杨林里,或许就不这么认为了。
老林子里,一株株胡杨树,围成高高的一堵堵墙挡在四周,再大的喊声也传不远,谁也听不见。
老林子里,一脚踩下去全是软乎乎的沙子,想跑,有沙子绊住脚,怎么跑也跑不动。
再说,老林子里,再没有别的人。野鸡、兔子倒是有,可它们一点忙也帮不上。
身单力薄的尕秀,喊也喊了,可没人听见;跑也跑了,可跑了没几步就跑不动了。何况,李大嘴不会让她喊,也不会让她跑。五大三粗的李大嘴,已到了发疯发癫的地步,一只可怜的羔羊,怎么能逃脱一头恶狼的猎杀呢?
尕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头栽倒了,两眼一黑,她什么都不知道了。
尕秀一连在屋里躺了两天、哭了两天,没有出门。尕秀把胡杨林里发生的事,对她妈全讲了,她妈也陪着尕秀流了两天泪。尕秀妈不能不伤心,女儿年纪轻轻的,就遭恶人糟蹋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全给毁了,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尕秀说,我要告这个坏蛋。
尕秀妈说,告!不能让李大嘴占便宜。
尕秀说,让公家把他抓起来,让他坐牢。
尕秀妈说,那畜生,关他十年八年都活该。
尕秀妈说完这话,过一会儿,忽然想到这事儿有些不好办。她苦着脸,望着自己可怜的女儿说,哎,再想想吧。尕秀说,有啥想的,还怕告不倒他?尕秀妈说,闺女,我看不能告啊。尕秀妈毕竟年岁大些,经历的事儿也多些,她认为,李大嘴有他当书记的舅舅袒护,不但告不倒李大嘴,反而会把自己的名声告臭了。一个臭了名声的女人,可是什么都毁了呀。
尕秀妈把心里的顾虑对尕秀讲了,尕秀心里风霜雨雪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半晌,尕秀哽着声音说,难道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尕秀妈长长短短地叹着气,颤着声说,谁让我们命苦啊。
过了一个月,来顺总算从固堤工地上回来了。一回来,来顺就心急火燎地去找尕秀。
尕秀不在家。尕秀妈说,尕秀到塔里木河边锄玉米去了。
来顺一听,着急地说,伯母,我不坐了,我去看尕秀。说完转身就出了门。
尕秀正在地里锄玉米。听到一串嚓嚓的脚步声,尕秀扭头一看,看到是来顺,脸上立刻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神色。可眨眼工夫,尕秀脸上的欣喜立刻消失了,显出的是一副忧伤的样子。尕秀觉得自己已不是原来的尕秀了,不再是那个纯洁无瑕的妹子了,而成了一个身子肮脏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脸面来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呢?
尕秀的冷漠,弄得来顺云里雾里的,不知咋回事。来顺心里一急,抓着尕秀的手说,你这是咋啦?生我气啦?尕秀还是闷头不说话。来顺更急了,又摇着尕秀的肩头,说,你咋不吭声?到底出了啥事?
尕秀本来不想把林子里发生的事告诉来顺的。尕秀早想过,一辈子把那件倒霉事烂在肚子里,对谁也不说。可是,当她看到来顺那痛苦的眼神,立刻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忍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下死死地抱住来顺,“哇”地一声号啕大哭起来。
尕秀终于把那事对来顺说了。来顺一下呆愣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一个男人,面对自己心爱的人的屈辱,比自己受了屈辱还要难过。只要是个男人,谁都咽不下这口恶气。而这种时候,一个血性男人,可能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
来顺二话没说,扭身就要走。尕秀知道这会儿的来顺心里想的是啥,也清楚这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尕秀死死拽住来顺不放,哽着声说,来顺哥,你不能硬来啊。接着,又噙着泪说,我俩的事就算了吧。算我对不起你。
来顺一下子蹲坐在地头上,用拳头狠命地捶打自己的脑袋,恨恨地说,他李大嘴不让我来顺好活,我来顺也不会让他李大嘴好过……
快入冬了,天气渐渐变得凉了,洛布海子周边的芦苇已是金黄一片。这时,海子里还没有结冰,还可以划着卡盆下海子打鱼。
李大嘴就经常下海子打鱼。可是有一天,李大嘴下海子打鱼再也没有回来。队上慌忙组织人下海子寻找,等到把李大嘴从海子里捞上来时,李大嘴早已淹死了。人们惊奇地发现,李大嘴的身上缠着一条挂网,看来是让网缠住活活闷死的。这就怪了,李大嘴怎么会让网缠住呢?李大嘴的死让人觉得十分蹊跷。
后来,公安上来了人,拿出网让队上的人辨认。大伙儿认了,都说那网就是李队长家的挂网。公安上的人查来查去,最终也没有查出个眉目来,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有人私下里說,还不是李大嘴坏事干多了,应了那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呗。
过了一些日子,又过了一些日子,尕秀和来顺结了婚。不过,尕秀没去来顺家,是来顺倒插门,成了尕秀她妈的上门女婿。婚后,小两口一块儿下地种庄稼,一块儿下海子打鱼、割芦苇,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后来,尕秀还给来顺生了个胖小子。
洛布海子人家的日子过得平平常常。过了一些年,又过了一些年。谁也没有想到,洛布海子竟然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尕秀一家也同其他水乡人家一样,搞起了风情游。在这儿,游人可以骑骆驼,爬沙山,划卡盆;可以钓野鱼,烤羊肉,吃抓饭;还可以捡野蘑菇,游胡杨林,听洛布民歌……
洛布海子,海子还是那些海子,水还是那汪水,林子还是那片林子,可它的名声早已传遍了天山南北。
谁也说不清楚,洛布海子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人们有理由相信,那片神奇的水域,还会发生许许多多新的故事和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