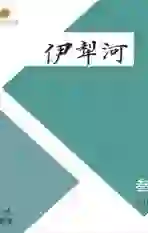从初春到深秋
2017-07-26程静
程静
灾难突然降临,令人惶恐不安,一股莫名的铁腥气在直觉中蔓延,生涩、坚硬,但还没有感觉到天塌下来般的黑暗与重负,因为还不知道灾难的深度,就像刀子切割肉体,看到皮肉绽开,鲜血流动,疼痛却还未到达。但疼痛紧跟其后,而且一旦到来,只能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持久。伴随疼痛而来的是对人世产生的沧桑感,内心的冷,如同冬天的寒意渐渐深入骨髓、血液,直到进入精神和意识,疼痛,终于变成无法消退的疤痕,成为命运和劫数。
妹夫身陷一场复杂的官司,说复杂,不是因为官司本身,而是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特殊事件,令人难以叙述。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身处社会种种决策与制约之中,个人的悲哀既是命运的,也是强加的。
整个四月和五月,全家人的心都悬着,因为不明真相,所以在现实与想象造成的各种惊慌中度日,唯有一点醒悟,就是所谓平民阶层,其实是一群束手无策的人,没有任何抵御能力,渺小、脆弱,如同被雨滴和落叶砸到的蚂蚁,哪怕一个不经意的意外,也会成为全部的伤害。我匆匆回到自己家,收拾了几样东西,就去了妹妹家,晚上,兩个人分析事情的前前后后,猜测、回忆、判断、想象,涉及的问题大部分超出了两个女人的生活经验和见识,虽然身处体制与人情世故的网中,但有很多领域都是陌生的,因为不关注,因为不涉及。十多天过去了,妹夫仍处于“失踪”状态,没有任何消息。我和妹妹几乎没有过真正的睡眠,常常只是刚合眼,就突然心悸般地醒来,看着某处,目光凝聚,神思涣散。客厅里的灯整夜地亮着,一方面是觉得妹夫会突然回归(潜意识里对现实不接受而产生幻想),一方面想着可能会有知情人过来透露一点消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具体的情形和位置。此时,全家不仅在突发事件的席卷中失去方寸,而且对以后将要遭遇的官司、摧毁、折磨,以及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都是毫无预料。
毫无预料,是觉得与厄运尚有距离,不是上苍可能眷顾,而是家里每个人的性格,因某种单薄而形成一贯的谨言慎行,落于人后,甘于平庸,以一种隐没的状态来回避是非祸端。这样的处世态度,不祈求好运,惟愿上苍忽略,只有忽略,不管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还是地下飞来的横祸,都不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对于弱小者而言,忽略就是眷顾。
可现实情况是,厄运并不在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与善恶也无甚关联,它是命运中的不可知,动荡因子,因毫无规律而无法掌握。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厄运一直存在,它蛰伏、隐匿于生命暗处,不露半点痕迹,如同一只悄无声息的猫,在某个时刻,突然跃起,优雅地显示出爆破般的力量与能力。或许也曾显露痕迹,只是很难察觉,就像妹妹后来也说过妹夫出事前的一些反常,事情已经露出端倪,她却毫无戒备。生活平静了许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忘记忧患,警惕的触角渐渐变得松散、迟钝,这不是谁的错误。
我每天都会回一次或数次父母家,担心他们担心,如果我不去,爸爸多晚都会到我家来,询问情况或者只是沉默地坐一会儿。而我除了让他和妈妈注意身体,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个事情关乎的层面,不是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我爸已退休十多年,虽然也曾在单位当过不大不小的领导,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思想言行受特定历史时期的塑造与影响,与现时代风气、形势都隔着距离,他的人生经验大多变得陈旧,每当听到我说单位里政治学习,他都要叮嘱我,该表态的时候一定要表态。这是他总结出来的自认有效的保全自身的生存之道,我不信,但也没有完全不信,所以常常人云亦云,并不独立。时代不同,政治环境此一时彼一时,重要的不是这些表面,而是对一些事物本质的认识,比如那些隐藏在权力四周的世道人心,那些在利益面前的陷害、倾轧、落井下石、幸灾乐祸,都会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不断地重复与上演。
但这些似乎已从他的记忆和经验里剔除。爸爸性格温和、宽厚,当然,这些词汇的背后还包含着懦弱、妥协、老好人、中庸,好不容易学到的一点丛林法则以及并不硬朗的手段,离开某种环境后遗失殆尽,而且年岁越大,想法越天真,且为世上天真的事情泪水涌动,小动物对他的依赖、院子里的花朵和蔬菜、外孙的软语央求,甚至对那些上门推销者的谎言和表演,他都毫无防范,有一次,在可恶的软磨硬泡中,他价格不菲地买下了人家四把同样的梳子……失去原则的良善,使他对周围的人和事缺乏理性认知,甚至毫无认知,我常常不能分辨他是更加清澈,还是越发昏聩,举止不像一个有过经历的老年人,沉稳有力,而是脆弱无助,像一个孩子那样需要他的孩子给予陪伴和安慰。
或许从前的他并非真正的他,只是社会、家庭需要的角色,一种强撑的姿态,真实的他在内心缩小,小到自己都快要忘记,时间终于使他脱离羁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他曾经跟我说过:退休之后才感觉到生活刚刚开始。孩子们长大成人,他终于可以卸下包袱与伪装,对世界对日常撒手,不管、不问、不做主。接下来的十多年光阴中,他常常沉溺于一个人的劳作,一片不大的菜园,花了不少心思,即使菜叶上生了虫也不打药,只是用手指将虫子一个个捉下来。他不过问现实的琐碎,凡事我妈说了算,也很少回顾过去,好像所有往事,不论羞耻或荣耀全部消失于记忆,他没有经验可以传授,也没有告诫需要叮咛。这就是他的选择,放弃这个世界。同年轻时候的激情相比,他现在如同一个高烧退去的人,进入一个安详、释然的睡眠状态,也如同一条逆流而上的鱼,把生活教给他的还给生活,靠近最初的快乐之源,也靠近最后的栖息地。暮色降临,他希望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能够与生活和谐共处,平安地度过晚年,但现在,生活的水面被丢下一粒石子,水花扑溅,击打的是一个人的猝不及防,他理解不了这样的恶作剧。
我们需要尽快请一个律师。大号的茶水杯里,每一片茶叶都像复活了一样碧绿轻盈。听说这个人在法律界很有名气,但我们不为所动,这个社会浪得虚名的人不在少数。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和丈夫、妹妹仔细倾听每一句话,努力在他的汩汩话语中观察、寻找,是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值得信赖并托付的人。毫不怀疑,眼前的这个人业务精通、思维敏锐,闲聊之中似乎无所不知,腐败与时局,谣言与内幕,言论大开大合,不纠结小处,法律的公正或者缺失贯穿所有新闻,令人感到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完全在于对法律的了解程度。暗条的格子衬衫似乎非常适合他,使他看起来洒脱自得。可我觉得他有些夸诞,并不那么正经,与想象中的律师形象不一样。但正经与不正经如何区别?我开始隐约觉得,一种属于正直或良知的气息如同从半开的窗户里漏进来的风,在屋子里不经意地缭绕。他身上的江湖气,或许只是一件外衣,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那样的一件外衣,内心虚弱的人披着强悍的外衣,奸邪之人披着忠厚的外衣,外衣出于对外部世界的不适应,是一个人的武器,同时包含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我爸也曾身披世俗的外衣。而我们最终决定相信这个律师,不是他的外衣,而是他对案件的不确定。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是一个名律师的水平,而是在这个案件之外,我感觉到他察觉了事件背后的某些因素,那些使人冤屈却喉咙喑哑的根源。其中的复杂性,犹如水草遍布的曲折水域,只有深谙其道,才能找到解救的方法。一切但愿如此。
不管他的外衣是什么样子,有一个身份我们必须明了,一个生意人。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依赖和托付,打官司需要钱,而且是个不小的数目,以他的职业素质、人脉以及一定程度的钱,一切就足够了。我想起一句俗语: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不多的积蓄一次次交出去,如同水位下降的堤坝,渐渐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我对钱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原先认为钱很重要,但不认为最重要,这个世界上比金钱更贵重的是爱情、亲情、自由、尊严,对一些人来说还包括艺术、信仰,它们都比金钱更加令人珍惜。应该说,这些认识都是对的,但不对的一点,就是它们不能拿来与金钱作比较,就像物质与精神无法比较,它们相互依存,一方常常因为获得另一方而得到提升和成全。这些认识不是来自生活经历,而是因为没有经历,没有遇到更大的难题,我还不懂得金钱的真正价值,对钱能救人、救命,甚至改变命运走向的强大力量没有体会。事实上,对于那样一个沉甸甸的物质,我和它始终隔着一种传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相遇。
籌钱、找人,所有的力气都没有白费,因为律师的介入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助,我们开始了解事情的原委与进展,很多时候,我一边听律师分析,一边经历着过去了的现实,倒述灾难,你会发现,每一个情节都走向陷落,每一个片断都处于险境,而在这期间,没有出现过一次希望。身在其中,绝对联想不到它们之间的关联,然而正是这个想不到,才导致了灾难。“生活底部藏着的残暴,让你痛感流水里也有刀剑”(雷平阳《浮土》)。苹果花已经开过,细小的青果掩映在绿叶问,走在路上,我不记得这些树木是什么时候度过的倒春寒。春天的阳光最具蛊惑性,温暖、芬芳,众多的蜜蜂围绕花朵,在弥漫着暖意与香味的风中鼓动翅膀。可是这些并不能确定危险已经过去,一场大风袭来,树木摇晃,碎屑飞上楼顶,气温急剧下降,深夜,人们被下雪的声音惊醒,第二天,满地残枝败叶,白雪压着花朵和绿叶,春天既意味着复活与重生,也意味着蒙难和不幸。从律师那里回来,我们讨论事情,爸爸神情专注地听着,一言不发,在他遗忘许多事情之后,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仍然充满敌意。
楼道里的灯坏了,黑暗中,我感觉到他脚底下的犹豫和试探,就伸手扶他,抓住他胳膊的那一下,突然感觉抓空了,好像袖子里并不存在一只胳膊,他的身体不知何时缩小,衣服空荡,不仅仅是胳膊,整个人都显得孤单和空旷。我闭上了嘴,停止了滔滔不绝,我说得太多了,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我一直跟他说这些事,是不是告诉他我们的磨难永不结束?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抱怨,抱怨他的软弱和回避?这是多么自私,又是多么残忍。该经历的都已经历,现在,他产生了困倦,我为什么不让他在没有困扰的梦境中,如同一个老婴儿,在最后的旅行中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既简单又轻松?
我不愿让我的亲人承受任何苦难。这样的话说出来,如同爱情的表白一样难以分辨其中的真切和缥缈。
一张不大的方桌旁边,围坐着爸爸、妈妈、妹妹和我。四个人,一边坐一个,吃饭、说笑或争吵,黄昏的燕子低飞,将啁啾之声和粪便一起丢向我们的窗台,玻璃上留下几处白色斑点。而在不同的光线中,落在窗台上的还有岁月的雨滴、落叶、云影、从雪山那边移过来的朝霞和晚霞……
这是我在上中学之后的记忆,而在此以前,家里并不止我们四个,还有爷爷、奶奶、三叔、四叔和最小的两个姑姑。但我对童年生活无法进行更多描述,许多往事都不记得,而且奇怪的是,同在一个屋檐下,我和妹妹的往事完全不同,我记得的事情她不知晓,她记得的事情我一概不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只是觉得蒙昧的时期在我身上似乎特别长久,这种状态,不仅仅童年,整个少年时代也都是恍恍惚惚、懵懂,不谙人事。直至现在,它们仍然是我披着理性外衣之下无法褪色的人生底片。我记得自己常在院子的葡萄架下画画、看书,阳光穿过葡萄叶片,光影斑驳,周围是另一个世界:天宇的光芒到达尘世,活跃而明亮,不停变幻出花朵、楼阁、羊群、马匹、幽灵、人影,灰尘像飞蛾一样在光束中旋转,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葡萄体内细小的水系发出巨大声响,盖过了春天的河流……往事虽不明朗,可如果想起什么,耳边就会莫名地听到铁器与铁器的碰撞声,咣当,咣当,从记忆深处传来,遥远而清脆。那时三叔结婚不久,三婶前额的发梢每天用铁夹烫卷,使她看起来崭新而亮丽。四叔和两个小姑正值青春,叽叽喳喳,脚步轻快,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他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一株草一样,随意拨开,然后从种着果树、蔬菜和葡萄的院落翩然飞过,外边,一定有一些年轻人在等。不断地进进出出,两扇铁门就在不断地打开与关闭、关闭与打开中发出声音。我听到了一种回声,那空间中震动的铮铮余音,轻微而持久,如同风中的细铁丝,颤抖于空廓,消失于幽深。后来新疆边境局势紧张,伊犁开始备战,几乎所有单位都在组织人力挖防空洞,兵团民兵日夜巡逻,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防患未然,许多家庭将老人和孩子送往内地。爷爷奶奶也回到了内地,直至多年后离世,在当初离开家乡的地方彻底离开,他们的坟茔旁边,长满中原山区的泡桐和野蔷薇。随后,叔叔和姑姑们也在那些年陆续离开新疆,不是因为局势,而是因为各自命运,死亡、迁徙、远嫁、逃离。一切分崩离析,不过两三年时间,一个大家庭产生的喧哗,最终像厨房将尽的烟火一样变得稀冷。
大部分事情我不知道,但记忆里,事情好像总发生于深夜。有人夜里起身,光线昏暗,影子飘摇,大人们快步走动,或隔窗呼唤,说话时压着嗓子,声音断断续续。我闭着眼睛,感觉到不同寻常,感觉到夜晚说话的人声和白天不一样,有时异常清晰,警句般在耳边字字句句地说出来,有时又很模糊,好像风雨中的呼喊,虚飘而含混。一切都显得那样失真。倦意再次袭来,朦胧中,听见铁门发出响亮而空旷的回响,咣当,咣当……早晨起来,夜间的寒气还未散去,院子里一片清凉,安静得如同白杨树上空空的鸟巢,突然想起夜里的事情,觉得只是一个梦境……
直到剩下我们一家。最后一年住在那个院子的时候,四个人,十多问屋子,大部分空着,里面零散堆积着一些家具和废旧物品,任其落满灰尘和昼夜变幻的长短光线。瞬间的沉寂与荒芜。我觉得世间没有长久的事情,什么都会崩散,像倒塌的沙丘一样消逝、离析,惟有时间永恒。漫长的时间中,每天都将面临一个明天,但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包含什么,我感觉未来就像一个模糊的面具,隐藏着各种变幻,不在于变幻了什么,而变幻本身,即是真相和本质。起先,这种察觉令我感到惊恐,可此后的经历,越来越证实这种察觉,它们并非来自感性和想象,而是事实,只是惊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化解,成为内心的隐隐不安,如同阳光底下的阴影,与人紧密相随。
四个人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数十年来从不改变。直到现在,吃饭的桌子已更换数次,我和妹妹每次回到父母家,也仍然坐在从前的位置上。我常常以为这个世界不会再发生什么变故,什么都已发生过,只要降低欲望,就会减少波折,当然还会有生死,但死亡不算灾难,只是规律。偶尔,我会突然在他们三个的背后看见一团浑然的白雾,虚空、深不可测,就像站在山顶上看到的那一片空茫。我不知道这样的幻觉因何而生,但我并不探究,其中的隐喻一眼就能看得到,人生虚无,失去是一种必然。我们总会彼此失去,这一天总会到来,但在何时,无法预知,我就像一个身藏珍宝的人,时刻警惕被时光和命运追杀。现在只是继续逃亡。
起先,我整天陪着妹妹,担心她承受不了打击而出现意外,但我忽视了另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成年人和母亲,在灾难面前,会出于生存本能而忘记哭泣,她要照顾孩子,安慰八十岁的公婆。没有办法,一些事情只能独立面对,即使最亲与最爱的人,也无法事事替代,于他人,更是无关痛痒。灾难,以魔法般的力量令人快速成熟。她在外面表现得很平静,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但还是有一些风言风语,人心不同,面孔各异,有人走过来,说些“想开点”之类的安慰话,或豪爽,或真诚,或按捺住好奇与兴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同,在人群当中,既然会接收到温暖、敞亮、无私与援助,自然也会接收到冷漠、麻木、无情与拒绝。这是生活显示内在平衡与公正法则的方式之一,没有绝对的美好,也没有绝对的恶意。而从人心与人性的缝隙间透过来的光亮,虽然有时短暂,只是一瞥,一瞬,但其中的善意,却让人觉得真实而长久。
八月,内地一些作家来伊犁采风。现在到新疆的人很多,在一些作家中,我发现使我产生好感的,都有一点相似,言语不多,但说出来的,多半与内心有关,他们的作品也是如此,关注生存状态,触摸灵魂反应,而不像那些新颖的词藻不断从嘴边滑过去的人,只是文字游戏,没有真正指向。这样的人属于大多数,我把他们当游客,说不上几句话,他们来到边疆产生的不由自主的优越感,或者一种故作姿态的谦虚,使我觉得不仅是对边疆,甚至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存在一种误会。这不是写作的事。沃尔科特说:“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不要问我的写作抵达了哪里,而要问我的生活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人的生活抵达了哪里,只是感到其内心的有限和世俗,尽管其中一些人的文字也很好,但我并不信任。
從草原回来,每个人都很兴奋。时值伊犁河谷最好的季节,天空湛蓝,草原碧色悠远,每一条河流都弥散着雪水融化后的冰凉气息。游牧生活还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一切都还坚实地存在,他们看见的毡房并不是景点上搭建的装饰物,而是一处处真实的毡房,毡房之中还同数百年前一样,气味腥膻,包裹着绵延的睡眠与生产,只是男人身上的佩刀不再用于战争,而是对付羊骨和肉。阳光使一切透明,草原清洁,所有的欲望都消失,人们目光明亮,看见许多不曾看见的事物,空中草原、地下石人、夏日积雪以及风与灵魂,更重要的是,自己看见了自己。这种体验并不常有,即使有,一生不过数次而已。离开伊犁那一天,本地文友在宾馆设宴相送。许多人喝醉了。出来时,我觉得如鲠在喉,喝下去的酒,全部聚积在胸口,仰望星星冰冷,旁边的欢笑不知轻重,在鲜花吐馨的花园旁边,突然产生无法抑制的呕吐感,伏在一个垃圾筒上,一下子吐了出来。我不知道这种强烈的呕吐感源自何处,此时离喝多尚远,平时也是可以喝一些的,更是毫无醉意,这种呕吐感很大程度上应该出自心理,而非生理上的不适,似乎不是要把酒吐出去,而是出于某种否定与拒绝。我想,这不过是一次偶然。在这之后,又参加过与文友们的几次聚会,每次都吐,喝一点都吐,后来一次干脆莫名其妙地吐出血来。我终于觉得自己强颜欢笑的时间太久了,所有的交往令人筋疲力尽。
九月,阳光仍然长时间悬挂在天上,晚上十一时以前天还亮着,这是令内地人感到惊讶的现象之一。天山在白亮的黑夜里显得格外绵长。这个时间之后,白天直接进入黑夜,夜色就像从天上抖下来的一块巨大幕布,哗啦展开,瞬间罩住了山川河流。没有黄昏的过渡,月光星辰突然出现。可是在越来越清楚的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哪件事情是没有过渡的,一件事是另一件事的阴影,一句话是另一句话的伏笔,从此处到彼处,都有一个过程,这个事情祸起妹夫不当的处理方法,无法推卸,可究竟什么是不当?许多事情经不起推敲。是一个人的罪与罚。然后事态像滚雪球一样叠加、失控,而在不断被异化的事件中,与此相关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渡、铺垫。
写到这里,正好也看到了网上热议的几宗案件:一个跨度21年的故意杀人案终于得到平反,这中间“一案两凶”引发的种种细节,无法准确解释,过程之离奇,堪比当代任何一部传奇小说;一个乡村青年,精心营造的婚房被强拆,举起手中的射钉枪当场将当权者射杀,是什么致使一个人心死,维权如此惨烈……每一宗都在网络上涌起一波一波的讨论,所有事件都迟迟得不到定论,其中人的性命与尊严不值一提。可我觉得世间没有复杂的事情,事实不会被湮灭,惟有人心。
不管有没有结论,每个人的生活都必须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如同屠格涅夫《白菜汤》里的那个女人,一个失去了独生儿子的穷寡妇——脸颊消瘦,眼睛红肿,站在小屋中央,“不慌不忙地从一只漆黑的锅底舀起稀薄的白菜汤来,一调羹一调羹地吞下肚去”,她说:“我活活地给人把心挖了去。然而汤是不应该糟蹋的,里面放的有盐呢。”——就是这样,任何事情,包括穷困、死亡、蒙冤、非难,什么都挡不住生活的继续。我和妹妹越来越平静,如果不走出来,把眼前的生活安排妥当,灾难不一定导致生活困顿,却会成为精神的困局。所以工作学习、老人孩子,一样一样都要照顾到。只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常,高烧、溃疡、突然到来的心悸与头晕,此起彼伏,时时发作。躯体的反应往往来自心境,冷暖自知,一切无法与外人道。就是现在,这些症状也没有消失,成了不正常中的正常,伴随我们,好像作为一种出了事情的家庭的标志。我发现妹妹额头上的丘疹一直长到了眉心和头发里,心情抑郁,气血郁结,她是离这个事情最近的人,厄运降临且自身承担,许多事情,再亲的人也无济于事。我无法安慰。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即使亲人,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苦痛和孤独,谁也无法替代谁。
到了十一月,在雪花照亮的路灯底下,冬天亮出了寒光。事情终于有了结果,虽然认为不公,但也只能如此,此时家人心态平和,与其说接受了结局,不如说接受了命运。
时代壮阔,如江河般滚滚奔腾,相比之下,个人再大的事情,也都是轻微、渺小的,可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骨肉相连,血浓于水,一个人的事故就是一个家庭的事故。而它带来的不仅是一个事件,而是心灵灾难,这种灾难遗留下来的恐惧将会无休无止,不仅令人感到死亡、疾病、离别等强暴般的力量,更令人感觉到命运当中那些不幸与灾难的不可逆转性,它们压过来,雷霆般轰鸣,谁也听不见个人的呼吸和叫喊。多丽丝·莱辛说:“东欧剧变后,那里的作家才发现了问题。”其实问题不是在剧变之后产生,而是在剧变之前,问题早就在那里,只是没有被发现,它被日常所遮蔽。许多问题都是如此,因为没有从一个高度审视而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意义。
我确定,我对此事的认知以及情绪并非妹夫的事件引起,而是因为事件的延伸性,它对我的提醒,犹如石子落入水中,涟漪离岸,水波已推远。从此,没有什么能够抚平这暗涌的悲伤,就像一把刀子迫近心脏,疼痛、冰凉,虽不致命,但刀口之深,此生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