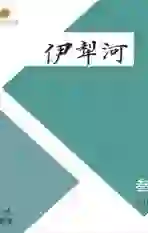扶贫
2017-07-26程静
程静
别克艾力的声音在电话里细微、断断续续,好像从他那里到我这里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经过山路、大雨、巴扎和迷路,终于找到了我,已经气若游丝,再加上汉语表达的障碍,我听了好一会儿才算明白,山里下着大雨,他的屋子里下着小雨……边地干旱,很少像今年这样多雨,整个早春,雨水清洗过的街道反射着光芒,植物润泽,空气清新,十多年前曾吐露玫瑰芬芳的这个城市的灵魂常常在雨后呈现……直到别克艾力说他家的房子漏雨,我才觉得羞愧,看待事物没有站在他人立场,雨水的清凉,并非人人都在享受,事物往往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带给人群的幸与不幸不能一概而论。
打电话给乡里的一个负责人,希望能够帮助解决,回答说不仅他们一家,土坯房基本如此,只要连续下雨,总有一些漏雨或倒塌,乡里正组织人力物资挨家查看。没有办法,只能祈祷。后来我再没有打电话问,觉得无法面对,问了又能怎样?房子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的是钱,而不是问候。
到了七月中旬,我决定去看一看。别克艾力的家在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的一个牧业村。尼勒克为蒙古语,意为婴儿,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称呢勒哈,其境内喀什河峡谷一带草原绵延纵深,古时候鹿狍成群,狼狐出没,直至清代,还是伊犁将军演兵、行猎、避暑之地,被称作围场。但草野苍茫,何为婴儿?我每次这样发问,脑海里都会出现一些画面:晚霞如同撕裂的丝绸,灿烂、冰凉,丝丝缕缕地落在山谷连片的芨芨草上,一个部落的人马行迹仓皇,他们需要尽快到达安营扎寨的地方。男子身背弓箭,右手时常摸向胯上弯刀。女人们衣衫黯淡,扶老携幼,头上发髻由于长时间奔走而摇摇欲坠。诸多的脚步和马蹄,尘土之下,青草来不及直立,就被车轮一次次地轮番碾压。一辆马车篷内,突然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声音稚嫩,好像破壳雏鸟般的清脆与纤弱,一听就知道刚刚降临人世,有人发现,那辆车底下的木板缝隙间不断有血滴跌落,落在草叶上,然后悄然渗进泥土。在遷徙或战争过程中,最使人为难的恐怕就是遇上妇人生孩子,可是这样的事情,谁也无法阻拦且预料,这是神的旨意,每次有新生命降临,都能感觉到神在近处,一只无形的手从每个人额前抚过,令人颤抖与喜悦。而在此地,这是出生的第一个婴儿,人们不禁喃喃出声,祈祷般咏诵:尼勒克,尼勒克……
虽然这些只是一个人的臆想,但大月氏、乌孙、匈奴、突厥、蒙古等的确都曾游牧于此,北部天山任何一片草原,不仅是大小游牧民族代代生息之地,也是对决之疆场,数不清的民族不断在此崛起或消亡,强盛或融合,漫漫风沙,最终成为最初的那一支渐行渐远的背影。时至今日,古代游牧生活早已消逝,但铁血与苍莽的气息从未消散,山河之间,依稀可见游牧文明遥远的轮廓与图景。
但边地并不因此而留下什么,总体上,除了青草,草原上空无一物,长风裹挟积雪的气息,凛冽、干燥,吹疼人的骨头和灵魂。与内地一些地域不同,古代遗存遍布,一脚踏上去,或许会踩到汉朝的一枚铜钱或瓦片,物质与文明皆在其中。对待历史,每个地域都会产生自身态度,对于这片土地而言,它不保存遗物,任何事物在它身上都不会留下痕迹,纷争与繁华随风而逝,事物的本质,不过是虚无与寂静。
加哈乌拉斯台乡所辖的这个牧业村,是我们单位的对口扶贫对象。可是一切都很难,地域偏僻,干旱缺水,民居分散山谷各处,如同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随意滚落。我们找不到要找的人家,只好站在路边等,路上没有人,好半天,从身后的山坡上冲下一位骑马的牧民,皮肤黝黑泛红,看起来粗犷、粗糙,听完问题,手一指:内(那)——个地方。我们也是新疆土著,根据他音调的长短可以判断出——那里,很远。虽然只是从这一家到那一家,邻居而已,却邻而不近,除了隔着栅栏或土墙圈起来的辽阔院落外,还可能隔着一片荒滩、一个山坡或无边的玉米地,远近的概念,消失于地域。道路湮没于青草,麦田整齐,到处都是旺盛的生命。一般有水和地势平缓的土地,已经被开发成连片的农业区,深山、浅山和盆地半荒漠地方才是牧区。一路上,牧区与农区交相混杂,大地繁华,贫困的是大地上的子民,要么物质,要么精神。
别克艾力的家坐落在自家草场上,平房独立,野花清凉,铁丝网长长地拦在路边,白蝴蝶从上面飞过,情景好似浮现于现实的一个梦境,美好得令人出神。
可是再梦幻的地方也脱离不了物质,现代生活已经到达任何一个偏僻之地。别克艾力一家四口,他和妻子古丽,还有一个9岁的男孩和11岁的女孩。生活来源主要靠别克艾力在外打工。三问土坯房,平房围成的小院简陋、空荡,院子里的野草和外面一样蓬勃,如同被圈起来的另一小片草原。这样的院子如果放在我家,我爸妈早就种上了各种蔬菜,所以汉族人看了,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种蔬菜?我理解的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懒惰与否的问题,他们能从数百只羊群中辨认出自家的羊,却无法分清种子与种子之间的差别。不同民族面对的世界不同,世界经验就不同,农耕民族面对的是土地,播种、耕地、秋收,游牧者面对的是自然,森林、草原、山川。虽然现在新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定居成为趋势,但这些刚刚放下牧鞭的人,仍然处于一种惯性,一时难以适应,“都不过是些牧羊人,终生不过依循了血统的教训”。(张承志,《正午的喀什》)
别克艾力两口子不会汉语。我们的对话,是同去的一个哈萨克族同事做的翻译。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懂汉语,意味着不能融入,脱节,生活的局限性更大,与社会以及大多数人存在距离。别克艾力小学文化,没什么技能,最擅长的是放牧,但目前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羊。
这些都写到了工作手册上,等回单位时汇报。到了午饭时间,炕桌上只是一些掰开的馕,几碗奶茶。粗茶淡饭。但这些不能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少数民族饮食基本如此,即使拥有数百只羊群的家庭,也不会天天手抓肉。以在此地几代人长久生活之经验,我知道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生活,对大多数少数民族家庭而言,无论城市乡村,这一家午餐与那一家几乎没什么区别,习俗而已,或许没有区别的还有:奶茶的沏兑方法,地毯上繁复的花纹,容易沸腾的歌舞和欢乐,以及类似于不思进取、满足现状的平和状态。
说到平和状态,这常常是令人感动又觉得不可理喻的一面,不管贫穷到什么程度,所走访的人家,在他们脸上几乎看不到愁苦和不满。默默劳作,默默等待,默默打扫庭院,默默铺上餐布和茶碗。为什么如此平和?又为什么甘于现状?我原先分析: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整日面对的是天空和原野,内心经过自然地理的无形塑造与影响,心灵纯朴简单,对生活的需求也简单,面对时代繁杂,无法快速适应,他们本能地以一种自然所赋予的原始力量对抗陌生,在无法知晓的事物面前保持沉默,在沉默中保持自身传统与本质。
或许并不是这样,一切都只是猜测。不过,每个民族心理不同,对于民族中的少数部分,他们的内心,的确有着汉民族或者说农耕民族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
冬天时候在特克斯县齐勒乌泽克村,随“访惠聚”的下村干部一同看过哈萨克族妇女刺绣工作间之后,大雪仍然不停,车辆无法行驶,晚饭就在一个村干部家吃,同去的还有几个村民。餐布上仍然只是奶茶、馕、酥油,以及夏天时候从山上采来的野酸梅和黑加仑熬成的果酱。说笑一会儿,主人随手拿起冬不拉,弹唱了几首民歌,异域情调瞬间在空气中飞扬。其中《黑黑的眼睛》每个伊犁人都熟悉,每次听到,都觉得是在夜晚的白杨林,歌声在密集的枝桠间缭绕。作家王蒙尤其喜欢这首维吾尔民歌。王蒙在伊犁巴彦岱乡生活了7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学会了许多伊犁民歌,但他承认始终没能学会这首歌,1973年王蒙离开伊犁,1981年重返时再次听到,他在散文《新疆的歌》中写道:“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我觉得难学之处,不是他认为的北疆民歌比南疆民歌“更散漫,更缠绕,更辽阔”,令人在“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抒不完的感情连结如环”的旋律中陷落和痴醉,而是因为往昔的伊犁——白杨深处的城——一切深沉得难以表达,而且了解越多,越觉得唱不出那个味道。
坐在主人旁边的一个老人接过冬不拉,唱了一首《康定情歌》,居然是哈萨克语版。后来介绍,他是这个村的老支书哈尼亚提,早已卸任。老支书有一颗年轻的心,喜欢歌手刀郎的《喀什噶尔的胡杨》,唱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咬字清晰,却仍有维吾尔人说汉语时的特殊发音,自成幽默,我们哈哈大笑,称赞他汉语歌曲唱得好,他也很高兴,说读过李白的诗,知道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冬不拉响起来,每个人不仅唱本民族的歌,也唱其他民族的,曲风混杂。坐在地毯上的十来个人,一半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每个人都是出色的歌手,轻轻松松地就表现出上苍赋予的抒情能力,热情、爽朗,声音明亮,令人感受到游牧文化对后世子孙强大而绵延的影响力。而抒情能力,在《诗经》里面纯真且酣畅地表达过之后,早已在一个浩大的群体中渐渐失去。我们几个汉族人,打着节拍,跟着哼唱,却不自然、不自信,虽然一同沉浸在欢乐中,但创造欢乐与被感染的欢乐并不是一回事,心灵状态肯定不同。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很好解释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舒展?抒情能力又是何时失去的?在新疆,歌舞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葡萄架下、果园、庭院,还是在田间地头的一片空地,只要情绪到了,随时都能歌舞起来,情绪是一盏灯,随时点亮,随时熄灭,没有任何先兆和计划。可是在歌舞即兴盛开的情况下,牢牢坐在位子上的,往往是汉族人,真是太可怜了,好像需要扶贫的不是其中某个人,而是那些手脚没地方放的人。
而更多的时候,财富无法被看出来。我们曾在山上遇到一座毡房,走进去,只有女主人。炕上铺着陈旧的羊皮褥子,灰尘虚浮,一个收音机是最重要的家电,带来外部世界的信息。腥膻的气味在毡房中弥漫。他的丈夫去放羊了,家里有二百多只羊,数十匹马。她很抱歉用来待客的茶碗的粗陋,漂亮的茶具都在山下定居的房子里。原来他们在山下有房子,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老人和孩子都在山下。定居是为了从艰苦的游牧生活中解脱出来,但为什么仍然游牧?她说:习惯了嘛。我理解的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夫人有刚柔异性,言音不同,斯则系风土之气,亦习俗之致也”(季羡林),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习俗,游牧民族对牧场的眷恋,已经融入血液骨髓,成为无法克服的生理需求,总会在草木蓬勃的季节,他们赶上羊群,返回草原,找到家园,重新成为自然之子。就是这样,当一个民族认为车子、房子是财富的时候,另一个民族在拥有众多羊群和马匹之后,仍然还是会住在透风的毡房,一日三餐喝着奶茶。他们不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而是依照自己的生活秩序、生活安排,他们拥有自己的世界。
但是这些已经令人难以想象和猜测,因为大多数人形成的一种生活形态,似乎代表了人类文明,人们只确认这一种生活方式,而那些属于少数人的生活,将会在强大的社会进程中被逐步消解、淡化。这使我想起歌舞中的冬不拉,面对现代生活,他们内心是否有两把冬不拉,传统冬不拉如何应对现代冬不拉?不同的音质与节奏,他们如何做出内心的翻译?我感觉到他们表面的平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存在着一个不被了解的地带。不过,可以看出来的是,这一家收入还比较可观,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在乌鲁木齐上大学,一个在县城上高中,女主人说起来,语气轻松而自豪。
当时秋天正在接近,阳光猛烈,山上积雪不化,低头吃草的羊只如同深草中的石头,一动不动,云朵飘动的影子在大地上掠过,如同死亡的阴影掠过,我感觉万物朝着同一方向奔涌。贫穷并非来自传统,它有失尊严,也不道德,可是对于财富,不同民族,就会有不同的标准和看法,财富对一些人意味着物质,但对另一些人,还有可能是信仰、自由或音乐。
世上没有惟一的生活方式,或许也没有先进生活与落后生活的划分,我觉得最好的生活方式应该与内心的舒适程度有关,在一个地方,安放肉体,更安放心灵。
远远地,我看见别克艾力的小儿子像兔子一样往家跑,他看见了我们,赶紧回去报信。他家的房子不漏了,夏天时候已经进行了维修。小儿子坐在我旁边,身上散发出温软的气息,让人感觉身边偎贴着一个毛茸茸的小动物,眼睛清澈,像他的父母一样没有阴影。我问别克艾力夫妇我可以做些什么,古丽说她希望能有一些鸡苗,这样大的院子,养个百十来只没有问题。我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满院子鸡飞鸡鸣的喧闹场面,他们养鸡其实没有别的方法,放在草场上任它刨食,散养而已。但正是这种方法,鸡才是真正的草原鸡,我想到时候不要等到他们拿到巴扎上去卖,号召一下周围的同事朋友,就能销售得差不多。其实不管时代怎样波澜壮阔,对于个体,面对的永远只能是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理想在现實中常常会沦为一种虚幻,无从着手,务实的看法应该是,只要付出劳动,就能在大地上立身,劳动是真理,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就是这样,安于现状,相信未来,对生活有一些计划,就是一种看得见的富裕。我心里做了计划,准备明年春天的时候去买些鸡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