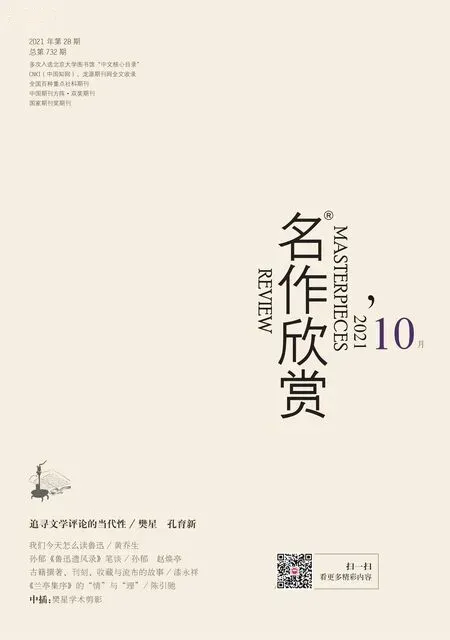论傅山弘扬国学的贡献与意义(上)
2017-07-15山西尹协理
山西 尹协理
论傅山弘扬国学的贡献与意义(上)
山西 尹协理
在清代初年民族危亡之时,傅山等一大批学者抱着“亡了国家,但不能亡文化”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奋力研究与弘扬国学,为国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傅山对狭义国学的整理与研究,包括了全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其范围之广,非一般人所能及。
傅山 国学 爱国情怀 知识分子
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一般已不是指学校,而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了。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章炳麟等人所说的“国学”仅限于汉文字记载的“经、史、子、集”,并不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献与学术文化。那么,少数民族的学术文化,如“藏学”“蒙学”等是不是“国学”呢?毫无疑问,当然是。于是,“国学”就有了两种涵义:一为包括少数民族学术文化在内的中华学术文化;一为汉族的学术文化。这样,我们便可以把前一种涵义的“国学”称为“广义的国学”,而把后一种涵义的“国学”称为“狭义的国学”。本文所说的傅山弘扬国学的贡献与意义,指的是“狭义的国学”。
至于佛教属不属于“国学”的范畴,要有所限定。我们知道,佛家起源于古印度,现在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因此,就“佛教”而论,它不属于中国的“国学”,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皇权、儒学、道教的争斗中已经逐步本土化了,即中国化。因此,“中国佛教”毫无疑问应该属于“国学”的范畴。《四库全书》把中国僧人的著作,如《弘明集》《广弘明集》《法苑珠林》《五灯会元》《宋高僧传》等多种佛学典籍收入“子部·释家”,将佛教视为诸子中的一“子”,就已经把“中国佛教”视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部分了。因此,“中国佛教”属于中国的“国学”应该没有争议。
由于学术界对“国学”的定义尚未统一,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提出一种意见,参加大家的讨论。
众多的国学研究成果
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发现傅山对狭义国学的整理与研究,包括了全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其范围之广,非一般人所能及。
在金石文字音韵学方面,新编《傅山全书》已经收录的有:《石鼓文集注》《尔雅注疏批注》《广韵音义批注》《六书索隐批注》《隶释批注》《杜诗韵字归部》《春秋人名韵》《西汉书姓名韵》《东汉书姓名韵》。在1991年版《傅山全书》中,除了三个《姓名韵》之外,均未能收录,使傅山在金石文字方面的研究和贡献不能彰显。2016年新编的《傅山全书》则增加了《石鼓文》《尔雅》《广韵》《六书索隐》《隶释》《杜诗韵字》六部著作,大大丰富了傅山在金石文字方面的研究资料。
在经学方面,新编《傅山全书》已经收录的有:《周易兼义批注》《毛诗注疏批注》《诗经物类编略》《仪礼注疏批注》《书小楷曾子问批语》《春秋左传注疏批注》《左传集锦》《春秋人名韵》《吕氏春秋批注》。其中《周易》和《仪礼》是新编《傅山全书》时加上的。傅山对《周易》肯定有很深的研究,但过去却没有见到他对《周易》的批注,新编《傅山全书》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仪礼》《周礼》与《礼记》的批注,旧版《傅山全书》均无,很容易给人们造成傅山不看礼书的印象。这次收进了“三礼”中的一部,虽然是个残本,但也能证明傅山并不排斥礼书。
在诸子学方面,新编《傅山全书》已经收录的有:《墨子校注》《管子批注》《管子评注》《鹖冠子精语》《庄子翼批注》《荀子批注》《荀子评注》《淮南子评注》《说苑批注》。其中《墨子校注》是新收入的。
在佛学方面,新编《傅山全书》已经收录的有:《金刚经注》《楞严经批注》《五灯会元批注》《女经》《翻译名义集批注》。
在正史方面,新编《傅山全书》已经收录的有:《史记列传批注》《汉书批注》《后汉书批注》《晋书批注》《宋书批注》《南齐书批注》《梁书批注》《陈书批注》《南史批注》《魏书批注》《北齐书批注》《周书批注》《北史批注》《隋书批注》《新唐书批注》《新五代史批注》《宋史批注》《金史批注》《元史批注》《西汉书姓名韵》《东汉书姓名韵》。
在野史和地理方面,新编《傅山全书》已经收录的有:《战国策批注》《孔氏谈苑批注》《拾遗记批注》《云溪友议批注》《宣室志批注》《路史后纪批注》《老学庵笔记批注》《睽车志批注》《蠡海集批注》《西京杂记批注》《侍儿小名录拾遗批注 》《李卓吾汇选见闻雅集外史类编批注》《山海经物类编略》《傅史》。其中有几部也是这次新编《傅山全书》时新收入的。
在文学方面,新编《傅山全书》已经收录的有:《古文苑批注》《张融海赋简评》《文选批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杜诗通批注》,还有剧本《红罗镜》《齐人乞食》《八仙庆寿》。
在书画篆刻艺术方面,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成本成篇的著作,但在《杂记》《家训》等文中都有大量的有关论述,并且给我们留下数量可观的书法、绘画和篆刻作品。200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傅山书法全集》收集了傅山大量的书法作品,但仍然没有收“全”。1965年和1982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两次出版的《傅山画集》更是只收录了傅山绘画的一小部分。傅山的篆刻还没有人认真收集和全面整理出版。广东学者苏海强先生在《北地孤峰峙印林——傅山篆刻世界探幽》一文(见《中国篆刻》2016年4、5月,总第8、9期)中说,傅山的篆刻,除了大家公认的西泠印社所藏的白文印“韩岩私印”原石,与清代岭南收藏家、篆刻家潘仪增所辑《秋晓庵印存》中“披云”印蜕所附傅山题刻的四面草书边款墨拓外,广东书画、印章收藏家罗建峰先生(字云亭)的锄月庐收藏的近万方流派印中,有三十多方傅山篆刻原石。苏海强先生依据这些作品,对傅山的篆刻评价极高。但太原王新德先生对锄月庐所藏傅山篆刻原石有疑义,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傅山书法作品的真伪有一些也需要讨论,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傅山书法的真伪与评价的几个问题》,就几件“傅山书法作品”的真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文即将发表。
在医学方面,新编《傅山全书》已经收录的有:《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批注(国家图书馆本)》《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批注(北京大学图书馆本)》《黄帝素问灵枢经批注》《傅青主女科》《产后编》《傅氏家抄医学抄本》《临产须知全集》《产科四十三症》《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小儿科》《大小诸症方论》。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三部关于《黄帝内经》的批注。过去医学界对傅山的医学著作一直持有争议,甚至连《傅青主女科》这样的著作也有人怀疑是后人的伪托,似乎傅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医大夫而已,对医学理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更不可能有医学著作问世。而三部《黄帝内经》批注的发现,则有力地证明了傅山对中医学不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对中医学理论同样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他曾经著述过医学著作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这些成部、成篇的著作外,《傅山全书》还收录了傅山大量的《杂记》《杂文》《经子解》(包括《百泉帖》)《家训》等,这些杂记、杂文中,都包含了许多对传统学术文化即国学的研究成果。
上面列举的仅仅是新编《傅山全书》收录的部分,还应该有大量的傅山对传统学术文化即国学研究的著作和杂记深藏在博物馆和图书馆,或者散落在民间,需要进一步发掘。
弘扬国学的全部
傅山以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弘扬国学就要弘扬国学的全部,而不是像过去只重视“四书”“五经”那样只重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傅山十分重视全部的诸子学著作。傅山一反过去统治者只重视“四书”“五经”的偏向,主张“经子平等”。他最著名的言论就是:“经子之争也未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孔子》《孟子》不称‘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见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岂不皆发一笑?”(《傅山全书》卷三十八《经子之争》,第三册,第71页)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文章已经很多了,傅山学社曾于2016年8月专门召开过傅山“经子平等、诸子平等”的学术讨论会,并将会议论文整理出版成《经子平等、诸子平等》一书(三晋出版社2017年版),因而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只是想强调一个问题:傅山研究过的诸子,除了本文第二部分列举的之外,从他的杂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研究过《申子》《商君书》(亦称《商子》)《论语》《孟子》《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又称《吕览》)《论衡》《太玄经》《抱朴子》《裴崇有论》以及邵雍、二程、朱熹、陈亮、许衡、刘因、王阳明、王龙溪、罗洪先、薛瑄等人的著作。也就是说,傅山研究的是诸子学著作的全部,这是与清初其他学者不同的地方。“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对金石学、音韵学等有较深的研究,但对于先秦诸子却研究较少。黄宗羲对于先秦诸子,主要是研究“四书”,其著作有《孟子师说》(《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但对于其他诸子,则少有问津。王夫之著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吕览释》《老庄申韩论》等,他肯定老庄道家学说,但排斥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法家的学说。他说:“损其心以任气,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而毒及万世者,申、韩也。”(《王船山诗文集·姜斋文集》卷一《老庄申韩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页)而傅山则不同,他说:“申、商、管、韩之书,细读之,诚洗东汉、唐、宋以后之黏一条好皂角也。”(新编《傅山全书》卷四十二《杂记六》第三册,第7页)又说:“‘申、韩说得不好,却脚踏实地;王介甫说得好,却踏不着实地,所以王不成王,伯不成伯。’此语极有斤两。”(同上书,第49页)可见傅山对于申不害、商鞅、管子、韩非子的著作不但仔细研究过,而且评价还比较高。应该说,傅山研究了先秦诸子的全部,而“顾、黄、王”则不是。
第二,傅山主张经子平等,但并不是只重视诸子学,不重视经学,而只是在统治者不大重视诸子学的两千年后,主张“经子平等”,自然要对诸子给予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傅山在重视诸子学的同时,也一样十分重视经学,他应该对“十三经”都做过研究,只是没有完全保存下来而已。在傅山去世后不久,时任阳曲县(今太原市)知县的戴梦熊在《傅征君传》中讲到傅山的著作,只提到两部:一部是《性史》,一部是《十三经字区》(新编《傅山全书》附录四,第二十册,第40页)。在戴梦熊看来《,十三经字区》是傅山的重要著作。由此可知,傅山对全部“十三经”都是做过深入研究的,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都失传了。傅山曾说:“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注疏泛滥矣,其精处非后儒所及,不可不知。”(《傅山全书》卷三十八《五经四书》,第三册,第71页)傅山一方面认为,《五经》《四书》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也是为那个时代服务的,并不是千古不能变的“道统”,现在时代变了,这些内容也应该跟着变化。另一方面,傅山又认为,经学中的精华则需要继承和发展,“其精处非后儒所及,不可不知”。可见傅山一点也不排斥经学,只是反对只重视经学的偏向,反对把经学作为千古不变的“道统”而已。傅山的意思,就是要吸收经学中的精华,并依据时代的需要做出适应时代的改变和发展。傅山的这个主张,对于今天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值得借鉴。
第三,傅山在重视诸子百家的同时,还十分重视佛教和道教典籍的研究。傅山在明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寿阳县的太安驿拜郭静中为师,出家当了道士(新编《傅山全书》卷十五《甲申八月访道师五峰龙池不遇》、《傅山全书》附录六《刑部尚书任濬等人题本》),认真研究道教典籍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对于佛教,则不是每一个道士,也不是每一个儒者都会去认真研究的。如傅山的好友顾炎武(1613—1682年),就“生平不读佛书”(见《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2页)。与傅山同时而稍后的王夫之(1619—1692年)更是极力排斥佛道二教。他曾说:“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佛教)也,申韩(申不害、韩非子)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16—1317页)既然排斥佛教,也就谈不上认真研究佛教典籍了。而傅山则不同,他认真研究了许多佛教典籍,除了本文第二部分列出的以外,从他的杂记等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还一定研究过《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因果经》《四分律》《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大毗婆沙论》《转识论》《弘明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藏一览》等,涉及佛教的经、律、论、传全部典籍。傅山认为,佛教的典籍虽然过于繁琐,说“《老》简于《庄》,《孔》简于《孟》。简者其至乎!然而佛则愈繁也”(新编《傅山全书》卷四十三《杂记七》,第三册,第57页),但中国佛教也是国学的一部分,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异端”而排斥它。傅山说:“今之谈者云:‘二氏只成得己,不足成物。’无论是隔靴搔痒话,便只成得己,有何不妙?而烦以为异(端)而辟之也?”(同上书,第255页)这也应该是傅山与许多清初学者不同的地方。
第四,在史学方面,傅山不但研究“正史”,而且研究“野史”、地方志和地理书。“正史”指各代官修的史书,在傅山之前是“二十一史”,此后增加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成为“二十三史”,清代撰成《明史》后便成为我们现在常说的“二十四史”。所谓“野史”,是指非官方的私家所撰写的史书,又称为“稗官野史”“小说”。语出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45页)“稗官”是指与水稻田中稗子一样的采录民俗民情的小官。稗子是野生的,所以“稗史”便又称为“野史”。一般认为野史的可靠性很差,上不了大雅之堂。但野史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也有不少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说:“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第十三回原评)相比较而言,正史的史料更可靠、更权威,也更可信,但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及其他种种原因,也删去了一些本该记入正史的事情。例如隋代的王通,本来是真实存在并且有重要著作,又设坛讲学,在隋代有很大影响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唐代撰写的《隋书》却没有为王通列传(拙著:《王通评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7页)。与此同时,正史记载的大多是与朝廷有比较重要关系的事情,野史则记载了许多民间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正史所不可能记载的。而且野史是从民众的视角来观察历史的一个侧面,它摒弃了正史“为尊者饰、为贤者讳”的观念。由此,野史便成为正史的重要补充。傅山对野史情有独钟,他在研究正史的同时,还研究了很多野史,除了本文第二部分列出的成本成篇的著作外,在杂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傅山曾经研究过的野史有:《古史考》《博物志》《汉册秘辛》《逸士传》《刘向别录》《路史》《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墨庄漫录》《东坡志林》《江邻几杂志》《癸辛杂志》《渑水燕谈录》《沅川记》等。
除了野史,傅山对地方志也是重视的,如他的杂记中记载了关于“《静乐县志·人物》中收孙行者”的笑谈(《傅山全书》卷四十一《杂记五》,第三册,第206页),说明他看过的地方志也不在少数。
在地理书方面,除了本文第二部分列出的《山海经》外,傅山一定还研究过《水经注》(同上书,第205页)等著作。
可见,傅山不但重视正史,同样也重视野史、地方志和地理著作。
第五,在书法上,傅山既重视帖学,重视魏晋和唐代的真、行、草,也重视碑学,重视篆、隶,尤其是汉隶。关于这个问题,白谦慎先生已经说得很详细了(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傅山对书法的真、行、草、篆、隶均有很深的研究,但由于篆、隶是汉代和汉代以前的古法,至唐以后真、行、草流行,人们遂丢失了篆、隶的原貌,所以傅山更加重视篆、隶,认为真、行、草是从篆、隶演变而来,因此学习书法也应该先学篆、隶。这与傅山的“经子平等”“有子而后有作经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傅山在金石学、文字学、音韵学、校雠学、考据学、训诂学、医学、文学、杂剧等国学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并有一定的研究,为全面弘扬国学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总之,傅山弘扬国学,不是只弘扬国学的哪一部分,而是国学的全部,所以傅山的好友、大陵(今文水县)郭鈜在《征君傅先生传》中说:“(先生)奇才绝世,酷嗜学,博极群书,时称‘学海’。”(新编《傅山全书》附录四,第二十册,第44页)这是对傅山全面弘扬国学的很恰当的评价,也是傅山胜过“清初三大家”以至其他各“家”的地方。
对国学古籍的整理
国学古籍经过长期的社会变迁,流传到明末清初时,已经有不少失传了,保留下来的也有些错乱,特别是长期不被统治者重视的子学著作更是如此。即使像“五经”和“二十一史”(明代称“二十一史”,不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当然也不包括还没有写的《明史》,后来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加上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明史》,于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由武英殿刻印《钦定二十四史》刊行)这样的官方十分重视的国学典籍,由于流传刻印有许多版本,也出现了有少数文字歧义的现象。与此同时,有许多古籍,特别是先秦诸子,由于年代久远,句读与对文意的理解都比较困难,要研究国学,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国学古籍的校勘、整理与注释。
在前面列举的傅山的各种著作和杂记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些古籍的校勘、整理与注释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对过去官方不重视,因而错乱较多的《墨子》和《管子》等子学著作的校勘、整理与注释。
《墨子》是研究先秦墨家学派及其创始人墨翟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内容主要是记载墨子的言论和活动。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逻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学术界还有人认为书中的《亲士》和《修身》等篇章可能是后人掺入的伪作。书中关于守城拒敌方法的内容,也许有些是汉代人的文字,但大体保存了墨家的守城技术和方法。由于过去历代统治者不提倡墨学,因此自秦汉直至清代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很少有人研究《墨子》。先秦各大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大多都有唐宋以前学者流传下来的旧注,唯独《墨子》没有。史书上虽记载有西晋的代郡人鲁胜曾注《墨辩》(即《经说》四篇,《晋书》卷九十四《鲁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八册,第2433页),又有乐台(一说为乐壹)曾作《墨子注》三卷(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第六·墨家》,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52页),但此二书均早已失传。在傅山之前,《墨子》不但没有前人的注释,就是原文也十分混乱,有些篇章已经亡佚,有些篇章如《经》《经说》《大取》《小取》及论城守诸篇,错伪严重,以致有无法句读者。总之,《墨子》是先秦诸子书中内容最为丰富,也是最为混乱的著作。
在傅山之后,乾隆年间扬州学派的汪中(1745—1794年)曾整理过《墨子校本》(汪中:《述学》内篇三《墨子序》,又见台湾“中央研究院”2000年版《汪中集》文集卷四《墨子序》和《墨子后序》,该书第135—143页),但此书并未刊刻印行。与汪中同时的毕沅(1730—1797年)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西安刊印了他以《道藏》为底本的校勘与简要注释本《墨子》(光绪二十三年图书集成局据毕氏灵岩山馆本的校印本)。乾嘉学派的王念孙(1744—1832年)、王引之(1766—1834年)父子与后来的俞樾(1821—1907年)等人开始重视《墨子》,做了一些“杂记”的文字,对《墨子》进行了部分校勘与注释。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1848—1908年)采前人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见解,著成《墨子闲诂》十卷,于宣统二年(1910年)刊印问世。《墨子闲诂》可以说是清代《墨子》整理校勘的最好成果。
然而,傅山对《墨子》的校勘与整理比他们都早,新版《傅山全书》中收录了傅山的《墨子校注》,这无疑是历史上现存最早校勘与整理《墨子》的著作。有趣的是,傅山的这本校注,在他去世后不久,便流传到了清代著名的校勘学家、藏书家卢文弨(1717—1795年)的手中。卢文弨一生多从事文献整理校勘工作,最精于校勘学。他在傅山的《墨子校注》卷一题下用硃笔题记曰:“此书傅青主先生校勘过。乾隆癸卯(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杭人卢文弨弓父又细订正其所可知者。”(见新编《傅山全书》卷五十九,第五册,第1页。遗憾的是《傅山全书》此处把“卢文弨”错排成了“卢文绍”,校对时未能改正,这里谨向读者致歉,请大家改正过来。)说明他不但仔细研读了傅山的校注全文,而且还加上了自己的看法,对《墨子》的校勘做出了重要贡献。毕沅在校勘整理《墨子》时,就吸收了卢文弨的研究成果。他在《墨子叙》中说:“先是,仁和卢学士文弨、阳湖孙明经星衍互校此书,略有端绪,沅始集其成。”(见光绪二十三年图书集成局据毕氏灵岩山馆本的校印本)而毕沅的校注,被后来的孙诒让作《墨子闲诂》时多有采纳。孙诒让在《自序》中说:“(《墨子》)旧有孟胜、乐台注,今久不传。近代镇洋毕尚书沅始为之注……余昔事雠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于毕本外,又获见吴宽写本”云云(见《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新编丛书集成》本)。可见,清代校勘整理《墨子》的最高成果《墨子闲诂》吸收了毕沅的研究成果,而毕沅校注的《墨子》又吸收了卢文弨的研究成果。从傅山的《墨子校注》手稿中,我们又看到了卢文弨的墨迹,说明卢文弨对《墨子》的校勘与整理是吸收了傅山的研究成果的,但遗憾的是卢文弨这位清代十分著名的校勘学家,却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只字未提傅山。他也许认为傅山的校注原稿在他这里,别人谁也不知道,于是便把傅山的研究成果攫为己有了。后来的毕沅、孙诒让等人在采纳卢文弨的研究成果时,也就未能注明其中有傅山的研究成果。这对傅山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不能不说是一件历史的冤案,这个冤案至新编《傅山全书》问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傅山不但有《墨子校注》,而且有《墨子大取篇释》与《墨子经简注》(见新编《傅山全书》第五册),在《杂记》中还有多篇对《墨子》的研究成果(见新编《傅山全书》第三册)。应该说,毫无疑问,傅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保存下来的校勘、整理与注释《墨子》的第一位学者。
《管子》在历史上的“命运”比《墨子》稍好一点,唐代有国子学士尹知章对《管子》做过注释,明代弘治年间的刘绩做过《管子补注》二十四卷(《四库全书·子部三》),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朱长春著有《管子榷》(明万历四十年张维枢刊本)。但这些并没有改变多少《管子》文字错乱的局面,新编《傅山全书》所收傅山的《管子批注》《管子评注》与杂记等,表明了傅山对校勘、整理与注释《管子》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由于笔者就傅山对《管子》的研究写过文章(拙文:《傅山对〈管子〉的研究及其贡献》,《名作欣赏》2017年第3、4、5、6期),因而这里便不再赘述。
傅山对《墨子》与《管子》的校勘、整理与注释不但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傅山对其他古籍的校勘、整理与注释也同《墨子》与《管子》一样,都做出了艰巨的努力与突出的成就。
作者:
尹协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著作及编著有《王通论》《王通评传》《宋明理学》《白话列子》《傅山年谱》等。编辑:
得一 3121763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