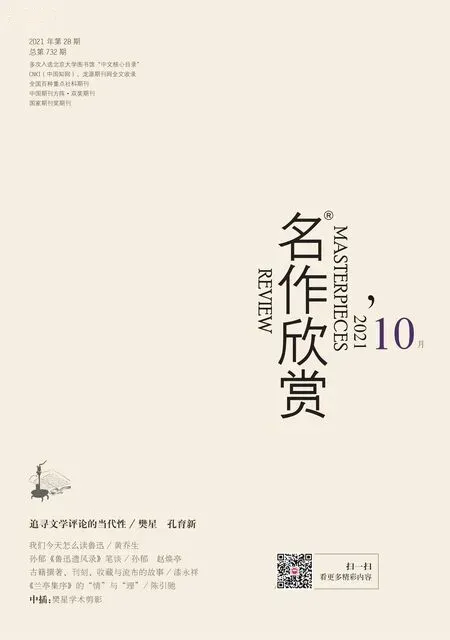知人论世与读者的话语霸权
——《莺莺传》的阐释传统及其反思
2017-07-15江苏滕汉洋
江苏 滕汉洋
知人论世与读者的话语霸权——《莺莺传》的阐释传统及其反思
江苏 滕汉洋
知人论世的阐释模式屏蔽了元稹对于小说主旨的说明,导致张生乃元稹自寓的观点主导了对作品的解读倾向,使绝大多数读者沉迷于在其中发现唐代士人猎艳经历和对张生的“忍情说”进行道德批判的快感之中。《莺莺传》的接受史,实际上是读者的话语权不断膨胀而作者的话语权不断消解的历史。
元稹 《莺莺传》 阐释传统 反思
通常情况下,文学作品一旦宣告完成并广为传播之后,对作品的话语权也随即由作者一方转移到读者一方,相关作品也因之由作家的个人表达变成一种社会共享话语。然而对于作者来讲,这一过程虽然必不可少,却隐含着某种不可控制的危险,受制于作家个人表达能力和读者的认知能力以及语言词不达意、言不尽意的可能性局限,读者在追寻和阐释作品的同时,偏离作者预设表达意图的解读乃至直接的误读时有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兰·巴特所宣称的“作者死亡,写作开始”,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对于这种情况,作者和读者双方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为了将这种解构作者创作意图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一方面,作者往往在作品中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出现,试图对读者的阅读理解进行引导和控制;另一方面,读者一方也试图构建一些解读的规范以求作者的本心。然而,这种作者与读者双方共同避免偏差的努力,却有可能因为着力点的不同而南辕北辙。唐传奇《莺莺传》的阐释传统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如同中唐时代的许多爱情传奇一样,作为一种社会消遣性的文学读本,《莺莺传》可以说是当时都市风流的产物,才子佳人的遇合与分散,艳情的强调与渲染,似乎都昭示着这类作品迎合市民趣味的世情化、娱乐化特质。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有时候还可以作为行卷、温卷来使用,相对于古代士大夫抒情言志的主要载体——诗、文来讲,其在诸体文学中的地位似乎并不低,甚至被当作个人综合性文学修养的展示方式之一。虽然我们在《莺莺传》之类作品中,并未发现此种具有投献功能的痕迹,但考虑到这类作品一般都具有极强的传播效应,而作者本身多为在社会序列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士人,其言行在一定程度上须受到礼法的约束,创作者对其创作意图初始化的重视应该是可以被确认的,也就是说,作者至少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会被完全认为是一种毫无寄托的游戏之作而受到不必要的非议和指责。因此,在唐代的一些著名的单篇传奇中的某个位置,作者常常跳出来,用第一人称的视角交代故事的来源、对此具有共同兴趣的同道为何人、这一故事所具有的意义等信息。这一据说是沿袭自史书序赞体例的惯常表达模式在白行简的《李娃传》、沈既济的《任氏传》等爱情传奇乃至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等神怪题材作品中都有所保留,可见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同时也与此类作品多以“传”为名的文本形式本来就直接导源自纪传体史书相关。与此类似,在叙述了张生与崔莺莺令人感叹和惋惜的爱情故事之后,元稹在《莺莺传》的最后也做了遵从惯例的表达:“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在这一段话中,元稹对于自己创作《莺莺传》的意图做了明确的说明,那就是通过张生的经历,告诫如同张生一样的年轻友人们“知者不为,为之不惑”,即以小说中张生所谓的“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的方式抵御美色乃至一切外在的诱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莺莺传》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篇宣扬年轻的读书人应该秉持禁欲主义观念的小说文本,是元稹借友人张生的经历来表达自己对于抵御外界诱惑的看法,明显具有劝世讽世的创作目的。
按理说,这类文字出自作者之手,应是我们解读相关作品意蕴和理解其主题内涵的重要立足点——起码是立足点之一。毕竟,张生作为年轻的应考举子,在本应该全身心投入读书学习的时刻,一旦遇见“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莺莺,心中“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道德堤防瞬间崩塌,虽然最终抱得美人归,但在与莺莺缠绵悱恻之际却忘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最终赢得一个“文战不胜”的落第结果。这对于一个尚未科举及第而正在考前集中复习的年轻读书人来讲,难道不是值得警惕的吗?在小说中,张生与莺莺分手后所发表的一番“忍情”的理论,虽然被鲁迅指为“文过饰非”,但却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主题内涵。张生在比莺莺为妲己、褒姒,称其为“尤物”“妖孽”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忍情”理论,固然无法获得绝大多数现代读者的认同,但这一翻版的红颜祸水理论,无论我们赞成与否,在古代社会却是很有市场的一种论调。古人一方面认识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但对于迷恋女色却又时时心存警惕。例如,关于“好色”的讨论,在中国古代便有极强的伦理政治和文学传统。战国时期的宋玉在其《登徒子好色赋》中设置了三个对于“好色”持不同立场的人物——登徒子、宋玉和章华大夫。在赋的开篇,“好色”成为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诋责宋玉的借口,但这一负面的道德评判遭到了宋玉的有力反驳。宋玉一方面从登徒子与“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的妻子育有五子的角度说明登徒子才是真正的好色者;另一方面则从自己对“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的东家之子的诱惑所采取的断然拒绝态度,来证明自己具有坐怀不乱的道德定力。虽然赋中章华大夫对于女色“目欲其颜,心顾其义”亦即“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态度较登徒子和宋玉而言更符合人伦之常情,但宋玉的态度在赋中显然被视为论辩中的胜利一方——在美色的诱惑面前,深刻的自我抑制和精神制裁被视为一种具有道德坚守意义的美德而受到推崇。滥觞于宋玉的这一道德叙述模式在汉代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几乎被原样照搬,并最终形成一种道德文学叙述的传统,直到清代蒲松龄《画皮》之类的鬼魅故事中,依然可以见到其影子。如果我们循此思路观照《莺莺传》的叙事结构,元稹恰是对这种道德文学叙述的承袭。在小说的开篇,张生即宣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而张生嗣后的经历也表明,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好色”所致。只不过在宋玉、司马相如那里,“好色”是避之唯恐不及的道德污点,深厚的道德修养的加持成为他们抵御诱惑的定力。而在张生这里,“真好色”成为堂而皇之的自我标榜,并最终使他成为爱欲的俘虏而迷失方向。
因此,“好色——忍情——补过”的叙述结构在《莺莺传》的核心处俨然存在。《莺莺传》的主旨并非是津津乐道一则“始乱终弃”的凄凉爱情故事,而是想通过友人张生的经历告诉身边具有同样困惑的年轻读书人:在科举的愿望未能达成之前,必须严格控制“好色”的欲望,而一旦沉迷于爱欲的泥潭,除了当机立断地提出分手,自身便不会得到反省的机会而回归理智。这应是符合中国古代道德文学叙事传统的解读,同时也是符合故事逻辑的解读。
然而不幸的是,文学作品通常被认为来源于生活,尤其是小说这种具有明显的事件性、现实性的文学体裁,更被许多批评家认为是现实的某种投射,乃至是作者个人经历的投射。解构浮于文字之上的虚构性叙述,显露现实的底色,似乎是读者在理解此类作品时本能的条件反射。我们对古代文学作品解读时所最为常用也是被认为最为合适的“知人论世”的解读方式,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而一旦采用这种被认为是恰当的解读方式,《莺莺传》的意蕴和主旨便会呈现出另一番模样,因为它很容易使读者成为历史的考据癖者,纠缠于历史的真实而非文学的真实,将小说中的人和事与历史事实和作者的个人经历对号入座,乃至将小说视为一种个人的自传,从而对文学研究的本意失去兴趣,对作者于小说中的任何宣示视而不见。
从历史事实来看,《莺莺传》中的张生的确与元稹的真实经历有相当部分的重叠,而且元稹本人也和张生一样“美风容”。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元稹似乎对于女色有着特殊的偏好,而其对于女性的道德观却存在瑕疵。元稹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曾前无古人地列出了“艳诗”的条目,虽然按照他自己的解释,这类诗歌主要在于描写女性的容貌服饰,且具有“干教化”的目的,与艳情的描写乃至色情的暗示毫无关联。所谓的“艳诗”,在现在能看到的元稹文集中已经无法准确地指实为哪些作品,但考虑到元稹当时的诗名,这种宣示很难让人相信,因为与元稹同时的李肇已经明言当时人的诗歌“学淫靡于元稹”,稍后的李戡也曾将元稹与他的好友白居易捆绑在一起加以批评,说他们的诗歌“纤艳不逞”“淫言媟语”,产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深恶痛绝的态度溢于言表。与此相关的是,在“诗言志”的批评模式下,元稹的一部分诗歌所表达的感情也被视为虚伪矫饰,尤其是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显示出道德修养的缺失。如其千百年来感动无数读者的三首悼念亡妻韦丛的《遣悲怀》,在一部分人眼中,不但没有体现对于亡妻的深情,反而是虚伪矫饰之至。陈寅恪对于其中的“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评曰:“所谓长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其后娶继配裴淑,已违一时情感之语,亦可不论。唯韦氏亡后未久,裴氏未娶之前,已纳妾安氏。”虽然陈氏自己也认为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对元稹做苛刻之评论,但其在对“长开眼”过度阐释的基础上所推导出的元稹的女性观所展现出的褊狭,还是令人吃惊的。至于清人潘德舆对于其中的“潘岳悼亡犹费词”一句评曰:“安仁《悼亡》诗诚不高洁,然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娄百事乖”一句又评曰:“元九岂黔娄哉!”可以说相较于陈寅恪的解读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已经完全溢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之外,具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了。客观来讲,以上这些对元稹诗歌的解读一定程度上与解读者认为《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元稹自己的认识相关,尤其是对于后代读者而言,《莺莺传》中张生所表达的猎色观及其抛弃莺莺所展示出的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元稹自己的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女性观念如出一辙。读者也就很容易由对小说中张生的反感,走向对小说作者元稹的非难与攻击,进而由文学的欣赏转向对被认为是元稹原型的张生的道德评判。更何况,如果说张生就是元稹,似乎也有历史背景的现实根据,并不能被完全看作是空穴来风。因为唐代文人的猎艳奇闻,很多是被指名道姓的当作事实予以记载的。如被称为“闽学鼻祖”的唐代著名文人欧阳詹与太原妓的爱情,就是一段佳话,小说的敷衍之外,确实可以得到他自己的《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等诗的印证。即如与《莺莺传》同被列入中唐三大爱情传奇的《霍小玉传》,也被明确地记载为是中唐著名文人李益的真实经历;《李娃传》虽然对于其中的男主角郑生避其名讳,但作者白行简在小说中也直言:“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从侧面说明小说所依据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对于读者而言,元稹所生活的时代,读书人枯燥的读书行役生活中,猎艳的行为并不罕见,相反却是比比皆是。由此,在热衷于历史索隐的读者眼中,元稹的为人及其并不严肃的女性观念,加上时代风气的沾染,张生为什么不可以是元稹呢?这似乎是知其人而论其世的必然结果。
于是我们看到,在知人论世的解读模式下,从北宋时期王铚的《传奇辩证》开始,到现代学者陈寅恪的《读莺莺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乃至当代的诸多唐传奇研究者,《莺莺传》的主人公张生就是年轻时期的作者元稹,而崔莺莺就是他在与出身高门大姓的韦丛结婚前夕抛弃的情人这一观点,几乎被毫不质疑地加以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论证。甚至,为了弥合小说与元稹真实经历上的某些龃龉不合之处,一部分研究者不惜改动小说的文本。如王铚为了配合自己的考证,将小说中张生“年二十三”改为“二十二”;更有一部分学者如陈寅恪等人在元稹的诗歌文本中寻找崔莺莺的原型,那就是元稹多次提及的“双文”,以证成其说。经过这样严密的索隐钩沉,张生乃元稹自寓,成为绝大多数人阅读《莺莺传》时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先入为主的看法。虽然元稹在小说中一再地宣称张生乃是其友人,张生作为一个“善补过者”的形象也是其朋友圈的共识,而且在小说的末尾也对读者基于这一传奇故事的认知试图加以限制和引导,但却被这众声喧哗所屏蔽,或者被认为是一种掩盖自己早年不良经历的企图。这恐怕是元稹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事情。于是,在《莺莺传》的接受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的解读始终难成气候,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失语的状态,而伦理的道德的解读始终占据主流。读者对于这篇小说的阅读兴趣,不在于情感意象,不在于文学叙事的策略,而是沉迷于在其中发现唐代士人猎艳经历和对张生抛弃莺莺而又美其名曰“补过”进行道德批判的快感之中。一个原本可以进行深度解读的文学文本,至此沦为文人的八卦和好事者的谈资。
纵观《莺莺传》的一部接受史,作者元稹对于小说的主题意蕴的叙述,可以说始终处于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境地。而读者在知人论世的解读模式下,以己之心度古人之腹,对小说却得出了完全不同于作者的认知。正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对这两种解读进行对错和优劣的评判,只是想说明,在文学作品实际的接受过程中,作者确实可以被视为弱势的一方,因为文学文本一旦形成之后,作者基本上就失去了解释的权力,其意蕴与主题都有赖于读者在阐释的过程中确立,而对作品进行解读的方向和思路,又取决于他们选择以何种方式进入文本。文学作品的解读绝不应像罗兰·巴特宣称的那样,被视为是作者向读者进行话语权的让渡,而应是两者的合力所形成的共识。接受美学固然承认读者的重要性,但也强调其立场的客观性和阅读方式的科学性,并强调从作者、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角度研究文学。而在中国的文学阅读传统中,知人论世被认为是文学解读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一方法表面上看对于作者极其重视,但却很容易使读者沦为历史考据的操手而导致话语霸权,使历史与美学的二元化批评向一元化倾斜。这一现象在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传统中表现得极其明显。《莺莺传》的传统阐述模式,不过是为此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
①罗兰·巴特:《作者之死》,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07页。
②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1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④元稹:《叙诗寄乐天》,《元稹集》卷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1页。
⑤李肇:《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⑥杜牧:《李戡墓志》,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44页。
⑦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1页。
⑧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六,《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8页。
作者:
滕汉洋,文学博士,现为盐城师范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编辑:
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