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州彭氏的教育事业探论
2017-07-05葛慧烨黄鸿山
葛慧烨,黄鸿山
(1.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江苏 苏州 215000;2.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清代苏州彭氏的教育事业探论
葛慧烨1,黄鸿山2
(1.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江苏 苏州 215000;2.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清代苏州彭氏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彭氏家族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氛围浓厚、教育制度完备,为其家族科举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彭氏还积极推动苏州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热心参与县府学、书院等地方教育机构的修葺完善,而且有族人长期担任地方书院山长,对苏州崇文乐学之风的培育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彭氏在教育方面既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还注重编印传播劝善书,着力劝人向善,表现出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并重的特色。这是彭氏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苏州;教育;彭定求;彭启丰;科举;书院
苏州彭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科举和文化世家。彭氏原籍江西清江,其迁苏始祖为彭学一。彭学一为军籍,明洪武四年(1371)随军徙隶苏州卫左千户所。彭学一身后无子,官府以其外甥杨仲英来苏补役,杨仲英承继了彭学一的军籍,遂改姓彭。从此,彭氏定居苏州,世居葑门内十全街附近。
彭氏原属军籍,世代习武,传至仲英之孙彭淳时发生重大转折。彭淳“尝言吾家世习武,子孙当以文显,教其子读书”[1]569。此后彭氏由文转武,世代鼓励和支持族人读书应考,成为明清时期苏州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世家。明代彭氏已初显文脉勃兴之象,中进士2名、举人3名。清代彭氏步入全盛时期,累计中进士14名、举人33名。其中彭定求、彭启丰祖孙二人先后于康熙十五年(1676)、雍正五年(1727)状元及第,成就科举史上“祖孙状元”的佳话。
科举的成功为彭氏带来了高官显禄。彭启丰在乾隆年间官至兵部尚书,彭启丰之孙彭希濂嘉庆年间官至福建按察使、刑部侍郎,彭启丰曾孙彭蕴章咸丰年间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彭蕴章之子彭祖贤光绪年间官至湖北巡抚。彭氏由此成为清代苏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科举仕宦世家之一。不仅如此,彭氏族人在其他方面也作出杰出贡献。如彭定求是清初理学名家,被称为“理学儒宗”;彭绍升是清代中期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和著名慈善家;近代以来,彭翼仲先后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是近代中国报业先驱。作为苏州著名的文化世家,彭氏格外注重教育,在家族和地方教育事业方面建树颇多。①学界对苏州彭氏多有关注。以往成果主要关注彭氏家族在科举、政治、文化和慈善方面的贡献,主要成果有:朱焱炜:《明清苏州状元与文学》,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版;葛慧烨、王卫平:《清代文化世家从事慈善事业的原因—以苏州彭氏为例》,《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3期;徐茂明:《明清时期苏州的宗族观念与文化世族》,《史林》2010年6期;王卫平、黄鸿山:《继承与创新:清代前期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以彭绍升为中心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3期;黄阿明:《康熙十五年状元彭定求生平史实述略》,《历史档案》2013年4期。亦有学者关注到彭氏宗族的人口情况,见余新忠:《从苏州〈彭氏宗谱〉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兼论谱牒与人口史研究》,《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2期,等等。
一、彭氏的家族教育
彭氏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问题。《彭氏宗谱》的《修谱条例》中明确规定:“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理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书。”①见《彭氏宗谱条例》第6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可见,彭氏将“读书习礼”视作族人最优先的选择。
彭氏家训中还对子弟如何治学提出具体意见。彭蕴章撰《家塾五箴》,针对家族中读书治学之人,提出“务实”“立志”“刚立”“去取”和“静坐”五个要求。[2]595指出治学要有务实的态度,要潜心向学,做好学者的本分,不要沽名钓誉,夸夸其谈;治学还需立志,树立明确目标;需要有坚定的信心,不畏艰难困苦,一意前行;需要静心,耐得住寂寞,摒绝声色犬马,等等。
除注重教导子弟勤奋读书外,彭氏还格外注重对族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彭氏宗谱》中强调“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这里的“习礼”便具有思想品德教育的涵义。彭定求曾撰写《治家格言》,规劝家族子弟处家要牢记“孝父母,敬兄嫂,为夫妇,和顺好”,处事应坚守“贫不欺,富不扰。官钱粮,先要了”,做一个敦亲睦邻、安守本分的百姓。[3]1185又说“学手艺,要心巧。做买卖,要公道。耕种田,勤耨草”[3]1185,谆谆教导子弟从事各行各业都要坚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到诚实经营、勤奋致富。彭蕴章撰有《交友四箴》《居心箴》《居官箴》《恃才箴》《怙过箴》《玩物箴》《玩日箴》等家训家规,对族中子弟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提出要求。《交友四箴》包括滥箴、谑箴、傲箴和言箴,重在教导子弟如何择友以及与人相处,指出择友应当慎重,宁缺毋滥;与友人相处应当敬人以礼,不可揭人之短、谑人之过;待人接物应谦逊有礼,不可倚势倚才傲世;言语要注意分寸,和颜悦色,不急不躁。《居心箴》则教人心正,心正才能言行不偏。《居官箴》劝勉为官者恪守清白、勤勉为政,不可怠于政事、尸位素餐。《恃才箴》劝诫子弟待人接物应谦虚低调,不能恃才自矜。《怙过箴》指出为人应不时自省,以便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玩物箴》告诫子弟不要玩物丧志,沉溺于物欲。《玩日箴》告诫子弟应当珍惜光阴,不要饱食终日,无所事事。[2]594-595由此可见,重视思想品德修养,也是彭氏家族教育的特色之一。而从实际情况看,彭氏的确能够世代传承清白家风,得到世人赞誉。约在道光初年,江藩曾称赞道:彭氏虽“一门鼎贵,为三吴望族”,但“至今子弟恪守庭训,不踰规矩,有万石之遗风。江南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当以彭氏为矜式焉”。[4]173
彭氏一方面通过家规家训谆谆告诫子弟要努力读书和修身养性,另一方面通过设立教育专项资金、创办宗族义学等方式为家族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了保证子弟的教育经费,彭定求晚年分析家产时,特别划出阊门外、崇真宫前、相王巷口三处房屋,每年所收租金计一百二十二两,专门用于子孙的教育,供给“束脩膳食之用”②见《闲家录》第28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其子彭正乾在遗嘱中也特别要求留出田产,专供子孙读书,其中“长孙田二十亩,二、三两孙各十亩,为读书资”③见《惕斋府君遗嘱》第42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
乾隆年间彭绍升曾创立“润族田”,以保障彭氏族人生活为目的。由于经费有限,彭氏润族田未能像许多其他宗族义庄一样创立义学,供族人子弟读书。彭绍升对此深感遗憾,特别在遗嘱中要求,如果日后收入增加,“当设一宗学以教诸童,否则量加读书之费”④见《庄规》第17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即一定要重视族人的教育问题。光绪二年(1876)彭氏谊庄成立时,彭氏族人商议在“南园东偏添建庄房,专设一斋,名曰庄塾,课本族子弟之无力读书者,以遵二林公⑤引者注:“二林公”即彭绍升。遗训”。⑥同④。彭绍升的遗愿终于实现。根据彭氏制定的庄塾规条,庄塾出资聘请品学俱优的塾师,免费教育彭氏家族中没有能力延师就读的子弟,子弟在庄塾学习期间一应费用全免。如果有子弟住处较远,不便入庄塾读书,亦可由谊庄资助其学费,就近择师附学。此外,谊庄还为部分特别困难的子弟免费发放书本。但凡入庄塾读书或接受学费资助的子弟,由谊庄定期予以考核:成绩优良,“文理清顺,字画端正”者将得到纸笔钱的奖励;特别优秀的“实堪造就者”,额外提供助学资金;学业荒废以致考课不合格者,以及无故缺席不参加考课者,酌情停减或中止资助,实在不认真学习的纨绔子弟,将被逐出庄塾。①见《庄规》第21—22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
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庄塾学生,谊庄将进行资助,“县府试正场助五百文,每复一次及考性理三百文。生童岁科试正场及经古复试与县府试同,均于正案已发后,支总汇报各人每场名次,并以逐次浮票为凭,按规支发,无票不发”②见《庄规》第22—23页,彭慰高、彭祖贤重修:《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光绪七年(1881)。。对考试中式者予以奖励,考中秀才者奖励四千文;参加乡试者资助十千文,考中举人加贺金十千文,若举人头名贺金二十千文;参加会试者资助三十千文,中式者加给贺金二十千文,若考中会元及状元、榜眼、探花、传胪,贺金加倍发给。对于部分“质钝不能进业”的学生,庄塾规定待其年满十五岁后,鼓励并资助其充当学徒,学习谋生技艺,所谓“读书不成者,习业亦足以谋生。凡子姓无力者,始习业由支总报明,助钱四千文,备置铺陈。进店后至写立关书,由支总查明本店人作保,再报助钱十千文”。③同②。
清末科举停废后,彭氏庄塾改为私立两等学堂,本族子弟入学者学膳费用一概免除。民国年间彭氏《续纂庄规》中的《庄事商榷书》仍规定,宗族将对求学子弟进行资助,“入国民学校及蒙养院者,每年给学费银元六元,入高等小学者,给学费银元十二元,入中等学校者,给学费银元二十四元,入高级中学或专门预科者每年给学费银元三十六元,入大学或专门本科及至日本留学者,每年给学费银元六十元,欧美加倍”④见《续纂庄规》第29—33页,彭文杰、彭钟岱:《彭氏宗谱》,苏州衣言庄刻本,民国十一年(1922)。。并增加了关于女子教育的内容,“女子同为子弟,自应一视同仁,支给学费”,由于庄款有限,“公议女子以高小学卒业为限,比照男生一律支给学费,若有力,房族升入中学以上各校者,本庄亦只照高小班给费,以示限制”。⑤同④。可见彭氏对女性族人的教育也开始有所重视,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
上述记载表明,彭氏十分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问题,这种重视并不仅仅流于空洞的口头说教,而是付诸实际行动,以设置教育基金、族学和给予经济资助等方式加以保证。这不仅极大地鼓励了彭氏子弟读书习业的积极性,而且解决了寒素之家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从制度层面为彭氏读书重学家风的代代传承提供了保障。彭氏之所以成为明清苏州首屈一指的科举世家,并非偶然。
二、彭氏与苏州地方教育事业
彭氏还为苏州地方社会的教育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彭定求的父亲彭珑是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曾任广东长宁知县。他晚年在苏州城东文星阁(今苏州大学内)讲学,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间,坚持八九年之久而不中断。“月之朔望,分题校课”,并“集诸生为会,课其制义而引之于道”[1]571。一时间在苏州城内影响颇著,据称“从游者常三百许人”[1]571。有人对其如此勤奋讲学感到不理解,他回答:“吾不忍后生之无闻也。”[1]571其学问品性曾上达天听,“汤文正知珑学,尝称之圣祖前”[4]173,即江苏巡抚汤斌曾在康熙帝前称赞彭珑。
康熙三十三年(1694),彭定求告病归乡,此后大部分时间“甘居乡里”,与师友、门生举文会、论学术,他晚年曾执掌苏州紫阳书院(原址在今苏州中学内),悉心于教学。彭定求认为“书院之建,表扬风化,诚属一方嘉庇”[5]468,因此尤其注重苏州地方书院的修缮与建设。康熙二十年(1681),彭定求参与修葺扩建苏州城东文星阁。[6]康熙二十一年(1682),长洲县学殿堂破败坍塌,彭定求“请于当路诸公捐金若干”,请求苏州地方官员捐款,第二年又“请于乡先生在朝者捐金若干”,发动在外地做官的苏州人捐款,最终使长洲县学得以修葺完善。[5]293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再次发起募捐,集银一千七百多两用于扩建长洲县学。[5]294此外,彭定求还曾经募修苏州东南尹山上的澹台书院。[5]468
彭启丰对苏州地方教育的发展也多有贡献。乾隆二十五年(1760),彭启丰募资修复了彭珑、彭定求等讲学所用的文昌阁时习堂,重现读书会文的勃勃生机。苏城内外读书士人不仅“往来肄业于其间”,而且“时以所作文就质于余”[7]517,即经常向彭启丰请教作文之法。彭启丰对此喜闻乐见,不仅“为论其得失雌黄而甲乙之”,而且将其中优秀的诗赋文章汇刻出版,使之广为流传。[7]517
乾隆三十四年(1769),致仕归乡的彭启丰被官府延聘为紫阳书院山长。在执掌书院期间,彭启丰的教学风格非常鲜明,在教学上有着独特见解,曾作《论学一则》《论文二则》教导紫阳书院学生。他反对“往昔圣贤所垂训言高深不可几及,仅取以为时文作料”的浮躁学风,认为“圣贤千言万语,非有难解难行之事,无非教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教导学生要保持“本心不失”,认真研读古书,逐渐消化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7]496他驳斥“古今时异,为古之文者,不宜于今”的观点,指出“文有古今,而为文之心则无古今”[7]497,要求学生体察圣贤之心,把握古文的精髓。他指出:“谦者日见其不足,傲者日见其有余。日见其不足则德修而业进……日见其有余则德堕而业弛。”告诫学生要保持谦虚,谦虚才能进步。[7]497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彭启丰执掌紫阳书院前后达十五年之久,其治学理念和教学实践影响了苏州一代学风。
与此同时,彭氏还世代诵读及撰著劝善书,致力于劝善书的编印与传播。彭氏所编印的劝善文字涉及劝孝、敬字、劝诫溺女、戒斗、遏欲、戒杀、放生等诸多方面。其编印和散发善书,主旨在于劝人改过向善,广义上亦属教育事业的范畴。如彭定求自幼习读《感应篇》,奉行《阴骘文》、功过格,盛称《汇纂功过格》“与经史相表里,吾至老读之不厌”[8]92。还积极从事善书著述,撰有《元宰必读书》《保富确言》《文昌玉局心忏》《质神录》等劝善书。彭启丰曾为多部善书作序。彭氏编印和散发善书,对改善地方社会风气,营造善风良俗起到积极作用。其影响很大,以至于乾隆年间有人称,彭氏“世代积德累仁,刊刻一切三教善书,广行布送,因此世代显宦”[8]92,即彭氏之所以能在科举方面取得傲人的成绩,正是其刊印善书的福报。
三、余论
总之,作为苏州著名的文化世家,彭氏对教育事业格外重视。这种重视不仅针对族人,还体现为在地方教育事业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就教育内容而言,彭氏的教育事业包括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两个方面,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彭氏在文化知识教育方面的成功,少有人注意其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彭氏并不仅仅只是传授文化知识,培养状元之类的科举人才,更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要求族人子弟严于自律、遵纪守法和与人为善,树立良好家风,维护家族形象;并着力编印传播劝善书,着力改良社会风气,营造良好乡风。
彭氏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绵延数百年而不衰,并受到时人赞誉,其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的做法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为彭氏打开了科举仕宦的“成功之门”,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则为彭氏有效地堵上了“败家之路”,并为族人的发展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二者对彭氏家族的成功均具有重要作用,不可偏废。这种情况表明,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优秀代表,苏州彭氏已注意到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塑造良好家风乡风的重要性,并努力付诸实践。时至今日,党中央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和“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9],并大力提倡“树立文明乡风”[10]。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彭氏这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塑造良好家风乡风的做法仍有值得今人学习借鉴之处。
[1] 彭绍升.二林居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 彭蕴章.归朴龛丛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 张鸣,丁明.中华大家名门家训集成:下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4]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彭定求.南畇文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 彭祖贤.南畇老人自订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33.
[7] 彭启丰.芝庭先生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 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9]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EB/OL].(2015-10-21)[2017-01-22].http://news.xinhuanet.com/2015-10/21/c_1116895782.htm.
[10] 南方日报: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树立文明乡风[EB/OL].(2016-11-30)[2017-01-22].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130/c1003-28912069.html.
(责任编辑:时 新)
中国通俗文学:“张恨水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栏目特邀主持人:汤哲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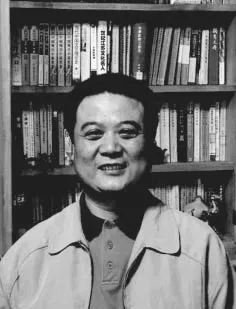
1967年2月15日清晨,带着无尽的遗憾与未完的心愿,“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张恨水先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恨水先生是作为“文学奇观”而存在的—以一己之力,一生留下三千余万言的煌煌巨作,读者对其中很多作品的热情近一个世纪而不衰。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以精英文学作为主流话语,有别于精英文学的张恨水也就成为了一种“文学史困惑”,正如杨义先生所说:面对张恨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长期面临着盖好房子才去找地皮的尴尬”。张恨水先生一生的创作成就,触发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深层次问题,文学观念、文学史写作、文学研究方法……都随着张恨水研究的深化得到反思、关注和调整。对于现代文坛而言,作为一位全能报人和红极一时的小说家,张恨水先生的小说是一个时代的“信史”,而对于现代文学史写作和研究而言,张恨水先生的成就则是一个“事件”。他对现代中国的贡献,恐怕远非小说创作技巧、思想内核以及艺术成就所能涵括,他的作品,是一座巨大的“富矿”,除去文学史价值,这座“富矿”中所蕴含的媒介史、社会史、文化史的丰富内涵,仍有巨大的言说空间。今年是恨水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对于作家及其后人而言,逝世五十周年,意义非比寻常。不久,安徽潜山张恨水研究会将以恨水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为主题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目前活动正在筹备中。与此相呼应,我们特别组织了本期专题,以共同纪念这位以三千余万言为现代中国绘像的文学大师。
本期三篇文章的作者均为博士,他们分别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张恨水研究的当下进展。通俗文学作品的二次改编是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的新走向,电影、戏剧、评弹改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三种文艺形式。房莹女士的博士学位论文主攻陆澹安研究,通过上海图书馆查阅胶片、走访陆澹安后人,掌握了大量关于陆澹安先生生平及创作活动的一手资料。她本次对《啼笑因缘弹词》创作始末史料的梳理和价值分析,厘清了《啼笑因缘弹词》几个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复创作的原因,指出了陆澹安《啼笑因缘》弹词改编的独特性—“兼具‘书场’和‘案头’双重特点”,细化了张恨水小说二次改编的研究,是很好的补充。同时,将陆澹安改编的《啼笑因缘弹词》放到弹词发展史中评价其价值,认为这部改编作品具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以及传播价值。特别难得的是作者在梳理问题的过程中格外关注到了小说与弹词之间的互文关系,成为本研究的点睛之笔。文章史料十分翔实,细节生动,文笔流畅,逻辑清晰,现场感很强。可能由于篇幅关系,作者对《啼笑因缘》小说与弹词之间的互文关系阐释不足,若能够进一步梳理,会更见精彩。北京大学刘凯健博士的《理想社会的历史轨迹—以〈桃花源记〉〈镜花缘〉〈秘密谷〉为线索》一文,巧妙选取了历史上的三部著名小说,围绕着“理想社会”这一主题,通过三部作品的纵向比较呈现不同时代对“理想社会”的不同诉求。长期以来,张恨水研究一直以内部研究为主,外部横向纵向比较研究不足,本文采取文本抽样的方法,角度选取得比较巧妙。由于时代不同、作者的理想不同,将之放到同一主题之下进行对比研究,自然就会有论述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张恨水价值评判的局限,对张恨水研究是很好的补充。然而,若将各部小说分开来看,作者的分析方法以及评价未能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有所深入,若能在此处稍加用力,会更见亮色。张恨水前期小说研究成果较多,抗战时期创作研究不足。唐娒嘉博士的《战时知识分子的“歧路彷徨”与张恨水的道德理想—以〈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傲霜花〉为中心》一文对张恨水对战时知识分子的型塑从性别角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对拓展张恨水小说的研究广度有一定帮助。在分析过程中,作者对张恨水的创作局限较为敏感,如他对男性知识分子战时选择基于道德评价,对女性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未跳出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本文的闪光点,展示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但论述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比如语言的思辨性以及研究视角的适应性问题。
三篇文章的作者均为80后、90后,研究虽略嫌青涩,但史料的谨严、选题的新颖、眼光的敏锐、行文的细密流畅都可圈可点。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呈现了张恨水研究未来的多重可能。
Suzhou Peng Family’s Edu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GE Huiye1, HUANG Hongshan2
(1. No.10 Middle School of Jiangsu Province, Suzhou 215000, China;2. School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Peng Family was a famous cultural family in the Qing Dynasty. Peng Family had a tradition of valuing education, and their education atmosphere was thick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was complete,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amily’s succes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Peng Family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uzhou local education. They not only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schools,academies and other lo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ut also had long served as the dean of local academies,and the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atmosphere of advocating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Suzhou.In education, Peng Fami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both cultur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cultiva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Peng Family, which was worthy of learning by people today.
Suzhou; education; Peng Dingqiu; Peng Qife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cademy
G40-09
:A
:1008-7931(2017)03-0035-05
10.16217/j.cnki.szxbsk.2017.03.006
2017-01-2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ZS037);2016年度江苏省“青蓝工程”项目
葛慧烨(1982—),女,江苏溧阳人,中学一级教师,硕士,研究方向:吴文化和江南区域史;黄鸿山(1977—),男,江苏兴化人,教授,硕导,博士,研究方向:吴文化和江南区域史。
葛慧烨,黄鸿山.清代苏州彭氏的教育事业探论[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3):3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