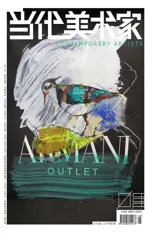“景观神话”:管窥T. J.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
2017-06-19诸葛沂ZhuGeyi
诸葛沂 Zhu Geyi
“景观神话”:管窥T. J.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
诸葛沂 Zhu Geyi

马奈马奈与家人在阿让特伊的花园中布面油画61cm×99.7cm 1874
在《现代生活的画像》中,T.J.克拉克将奥斯曼巴黎改造和商业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作为“景观”的大背景,描述19世纪下半叶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兴起及其对生活方式、审美兴趣的特殊追求,从而揭示马奈画作的复杂性、暧昧性。在他看来,马奈及其追随者的绘画,正是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和后果:视觉空间的平面性,对社会阶级的不充分或含糊的再现。《现代生活的画像》以马奈四幅画为论述对象,并向它们对应的城市生活显示出了“景观”从公共场所向私人场所、向日常生活世界侵袭的过程:城市街道—展览馆—郊区—咖啡馆。克拉克认为,现代性的神话正是景观侵入社会方方面面、侵入日常生活世界的神话。
T.J.克拉克,“景观”,马奈,意识形态,日常生活

马奈秋(玛丽·劳伦的肖像)布面油画72cm×51.5cm 1881
自1973年出版《绝对的资产阶级:法国1848—1851年的艺术家和政治》和《人民的形象:古斯塔夫·库尔贝和1848年革命》之后,当代著名艺术社会史家T. J.克拉克(T.J.Clark,1943 — )的第三著作(也是他最成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史的巴黎》在他暌违十一年之后出版了。在今天看来,这本书已经成为历史专业(不仅仅是艺术史)的重要必读书,尤其在印象主义研究领域享有绝对权威的地位。这是克拉克花费了其整个30—40岁的人生时光来成就的厚重作品,尽管这期间他遇到了来自时间、计划甚至政治上的困难。他在1999年再版前言中所说:“读者是否可以感到,尽管我觉得完成这本书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但回首这本书时,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的确,我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正冗务缠身;再回头看这个任务(我花的时间似乎太多了),它似乎无比艰难;我的写作风格,令现在的我感到吃惊,我竭尽全力才能避免魔鬼的侵扰——这其中就有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应该这样讲,他在研究中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情境主义策略,显然与七八十年代西方世界的政治导向龃龉、柢梧。2013年,该名著由沈语冰教授与我共同翻译完成,被列入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系列”出版,随即便获得第八届AC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年度艺术类出版物”提名奖。尽管此书饱受关注与赞誉,但国内对其的研究仍嫌不足。本文愿抛砖引玉,聊作芹献。
早在《人民的形象》中,克拉克便发展出一种研究方法,即将艺术作品与其他社会进程联系起来,放在一个历史情境中来考察,并找寻到图画中的失调之处,进而分析这种与传统艺术惯例相异的新形式是怎样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状况的变化的。
在《现代生活的画像》中,这种方法得到了更极致的发挥。克拉克还在导论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策略。“在我看来,一幅画并不能真正表现‘阶级’、‘女人’或‘景观’,除非这些范畴开始影响作品的视觉结构,迫使有关‘绘画’的既定概念接受考验。(这是像绘画这样的手艺传统表面上守旧性的另一面:只有在传统规则和惯例仍然在影响决策的实践中,改变或打破规则的目的——及其力量和重要性——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因为只有当一幅画重塑或调整其程序——有关视觉化、相似性、向观者传达情感、尺寸、笔触、优美的素描和立体造型、清晰的结构等程序时,它才不仅将社会细节,而且将社会结构置于压力之下。”
这就不仅呼应而且具体化了他在1973年的论述——“视觉表现的有效系统,艺术的最近理论,其他意识形态、社会阶级,以及更一般的历史结构和过程”,是如何以复杂和不确定的方式,在一个单一艺术作品中结合的。而这种结合是在一个现代艺术的历史时刻发生的,“至少在某一刻,它就有可能抓住一般文化现象的固定表达方式,以及同一性与差异的生产方式——有关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自由与自我意识等的同一性与差异。换句话说,不单单是‘景观’和‘阶级’,而是特定形式下的视觉化了的景观和阶级,将世界划分为客观性、内在性和欲望的封闭领域”。
克拉克在《现代生活的画像》中着眼于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他发现这座城市正经受着如大卫·哈维所称的“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之中,奥斯曼改造和景观神话的侵袭,让老巴黎的景象烟消云散。克拉克认为,奥斯曼对于第二帝国巴黎的重新形塑,背后仰赖的是资本主义对于巴黎是什么与巴黎会是什么的再想象。他指出,资本“并不需要地上的砖瓦或祭坛来呈现自我,也不需要在城市居民的心理铭刻地图。人们甚至可以说,资本宁愿让巴黎失去图像——不具形式、难以想象、无法阅读与误读、无法产生空间主张的冲突——然后再大规模生产自己的图像以取代原先资本所摧毁之物”。而克拉克要处理的,正是马奈等艺术家在面对社会表征符号的崩溃、表征体系的危机时的应对方式。

马奈阳台布面油画170cm×125cm 1868-1869
在书中,克拉克主要具体分析了四幅马奈之作,在每一章里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利用这种方法,找出作品中对传统或惯例的改变,揭示其对社会现实的间接反应。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章,便是第二章:《奥林匹亚的选择》。
早在1880年,克拉克就已在《屏幕》(Screen)杂志上发表了长文《对1865年奥林匹亚的一种可能性解读的初步研究》(Preliminaries to a Possible Treatment of Olympia in 1865)。1880年的文章内容更为凝练、简洁,更反映出作者的研究思路,而著作第二章则更为详尽。因为沈语冰教授对这一章中的内容和思路进行了细致的提析(可参沈语冰,《图画的秘密:T.J.克拉克艺术社会史方法举要》,《文艺研究》,2013(5):99-105),所以,在此处便只进行概况性的介绍。
首先,克拉克炫耀了他对于当时报纸上的共时性评论进行的巨细无遗的研究,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相当多的各不相同的评论,而所有的都具有价值。在对19世纪60年代巴黎出版业高峰期的报章杂志进行的考察中,他发现沙龙艺术评论几乎成了众所期待的栏目,有关1865年沙龙的80篇奇怪的评论中有近70篇提到了马奈,但只有四篇是肯定的。“我完全感觉到,他们自己就像一个家庭里的数个成员,相互嘲笑着各自的偏爱,来回借用着各自文章的短语,在一个单调而严厉的对话中争斗着机会(为了原创性而争斗)。”面对这些丑闻报道和漫讽刺画,面对公众反应和批评家们的压倒性的嘲讽反应,克拉克指出,忽略它们而只重视肯定性评价是不负责任的。他认为,这些评论中出现的不可饶恕的刻薄挖苦,本身就是19世纪艺术批评必需的修辞手法,但是肯定有一种基础决定了一边倒的批评和反对。这显然暗示出了《奥林匹亚》的先锋性,它可能是一个对现成流行的符码(或惯例)进行的无效的颠覆、拒绝的案例。也就是说,克拉克想要了解的,是“奥林匹亚在1865年遇到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论述话语环境,而且这种相遇为何如此不愉快”的原因。
遵循这一思路,克拉克将当时批评中的沉默、忽略和隐瞒,从潜藏状态抬到了显微镜下来观察。这种沉默,正如人们当时对《奥南的葬礼》的沉默一样,显现了意识形态神话的遮蔽,一旦将它撩开,便能在虚假的遮盖下面发现真实。克拉克列出了许多卖淫业的社会纪实材料,虽然它们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述,但是展现了1865年《奥林匹亚》中的阶级模糊性,他认为评论者对于这点是缄默的;更重要的是,他发现批评家们居然未将此画与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进行比较,从而“没有被给予任何可以参照的首要的所指系统,来作为一个对背离/偏向的检验”。
克拉克指出,与提香的画作相比,“传统在《奥林匹亚》中被滑稽化了:它隶属于某种退化的类人猿形象,裸女在其中被剥夺了最后的女性特质、肉感和人性,而只剩下‘随便什么东西的形式’——一只来自橡胶林的黑猩猩,手挠着外生殖器”。“在这种逃离了传统体统的制约这一点上,她已经不是以那种清晰展现出性征的传统裸体画法所描绘出来的一个修正形象。”所以,她看上去,既不是一个裸体,也不是一个妓女。“我的观点是,它改变了、甚至破坏了传统文化一直试图保持不变的东西,特别是对于裸女和妓女的看法。这也是《奥林匹亚》如此不受欢迎的原因。”
对于流行观念和流行图像的考察,在《人民的形象》中就已经成为相当成功的策略。克拉克接着阐述了《奥林匹亚》是如何背离、颠覆了传统文化中裸女画和妓女这两种形象的。假若“奥林匹亚是一个妓女”,那么按照当时的风化和画坛对妓女生活场景画的包容,马奈的画就不应该倍受苛责;关键之处在于,“《奥林匹亚》却试图更为彻底地描绘这一力量;它试图通过在妓女阶层与其赤身露体之间建构一种不同类型的关系,来拆解交际花这一范畴”。
要说清《奥林匹亚》对交际花神话的挑战,就要细细地观察它与西方裸体艺术(“裸女”)的传统或惯例的相异之处。在《对1865年奥林匹亚的一种可能性解读的初步研究》中,克拉克将这种观察称为“内行细看”,尽管当时也有批评家发现其中几点,但却没有将它们作为焦点来阐述,而克拉克要做的正是这些。
克拉克相当聪明地给出了一幅1865年的沙龙照片:《奥林匹亚》被学院派裸体画团团包围,显得如此突兀。奥林匹亚,是多么不同于那些官方认可的裸体啊!
正如肯尼思·克拉克在《裸体艺术》开头所说:“任何一个裸像,无论它如何抽象,从来没有不唤起观者的零星情欲,即便是最微弱的念头。如果不是这样,它反而是低劣的艺术,是虚伪的道德。”裸体画与单纯的赤身裸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艺术的一种语言,美的一种符号。但这是20世纪的想法,在19世纪60年代,裸女的负担是“得体”与“性愉悦”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想在没有太大的道德危险的情况下,通过她的赤身露体了解裸女,因为她的肉体与性是分离的,肉体得以显露,被赋予特点,并被归入秩序,不再成为问题的场所。但是,这种分离在19世纪60年代的裸体艺术中很难实现,这就让当时这一画种的位置显得尴尬。克拉克认为,《奥林匹亚》所做的,正是以一种视觉形式来坚持这种尴尬。这种视觉形式所体现出来的不可协调性(uncooperativeness)是相当微妙的,主要在四个方面背离了惯例:①画作展示方式(被悬挂在一个特定的、故意的、挑衅性的位置);②绘画中的“不正确”之处(身体的错位、畸形和线条的尖锐); ③对“性的标记”(居然有体毛和秃发症);④强调了材料的物质性。
由此,克拉克指出了马奈的《奥林匹亚》是对19世纪60年代法国巴黎的妓女神话与裸女惯例的双重挑战与颠覆。结果是,这种挑战造成了一种理解障碍和评论失语。尽管“想将马奈当作一个库尔贝式的现实主义者,但是,奥林匹亚……既不是按照裸画的图像来处置的,也不是按照现实主义那种对传统的激烈驳斥来处理的,它所策划的是一种僵局,一种障碍”。这种“体统和羞耻的奇怪共存……就是1865年这幅画的难处”。
经过长篇累牍的解析后,克拉克总结到,裸体是一个阶级标志,批评家在将《奥林匹亚》进行分类时的困难,其所产生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去看到,阶级的标志物是她的裸体上,而不是她的附属物上。“她实际上来自社会底层。”克拉克认为,这显然暗示出了《奥林匹亚》的先锋性,它可能是一个对现成流行的符码(或惯例)进行的无效的颠覆、拒绝的案例。虽然克拉克并未肯定马奈具有革命性,但是在克拉克看来,他已经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也已经以敏锐的背离传统惯例的新风格快速地记录下了他们那个世界的某些关键的变位(dislocations)。
不得不说,克拉克对《奥林匹亚》这幅画作进行的长达三十页的视觉分析文本,是稠密、迂回而迷人的,但却不容易把握主旨。如果我们游离于《现代生活的画像》这本书的主线,就有可能抓不住克拉克笔下最为基础性、决定性的主旨。一旦我们细究这一章,就能明白克拉克摁在时代的动脉上——“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妓女是最重要商品的供应商。”“商品”或“商品化”这个词鞭策着所有章节的展开,决定了章节的结构,它构成了克拉克在导论中所说的“社会总体实践”——“景观”。
在《现代生活的画像》中,克拉克将奥斯曼巴黎改造和商业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作为“景观”的大背景,描述19世纪下半叶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兴起及其对生活方式、审美兴趣的特殊追求,从而揭示马奈画作的复杂性、暧昧性。在他看来,马奈及其追随者的绘画,正是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和后果:视觉空间的平面性,对社会阶级的不充分或含糊的再现。
以“景观”作为坐标点和视角来看《现代生活的画像》的篇章结构,其逻辑不是一目了然的吗?四幅马奈画作:《1867年的展览会》(1867)、《奥林匹亚》(1863)、《阿让特伊的划船者》(1874)和《女神娱乐场的酒吧间》(1882),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的,而它们相对应的社会现象,亦是景观循序渐进的侵袭过程:
(1)巴黎的奥斯曼城市改造及公众对其的接受;(2)第二帝国时期的卖淫业的社会生态;(3)巴黎的郊区,被一个新的未确定的阶级的度假生活所侵入,这个阶级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模糊不清的交界面上;(4)城市私人生活的面向,即新兴阶级在音乐咖啡馆里的生活。正如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的中肯评价,那些是“一系列排列的图像所构成的地方,这些图像的关系,在不经意间,揭示了那文化想要抑制的严酷现实”,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城市、女人、郊区和咖啡馆”都逐渐成了景观的表象。在我看来,这四幅画安排并对应的城市生活,显示出了“景观”从公共场所向私人场所、向日常生活世界侵袭的过程:城市街道—展览馆—郊区—咖啡馆。
克拉克在修订版前言的开篇指出:“《现代生活的画像》讲的究竟是什么?我想,首先,它讲的是绘画与某种现代性神话之间的邂逅,以及这一邂逅验证现代性神话的方式和时机;还有绘画发现了整体上在巴黎(以及关于巴黎)所提供的图像及其理解框架的种种缺陷,并对同样的材料建构出另一个形象(另一种理解框架)。”
而这个现代性神话,正是景观侵入社会方方面面、侵入日常生活世界的神话。
The “Spectacular Myth”: On T. J. Clark’s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In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T.J. Clark takes the reformation of Osman Paris and commercial capitalism’s rapid growth as the background of “spectacle”, depicting the rising of petty bourgeoisie, and their special pursuit of lifestyle, aesthetic interes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of Manet’s painting. From his perspective,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paintings are the re fl ection and resul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the parallelism of visual space and the insufficient or ambiguous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lasses. Four pictures of Manet are the discussing object of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manifesting the process of Spectacle’s invasion from public sites to private ones or daily life: city street—exhibition hall—suburb—café. From Clark’s opinion, the legend of Modernism is the invasion of spectacle everywhere in the society, or the invasion into the daily life.
T.J. Clark, “Spectacle”, Manet, Ideology, Dail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