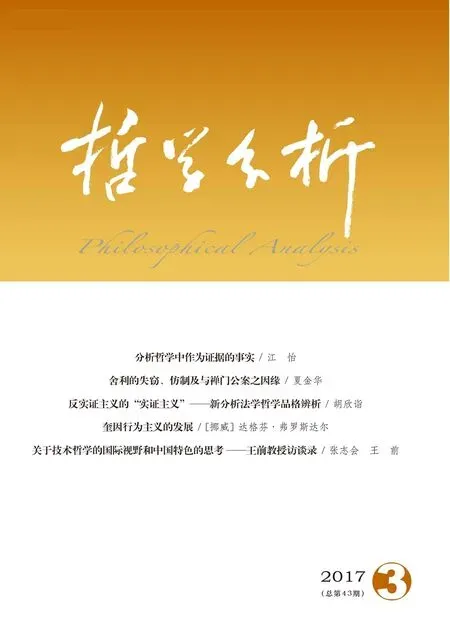奎因行为主义的发展a
2017-06-15挪威达格芬弗罗斯达尔
[挪威]达格芬·弗罗斯达尔/文
钱立卿/译
·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
奎因行为主义的发展a
[挪威]达格芬·弗罗斯达尔/文
钱立卿/译
奎因从早年起就主张一种行为主义,但这种行为主义必须通过分析语言、感觉材料、刺激与被刺激等概念来理解。对奎因而言,语言理解与翻译的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些概念之间的交合关系。语言是一种社交性的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技能,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通用的提示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信号。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我们也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对语言的意义。奎因认为,从简单的交流到复杂的理解,体现出理论与意义的交互作用具有越来越高的普遍性,我们直接感知到的总是有意义构造的各种整体,它们只有在共同认知与理解的意义上才能被视为行为证据。个体性并不是认知的出发点,我们恰恰必须基于共同体的一致性才能给出个体化的确认。
行为主义;证据;刺激;三角测量
一
常有人说,奎因的行为主义是从斯金纳那里来的,他们两人在1933年成为哈佛学社的第一批青年学者(Harvard Junior Fellows)。然而据奎因说,他的行为主义更早的时候就有苗头:“早在20年代我在欧柏林读书的时候,就接受了雷蒙德·斯特森(Raymond Stetson)的行为主义,他很明智地让我们读约翰·B.华生的著作《从行为主义的观点看心理学》。几年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我又因鲁道夫·卡尔纳普在《物理主义话语中的心理学》中表达的物理主义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行为主义。所以弗雷德(斯金纳)和我在嘲讽心灵实体(mental entities)的时候立场是一致的。我们都认为‘心灵不灵’(mind schmind)。①按照弗罗斯达尔的解释,这句话仅仅是一个押韵的文字游戏,schmind类似英语里blabl①,表示不知所云或无足轻重的意思。这个表达是奎因用来讽刺以“心灵”作为哲学切入点的做法。弗罗斯达尔建议在中文里也找一个类似的说法,既能表现出字面和音韵上的关联,又能表达出这种讽刺意味。笔者权且作是译。—— 译者注心理对象当然不同于鸟类。更不用说关于自由和尊严这种话题了。”②“Quine at Skinner Retirement Party”, in Quine in Dialogue, edited by D. Føllesdal and D. Quin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91.
奎因的行为主义在他一生中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本文将追溯这些变化以及背后的动机。作为讨论的背景,我们先要概述以下两个问题:什么是行为主义?为什么会有人成为一个行为主义者?(一) 什么是行为主义?
各式各样的不同观点都在使用“行为主义”这个标签,但这个词并非总是有明确的定义。30多年前,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在《解释斯金纳》一文中c,区分了许多种类的行为主义,自此以后这个词就增添了更多种新的含义。大致来讲,这些行为主义可以分为两类,即本体论行为主义与证据行为主义。本体论行为主义认为,不存在什么心理对象;而证据行为主义的观点是,行为提供了心理对象及其性质的唯一证据。
早期的奎因似乎是个本体论行为主义者,他说“心灵不灵”。本体论行为主义往往是教条的,它默认了本体论观点,但不需要证据。奎因很早就摆脱了他不成熟的教条观点,开始专注于证据。一般而言,他的本体论观点来自科学: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时代最好的科学理论所需要的实体存在。对早期奎因来说,心理对象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在科学理论中似乎从不起到解释的作用。谈论心理物就像谈论意义一样—— 正如我们没有意义的同一性标准,我们也没有关于心理状态的同一性标准。从1957年开始,奎因一再地强调他要求的本体论的最小前提:“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④奎因的这个短语似乎第一次出现在他1957年12月的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致辞中,第一次刊印于协会1958年的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重印见于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3。
最终,奎因的行为主义源自其经验主义,即关于我们世界及他人的所有知识都要通过感官呈现给我们。在1994年的《哈佛评论》里,奎因说:“行为主义,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只是一种主体间的经验论。它在态度方面是经验论的,但并不能以胡塞尔或旧的认识论者的方式,满足于私人的、内省的材料。如果你把自己的知觉当作你的材料,把你同伴那里的材料也合并到一起,给它们共同的命名,那么你就有了与主体间行为主义层面上的科学相关的那些材料。我不觉得这超出了每个现代科学家都会理所当然认同的观点。”①Bradley Edmisterand Michael O’She①, “W.V. Quine: Perspectives on Logic, Science and Philosophy,” Harvard Review, 1994. 此处引自Quine in Dialogue,p.47。
这段话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奎因在反思行为主义的时候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但对本文而言却是关键的—— 与行为主义相关的主体间性不只是把你和同伴的知觉材料混到一起那么简单。我们在科学中就是这么处理所有材料的,比如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材料。对行为主义而言重要的是,材料与行为有关,而且必须可被社交性地获得(socially accessible)。也就是说,行为主义并没有囊括所有经验证据,而只是考虑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获得的那些与行为相关的材料。(二) 为什么是行为主义?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背景问题:为什么会有人成为一个行为主义者?
做一个行为主义者的理由在于,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某些社交现象时,比如说语言的学习与使用,我们必须专注于参与者在相应的社交情形下可获得的证据。这种证据是经验性的,通过我们的感官来获取。哪怕是相信心灵感应的人也很少宣称心灵感应无所不及,甚至在语言学习中也有作用。然而,所有通过感官渠道获取的东西并非全都能在正常的公共交流中获得。比如说,脑科学家在研究大脑活动过程中得到的洞见或许能帮我们理解,我们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时候,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这些见解并不属于语言生成或代际语言学习及使用中起作用的那些证据。实验室观察也尚未成为此类情形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要理解语言如何产生、如何学习及如何使用,就必须把焦点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所能获得的证据上。
这就是我们称为“行为证据” (behavioral evidence)的东西。证据行为主义的观点是,为了研究某些类型的社交现象,人们必须特别关注这类证据。
(三) 语言的社交特性
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常说语言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可是,他们很快就忘了这点,而接受了那些不可以社交的方式获取的意义观念,也不清楚那些东西是怎么被我们理解的。弗雷格的“意义”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他没有假装对语言的社交特性发表长篇大论。当人们已经表示语言是社交性的时候,再去诉诸意义、概念或其他类似弗雷格的“意义”的东西时,就不太有说服力了。
奎因是第一个认真对待语言的社交特性并为了意义与交流而探究语言之影响的人。他的出发点今天似乎每个人都同意,即语言是社交的。然而,他对问题特有的敏感使其在别人觉得一帆风顺的地方看出了问题。这也让他得到了一些革命性的、成果丰富的洞见。我们现在来看看。
二
(一) 奎因论彻底的翻译
奎因对翻译的看法也影射了他把行为看作证据的观点。他认为,把两种语言相互关联起来的翻译手册,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
(1) 观察。大致说来,各种翻译手册应该把一种语言里的观察句映射成另一种语言里具有同样“刺激意义” (stimulus meaning)的观察句。我这里不解释“观察句”和“刺激意义”的概念,因为后面会表明,奎因对此看法的细节无关紧要。
(2) 善意。不要把当地人都赞同的语句翻译成你觉得荒谬的句子,亦即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当真的句子。也不要把当地人都不同意的语句翻译成你觉得显然为真的句子,亦即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当假的句子。
第一条限制诉诸刺激物和刺激意义。奎因表示,这就是行为主义出现的地方。在两种语言之间做翻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两种语言使用者的感受情形。
从当前的目的来看,对一个视觉刺激最好的确认,或许是眼睛的色彩辐照。深入主体的头部细看,会是一种不适当、甚至错误的做法,因为我们需要避开特异的神经路径或私人习性构成的历史。我们考察的是他受社交灌输形成的语言使用法,因此他对各种情形的反应也通常是从属于社交性评价的。眼球辐照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考虑到说话者的定向以及客体间相对位置而进行的主体间的检验。①W. V. Quine,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0, p.31.黑体为作者所加。
奎因把行为主义和对刺激物的研究等同起来,这种做法是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的。然而,我们首先要注意,上述两种限制反映了奎因所见到的诸信念与意义之间的紧密关联。语句的一个主要用处是表达我们的各种信念。听别人说话,注意他们同意哪些语句、不同意哪些语句,我们就能对他们如何构想世界及其性质获得越来越形象的理解。翻译是一种分离意义与信念的方式,而做翻译手册的方法是让我们能够把别人看似拥有的各种信念归给他们。我们对似真性的思考涉及两个对认识论至关重要的因素:知觉和推理,两者反映在上述两个限制里。观察限制集中在知觉上,善意限制集中在推理上,两个因素间的互动也很多。不过,我们现在要继续探讨行为主义的问题了。
(二) 刺激
首先,我们要注意在《语词和对象》里有两个互相冲突的刺激概念。在此书开头的地方,奎因暗示了一种神经学的刺激概念,他写道:“那些截然不同的光化学效应通过红光的影响作用在人的视网膜上。”①W. V. Quine, Word and Object,p.6.不过,奎因在书里的其他地方把一种视觉刺激模式当作眼球的色彩辐照,②Ibid., p.31.通过这个用词来表明他心里想的不是受激的神经末梢,而是可以映在照相底片上且被每个人确认的那种光影图案。有些地方他把这种图案当作景象,③Ibid., p.32.而且是受到感官的阻碍的。④Ibid., p.33.在《语词和对象》里更加技术性地讨论刺激问题之前,奎因就已经提到,某些刺激是口头的。当有人问“这是什么颜色”的时候,“引起“红”的刺激物是个复合物—— 红色的光冲击眼睛,而问题刺激到耳朵”。⑤Ibid., p.10.当此书出版的时候,我正好是奎因的学生,我把“刺激”看作意指到达感官的东西,比如说,在视觉刺激中光的图案到达眼睛,而这也可以被指向同方向的、感应到同波长的照相机拍下来。然而,奎因告诉我,这不是他想说的意思,他说的是被触发到的神经末梢。
神经末梢的观点涉及两个问题。首先,奎因想要比较不同人接受到的那些刺激物,他一开始试图通过对比两个人受刺激的神经末梢来达到目的。然而这种对比很困难,因为,比如说在不同的人的视网膜里,神经末梢数量不相等,排列方式也不相似。奎因在《词语和对象》里已经注意到这点:“不同的人在同一种语言环境里成长的方式就好比不同的灌木被修剪并培育成一模一样的大象形状。不同灌木之间的枝叶在解剖学方面的具体形状会使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构造出大象的形状,而最后整体上的结果是差不多的。”⑥Ibid., p.8.
奎因多次提到这一点,最初是在1965年,在《命题对象》一文里。⑦W. V. Quine, “Propositional Objects,”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lumbi①, 1969,p.157.在1973年的保罗·卡鲁斯讲座里,他注意到达尔文已经在《物种起源》里写道:“即使从一窝昆虫里任意挑出一些来,也能发现它们在神经模式上有巨大的差异。”⑧W. V. Quine,The Roots of Reference,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74, p.24;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London: John Murray, 1859, pp.45—46.奎因经常回到这一点上,甚至在他最后的著述中也提到了,比如,“The Growth of Mind and Language”, University of Oldenburg, Germany, June 5, 1997,reprinted in Confessions of a Confirmed Extensionalist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D. Follesdal and D. Quine,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84。(以下简称该书为Confessions—— 译者注)此外还有“Progress on Two Fronts” (1996), Confessions, p.474,以及“Three Networks: Similarity, Implication, and Membership”(2000), in Confessions, p.493。
把视觉刺激物视为射入眼睛的辐照模式就能解决上述第一项反对意见,因为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比较这些模式。这些刺激能算是行为证据吗?显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研究人们接受到什么样的光线。我们更倾向于观察他们在看哪儿,而不是去想象何种光线射入他们眼帘。然而,我们稍后就会发现,不能简单地拒斥光线入眼的问题,实际情况比我们所想的更为复 杂。
(三) 戴维森:一致性的最大化
唐纳德·戴维森看到了刺激物中的困难,无论如何理解它们都会出问题。他没有去设计一条新的路线来处理知觉问题,而是主张彻底抛弃奎因翻译手册的第一个条件,并把交流和语言学习完全置于第二个条件之上,即善意原则。戴维森把这条原则强化为一致性最大化原则:把他者的意思按照取得最大限度同意的方式去诠释。“一致性最大化”这个表述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反复出现在戴维森的论文里,比如《真理与意义》 (1967年)里是这么解释的:“语言学家会试图构建一种在外国人看起来为真的特征描述,即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种映射,把外国人认为真(或假)的句子映射为语言学家认为真(或假)的句子。”①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Synthese, Vol. 17, 1967, pp.304—323, reprinted in Donald Davidso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在比较不同的诠释时会有一些问题,一种诠释在某些点上获得了一致,另一种在别的点上取得了一致。那么,我们该如何考虑或测度一致与不一致呢?
可是,戴维森的一致最大化原则里还有个严重得多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直觉上希望取得一致的情形。比如,我和一个当地的向导一起跑到森林里去,这时我看到一只兔子并做出了一个尝试性的假设,即向导说的gavagai和兔子有某种关联,然后我要通过说出gavagai来验证我的假设。如果我的向导不同意,那么根据戴维森,我会认为这推翻了我的假设,可能就会放弃这个猜测。然而,如果我注意到我的向导被一棵树挡住,看不到兔子,那我可能反而会把他的不同意见视为对假设的证实。我不会期待向导的视线能穿透这棵树,这是我从过往生活当中获得的基本知识。这就意味着,我确实考虑到我的向导是如何获得其信念的。所以,认识论在这里是起作用的。我不应该只是把一致性最大化,但在我应该接受一致性的时候我得把它最大化。知觉在认识论里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又得再次回到奎因。②关于这方面更多的论述,参见我的文章“Meaning and Experience,” in Mind and Language: Wolfson College Lectures 1974,edited by Samuel Guttenpl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p.25—44, 特别是pp.39—40。
(四) 戴维森:三角测量
1973年,戴维森在了解到树后面的兔子这个案例以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不再提一致性最大化了。然而,几年以后他又提出一种想法,即三角测量。这仍然是个简单的想法。简而言之,一门语言开始部分的学习,也就是很接近知觉的那部分,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教师、学生和对象,它们形成一个三角形。当对象对于教师和学生都很明显的时候,教师给出了一个与对象有关的表达,比如gavagai。学生把声音与这个明显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从现在开始也使用gavagai来表达对这个对象的注意。
这个例子里隐藏着好几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来研究。然而,戴维森余生都坚持这种三角测量观点,而且他对奎因不接受这种观点感到遗憾与震惊。特别是,1986年斯坦福的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主办了一次长达一周的紧张激烈的讨论会,三角测量的问题成为会上的焦点议题,而奎因从始至终坚持认为尽管三角测量的想法具有真理的核心,但也掩盖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
(五) 奎因论“远端”与“近端”
那么,这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呢?事实上,奎因在《语词和对象》的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观点。此书序言的第一句话就简要地表达了他的观点:“语言是一种社交性的技能,为了获得这种技能,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通用的提示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信号。因此,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我们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对语言的意义。”①W. V. Quine, Word and Object, p.ix.在正文的第一节里他又重复说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人们相互沟通、交流中,通过可见的谈话动作从他人那里学会自己的语言的。”②Ibid., p.1.他在下一句话里对此作了解释:“从语言学上,因而也是从概念上看,只有那些可公共谈论、可经常谈论并可用名字标志和学习的事物才是处于中心的事物。语词首先便是用之于这些事物的。”③Ibid.
人们往往会拿奎因的“近端”观点与戴维森的“远端”观点对照:奎因被认为是坚称我们对刺激做出反应,而远端观点则认为我们对临近范围内的日常对象做出反应。
远端观点看起来更加可信,可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见,奎因在《语词和对象》的开头就把这个观点视为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在面对可共同看到的事物时,通过主体间的谈话动作来学习语言。
所以,奎因在《语词和对象》一开头就具有了一种远端的观点。那为什么他到了第二章里开始讨论刺激?我认为,原因在于,奎因一如既往地看到了其他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奎因问道:“我们如何知道他人把世界当作在彼此看起来都是同样的客体?”如果我们预设他们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把问题本身当论据。学习一门语言并用来交流的一个原因正是我们想搞清楚别人对世界是怎么看的。奎因在《对真理的追求》中又谈起了斯坦福的那次讨论,他说:“他(戴维森)对兔子与类似案例的具体化对我而言是他整个策略的一部分,不能当作设定的一部分忽略过去。”①W. V. Quine, Th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2.奎因在从《语词和对象》起直到最后的著作中都在努力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六) 接受与知觉
奎因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知觉到的对象是刺激。我们知觉到了物理对象。这就关涉到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我们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使用的证据是大家都可以获得的。至于第一个问题,即主体间刺激的比较,奎因在《指称的根源》 (1974年)里已经开始逐渐弄清楚了。他引入了接受和知觉的区分,并在后来的著作中再度加以讨论。在他最后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叫《我、你和它:一个认识论三角形》 (1999年),②W. V. Quine, “I, You, and It: An Epistemological Triangle” 最初出版于Alex Orenstein和PetrKotatko主编的Knowledge, Language and Logic: Questions for Quine,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p.1—6。正文中涉及的部分见于重印的Confessions, Chapter 44。其中通过一个三角形来表明了一个想法—— “戴维森偶尔会提到”。
在这个三角形里,你是一个顶点,我是另一个顶点,第三个顶点上有某个对象,一个我不熟悉的生物。你告诉我它的名字叫土豚(aardvark)。③Confessions, p.485.(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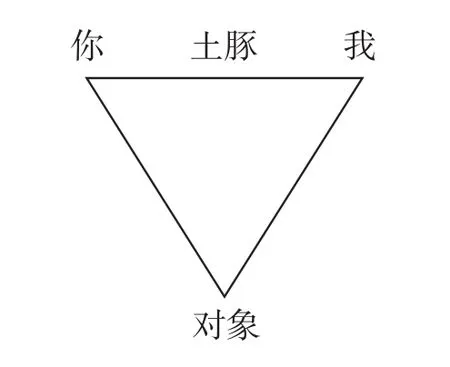
图1
奎因指出,我们是以不同方式被联结的:“当我们观察土豚的时候,在你我的神经系统里发生的事情根据视角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差别而出现不同之处。我们的联结方式不同,感觉也可能不一样,如果这种说法有意义的话。我们明显共享着的所有事情是我们神经事态的远端的原因:土豚。最后我还是把这个词和我的刺激联系在一起,正如你通过你不同的神经摄取那样,我的神经当然也在摄取数量上不同、其他地方也有着某些不同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一致用词的近端原因上也存在差异,但我们共享了远端原因,即在我们因果链远处的那个指称。”①Confessions,p.485.
(七) 接受性差异—知觉性相似
当我从你那里学到了土豚这个词以后,下次当一个土豚出现时,我们两个都看到了,我说“有个土豚”,而你表示同意。
我们接受到的东西是不同的,我们神经末梢的触发配置和神经网络中发生的事情也是不同的。然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知觉到土豚的时候,我的神经摄取产生了相同的语词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相似的。奎因说,神经摄取有知觉性的相似,这对你而言也一样。所以,尽管我接受到的东西和你接受到的东西有巨大的差别,我们的知觉判断还是一致的。
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知觉相似性的标准,这些标准与自然事件的相继过程有着较好的吻合程度。这些标准似乎也有助于交流。但交流亦会导致我们知觉相似性标准的变更。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八) 前定和谐
总的来说,如果第三个顶点上的事件在两个场合下产生了我和你的神经摄取,那么你我各自的摄取对自己而言都是知觉性相似的。奎因把这种平行的情况叫做你我的知觉相似性标准之间的前定和谐。多亏了这种和谐,你我的知觉相似性尺度才能非常好地配成对。
奎因注意到,这也适用于我们语言中的声音部分:“考虑我们心智的契合时,需要前定和谐的方面不仅限于土豚,同样还包括用什么来称呼它们—— 优美的荷兰式双音节aardvark。一个词在语音上的恒常性,从一种发音到另一种,其自身就是说话者主观的知觉相似性标准的产物。多亏了这种和谐,交流才能飞快地进行。啊,我们听起来很像,啊,谁这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觉相似性标准,这些标准都处于和谐之中。”②Ibid., p.486.
(九) 知觉相似性与自然选择
不仅语言学习,所有的学习也都基于我们神经摄取的知觉相似性。期望、归纳和习惯养成都依赖它。既然知觉相似性是学习的前提,它就必须至少一部分是天生的,但它被乔装打扮成了学习中的进步。
作为语言学习基础的平行的相似性标准也让间接性的归纳得以可能—— 我可以学习世上的一切,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以及学习他人经验来调整自己的期望和习惯。这既解释了天生性,也解释了前定和谐,两者都有利于自然选择下的生存。
三
(一) 相同和不同
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在讲相似性,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心灵如何在相似的对象和对象的称呼上遭遇彼此。可是,我们现在要来思考一个例子,它会带来全新的东西。你告诉我“土豚”这个术语时,一个陌生人走过来,我指着那个土豚,而他说“Fido”。啊哈,我猜想这是另一种语言了。我再次指向土豚并说“Fido”,这个陌生人赞同地点头。土豚又一次过来了,我又说了“Fido”,但陌生人似乎不同意。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下次我们到看到土豚的时候,我开始迷茫了。对我而言,土豚看起来是一样的,我徒劳地尝试记录差异来解释陌生人是如何使用“Fido”一词的。我知道我不是土豚专家,之前也在区分榆树和山毛榉的时候遇到困难,所以我假定自己必须多学一点关于陌生人叫做“Fido”的那些动物的知识。
不过我的土豚研究可能一无所获。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不仅限于相似性。我们认为世界是由对象构成的,它们彼此各不相同,尽管其中一些看起来很像。反过来说,同一个对象也可能在不同角度、不同时间看起来会有差别。为了掌握一门标准语言以及理解他人如何构想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掌握两种相互配套的设置:相似性与差异性、等同与不同。它们能以四种不同的方式结合,图示如下:

图2
掌握这两套对立的组合对我们要求很高。我们必须把握空间、时间、因果性以及重复出现的持续对象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一股脑儿出现的,而对儿童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表明,他们要花数年时间才能掌握这些复杂的东西。孩子或许很早就能够使用表达不同指称的词语,比如“狗”或“球”,但有些词是用来指示像一大堆东西那样的事物,比如“水”,这只有在孩子掌握了个体化与指称的整个使用方式后才能理解。
(二) 个体化
这就把三角测量的情况弄得更复杂了。为了解释他者,只是把相似的判断匹配起来是不够的。我们还得以相似的方式把世界分割成各种对象。刺激并不充分决定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来保证我们把世界以同样的方式个体化。怠惰通过我们神经系统的特征被还原掉了,在这方面奎因提到了胡贝尔和维塞尔以及许多其他研究者的工作,即对环境中不同的特征所做出的选择性反应,比如特殊的对角线、从右上到左下、两侧对称,等等。①奎因对此最详细的探讨见于“In Praise of Observation Sentenc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90, 1993,pp.107—116,reprinted in Confessions,p.417。
我们生来就有许多倾向与能力,可以表达世界的某些特征以及归纳式地推广出去。这些能力对知觉和行动以及语言学习而言都有决定性意义,通过学习语言,这些能力就会更发达、更高超,反过来也促进了进一步的语言学习。
我们开始学一门语言的时候,会在彼此都能接触到的证据之上把语言表达与我们不同的期望与其他一些倾向联系起来。在知觉中,我们有很多期待和暗中的假设,它们可能被证实也可能被否证。期待有可能是错的,但毕竟还存在着可以对或错的事情,因为存在着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判断。因此,有许多东西未充分确定,但很少有不确定的东西。然而,只要我们从知觉领域向理论区域外推的时候,理论与意义的交互作用就会更加普遍。因此在理论领域中,翻译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会更显突出。这些领域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把意义当作一开始存在于我们心里然后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正如福多和其他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并没有什么原始意义存在于我们心里。在心灵和意义之间有密切而有趣的关联,但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语言的公共性质,就会对这些关联产生错误的理解。
奎因的语言学习理论不是近端而是远端的,这一点并没有消除或还原掉翻译的不确定性。恰恰相反,比起近端观点,远端观点包含的不确定性会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假定一个人知觉到了哪些对象,而这些假定比起假定他受到了哪些刺激来说,远为不充分确定。这里我们有部分的不充分决定性和部分的不确定性,其中不充分决定性是说,存在着搞对或搞错的事情,这与自然科学里的情况相似。
除此以外,另一方面,翻译的不确定性比起《语词和对象》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也要少一些。大量的人类活动、实践与习俗里都对交流有作用,因此这些活动也帮助建立起了语言表达的含义与指称。②“Meaning and Experience”, in Mind and Language: Wolfson College Lectures, edited by Samuel Guttenpla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5—44.所有这类证据都应该纳入翻译和解释的意义研究,而不只是赞同和分歧的事情。
个体化,或者奎因经常说的具体化,对我们的理论来说是相当基础的过程,同时个体化也要基于这些理论。在我看来,这对语言学习和交流也至关重要。当我们想理解另一个人,我们必须假定他人知觉到了什么对象,他认为这些对象具有哪些性质,也就是假定他人关于所知觉到的对象的理论和结构。当理解的过程进行的时候,这些假定可以在大家都能接触到的证据基础上得到修正,如同纽拉特修正他的船那样。我们的理解总是尝试性的,没有船坞给我们提供一个坚实的、非内涵的基础来构建我们的理解,比如刺激或因果性。因此我们在一个圆圈上前行,我们使用关于知觉的假设去理解语言,利用尝试性的语言理解去改进我们对知觉的假定。但这不是恶性循环,我们只是在拓展纽拉特之船的明喻,从科学拓展到翻译与解释。
在《指称的根源》 (1974年)里,奎因论证说,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贝克莱与休谟讨论过的那种简单的感觉元素,而是有意义构造的各种整体:“面对围绕一个点均匀分布的七个点,主体是对组合而成的圆周有反应,而不是对圆周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产生反应。面对一个固体,主体直接感受到了一个有深度的物体。他没有经历过贝克莱那种关于纵深维度的推理构造,因为他没有意识到那种构造的二维材料。”①W. V. Quine, Roots of Reference,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pp.1—2.
(三) 奎因与胡塞尔
在这种联系下,奎因赞同地提到了格式塔心理学家。他本来是可以提到胡塞尔的,因为胡塞尔在更早时候的工作启发了格式塔心理学家,并且对个体化、知觉与交互主体性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像奎因那样,胡塞尔认为,我们知觉到了物理对象而不是感觉材料;他也主张,我们直接知觉到了行为,而不是物理运动,知觉到了人,而不是躯体。知觉和语言依赖于主体间的相互适应。胡塞尔极其详尽地研究了这种适应关系并得出结论说:“即便是直接知觉到的东西也是共同的。”②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覿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 The Hague:Nijhoff, 1954, Husserlian①,VI, §47, 166.19—22. Edmund Husserl,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David Carr,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p.163.
1973年,奎因在他的保罗·卡鲁斯讲座里也注意到了知觉的社交特性:“我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知觉是这样一种私人的事情,但是最能够证明什么可以算作知觉的东西却还得具有社交层面的一致性。”③W. V. Quine, Roots of Reference, p.23.
奎因从来没有研究过胡塞尔,但他的研究越来越沿着胡塞尔的方向去。他后来也发现了这点。在1994年接受吉奥瓦那·波拉多里(Giovanna Borradori)采访的时候,奎因说:“我发现胡塞尔和我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说出了同样的东西。”①Quine in Dialogue, p.64.
四
奎因的早期洞见仍然是有效的: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某些社交现象,比如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我们必须关注相关社交情境下的参与者都可以接触到的证据。这是奎因对待语言、意义与交流的全新处理方式的基础。证据是经验性的,通过感官来给予我们。对证据的进一步研究使得奎因的立场很接近胡塞尔,尽管胡塞尔有时被当作行为主义的一个极端对立面。然而,考虑到奎因对语言之公共特性的洞见有着根本上的重要性,我们不妨把“行为主义”这个标签贴在这个新的立场上,因为别的地方似乎也用不着这个标签。
(责任编辑:韦海波)
B94
A
2095-0047(2017)03-0120-13
①原文载于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48, No. 3, July 2011, pp.273—282。
达格芬·弗罗斯达尔(Dagfinn Føllesdal),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钱立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