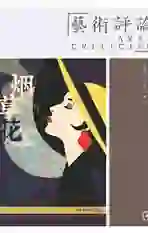两宋山水画中“风意”的表现研究初探
2017-06-14崔朝阳
崔朝阳
一、引言:“风意”图像的界定
“风意”图像是两宋绘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类别,主要指画面体现或者凸显一种“风”的在场状态。“风意”的存在使画面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表现力,在静止的图像中暗含一种动态的表达,渲染出特定的画面氛围。这种“风意”又因和画面其他景物的搭配组合,从而分化出不同的表现类型和画面意境。
因为“风意”的原型来自于自然界的大气变化而形成的特殊情景,又以在室外的表现最为普遍和突出。所以“风意”大多体现在两宋时期的山水画中,另一部分则体现在当时流行的以自然山水为背景的风俗人物绘画当中。
二、宋代山水画中“风意”图像出现的历史条件
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脉络来看,自汉魏六朝到隋唐时期,山水画多为人物画的附庸,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从晚唐到五代时期,山水画才经历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并在宋代进入中国山水画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具有“风意”的山水画图像才开始出现并日渐凸显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此前对山水审美的笼统、粗浅,反映在艺术表现上则又受制于山水画技法的时代水平而力不从心。
我们不妨据此来梳理一下中国山水画在宋代之前的阶段性水平。
魏晋时期作为山水画的萌芽阶段,伴随着道家思想的兴盛和山水诗的大量出现,审美关注开始投向自然山水,出现了一些有关山水画的论述。比如《画云台山记》和《画山水序》等早期山水画文献。前者主要记述了山水画的构图、着色等技术问题。而后者则重点从观道、体道的角度阐明了山水画的功能,所谓“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山水以形媚道”。至于南朝宋的王微《叙画》中所言及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
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 ”[1]则主要从审美观照的角度探讨一种主体情感的审美体验。
但魏晋时期真实的山水画状况呈现的却是这样的面貌。正如《历代名画记》(卷一)所描述的那样:“魏晋以降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 ”[2]可以说,魏晋时期山水画论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山水画开始脱离人物画的附庸,也奠定了后世山水画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基础,但在相应的艺术实践上却并没有实现同步。
隋唐时期(尤其是中唐以后)是山水画的重要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山水画作为独立画科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和技法上的进步。虽然直至唐初山水画仍多数是宫廷、台阁等建筑绘画的附庸,但在空间关系、树石比例等艺术处理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中唐时期的吴道子又促进了山水画技法多样性的变革,正如张彦远所记载的那样:“离、披、点、画,时见缺落。 ”大小李将军尤其是李昭道更是在李思训和吴道子的基础上推动了笔法、墨法以及设色之间的相互运用。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中论述的:“国初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 ”[3]唐代的王维、张.等一批画家也在前人的启发下,在墨法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形成一种不同于青碧山水体系的新画法——水墨渲染之法。从传为王维所做的《雪溪图》,以及结合张彦远评价其画“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来看,他确实是一改勾勒填色的古法,创造了一种“水晕墨章”的新画风。
如果说勾斫填色之法一直使山水画笼罩在一个略带装饰意味的稚拙阶段,王维、张.以及王洽等人所发扬的水墨渲染之法则直接促成了山水画向细致入微的“写真”方向发展,从而把山水画引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五代时期正是这种笔法和墨法交融整合的时期,尽管荆浩很大程度上发展了山水画的皴法,但从荆浩、关仝的山水画上可以看出两者尚处于一个初步探索的阶段。荆浩虽说:“吴道子有笔无墨,项容有墨无笔,吾当采二子之长,成一家之体。 ”[4]但从山水画史的整体来看,他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画家在笔、墨、皴、染等技法的结合上仍不能达到笔精墨妙、神形俱胜的地步。
以上所述可知,宋代之前的山水画仍然处于探索构图、比例、笔墨等基本问题的阶段,尚未形成技法系统的完整性。而对于山水画因为审美关注、季节时令、地域特点等因素所展现出的深刻性、丰富性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山水画中带有“风意”的图像作为一种微妙的艺术表现,在受限的历史条件下自然难以实现。宋人的山水画技法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趋于成熟和完善,从而具备了与“风意”表达相匹配的艺术表现力,也使“风意”图像的出现具有了可能。
三、“风意”原型的转换——从“诗词之风”到“画中之风”
宋代之前累积形成的山水画技法虽然为“风意”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前提。但“风意”图像出现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则在于当时文人画观念的深刻影响。
宋朝历代皇室对绘画的大力推崇,皇家画院的设立以及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参与,加之山水画在唐末五代时期的巨大进步,这些因素都促成山水画在宋代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景象。
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们不仅懂得区别“东南之山多奇秀”“西北之山多浑厚”的地域特征,对于气候的时令特征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郭熙《林泉高致集》中说:“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暗淡。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 ”[5]宋代山水画家对于自然中四季特征的敏感和关注反映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在审美意识方面的进步,不仅走出了“丈山尺树,寸马豆人 ”等艺术表現的基本层面,也标志着开始探索与画面整体氛围有关的意境表现。这种探索与改变在宋代中期开始的文人画观念影响之下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了新的审美风尚和艺术关注。
由于以中原为核心的宋王朝以及当时文化较为活跃的地区大多处于季风性气候的影响之下,所以四季交替的时间感存在常常是以风为标志的,生活在这一区域气候影响之下的画家们自然是感同身受。但山水画中的“风意”并非仅仅是一种对这种自然现象的简单再现,而是在其中暗含某种观念性的特质。
两宋时期尤其是宋朝中期以后,在文人画观念的影响之下,诗词等文学艺术开始逐渐渗入绘画。文人画家的创作自不待言,即使是职业的院体画家,从画院当时所实施的命题考核方式,我们也可以一窥“意境”“情趣”等本是文学评判的标准对于绘画施加的影响。作为宋代院体画家的典型代表,郭熙在《林泉高致 ·画意》中说: “前人言‘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哲人多谈此言,吾人所师。余因暇日,阅晋唐古今诗什,其中佳句有道尽人腹中之事,有装出目前之景” [6]由此可知,画师修习诗词文学,并且以此造境已经趋于流行。当时的山水画也因此开始进入一个“诗画融合 ”的成熟时期。
鉴于此,为了了解当时的画师们将怎样的诗词情怀融入画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宋代文人的诗词作品中大量出现的“风意”描述。比如:“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八声甘州》)[7]。“昨夜西风凋碧樹。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8]。“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9]。“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张元干《贺新郎》)[10]。“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11]。
由以上诗词作品不难看出,这些与“风意”有关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写景的,另一方面也具有一种隐喻的意味。文人们对一年四季中的气候变化有着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切身体会。加上中国自上古时代就已经流传下来的“比、兴”的人文传统,四季的风雨明晦也影响到文人画家对自然的感官认知,并因此在四季变化之中投射出自己的人文情怀,赋予各不相同的个人情感和精神意蕴。所以“风意”便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对外在自然的描摹,而是具有了某种特殊的精神指向。
从魏晋一直到五代时期,山水画作品大多处于“状物”的阶段,更加注重对山川自然等客体之美进行表现。但到宋代开始逐渐从“状物”过渡到“尚意”的阶段,追求主客融合。这种审美趣味的转变主要来自苏东坡、米芾等文人士大夫的大力提倡,他们所推崇的“诗画本一律”的艺术观念使得饱含文人审美情怀的诗词作品被导入到当时的山水画创作之中。在追求“意境”“意趣”的两宋山水画时期,因为诗词中对于“风”的描述俯首皆是,作为与文学作品紧密相关的“风意”图像的出现也成为一种由此及彼的必然。这种趋势随着北宋后期文人画观念的日渐深入开始凸显,但直到南宋时期则由于这种艺术观念的日渐深化而更为明显。
在追求山水画具有文学情景化的过程中,具有“风意”的图像很好地体现了这种需要,从而充当了重要媒介。因为带有“风意”的图像会更富于动感、动态,其中会显现出某种时间的流程在里面,因此很容易构建起一个具有叙事性场景的诗意空间,使得山水画具有了文学性。而且,这种“风意”会因和画面其他景物之间的组合关系不同而渲染出不同的情景,分化为不同的“风意”——无论是和煦的暖风或是凛冽的寒风。
一般而言,这种“风意”常常被引申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含义 ——“悠然之境”和“苦寒之境”。
“悠然之境”往往和暖风相关联,画面重在表达春日里煦暖的蓬勃胜景。画面中描绘的或者是漫步在柳树下的不羁高士,或者是在岸边悠然自得的放牧孩童,这类“风意”作品传达出的都是一种田园风光式的闲适图景。例如宋代佚名之作《柳塘呼犊图》。
“苦寒之境”则重在表现气象萧疏的秋冬景象,常常还会加上凄凄雨雪。这类“风意”往往和嵯岈枯木、滔滔江面、苍茫远山相结合,在落木萧萧的画面意境中传达出一种孤寂荒凉的感受,或者抒发一种登高怀古之意。例如李唐的《江山小景图》。
对于以自然山水为背景的宋代风俗画而言,带有“风意”的图像更容易打破一般画面的稳定状态,充当戏剧性场面的画面逻辑,表达一些突然偶发的场景,渲染出一种富于情节戏剧化的趣味。例如宋代的《风雨归牧图》《灸艾图》等。
所以,“风意”图像并非一种对外在自然的直接描绘,和西方自然风景画中的“风”(法国柯罗的风景画)有着很大不同,它反映着中国古代“主客一体”的审美观照方法。写景也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宋代的梅尧臣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表达了人受外物触动而引起主观情感的变化,又把情感寄托、渗透到物象之中的观点。
对于山水画而言,因为“风意”图像构建的是一个充满“比、兴”色彩的诗意空间,所以更容易拓展出一种境外之境,象外之象,也因此在宋代及其以后被众多画家所热衷。
四、“风意”图像的形式要素分析
在两宋时期的山水画作品中,“风意”图像体现在画面众多的形式要素中,其中首先是和构图的样式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新的构图样式才使得“风意”图像得以显露出来。对此而言,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从全景式构图到特写式构图的转变。
魏晋时期的独立山水画不得而见,无从考证。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即使是北宋时期的摹品,也可以作为当时构图样式的例证。反映在空间处理上,《游春图》着力描绘的是“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对于画面空间纵深度的处理,重点放在中景和远景的表现上,对于近景则缺乏细致深入的刻画。
唐代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和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等中唐山水画作品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即在构图取景上,主要刻画中景、远景,而不突出近景的描绘。从传为王维的《雪溪图》和同时期卢鸿的《草堂图》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共同风格。乃至到了五代的荆、关、董、巨之时,我们仍然可以从其《匡庐图》《龙袖郊民图》等作品中看到类似的情景。在北宋初中期的李成、范宽等人的作品中,往往通过高度写实的笔墨技巧来表达自然山水的蓬勃生机,于传神写照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构图布景上仍然多是巨嶂山水的全景式格局。
在北宋中后期文人画观念的推动之下,审美情趣、艺术追求开始转移,随之带动的是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从宋哲宗时期开始,雅致、精美的画风日益流行,以致于郭熙的画一度受到冷遇。这种审美分野在北宋后期初露端倪,终于在南宋开始确立了主体地位,此后注重画面情景、韵致的审美风尚大行其道。先前那种重峦叠嶂的全景式构图已经不适应艺术表现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近景为重点描绘的构图样式。在这种构图样式中,选取景物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所取视点逐渐拉进,画家更容易在画面上表达自己的匠心意旨,在对景物刻画上营造出一种情景交融的诗意空间。马远、夏圭所偏爱的“边角之景”山水作品堪称当时的典型代表。在前、中、远的空间结构中,近景描绘一时成为山水画的刻画重点。带有“风意”的图像作为一种自然形态的微妙变化只有在近景的特写构图中才能体现出来。
除了构图之外,对于“风意”的表达,当时的很多画家还通过不同景物的描绘反衬出“风”的存在。这些景物包括树木、落叶、水面、风帆等容易显现自身动态变化的物体。当然,有时候也会通过点景人物的衣襟、动势等来暗示,比如飘动的衣带、蜷缩的身体,或者悠然的步态。通过这些景物之间的组合关系来指明“风”的在场状态。
在笔墨等艺术语言的运用上,这些图像也与一般“无风”状态下的画面有所不同。画面中的点、线条的形态也有其一定的特征与规律。比如点线的运动具有较为统一的方向感,也具有很强的连贯性,以暗示“风”的存在与影响。在树木等具体形象的刻画上,常常打破一种静态的平衡感,表现树木的高低起伏和倾向一边的侧感,从而强化一种画面的动势。
五、结语
中国山水画中的“风意”不同于西方风景画中自然主义观照下对“风”的认知,而具有一种“比、兴”色彩。因为北宋中期以后文人画观念的影响,山水画逐渐开始对诗词文学“意境”“情趣”的追求,并在构图方式、景物选择和艺术表现上产生新的变化,“风意”图像因此成为山水画情景交融的一个典型反映。
由于带有“风意”的图像所具有的审美感兴特点和特殊的审美意蕴,“风意”图像逐渐成为山水画中的一种表现类型,对于宋代之后的山水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风意”图像往往和林泉中的高士、悠闲的渔夫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图像。
时至今日,全球化语境下的我们身处各种艺术观念的纷扰之下,困惑而盲目。关注并研究中国画中久被忽视的“风意”图像,有助于我们体会中国画的艺术特质,探寻富于人文情怀的中国画精神,在缤纷喧嚣的当代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