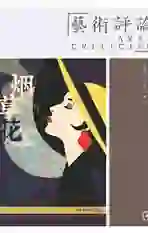最远的自由是梦想
2017-06-14张同道
张同道:你曾经从事过电影表演和制片,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什么突然转向纪录片?
雅克·贝汉:我的转向是为了开始。我一直对剧情片感兴趣,但是纪录电影对我来说变得必要,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生命被忽略,那就是动物。我认为它们很重要,我们生活在它们周围或者其中却不自知,唤起它们的存在非常重要。对我们而言,动物仅仅是陪伴,我们不怎么注意,然而它们是存在的。从历史得知,我们曾经来自它们,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与其他动物一起生存。一万年来,动物们的重要性是同等的,人并没有比它们更重要。然而,不知何时,人开始渴望征服,征服星球。人希望比树木更强,比植物更强,比其他生命更强,这不公正。人赢了,但赢到了什么呢?赢到了灾难。其实人所做的不太漂亮。如果我们果真获得了全胜,完全清除了动物,那就是最可怕的征服,因为人们可能孤独一生。如果只剩下我们,一位教授曾对我说,只剩下人类是最不人道的。我们需要其他生命!因此我对自己说,这在今天尤为重要。农业是必
不可缺的不仅保护植物,还有动物,它们一起存活。我们需要保护自己,而拼命地自我保护使我们变得脆弱。这样不行,我对自己说,一定要表现动物们的存在。那么,我相信我们需要的第一抹清新的空气,就是其他生命的在场,尊重他物就是尊重自己。不要用斗争,斗争曾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在欧洲和法国,大量的动物消失了,我想中国也是如此。是恢复的时候了,是停顿的时候了,是与它们和谐共处的时候了。我们尊重他物,就是尊重自己。为了关注他人或自我,首先要关注他物。
张同道:1989年你制片的《猴族》,标志着动物电影在法国的崛起,这部影片带给你制片系列动物电影的念头吗?
雅克·贝汉:对, 25年了。那时我在印尼拍摄,当时印尼有很多大猩猩。 25年后,一部分森林已经消失了。当森林消失,猩猩们失去了生存的原生树木,属于灵长猿类的红毛猩猩也都消失了。不再有森林,不再有动物,不再有欢乐。如果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在水泥世界里,生活在汽车、污染之中,那就完蛋了,无可挽救了!就没必要继续存在了。如果我们停下来,就像在中国或法国,停止污染几天,这足够吗?显然不够,那只是几天的补救措施,并不是深层的治理方法。
现代世界的科技工业发展非常快,大家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我们会窒息,会窒息!我们不要窒息,要找到生活的愉悦,生活的和谐。你知道大自然怎么能够恢复我们对自然所做的破坏吗?这并不难,什么都不要做,就让它安静,它会独自重新开始。你知道海洋,有些地方鱼消失了,不再有鱼,我们做保护区,不准捕鱼,不准游览,让大海安静, 10年后,鱼又出现了。 10年后形形色色的植物,海底草本都长出来了。因此我们留一些地作为休耕地,一年两年内不动它,这样妙极了,大自然和土地得到了恢复。但是现在农药和杀虫产品正在耗尽自然。
你知道对于土地最重要的动物是什么?是蚯蚓!蚯蚓在地里钻洞,它们钻出的小路渗透进来空气,通气让土地恢复。但是如果我们放杀虫剂或者夯实泥土,就会变成水泥,会死亡!为了明天的健康,为了未来的一代我们的孩子,现在就要做准备。中国很大,欧洲很大,大家可以去很多地方,未必都要集中在人口稠密区。当然也要有贤人,权力阶层应该与哲学家、自然主义者、科学家配合。科学并非留在实验室,而是要为社会服务,权力阶层要利用他们的建议和知识,联合起各方精英,引导国家和谐发展。
张同道:《微观世界》的创意是从哪里来的?
雅克 ·贝汉:当我开始制作《微观世界》这部影片时,我以制片人的身份去见资助商,告诉他我要拍一部关于昆虫的电影。他们说:“什么?昆虫?蜘蛛?蚯蚓?没人感兴趣!太可怕了! ”我说不会,这很重要。我刚才讲了蚯蚓的重要性。大树如何生长?谁会在土里播种?昆虫和植物互相依存!蜜蜂吃很多的花粉,弄得到处都是,然后它飞的时候也是到处撒粉。有人断言,如果没有蜜蜂,那就是世界末日!但是很遗憾,现在很多蜜蜂消失了。这些小事我们曾经认为是无益的。当我拍电影时,人们脚踩昆虫,从不注意。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毕竟,我们喷向昆虫的杀虫剂,能杀死所有的昆虫。当家里出现蚂蚁,只要用柠檬涂在蚂蚁经过的路上,它们就不会来了。不用屠杀,不用杀光我们周围的昆虫,就可以保护昆虫们的生命。经常有人问我,狼变成了什么?动物们怎样了?我解释说拍完电影之后,我还照料它们,我把它们放回可以继续生活的地方,不会因为拍完就不管了。但是有人问我,《微观世界》里的昆虫变成什么样了?我也不知道,不知道那个苍蝇去哪儿了,蜜蜂飞哪儿了。(笑。)
张同道:因为《微观世界》你获得了恺撒最佳制片人奖,随后转为导演,为什么?
雅克·贝汉:我想做制片是希望负责。做演员只是等待,然后做表情,然后休息。这不够,我希望统筹,负责任。我制片了很多电影,你也知道得过奥斯卡奖,我很喜欢筹备电影。制片也是导演,即项目导演,不是電影导演。然后我想走得更远,为了想象一些不存在的事,让一些头脑中的想象落实下来。一些演员可能说,这不自然,什么是自然的?假的。我喜欢想象的游戏,联想的游戏,我喜欢使之成型。我联想的都是真的,是真的,虚构的真实。孩子们玩捉迷藏,过家家,不是真的,但是他们相信,就好像是现实。想象的力量是巨大的。真正的自由是交流。地平线是最远的,更远的看不到的,就是想象,地球之外,星空之外,微观世界。自由就是想象,不要自闭在现实中,就是第一个概念:独立和自由。
张同道:从《微观世界》中发现小动物之美,到《鸟的迁徙》里发现鸟的伤害,再到《海洋》里灭绝的动物,最后在《季节》里,你几乎是在呐喊:人啊,请与动物分享地球。你是不是对自然的未来已经绝望?
雅克·贝汉:是的,无望的。其实本可以更好,人有理智的能力,就好像当人富有了就渴望更多,人赢了就认为能赢更多,然后还要更多。面对死亡我们并没有赢。幸运的是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努力渴望,努力想要全部占有,结果呢,生活得不幸福,或者不如原本可以有的那样幸福。利用和分享,懂得分享是伟大的美德之一。我们无异于其他生命,我们生活在动物的旁边。实际上,没有整体而言的动物,就好像人类和个人。人类由很多个体构成,许许多多的个体繁殖成百,成千,百万,十亿。
当我跟你讲话时我们对视,有交流!我们以为跟动物没有交流,它们只在园林深处。其实不是!我拍电影时发现它们
有眼神!能理解,有很多个体。有些动物跟其他完全不同。当我和鸟一起飞行,通常有头鸟打头阵,其他则静静地跟着。我们感受到它们心理和性格的不同,每个个体、每种类别都是重要的。世界不是笼统的,世界是由成群的各不相同的个体组成。是这些在一起形成了生命。不只有印度人,中国人,法国人,不是,是全部的个体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动物们并不笨。在《猴族》里,我发现了温情,情感就是智力的证明。我们有孩子,我们会抚摸他,关注他,因为我们有智力。当我们看那些动物,它们也会保护弱小。我们拍摄猩猩的时候,有一个林中的小细枝快要刺碰到小猩猩的脸时,大猩猩小心翼翼地推开,这就是智力的证明,天生的智力。两个月大的婴儿丢在自然里,可能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动物们,它们摆脱困境,善于应付。它们东寻西找,找东西吃,寻求生存下去。鸟儿飞行,为什么飞?并不是为了愉悦,而是为了生存!因为它们竭尽努力,竭尽翅膀所能,飞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能够果腹、能够吃饭的地方。
我发现动物们长大到 6个月时,它们一起游戏就像孩童在校园里一样,它们开始有所区别,有的想比同类更厉害,要占地盘,有的甚至在建立权威的时候发生暴动。有些勇敢的想要获取权利,当它们获得权利以后,又要防止别的动物抢占,一场永久的战斗就像人类一样。不过动物打仗都是一对一,而人打仗则是一对百万。一个炸弹扔出去,我们甚至不知道杀了谁。而动物们知道,为了自我防御,战斗之后是为了赢得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赢得生活,是毁灭,毁坏了别人,也毁坏自己。所以需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所相信的绝对价值。绝对的价值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也应该向动物们学习。
张同道:从你的影片里我看到了人类的精神历程,像鸟的飞翔就是一种精神追求。
雅克·贝汉:鸟飞向何处?高处!高于你们,并且逃离你们。它飞往远方。它去远方看,一直在寻找好天气,适宜的天气。它飞翔,如果有山,它超越山脉。它变换景色,变换环境。生活变得不同,变换环境就是变换生活。它绕着地面飞行,然后再回来。因此它在旅行,它的精神世界里有很多不同的风景。这就是自由,去比地平线更远的地方。最远的自由,是梦想。比地平线更远,它也是想像,更远。
我们所谓的边界,巴基斯坦,中国,印度,美国,边界是什么?我们生活在自然里,下雨,冬天,我们穿衣服。注意那边有敌人。什么敌人?好像是,跟我们一样的,不对,是一个敌人。为什么他是敌人?好吧,我们拿起枪,啪!太可怕了!我们生活依靠土地给我们食物,生活得很好,就没有战争。动物中间不存在的一件事,就是嫉妒,贪婪,金钱!用金钱来战斗,这太可怕了。口袋里满是钱,我很强大,因为我很富有。上帝啊,多么虚荣!世界上充满着虚荣。如果没有钱会做什么?就失败了。我们不知道怎样自我保护,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都需要防御。御寒,避雨,防御防御,不停地防御,而且要防御别人。我们远离别人。
我不知道人道的演变,但是毕竟几万年了,我還没说百万年,自从人类文明两万年以来,自从亚洲人越过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就开始了我们的文明。我认为我们做了很多坏事,对他物,对土地,对我们自己都造成不幸。因此这是理智的时候了。
你知道,一首诗, 4个词,就可以描写伟大的天地万物。很多书需要描写很多页,而2页诗歌就都能表现了。我尝试着把我的影片——不是变成诗歌,而是拍摄成电影诗。我不想说什么,我想表现,我想进入到理解层面,我想达到协调。所有的影像,都是谜题,近距离地观看令人着迷。我们爱慕花朵,爱慕昆虫,这才有意思,就像几行诗带给我们的感受。因此我也会做些细微的、触动情感理解的事情。情感是一种语言,一种真正的语言,它能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的事情。
张同道:多谢你在百忙中接受采访!非常期待你的下一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