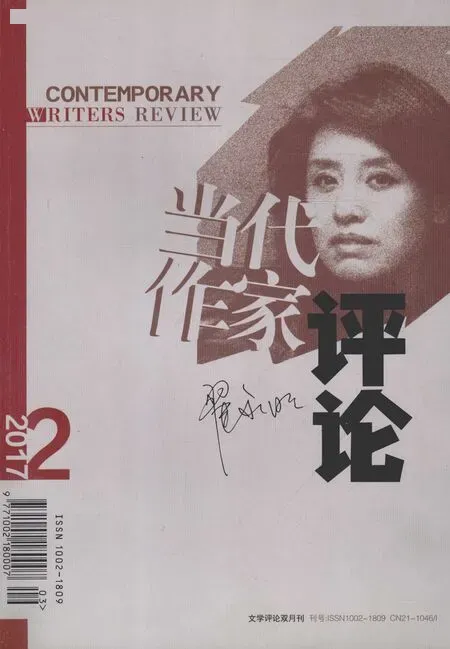古筝与小提琴的协奏曲
——麦家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的启示
2017-06-05时贵仁
时贵仁

——麦家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的启示
时贵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对外开放规模的扩大,中外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对抗已演变为对中外文学规律的探索。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的速度日益加快,由此引起的反响也越来越强烈。“2009年鲁迅的作品在经历了82年后终于以全译本的形式走向广大海外读者,2012年莫言的著作在海外传播22年后,最终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而麦家的《解密》则在海外上市的当天便创下了骄人的成绩。”当然,这并不是中国文学作品海外传播的起始,但这无疑是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成功的尝试。谍战、推理小说在海外的读者数量庞大,又有东方血统的神秘性,麦家小说进入海外大众视野并受到欢迎也并非偶然。本文将通过分析麦家作品中包含的文学元素以及推广到海外的过程来解析中国文学作品畅销海外的原因,为我国进一步拓展文化阵地提供借鉴,并深入挖掘我国文化传播中尚需改进之处。
麦家是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编剧,同时也是首位被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作品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此之前,我国现代作家鲁迅、钱锺书和张爱玲的作品收入其中。2014年3月18日,麦家的经典小说《解密》的英文版(英译名Decoded)在上市当天即创造了中国文学作品排名的最好成绩:英国亚马逊综合排名385位,美国亚马逊综合排名473位,位列世界文学图书榜22位。继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和美国FSG出版社签约出版《解密》之后,《解密》和《暗算》等作品相继与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俄罗斯、德国、以色列、土耳其、波兰、匈牙利、瑞典、捷克等国家的21家出版社签约,还被翻译为加泰隆尼亚语和希伯莱语。在惊叹麦家文学作品“大红大紫”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他的作品能够跨越地理与文化的鸿沟,将中国文学之风吹进海外读者的脑海里,国内语境下的“麦家热”又是怎样与国外接受主体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
一、中西文学元素的共鸣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是以语言和文字为工具,表达对世界、对人生、对自然的思考。不同的文学形式以及其中包含的情节构架、人物塑造、言辞选择和叙述方法等构成了文学创作中的元素,这些元素共同构建起作者的思想世界以及与读者沟通的坚实桥梁。同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的交流也需要彼此都能理解和接纳的文学元素作为沟通的媒介。麦家的作品正是抓住了能同时引起中外读者“文化快感”的要素,并通过这些要素将文化的差异变成了文化的共鸣。
英雄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常常透露出对英雄的崇拜。“从早期希腊神话中对奥林匹克式英雄和原欲型英雄的崇拜,近现代对尼采式英雄的着迷,到当代‘反英雄’式英雄的流行”,这种与个人主义分不开的英雄崇拜便一直弥漫在西方文学潮流之中。特别是“反英雄”式英雄既拥有超越常人的智慧,又具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弱点,他们也会恐惧、偏执、孤僻,这些英雄形象彰显出作为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真实才最有感染力,同时英雄们无法与命运抗争的悲剧也更能唤起读者的情感。这也是勃朗特笔下的希斯克利夫,乔治·R.R.马丁笔下的艾德·史塔克备受西方读者喜爱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麦家塑造的英雄人物也同样具有这些特点。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英雄形象,麦家笔下的英雄多是极具个性化特点的密码破译天才,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但是这些英雄并不是完美的,他们也有着各式各样的缺陷。比如,《解密》中的容金珍虽然是数学奇才,却为人多疑猜忌;《暗算》中的瞎子阿炳虽然耳力过人,能破译多个敌台密码,却又有着智力上的缺陷。这种对英雄的描写方式,一改传统的对英雄人物样板式的“崇高化”、“完美化”,而是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深刻理解“英雄”的含义,理解英雄的伟大与不幸,这与西方悲剧学说中的英雄形象不谋而合。麦家对英雄人物塑造的另一个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英雄人性的描写。他的作品揭示了即使在战争这一冷酷的、践踏人性的环境之下,即使是肩负着无数重任而不得不放弃个人情感的英雄身上,也时时刻刻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比如《风声》中的李宁玉在潘老的眼中是为了国家牺牲一切的“机器”般的人,但作者却借顾小梦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李宁玉。这种人性化的英雄叙事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同时轻松地触发接受主体的认知趣味进而接受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兼具中西方文学特点的英雄人物便能很快地将中西方读者的目光聚焦在一起。
西方的文学体系中,推理和悬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从爱伦·坡的《莫格街血案》到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从勒布朗的《亚森·罗宾探案集》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西方的推理悬疑小说成功地将推理、惊悚等文学元素系统地整合在一起,牢牢地抓住了西方读者的心弦,乃至成为了流行的符号。相比而言,我国的传统文化要求文学必须有教化世人,传经讲道的特点,这类主题较为严肃或者带有说教性质的文学作品显然无法挑动西方读者的神经。虽然我国也有《施公案》等含有一定推理因素的公案类小说,但是始终没有形成系统的写作体系,建国后“反特”题材的推理小说则趋向于模式化,情节过于简单,对手又显得过于愚蠢,缺失了复杂多变的叙事和环环相扣的情节也就等于主动抛弃了推理小说的核心所在。为这些因素所拘囿,我国改革开放后推理作品曾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艰难境地。麦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他既抓住了我国特有的历史背景,又能突破我国传统推理小说的局限,将国外的优秀推理小说写作经验与我国特有的时代背景相合,从而创作出能同时满足国内外读者群体口味的文学佳肴。比如在故事叙述上,“西方读者在审美趣味上更习惯于小说的故事性和可读性”,麦家充分把握了悬疑叙事的技巧,在他的作品《刀尖》中,林婴婴的司机的真实身份之所以能让读者大吃一惊,就在于麦家设置了封闭式悬念。在小说前半部分对这位司机的介绍始终是寥寥数笔,给读者留下一丝不经意的疑惑,却没留给读者猜测的余地,直到最后才一点点揭示出他的多重身份,“这种作者为了造成故事的逼真效果而从多角度对人物聚焦,从不同侧面照射主人公的写法”,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工力。除了对悬疑叙事的充分利用,麦家在小说结构上也为读者设下层层悬念,他创作的故事初看起来似乎并无联系,但它们就像抽屉一样,当读者一层层拉开这些抽屉,最后会发现这些貌似独立的故事实际上共同指向着作家的写作意图。同时,麦家将自己小说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文化特点、科学技术、逻辑问题等巧妙地混而为一,使读者不知不觉淹没于推理的混沌之中,从而使小说有了一种似真似幻的感觉。
在中西方的文学著作中,爱情元素贯穿始终,并在近现代逐渐成为了“流行”的必备元素,甚至可以说缺少爱情的文学作品是无法为大众所接受的。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对爱情的理解和表现形式则有较大不同,西方文学作品更强调自由不受拘束地表达爱情,我国则推崇含蓄地表达爱意;西方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对爱情的描写,“爱情”被当作增加真实感的必要元素,即使是看似与爱情绝缘的推理小说也会包含对爱情的描写,借此拉近作品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比如柯南·道尔的《四签名》中就提到了华生与梅丽的爱情与婚姻,在《波西米亚丑闻》中,即使是机器般的福尔摩斯也会对艾德勒小姐产生好感。而我国早期的谍战作品采取了“革命”与“爱情”的简单叠加,革命与性别身份的互动也预示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困境。这里的爱情大多是对英雄崇拜的产物,是烘托英雄形象的陪衬,同时也带有作者较强的个人宣传教化意图,显得样板化,缺少了真实感。由此可见如何将爱情写得不落窠臼,真实动人是决定一部文学著作质量的重要一环,这也是我国的作品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麦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充分总结了我国较早时期的谍战作品对爱情描写的缺陷,对爱情的描写更贴近真实生活,更贴近真实的“人”。比如在《暗算》中,由于阿炳破译密码的功劳,组织促成了林小芳与阿炳的婚姻,她将阿炳看作革命的英雄,并对未来充满了幸福的渴望。但是思想单纯,甚至愚笨的阿炳并不能理解林小芳对他的感情,也无法应对家庭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他看来,家庭是比密码复杂得多的难题,最终阿炳也因此走上了绝路。这里麦家对爱情的描写并没有重复传统“大团圆”的结局模式,但是却更接近冰冷的现实,也正是这种真实的、零度的,甚至于残酷的描写,更能震撼读者的内心,同时也从不同维度展示了爱情的真实面貌。这种开放直白的写作手法,不仅使国内读者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也使国外读者目睹了我国推理小说写作技巧的发展。
以麦家作品中的文学元素为例,中国作家在将作品推向海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提升自身的写作技巧,敢于创新并积极改革传统的写作模式,使写作内容和风格紧跟时代,紧跟读者的审美标准和阅读需要,并与社会和现实结合,创作出真实可信的情节与有血有肉的角色。在充分发掘我国历史文化宝藏同时,与国外优秀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学元素相结合,兼收并蓄,演奏出既包含我国文化特色又能为海外读者接受的“交响乐”。
二、中国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的桥梁——译介
一种文化语境下产生的作品在试图渗入另一种文化市场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身的语言与文化符号以对方可以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一过程包含译和介两个部分。“译当然就是指翻译,介则包括文本的选择、产生、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译介的基本途径主要包括:“1.出版社,出版社在作品出版之前综合评估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并实现作者、译者和出版社的三方合作;2.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3.文学代理人,即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的纽带;4.书展。”译介构成了不同文化间沟通的桥梁,也构成了作品与市场之间沟通的渠道。“良好的译介过程不仅需要译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能够充分理解原著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把握其中与自身文化的相通之处,还需要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能综合译介过程中的所有途径,考虑到传播、市场以及读者接受能力等因素,将原著推销到广阔的市场之中。”麦家《解密》英译本的风行,就得益于译者不仅具有丰富的语言学和翻译学知识,还在推介的过程中深谙文学在市场中的生存之路,在并不完全依附市场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了传播、宣传、受众与时代背景等各方面因素,有效地利用了译介的各种途径,最终成功地使作品走向海外市场。
以麦家《解密》的译介过程为例,作品的第一译者英国人米欧敏(Olivia Milburn)出生于语言学研究世家, “她的父亲是讲授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教授,母亲则是波斯语教授,她本人曾获得牛津大学古汉语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先秦历史,对汉语的掌握十分娴熟,同时还出版过多部有关古代中国的学术著作,曾经在韩国的首尔大学教过中文,这充分保证了译者翻译的专业性,构成了译介的基本要素。对米欧敏翻译起到重要影响的另一因素来自她的家庭,“米欧敏的爷爷是一位破译家,曾在二战时期于破译家阿兰·图灵工作的地方——英国的布雷奇利庄园任职,这里曾是英国破译德国密码的大本营”。正是汉文化的专业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米欧敏在翻译措辞、翻译策略和原著选择方面更倾向于谍战类文学作品。事实上,米欧敏翻译《解密》的初衷正是要将之与爷爷共同分享,这种对谍战类作品的兴趣也使她具有其他译者无法匹敌的优势,这具体表现在:首先,译者对翻译的选材是出于兴趣而非纯粹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这保证了译著的文学性和翻译质量;其次,翻译后的作品有固定的文学接受和阅读主体(米欧敏的爷爷),这使译者有坚持翻译的动力并产生良性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互动;第三,米欧敏在翻译《解密》时尚属翻译新人,因此其翻译观念倾向于忠实地展现原著内容,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翻译方法保持了故事的原汁原味,翻译完整地展现了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米欧敏在读者接受角度上对语言审美的观照,在翻译过程中有意避免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以及中西方文化间较大的差异,甚至力求中西文化传播的互动与关联。此外,米欧敏对古汉语的研究经历又使她的译著带有一种古典美。这种以直译和异化为主的翻译方法得到了海外读者的充分肯定。
但仅仅靠原著优秀的内容,专业的翻译人员和翻译方法还不足以使原著顺利地走进海外市场。麦家承认在整个作品推向海外的过程中,他并没有选择权。虽然麦家急于将自己的作品推向海外,但他除了自身的才华外并不具备充分的社会资本,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国内文学作品走向海外一般只能依赖在国内市场建立较大的知名度,再借用本土的影响力将作品推向海外市场,莫言的成功就是这种模式的最好诠释。而麦家的作品则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无法在国内积累自身的文化与社会资本,导致其作品走出去的模式不是主动地“译出”而是被动地“译入”。在作品于海外获得巨大成功后,麦家不无心酸地说:“被冷落了十多年后,也许是博得了上帝的同情,给了我一块馅饼吃。”尽管麦家所拥有的资源比译者还要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密》的译者对作品的译介占有较大优势。米欧敏在翻译之时仅仅是兴趣使然,译者本人与出版社并没有深厚的联系,也没有经济力量对作品进行推介,这时社会因素对译著的推广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米欧敏翻译《解密》之后,她又将译稿给了蓝诗玲(Julia Lovell),作为米欧敏的大学校友,汉学家蓝诗玲具有良好的文化资质来推介麦家的作品,同时她又有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企鹅出版社合作关系良好,正是在她的推荐下,麦家的作品引起了编辑的注意,并主动承担了对麦家作品的宣传营销。国外出版营销一本著作前,首先需要各主流媒体与文学评论家先于读者对作品进行品评和宣传,最后由出版社根据市场反响以及经销商的订货数量来决定印刷数量。《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对麦家作品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同时“斯诺登事件”的发生也为西方读者打了一剂“谍战”兴奋剂。即使这一事件发生在企鹅出版社与麦家签约之后,但媒体充分抓住这一事件,使作品更加符合时代背景,更能迎合读者的口味,并使读者发掘到了麦家作品所具有的世界性,而麦家也用他的作品证明了“谍战”这一主题并不是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国家所专有的,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
得益于出版社与媒体有效的营销和宣传,麦家的作品才得以顺利地走进海外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麦家作品走向海外的过程包括原著和译著的优秀品质作为保证,译者对著作产生兴趣,将作品推介到出版社,著名汉学家的引荐,以及作者迫切希望作品走出国门的愿望,以及出版社的经济活动的大力支持,这些文化元素与社会元素相互作用,使译著顺利地进入到出版环节,而麦家的其他作品也逐渐在译者与出版社的主动合力下渐渐浮现于世人面前。麦家小说在海外出版的“奇迹”,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特别是由于文化上的隔膜以及译入译出作品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中国主动译出的作品进入海外市场困难重重,将作品交由海外译者译入,由海外出版社负责版税以及海外营销的出版途径确实值得尝试。
三、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误区
在中国的书店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国外文学作品在数量上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在文化阵地上,外国特别是欧美的文学作品一直保持着强势的侵入态势,而我国文学作品在国外尚未占据优势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比拼的擂台,西方国家借助其文学市场的优势将其意识形态强势推进到第三世界国家,我国如果不能有效应对,那么我国与西方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只能不断上演“文化逆差”。麦家的文学作品从侧面反映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发现目前我国文学作品走向海外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弊端。
(一)自2008年以来,麦家的作品带动了“谍战热”,谍战影视剧与谍战文学作品在短时间内迅速占据了我国的主要传播媒介市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股热潮中并没有哪一位作家如麦家一样展示出耀眼的光彩,也没有哪部作品能达到麦家作品的高度。原因之一在于大部分的谍战作品单纯迎合经济收益,“试图依靠做作且犀利的语言和浮夸的内容甚至是低俗的情节安排来迎合读者和观众,导致文学元素不得不退居二线,而哗众取宠则成了表现的基本方式,这也使很多谍战剧成了人们闲来无事的消遣,失去了深度和文学的影响力。”比如由《林海雪原》改编的电视剧中,“少剑波与白茹的感情被大大地渲染放大”,一部《林海雪原》变成了《林海情缘》。“文学原著的内涵被各种迎合大众趣味的影视改编所扭曲,无法发挥原有的文学魅力”,这种由影视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我国文学创作于推广上的误区值得检讨和深思。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一些优秀的谍战作品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来,但是在一些早期的谍战剧取得成功后,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跟风和模仿,量化的生产导致了大量样板化的情节和人物塑造模式的出现,观众或读者可以轻易地猜出故事的结局,谍战作品所特有的,能够满足观众好奇心理与求知心理的悬疑性与突变性被抹杀了。一旦作品中历史背景的特点,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人物鲜明的个性和多舛的命运被淡化,人工斧凿的痕迹过于明显,那么整个作品就失去了魅力,且不说走出国门,国内的读者和观众也将难以认同。因此避免刻板的模仿,在文学元素上保持真实性的基础上创新求变是一部成熟作品的必备要素。麦家的成功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描写英雄时,他并不掩饰英雄人物的缺陷,也不会避而不谈英雄命运的悲剧走向,他使读者看到,在历史的洪流中,无论怎样了不起的人物终究只是历史的一滴水滴,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性的人。这种真实的甚至于残酷的描写,使作品更有震撼力,也更有说服力,此时麦家的作品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推理悬疑小说,他对“真实”的展现使他的作品上升到人性的高度,具有了普遍意义。
(二)在我国,一些文学作者以及翻译家认为中国文学作品走不出去的原因在于作品的质量不过关,认为我国文学作品“缺乏人性的发掘,缺少灵魂的救赎和反思,很难引起共鸣”。还有人认为译者的水平不过关是导致我国作品无法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甚至许多人认为葛浩文和陈安娜才是真正的功臣,这样片面强调翻译家的主体性作用,显然已经陷入了过分强调翻译的误区。首先,文学作品质量的高低并没有统一的固定标准,往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评价。比如爱伦·坡生前其作品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在他去世多年后,其文学作品的价值才被发掘出来。现在人们所承认的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评价标准,其实仅仅是西方世界的评价标准,并不是文学评论的“万金油”,以文学质量来作为中国文学作品走不出去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的表现,这也是对本国文化的一种变相的否定。况且一部文学作品的畅销与否也与作品质量并无必然联系,优秀的作品被暂时埋没,粗制滥造的作品红极一时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事,不能单纯以海外市场的销售情况来评价我国文学作品的优劣。过分强调译者的作用,过分强调翻译质量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是片面的。因为“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话所表达的内容、风格、思想、感情和神韵的再现和表达,翻译的基础在于原话,翻译无法表达原著所没有的元素,这也决定了翻译不会是文学作品畅销与否的根本原因”。
单纯地对原著质量以及翻译质量的考量都不是我国作品走出国门的重点,这种简单地以文本为评价标准的想法导致人们忽视了文学之外的因素对文学作品推介的影响。参照麦家《解密》的海外市场化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出版社的宣传营销以及汉学家的推荐对《解密》在海外的畅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出版社充分调动了传播媒介并综合运用了市场因素,才使得《解密》迅速在海外获得了知名度,并在英译本正式出版前便已经在读者中间营造好声势,因此对市场因素的考量是我国文学作品走向海外过程中应该重视的要素之一。在市场的作用下,对于原著的改动只要基于原著的内涵,不会对我国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么这种改动是被允许的。而出于市场考虑,以市场运作的手法来运作文学作品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同样,出于销量的考虑,通俗小说的创作也不能简单地被界定为“不入流”,只有摒弃种种不恰当的偏见,充分调动各种社会与经济因素,我国的文学作品才能更顺利更好地走向海外市场,因为文化的影响力,文化的输出都需要市场来实现。
结 论
在文化软实力的比拼愈演愈烈的全球语境下,如何更好更有力地进行文化输出,成为了每个国家都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有效地解决文化输出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本国作品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尚需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麦家作品在海外市场的风靡为我国文学作品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经典的范例,“即通过原著与国外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元素的共鸣来激发海外读者的兴趣,通过良好有效的译介过程来使作品迅速地为海外读者所理解,再通过利用社会、经济因素迅速扩大作品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这些无疑为我国文学作品的海外推介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我国政府对文化事业大力扶植的背景下,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呈现在海外读者的面前,传递着中国文化的魅力。
〔本文系2016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6BWW009)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桂玲)
时贵仁,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