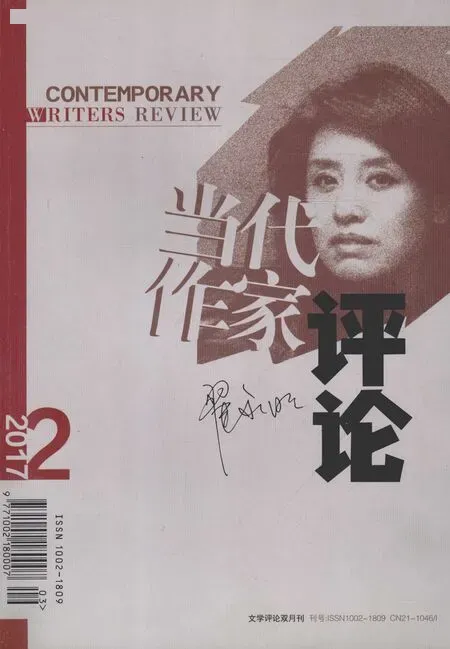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到“研究”
——关于程光炜与其人大弟子的当代文学史研究
2017-06-05钱文亮
钱文亮

——关于程光炜与其人大弟子的当代文学史研究
钱文亮
一
多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往往被视为一个没有“学问”的学科,一直到1999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问世,大陆学术界始有“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成熟、“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的感叹。不过,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虽然一度鼓舞了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编撰热潮,但其树立的高度及其带出的问题实际上却使真正有效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困难变大了。就在该书问世不久的2002年,李杨便在和洪子诚的通信中,对其以“一体”和“多元”对立的框架来结构当代文学史的合理性表达了自己的质疑,认为与“上编”“50-70年代的文学”那种对权力与文学复杂关系的极为细腻和深刻的分析相比,“下编”的精彩程度显然不如“上编”。而之所以如此,李杨认为原因就在于“知识考古/谱系学”的方法没能在分析80年代(本文所涉文学年代均在20世纪范围之内,以下不另说明——笔者注)以后文学的部分得到贯彻。对于李杨的评价,包括洪子诚本人在内的不少学者也表示过同感。只不过,洪子诚在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却带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将面对的大问题:“对于启蒙主义的‘信仰’和对它在现实中的意义,我并不愿轻易放弃;即使在启蒙理性从为问题提供解答,到转化为问题本身的90年代,也是如此。”
之所以说洪子诚在通信中所涉及的问题重大,是因为正是80年代的启蒙论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基础,对于它的解构或抛弃无疑关涉整体性的学科重构问题。如此看来,借用李杨的说法,这次以通信方式所进行的讨论实质上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90年代以来,包括文学史写作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知识状况”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于洪子诚的文学史叙述方式所表征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知识范型的转换”,同时也因为洪子诚在坚持启蒙主义的“信仰”与采取历史主义的“知识观”之间所产生的“犹豫不决”而备加凸显。
对于李杨所描述的变化及其带出的问题,洪子诚本人并非缺乏警觉。同样是在通信中,洪子诚已经明确表示:“我当然并不满意80年代以来确立的那种陈陈相因的叙述,知道必须重新审察‘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种种概念和与此相关的线性排列,重新审察‘文学复兴’、‘新时期’、‘第二个五四’、‘思想解放’等几乎已成共识的提法,对似乎已有定评的文本予以‘重读’。对‘新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之间的断裂性处理,也要重新考察。”而这种工作为何没有进行呢?洪子诚坦率地解释:“8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我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对于50-70年代文学,我下的功夫比较多。”洪子诚的话虽属自谦,但却显诚恳,因为学术本来就是薪火相传的长远事业。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堪称幸运的是,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等著述中所留下的问题与工作,不久便在李杨与程光炜发起的“重返80年代”的研究活动之后,在程光炜与其人大弟子的当代文学史的讨论和研究中,得到十分具体而卓有成效的回应与推进。
二
在近些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程光炜是一位对于当代文学的学科使命和自我的历史位置具有强烈“历史感”的不多的几位优秀学者之一。如果说,洪子诚是通过“价值中立”的态度洗刷掉当代文学研究中浓重的“文人气”而带出清晰的“学术感”,并以不断加引号的独特方式清理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的基本学科概念和关键词而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程光炜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则是以比较坚定的历史主义的“知识观”,将“知识考古/谱系学”和文学社会学以及文本细读的方法推广到了对于80年代及其前后文学部分的分析之中,并以“哲学的历史学家”的视野和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思维”逐渐建立起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三个十年的历史关联性,以至于“当代文学‘后三十年’的整体性。”
实际上,在多篇访谈和对话中,程光炜已经描述过在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突破与推进方面他和洪子诚、李杨、孟繁华、贺桂梅和蔡翔等学术同仁之间积极协作与互动的建设性关系。而且,读者通过《程光炜学术年谱》等也不难知悉,程光炜曾经是“80年代”文学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并在那个“新启蒙”话语蔚然成型的历史时期获得了理解当代中国60年乃至整个20世纪历史与文学的“认知性装置”。正因如此,程光炜在跟着洪子诚进行“十七年文学”研究后不久,便“很快退出了,回到80年代文学研究”。不过,经历过“80年代”的人不知凡几,程光炜之所以能够与李杨合作“重返80年代”,显然不会仅仅因为简单的个人原因,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意识到启蒙理性转化为问题本身的9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的知识状况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洪子诚具有开创性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方式的直接启发与鼓舞下,程光炜和李杨、贺桂梅等一批当代文学研究者忽然发现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突围”方向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有效基础和起点,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其实质正是李杨所指出的洪子诚所接受并成功付诸其当代文学史研究实践的那种新的“知识观”。这种明显植根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语境的“知识观”,其对现代主义理论语境中的启蒙话语的解构与挑战是必然的而且是致命的,它曾经给予洪子诚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以崭新的基础和起点(也导致了坚持启蒙理念的洪子诚的摇摆与犹疑),接下来也帮助李杨、程光炜及其人大弟子成功地“重返80年代”,有力地改变了已经被视为常识的自80年代以来一直支配着当代文学研究的启蒙主义的“认知性装置”,使得程光炜能够清醒地追问“我的‘知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现在想象历史和想象问题的方式又是怎样形成的?等等”。“因此,我的80年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从自我知识的清理开始。接着下来,当然会涉及到对我们这代人思想和知识的清理。”“我们想回到历史的复杂性里面去。”也正是借助于新的“知识观”,程光炜及其人大弟子获得了历史性的“宽幅”视野与方法,不仅使得“重返80年代”成为可能,也使其“重返80年代”的学术实践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崭新起点,“80年代作为方法”甚至延伸到了对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70年代文学以及90年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并如程光炜所计划的,“我就想这么一个历史节点一个历史节点地做,慢慢建立它们之间的关联”,在“大历史”的视野中最终建立起当代文学的整体性。
三
迄今为止,程光炜及其人大弟子以“80年代文学”为出发点的当代文学研究已经远远超过其预期,甚至“建构起了某种可以称之为‘文学史哲学’的问题视野和理论方法”。这种被称为“文学史哲学”的问题视野和“历史分析加后现代”的理论方法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将整个“80年代”的文学研究、思想学术作为问题,重新“陌生化”,继而将“80年代文学”重新“语境化”,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80年代文学研究(文学史、文学批评)的知识立场和逻辑进行考察、反思。程光炜及其人大弟子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仅在数量上已经堪称硕果累累,但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问题而建立起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在于其为当代文学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奠定了具有包容性和反思、对话能力的学术化基础。而且,他们对于“80年代”的问题与“80年代文学”的研究是通过花大力气收集文献材料,通过一系列重要的个案研究来推进的,表现出非常诚恳可靠的学术伦理。具体到他们的研究选题,确乎是抓住了80年代乃至“十七年文学”、“90年代”文学研究的知识立场和逻辑的原点,例如五四与“文化专制”、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人道主义”讨论、“共同美”论争、“主体性”问题大讨论、“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等等,这些80年代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命名和思想学术成果,的的确确构成了程光炜所归纳的80年代“告别文革”与“走向世界”的谱系性“知识”,塑造了大多数国人迄今为止想象历史和想象问题的“认知性装置”,并且长期支配着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些话题、命名与相关论断既深度参与到80年代文学的“建构”和“规范”之中,同时又以文学/政治、传统/现代二元区分的叙述方式形成此后文学史书写的基本价值标准与认知框架,同样没有避免80年代的意识形态性:
最近几年,通过当代文学史的出版,人们开始形成一种共识,即“先锋文学”思潮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的评价标准显然是一个“纯文学”或“文学性”的标准,“个人化”、“个人写作”被推崇为一种“真正”的文学写作,以致被认为对整个新时期文学都有某种“示范意义”。
显而易见,程光炜对于自己及其同代人的思想和知识的自觉清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是具有非常基础性、系统性的历史和理论意义的。
二、通过“历史化”的工作,促成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向“研究”的学术性转变。这一点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学科意识真正觉醒的标志。事实上,早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不久,程光炜就已敏锐地意识到这部著作的特殊之处主要在于其“进一步叩问了当代文学史‘建史’的深度机制——从而完成了当代文学‘评论’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刻转移”。如此清醒的学科意识即使在当年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都算是凤毛麟角。而具有60年历史跨度的当代文学在学科的系统、自足方面之所以远远逊色于只有“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意识的相对不足正是其症结所在。根据程光炜的观点,这种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仅仅把当代文学理解成“当下的文学”,而非“历史的文学”,同时也与80年代通过“文论化”(也即“批评化”)的研究方式建立起来的文学史面目直接相关。“批评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被等同于“文学史”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至今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其具体表现则被程光炜归纳为:与媒体批评区别不大的“现象批评”和宏观论述、对被预设的历史结论与别人研究方法的认同式研究、本质论历史叙述,等等。程光炜对于当代文学学科随意性的“批评化”状态的诊断可谓抓住了该学科建设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而更为可贵的是,程光炜还进一步给出了当代文学学科超越“批评化”的方法与范围,这就是他所特别强调的“历史化”,“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过程中,创作和评论已经不再代表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它们与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因素处于同一位置,已经沉淀为当代文学史的若干个部分,是平行但有关系的诸多组件之一”。其次,这种“历史化”既包括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包括研究主体自身;第三,如何实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在程光炜那里至少有相应配套的几种方案,包括文学史研究的“陌生化”、文学研究的参照性、讨论式的研究习惯、有距离的批评与研究、重视文献资料的具体化,以及文学研究的知识化,等等。可以说,正是因为程光炜以“历史化”为核心的学科意识与方法,他本人与其人大弟子新世纪以来总能不断贡献学术可靠性极高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佳作。
三、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相呼应,程光炜与其人大弟子进一 步地将埃斯卡皮等人的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和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相结合,有效呈现了80年代文学研究的“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周边”,既注意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部分的风景’”,同时也注意到“全部的风景”。*程光炜:《“当代文学”的理解》,《西部》2011年第1期。在这一方面,程光炜特别强调要有接通历史联系和建构历史过程的“体系化的眼光”和一种综合性的具有历史长度的视野,也正是这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批判视野与具体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研究的结合,使得程光炜清晰而深入洞察了“先锋小说”、“寻根文学”等与城市改革、国际汉学这些所谓文学周边/外部因素的异乎寻常的关系,揭示了它们之“一派独大”、成为“风景”(经典化)的历史“源头”,从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些“纯文学”的“不纯”的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成为程光炜克服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状态即“脱历史化”的倾向的成功实践。而其《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更是抓住了80年代向90年代转折的关键历史节点,对当时参与讨论的各种话语谱系和知识来源做出了客观清晰的评述,其最后的判断因此而极具逻辑性和历史的穿透力。
当然,程光炜与其人大弟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上所做出的努力与开拓远远不止上述。他们对当代文学学科普遍存在的现实难题所进行的广泛而有力的挑战,已经为当代文学趋近必要的学术自足和规范,做出了具有奠基性的贡献。
〔本文系“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中国语言文学)”(sponsored by Shanghai Gaofeng & Gaoyuan Project for Univers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李桂玲)
钱文亮,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