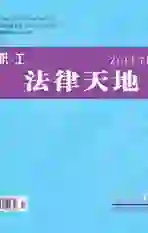融资租赁中的善意取得问题研究
2017-06-03周宇光
周宇光
摘 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融资租赁中租赁物善意取得问题做出了规定,然而租赁物善意取得问题并没有因为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尘埃落定,本文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围绕租赁物善意取得问题,对实践以及理论上仍然存在的問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融资租赁;善意取得;动产抵押;登记
一、问题提出
融资租赁是一种集融资、贸易和租赁为一体的新型交易方式,自从我国80年代引入后获得了长足发展,满足了大量企业的资金需求。但是由于这种交易方式灵活多变、结构复杂,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发生了众多制约融资租赁产业发展的问题。
《物权法》在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中规范了善意取得制度,这一制度是基于促进交易原则与所有权保护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促进和保护交易成为立法的重要方向。善意取得可以说是一种以牺牲财产的所有权的静态的安全为代价来保障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的制度。
在融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虽然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是其所有权与物的占有分离,出租人实际上仅仅享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尤其是对于动产,除了飞机、车、船等特殊动产外,其他在融资租赁中常见的机器设备以占有作为物权的公示方法。出租人作为动产的所有人无法对其进行所有权登记。在融资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占有动产的承租人就会自然被善意第三人认为具有动产的所有权,当承租人故意无权处分该财产时,就很可能发生财产被第三人善意取得,出租人无法基于所有权行使物权请求权,权利无法优先于其他债权人保护的问题。
作为所有权人的出租人长期与租赁物的占有分离,以机器设备等为主的租赁物长期被出租人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增加了出租人的所有权保护风险。同时,为了达到融资目的,企业间的资金拆借、一物二卖、重复抵押等违法违规现象比比皆是。企业通过融资租赁获得的重要的生产设备、大型交通工具、原材料等动产的价值已经成为企业资产的主体,企业将这些租赁物进行抵押、出卖等再次融资也就成为无法避免的顽疾。
然而针对融资租赁关系,无论是在《物权法》还是《合同法》的融资租赁合同一章中都未能对出租人所面临的这种风险做出应有的保障,在企业操作和审判实践中都急需对融资租赁中的善意取得问题做出专门的规范。
二、对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解读
2014年3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融资租赁中的善意取得问题做出了规定。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①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第三人在与承租人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②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③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或者地区主管部门的规定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④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
这一司法解释为解决融资租赁中的疑难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引,第九条规定的三种主张善意取得的例外情况更是总结实务经验的成果。然而,仅仅从实务经验的总结这一角度来研究司法解释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当从民法理论的角度探讨这一规定。
1.动产标记
针对第1种情形提到的在显著位置做出标识的方法公示动产的所有权,在我国目前的信用状况之下,出租人作为租赁物的实际占有人完全有可能对各种标识进行清除和涂改,所以这种方法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公示手段,尚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公示方法。对于保护出租人权益更有价值的是其后的两种方法。
2.特殊的抵押方式
司法解释将这种特殊的抵押方式表述为“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这种方式是指,出租人与承租人约定,由承租人将该动产抵押给出租人,出租人就在拥有所有权的同时又对该财产拥有了抵押权。由于机器设备等动产不存在所有权登记,承租人可以凭借占有而令第三人信任自己有所有权,所以此刻承租人实际上行使了所有权人为财产设定抵押的权利。
从实务的角度来看,在立法未明确租赁物登记机关的前提下,此种登记方式有效弥补了出租人物权保护的不足,亦未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有利于维护出租人的合法权益,限制承租人的恶意违约,确有认定其法律效力的必要。但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公证部门等登记机关进行动产抵押登记时是否会审查该动产的实际所有人是一个实务中较为巧妙地操作技巧。但在民法原理上似相当于出租人自甘将其所有权降低为抵押权,或可解释为出租人将其自身所有之物又抵押给自己,并不符合传统的民法理论。
3.融资租赁登记查询制度
司法解释对融资租赁登记制度在善意取得问题中的运用做出了协调,规定第三人的查询义务以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或地区主管部门的明确规定为前提,为融资租赁登记系统的发展做出了引导。目前融资租赁登记系统仅仅起到了行政管理以及信息公开的效果。根据物权法和现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动产登记机关应该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商务部建立的登记系统并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登记机关。在法律未就融资租赁登记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融资租赁登记究竟能否起到公示的作用,颇值研究。
目前我国已有的融资租赁交易登记查询系统: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开发运行的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这一系统建成于2009年,提供融资租赁登记、查询服务,目前已经成为融资租赁行业内部主要的登记平台。二是由商务部开发建设的融资租赁业务登记系统,2013年10月开始运行,主要针对非金融系统的融资租赁公司。商务部要求其监管的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及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在其系统上对租赁业务及租赁物进行登记。
商务部从2004年开始对融资租赁公司开始试点监控,目前已经确定11批监管企业。对于试点监管的企业,商务部要求使用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登记。2013年商务部出台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也规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租赁物的权属应当登记的,融资租赁企业须依法办理相关登记手續。若租赁物不属于需要登记的财产类别,鼓励融资租赁企业在商务主管部门指定的系统进行登记,明示租赁物所有权。”
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融资租赁登记系统还是商务部开发的登记系统,要求进行登记的主体都是融资租赁公司,商务部的管理办法仅对其监管的融资租赁公司进行了约束。而第三人在购买承租人的机器设备等动产时,并不被法规要求必须进行设备的登记查询,也难以达到阻却善意取得的效果。所以,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并不能使两个登记系统发挥公示承租人所有权,证明第三人非善意的作用。
三、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分析
1.抵押权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解决
承租人在占有租赁物期间,为达到恶意融资的目的,会采取抵押、出卖等方式处分租赁物,而抵押和出卖这两种不同的处分方式对于动产所产生的后果不同,出租人与承租人之前设计的这种特殊的抵押形式是否能够发挥保障出租人的所有权的效果也应当区别讨论。
(1)当第三人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的抵押权时,根据抵押权的优先顺位,登记在前的抵押权具有对抗登记在后的抵押权以及无登记的抵押权的效力,则此刻出租人可以主张对于该财产的抵押权的优先权利。
同时,第三人在取得动产的抵押权时,可以选择登记或者不登记。
如果第三人在取得动产抵押权的时候选择登记,则应当通过登记机关进行查询,必然会知晓该财产存在抵押权的现状,则发生阻却善意取得的效果;
如果第三人取得动产的抵押权时不进行登记,那么第三人虽然取得抵押权,但此抵押权不发生对抗效力。出租人即可以主张之前设立的抵押权。
对于不动产抵押,因为登记是抵押的抵押权生效要件,第三人取得欲取得所有权必须经过变更登记,第三人应当査明抵押财产的权利状态,如果其应当查明而没有查明,第三人也就不是善意。所以,不动产抵押较少发生善意取得问题。
(2)当承租人向第三人受让该动产租赁物时,第三人并没有查询抵押的义务。根据交易便利性的立法宗旨,动产的交易也不需要查询登记。并且之前的动产抵押权自合同生效后成立,即使登记后依然缺乏公示性,基于合理信任,从承租人处取得动产的占有,则第三人可以善意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
根据《物权法》108条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除外”。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取得的所有权是原始取得,此时的物权成为一个无瑕疵的物权,取得完全的所有权,之前设立的抵押权就会被善意取得制度消灭。
所以,根据《物权法》的制度,出租人的权利依然无法得到完全保障。
2.司法解释存在的越权问题
该司法解释直接规定: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出租人可以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包括所有权和其他物权)不成立,这就使得这种实践中的并不符合民法理论的这种特殊抵押权获得了阻却善意取得制度的效果。
可以认为,司法解释实际上行使了立法权,改变和突破了《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和抵押权制度。从法学理论的角度看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应当认为和法律发生了冲突。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的说明,必须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则。只有立法机关以及其授权的机关才有制定法律的权力,而法院超出法律的规定制定的司法解释条款可以认为是一种越权行为。但是以我国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弥补法律的不足,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其实际作用已经超出了理论上的权限,成为司法权扩张的工具。司法解释对于这种特殊的抵押形式效力的确认,在实践中也会起到引导实务操作和司法审判的作用,对于融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的权利保障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当防范这种非正规的抵押形式对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冲击,防止当事人滥用抵押、质押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3.对天津地区的实践的分析
天津市是我国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的活跃地区,由于天津市对于融资租赁行业的大力支持,全国70%以上融资租赁公司均在天津注册。融资租赁行业在天津获得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支持,为保障融资租赁行业的健康发展,天津市对于融资租赁查询制度构建了自己的体系。2011年,天津市出台了《关于做好融资租赁登记和查询工作的通知》。天津市的规定明确了登记系统的登记性质是对租赁物进行“物权状况”的登记,要求第三人在办理抵押、受让等业务是必须查询登记状况,认定第三人为查询登记的视为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不构成善意。在天津本地的实践中,这些具体而完整的规定,对于发挥融资租赁登记系统的作用,推动当地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最重要的作用。
然而,天津市的出台的《通知》属于地方政府规章,在我国法律效力的层次中处于较低位阶,相比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处于下位法的地位。在我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未对融资租赁登记制度涉及的查询义务进行规定的前提下,天津市出台的地方政府规章规定了第三人交易的查询义务,有超越自身权限的嫌疑。从法律效力的角度看,天津市出台的地方政府规章并不能够为融资租赁的登记查询制度提供合法有效的保障,当事人仍然面临着缺乏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保障的风险;然而,实践中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为特殊领域提供支持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各地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也会尊重本地区政府出台的各项规定,细化的规定为融资租赁登记查询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制度,这种不符合法理的行为也就获得了实际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高圣平,王思源.论融资租赁交易的法律构造[J].法律科学,2013,(1):160-169
[2]雷继平,原爽,李志刚.交易实践与司法回应:融资租赁合同若干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解读[J].法律适用,2014,(4):33-41
[3]杨善林,鲁振宇.试论我国融资租赁登记制度[J].经济问题探索,2011,(8):114-117
[4]王利明.抵押财产转让的法律规制[J].法学,2014,(1):107-116
[5]赵万忠.论抵押权追及效力制度之设计[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5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