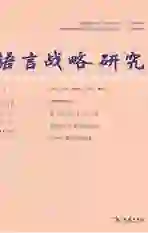全球华语国内研究综述
2017-05-30祝晓宏周同燕
祝晓宏 周同燕


提要 国内开始华语研究不过30多年。却已硕果累累,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研究视野也至少经历了三次转移:从境外华语到海外华语,再到全球华语。华语研究的格局也为之一变:从对全球华语本身的了解、华文教学的讨论发展到调查全球华语生活并将其与国家语言战略、全球华人的命运发展联系为一体。文章以时间为序、以地域为界,按照议题范围扩大的线索回顾了全球华语研究在国内的主要进展。
关键词 全球华语研究;国内;综述
华语研究始自海外,兴自中国。1974年新加坡南洋大学成立华语研究中心,这是有组织地开展华语相关研究的起始,但是真正将华语研究推向学术前台并使之走向兴盛的是中国。中国开始华语研究虽然才30多年,但已硕果累累,研究范围大大拓展,研究视野也至少经历了三次转移:从境外华语到海外华语,再到全球华语。华语研究的格局也为之一变:从对全球华语本身的了解、华文教学的讨论发展到调查全球华语生活并将其与国家语言战略、全球华人的命运发展联系为一体。
全球华语的大本营在中国,全球华语研究的主力也在中国,全球华语、全球华语研究的愿景很大程度上皆取决于中国。回顾华语研究在国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鉴往知来,自然意义重大。
一、八十年代的境外华语研究
国内华语研究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门打开,学术空气活跃,境外华语的相关状况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
首先,一些视野宽广的大家认识到汉语存在于境外的事实,并注意到域内外汉语之间的差异,从而扩展了现代汉语研究的范围。朱德熙(1987)在讨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对象是什么时,指出“作为现代汉语标准语的普通话还不十分稳定;至于台湾国语,由于与基础方言北京话隔绝,必然要发生变异,与基础方言隔绝的另一后果是失去了赖以维持其稳定性的制约力量,所以台湾国语较之于普通话,不稳定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汉语”条目中,朱德熙(1988:128)则明确指出:“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汉语的标准语在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虽然朱德熙没有对境外华语做过具体的研究,但这些言论却是在宏观层面上指明了华语研究和现代汉语研究的关系。在当时,持这种大现代汉语观的学者并不多,得风气先者如王希杰(1988)、廖秋忠(1989)、钱乃荣(1990)等。今天来看,朱德熙的思想对于华语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围绕华语具体进行研究的,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对中国大陆以外华语词语的研究,特别是对台湾华语词语的解释和海峡两岸用语差异的比较。改革开放之后,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希望对台湾语言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由大陆学者进行。例如,朱永锴(1988)、郑启五(1989)、徐幼军(1989)、彭小明(1989)等。黄国营(1984,1988)较早关注到海峡两岸汉语分歧,例举了境外华语与大陆汉语在词汇层面的诸多差异,强调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的课题。张维耿(1988)则讨论了不同华人社区词语在概念范围、褒贬色彩、缩略形式和语义内容上的差异,说明辨析这些差异对汉语二语教学的特殊意义,提出“编纂出不同华人华语相异词语全面比较手册”的设想。这些研究为之后编写华语对照词典乃至更大型的全球华语词典打下了基础。
在臺湾,从事华语研究的主要是一些社会语言学者。如Cheng(1985)、郑良伟(1987,1990)、魏岫明(1984)等,涉及语音、词语、语法和演变等层面,相对来说研究比较深入。
二是对中国大陆以外华语规划和使用情况的介评。例如徐志民(1983)介绍台湾报刊对语文改革的讨论,周有光(1984)对台湾语文改革和注音符号的评述,潘道生(1988)对香港地区华语态度和华语应用的研究。《国外语言学》《文字改革》《语文建设》等杂志介绍了新加坡语言国情及华语运动的一些情况,其目的大都是为国内推广普通话提供借鉴(田砥1980;詹伯慧1988)。可以看到,大陆这时对于新加坡华族标准语的称呼还不稳定。
这个时期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深港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依托该研究所,定期举办“深港片语言问题研讨会”,聚集一批关注港澳台语言问题的海内外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双语双方言》论文集里,其中很多都论及境外华语的问题,主要有:郭熙(1989)、周小兵(1989)、田小琳(1989)、郑良伟(1989)、王培光(1989)等。《双语双方言》一直出到现在,它对境外华语研究起到了持续的推动作用。从80年代到如今,其中还有不少学者仍在一直关注境内外华语问题,如邢福义(1989,1992,1994,2001,2005)、
郭熙(1992)等。这些可以算作是华语研究的先声。
整体而言,80年代的不少学者及其相关研究已经初具华语意识。从研究方法来看,基本上是依据书面材料,多带有了解、参考境外语情的目的。限于条件,这些研究虽没有展开实地调查,但却为国人了解境外华语情况打开了一个窗口,也为后续的华语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九十年代的海外华语研究
9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有机会陆续走出国门,零距离接触海外华语,能够实地调查和描写海外华语、华语使用和华文教学等情况。所见材料是一手的,加上研究者大都是现代汉语或教学研究方面的名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提高,华语研究开始真正起步。
(一)华语本体
华语各层面的特点受到关注,特别是词汇、语法层面的成果最多。
台湾华语的面貌多以两岸汉语差异比较呈现。例如邱质朴(1990)、朱景松、周维网(1990)、林文金(1992)、游汝杰(1992)、朱广祁(1992,1994)、刁晏斌(1994,1997,1998)等比较了台湾与大陆词语的差异。李青梅(1992)则比较了两岸字音差异。
香港华语的描写成果增多,令人瞩目。词汇以田小琳(1990,1996a,1997)、吴永德(1990)、陈建民(1994)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其中,田小琳(1996a)提出的“社区词”概念影响较大,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进展。
新加坡华语本身的特点引起关注。语法方面的研究当以陆俭明(1996)为代表,他的研究不仅比较全面、细致地勾画了新加坡华语语法特点,还提出了要关注华语跟普通话趋同的现象。词汇方面的细微描写则以周清海、萧国政(1999)、李临定(2002)为代表。萧国政(1998,1999)还探讨了新加坡华语的历史发展、分期和虚词变异等问题。
这一段的华语本体研究体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开始重视多地华语、多层面的比较研究(苏金智1994;汤志祥1995;陈瑞端、汤志祥1999),视域有所放大;二是重视接触视野下的华语研究,包括词汇的互动和融合、语法的接触等(李明1992;陈建民1996;石定栩、朱志瑜1999)。
(二)华语规划
90年代,香港、澳门陆续回归祖国,回归前后港澳的语言状况、语言规划等问题的重要性突显,华语地位、华语使用、华语关系等问题成为两岸学者关心的焦点。
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澳门。1992年召开“澳门过渡期语言发展路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见于《澳门语言论集》(程祥徽1992)。其他重要成果如刘羡冰(1994)、盛炎(1994,1999)、程祥徽(1999)等。这些研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描述澳门语言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讨论澳门语言规划问题,对如何处理中文、葡文和英文的关系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对澳门语言发展趋势做了初步预测。
香港方面,1995年召开“1997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会议成果为《一九九七与香港中国语文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1996)。代表作如詹伯慧(1996)、侯精一(1996)、邹嘉彦(1997)、石定栩(1998)、田小琳(1996b)、沈阳、邵敬敏(1997)等,这些研究涉及香港语言生活、语言政策制定、语文教学等诸多方面。
台湾地区以仇志群、范登堡(1994)为代表,该文介绍了台湾双语问题,特别论述了台湾华语研究的情况和国语的一些特点。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华语使用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97年暨南大学召开“第一届东南亚华人语言学术研讨会”,讨论东南亚华人语言生活、海外汉语方言等问題,会议成果收入《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李如龙2000)。对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的实证调查报告开始出现(陈松岑1999;萧国政、徐大明2000),另外,仍有学者关心新加坡华语规范问题(林杏光、张道防1992;田惠刚1994)。
(三)华文教学
90年代初,华文教育在海外的复苏带动了国内的华文教学和华文教育研究。
首先是介绍海外华文教育的情况。以国别而言,包括印尼(蓝小玲1999;温北炎2000)、菲律宾(周聿峨1993;王燕燕1998a)、马来西亚(林去病1998;詹冠群1999)、美国(樊培绪1998;梁培炽1998)、加拿大(王燕燕1998b),等等。
其次,关于华文教学的性质、方法的讨论增多。吕必松(1992)最早提出菲律宾华语教学的二语性质。这一观点影响较大。杨石泉(1993)论证华语作为二语教学的特点是突出语言交际工具的性质,加强语言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的训练。卢伟(1995)的问卷表明菲律宾华人社区的华语环境不佳,进行华语教学时应该通过交际法、任务法创设真实的华语环境。李坤(1998)则具体探讨了菲律宾华校华语课堂教学组织的几个问题。李方(1998)指出华文教学带有母语基因。显然,这一时期的华文教学讨论深受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影响,带有浓厚的二语教学色彩。
总的来看,90年代华语研究数量大增,质量也有提升,热点是东南亚华语研究。从学术阵地来看,香港的《词库建设通讯》为各地学者交流华语相关研究提供了平台。
三、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华语研究
新世纪后华语研究在学科意识、研究范围、实践应用、研究平台、研究队伍方面都大有进展。不同地区、不同背景学者的加入,使得华语研究成为海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华语研究的议题不断丰富,学科地位也愈发重要。
(一)华语学科
经过学者对华语名称的探讨,华语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清晰。以郭熙(2004a,2006a,2007)等论文为标志,华语研究有了自觉的学科意识。这一系列文章阐述了华语研究的性质、意义和任务,使得人们对华语研究的学术领地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2005年,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成立以及硕士、博士点的设立,为华语学科发展提供了平台保障和人才储备;2006年始,《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逐年发布华语传播、华文教育等方面的报告,华语研究汇人中国语言生活派的洪流;2010年,由中国学者主持、多地学者联合编纂的《全球华语词典》问世,2015年《全球华语》杂志创刊,2016年《全球华语大词典》推出。华语研究领域涌现的系列标志性成果和事件,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华语研究升格为国家语言战略的一部分。
(二)华语本体
华语本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
对华语语法特点的认识超过前期。例如邢福义(2005)对新加坡华语中虚词以“才”代“再”现象的研究,是华语语法描写的典范。邢福义2011年开始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带动了一系列华语语法研究成果的出现。例如香港华语语法的描写(田小琳、李斐2014;田小琳、马毛朋2013,2015)、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研究(李计伟2014,2015;王彩云2015,2016)、美国华语语法研究(陶红印2016)等。
华语口语语法研究取得突破。例如储泽祥、刘琪(2014)、方清明(2014)、赵敏、方清明(2015)等对台湾、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觉得说”、指代词“这/那”以及“酱”的研究。
华语词语的描写也更为细致。例如新加坡华语词语的解释(贾益民、许迎春2005;陈琪2008)、印尼华语词语的描写(刘文辉、宗世海2006;甘于恩、单珊2013;朱湘燕、黄淑萍2013)等。社区词的研究则以田小琳(2004)、邵敬敏、吴立红(2005)、谢永芳、张湘君(2015)、施春宏(2015)等为代表。
前期华语研究的集聚效应开始显现,出现了一些比较全面、系统的描写成果。例如刁晏斌(2000,2015a)、汤志祥(2001)、石定栩等(2014)、田小琳(2012)、祝晓宏(2016a)等。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况调查,既有单点的特征挖掘。也有多点的共时比较。
华语研究范围超越东南亚,延展至欧美等华人社会(杨荣华2011;朱丽丽2012;张聪2013)。
(三)华语规划
这个阶段的一大进展是对海外华语比以往更加包容和尊重,批评的声音少了很多。与此相应的是,华语规划研究不仅限于本体规划和规范标准方面的讨论,还提出华语的地位规划、功能规划、声望规划等研究类型。郭熙(2006b)论证了华语视角下中国语言规划的特点和任务,提出华语作为一种资源,需要开发利用,并列出了一些新的规划增长点。郭熙(2009)又提出华语规划模型,指出华语规划的内容是声望规划、获得规划和传播规划。
华语规划研究吸收“语言协调”这一语言规划学的重要理念(李宇明2000:33)。例如郭熙(2002a,2002b)讨论域内外汉语、普通话与新马华语词语的协调问题,李志江(2009:256—273)呼吁应该协调处理两岸语音差异。两岸用字问题也持续得到关注(张素格2013)。
华语地区规划出现了一些代表性成果。例如,李如龙(2004)、许长安(2011)、程祥徽(2000,2005)等。台湾的华语规划研究关注原住民语言复兴和家庭语言规划、海外华人社会语言规划等问题(张学谦2010,2013,2016)。
(四)华语词典
地区性的华语词典开始增多,如《两岸常用词典》(李行健2012)、《香港社区词词典》(田小琳2009)、《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邹嘉彦、游汝杰2007)等。《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的接续出版则是全球华语规划的重大成果。针对这些华语词典也有不少后续研究。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华语传播事业的发展,华语在各地的落地生根,不仅需要各种规模的华语词典,还需要各种类型、各种功能的工具书。例如华语应用文词典、华语人名对照词典、华语科技术语词典、华文教育词典等。
(五)华文教学
对华文教学的目标和特点的讨论增多,华文教学的性质越发明确。李宇明(2009)指出华文教学的母语性质。郭熙(2015a,2015b)则说明华文教学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既有一语性质的母语教学,也有二语性质的母语教学,还从认同角度区分了中文教学、母语教学和华文教学。这些认识都强调华文教学的认同功能,应该受到社会语言学认同建构思潮的影响。
同样是受认同思潮影响,华文教学当地化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例如,郭熙(2004b)以新加坡为例梳理了海外华语教学的类型,指出华语教学应该实行多样化模式。周明朗(2014)则指出华裔生对华语的认同有别于非华裔生对国际汉语的认识。这些讨论既强调要关注华文教学的本土实际,也要关注华人身份认同问题。
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也引起华文教学标准的讨论。郭熙(2008)提出华文教学的当地化问题。戴昭铭(2014)则延续其汉语规范的“中国立场、华夏本位”观(戴昭铭2007),对当地化提出质疑,认为会取消华语标准,扩大华语歧异。李泉(2015)提出语言标准上,国内宜采取“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双标准,海外采取“普通话”和“大华语”双标准,并认为多元标准有助于满足多元化汉语教学的需要,有助于加快汉语的国际化进程。
这一期间令人瞩目的是华文水平测试体系的立项和实施(王汉卫2016)。另外就是“华文教学研究丛书”的出版,这套丛书系统梳理了华文教学理论、技能方法、测试评估、教师培训、语言习得等多方面成果,是华文教育转型升级之际的适时总结。
(六)华语接触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华语大流通成为常态,各地华语中往往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华语接触研究势在必行。
两岸开启华语接触研究,词汇接触研究成为一大热门。李雄溪等(2009)集中讨论了港澳台词汇互動。刁晏斌(2015b)关注大陆词语融人国语的情况。李昱、施春宏(2011)、施春宏(2015)分别讨论了台湾、泰国与大陆华语词语互动的情况。陈保亚(2013)提出“语势”的概念,指出在马来西亚汉语和马来语是一种等势接触模式,对华语接触和传承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七)华语生活
华语生活是以华语为媒介的语言生活,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为丰富的概念,包括华语使用、华语态度、华语景观等。华语生活研究是联系社会生活、服务社会生活而进行的研究,因此需要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跨学科分支的滋养。
华语生活研究逐渐汇人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从国别、跨境到区域,华语生活调查范围逐步扩大(张兰仙2013;郭熙、祝晓宏2016;郭熙、李春风2016);调查项目也在深入,包括华语使用与态度(徐大明等2005)、华语接触与语言转用(邹嘉彦、游汝杰2001;许小颖2007;丁思志2013)、家庭语言使用与规划(康晓娟2015)等,华语生活的细节和全貌越发清晰。
同时,领域华语得到关注。例如香港广告语言分析(吴东英、林敏奋2012)、法律和工作场合华语调查(王培光2013,2014;李贵生、梁慧敏2010;梁慧敏2014);台湾新词语、饮食语、禁忌语观察(竺家宁2013;陈淑芬、陈力琦2011;陈力琦2011;李佩容2008)等。
总之,描写华语事实、调查华语生活是推进华语研究的双翼(祝晓宏2016b)。新世纪以来,很多学者不仅开始认真探究海内外华语之间存在的小异,也将华语调查的步伐迈向全球。
四、对于全球华语研究的总评
全球华语正在崛起,全球华语研究因之而兴起。就结构层次而言,全球华语研究有两种理解:一是全球华语+研究,二是全球+华语研究。第一种是以研究对象来区分,以大陆为视点,境外、海外、全球华语等各层次变体,都在考察范围之内。第二种是以研究者或研究地区来区分,从目前的阵容来看,国内学者构成这种华语研究的主力。
不管按哪一种理解,华语研究的特点,都是在大华语的视野下,以比较、发展的眼光来看汉语跨疆域的事实。因此,所有站在大陆的视角孤立地看待汉语标准语普通话的研究,即狭义的现代汉语研究就不再属于华语研究的重点。相对于后者而言,华语研究更有利于认识现代汉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语研究本身就暗含着一种更宽广的视野,或者说以超国界的视野来研究汉语。回顾国内华语研究30年,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种视野逐步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具体的一项项成果外,国内华语研究的主要进展体现为以下两点。
(一)凝聚共识.转换观念
首先是凝聚了对华语相关问题的一些共识。我们将近十年来华语研究在理论上的探索概括为:华语名称的确立、华语研究方法论的追求、华文教学性质的廓清、华语社区的提出、华语规范观的演变(祝晓宏2016c)。严格地说,这些共识还称不上是成熟的理论,但是在观念认识上确实推进了华语研究,乃至对一般语言学研究也有所启发。
确实,现在批评海外华语不规范的声音少了许多,怀疑华文教学独特地位的声音少了许多,称海外华语为普通话的现象少了许多。华语作为学术概念获得了空前的接受度。不妨选取《全球华语词典》收录的9个华语地区为例,考察新世纪后中国知网中“地区+华语/华文”的组合情况。
表1反映出两重信息:一是各地华语相关研究成果的比例,二是学者们对“华语”这一概念的接受和使用情况。可以看出,除香港、泰国外,有7个地区“华语/华文”使用总和都接近或超过“汉语/普通话”的数量。学术概念的“华语/华文”影响力可见一斑。
其次是华语研究的观念经历了几次转换。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的语言观也在逐步推进:华语不仅集中于中国,也分布在世界各地;华语作为一个概念,不仅指向汉语,也指向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华人共同语;华语作为交际工具和传习目标,需要研究其符号系统和教学规律;华语作为身份标记和经济文化资源,更要研究其认同价值乃至战略资源价值。
上述观念的转换一方面得益于华语研究视野的扩展:从关注境外华语,到海外华语,再到全球华语;另一方面缘于不同背景学科学者的加入,尤其是现代汉语、汉语国际教育、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语言生活研究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
当然,华语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和相邻学科如海外华文文学、华侨华人研究等缺乏必要的互动与对话。华语研究领域内,本体和应用研究也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华语描写的成果如何运用于华文教学和测试当中依旧是个难题,华语研究与华文教育的对接也是有待探索的课题。而要破解这些难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例如,华语研究已经认识到母语、汉语规划等概念的问题,对这些概念的修正或挑战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对待华语标准的看法也需要随之更新: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待海外华语应该做到包容或宽容,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问题是,包容或宽容这些说法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不平等的眼光,而另一面我们又承认各种华语是平等的。
(二)面向社会.注重应用
国内的华语研究的特色是面向海外华人社会,努力立足中国,注重应用。特别是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华语研究在论著发表数量、论文质量、相关课题创新、学科影响方面都有大幅度提升,其研究意义逐渐突显。
表2是三个阶段华语研究的各类成果统计。该表仅是以“华语”为主题词搜索得到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华语研究成果的总体论文数量、重要论文数量、著作数、学位论文数、课题数、学术会议举办次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论文分布的杂志数量也很喜人,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华语研究的覆盖面之广和影响力之大。
华语研究成果的剧增,离不開人们对其研究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华语研究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语言规划上的,多样化的华语变体和华语环境使得人们以一种包容、发展的心态看待现代汉语,看待中国语言规划,前述对于港澳语言路向的讨论以及《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成功出版可谓明证。其次,华语研究为华文教学与传播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使得华文教材的编纂、华文水平测试的开发、华文教师标准的认证等工作能够做到专业化。最后,华语研究有利于华语生活与华语发展,促进全球华语与其他国家民族语言的和谐并进。从根本上而言,这些价值不仅切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全球华人命运和发展的需要。华语研究要发挥更大的价值,应当继续面向社会、重视应用。
五、结语
本文以时间为序,以地域为界,梳理了全球华语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学科兴起的背景、议题范围、代表成果和主要进展。
全球华语研究只有30余年的历史。古人云三十而立,立身、立言、立德。对于一门学科而言,立德是底线,立身是根本——确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议题,回应社会关切,解决应用中的问题,以获得存在感。而要获得更多的认同感,立言是途经——建立学说,特别是建立能够影响邻近学科发展的理论学说,推动整个学科知识体系的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华语研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