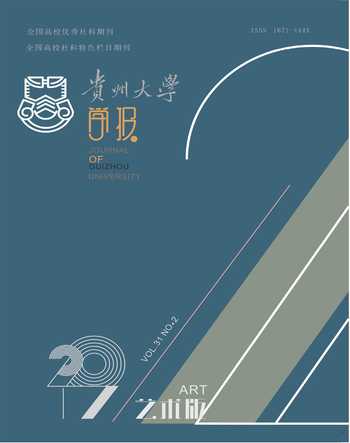黔东南雷山苗族铜鼓舞文化嬗变研究
2017-05-30王声珅
王声珅
摘 要:本文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对铜鼓舞进行跨时空的纵向与横向的考究及分析。文章将铜鼓舞不同的文化形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以宗教信仰为前提、以艺术为基础、以文化为核心,通过对铜鼓舞文化嬗变过程的梳理,揭示雷山苗族铜鼓舞的发生、成熟、传承与苗族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笔者认为雷山苗族铜鼓舞是以太阳崇拜为发生契机,传递苗族先民生生不息的生存愿望;成熟于苗族对祖先的崇拜,通过舞蹈达到“人神相融”的精神状态;传承于祭天祀祖的苗族宗教仪式,在苗族的祭天祀祖仪式中担任着“人”与“神”沟通的物质媒介,并逐渐转换成一种固定化的符号。
关键词:雷山苗族铜鼓舞;太阳崇拜;祖先崇拜;祭天祀祖仪式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2-0120-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7.02.020
铜鼓属中国古代一种礼乐器,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最为重要的民族历史文物之一。最早的铜鼓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距今已有2600余年。据史料记载,铜鼓约在战国末年至西汉之间传入贵州,早期的铜鼓被视作权力与神力的代表,需妥善保存,在隆重节日时方可请出表演,而今天的铜鼓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铜鼓是我国南方古濮、僚、蛮、越等部族的文化遗物。专家按地区和形态分为万家坝、石寨山、冷水、遵义、麻江、北流、灵山、西盟8种形式。从黔东南雷山地区的铜鼓形制来看,基本上属于麻江式铜鼓,时间约在唐宋两代。鼓身矮小,鼓面圆心为12芒纹,周围有游旗纹、花草、动物等图案。”[1]49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就有“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的记载。铜鼓及铜鼓舞文化的历史传承轨迹,记载了铜鼓的产生与古代南方民族适应、征服自然环境的过程以及族群繁衍、种族延续息息相关,是先民的集体记忆,反映出古代南方民族共有的原始思维以及生生不息的原始审美文化特征。
一、起源于太阳崇拜
“铜鼓舞”,苗语称“菊略”,以黔东南地区雷山县掌坳村的铜鼓舞为文化中心,是盛行于苗族群众中的一种民间舞蹈。铜鼓舞的起源与木鼓舞息息相关,相传苗族先祖迁徙到掌坳苗寨时,从树林中带回一截长九尺的枫香木,用49天将其做成大木鼓,每当击鼓作乐时,四方八寨的苗胞都会聚集起来,日夜围鼓而舞,祀神祭祖。然而,朝廷官员唯恐苗人击鼓作乱,当众点火烧了木鼓。木鼓虽亡,但鼓舞精神盛存,苗胞齐力凑钱购置黄铜,冶铸铜鼓,用铜鼓舞的方式保存苗族文化并传承至今,今日的雷山掌坳村亦被称为“铜鼓舞发源地”。雷山县掌坳村苗族铜鼓舞所使用的铜鼓重达29斤,长约26厘米,鼓面直径46.5厘米。鼓面是雷山苗族铜鼓的装饰重点,平展正圆,中心略微隆起,铸造了一轮凸现的太阳,称为“光体”;围绕着太阳的12道凸起向外辐射的光芒,简称“芒”;由“光体”与“芒”组成的铜鼓纹饰,称之为“太阳纹”。以太阳纹为中心,向外扩展9圈光晕,每一晕圈中都有各种纹样进行装饰,形成以“圆心定点”的“同心圆布局”概念。由此可见,铜鼓与铜鼓舞的发生是人类在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中太阳崇拜观念的物化体现。
自然界是宗教信仰中最初的对象,自然崇拜是少数民族先民最早的原始宗教观念主要形态之一。苗族古代先民因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环境制约,思维与认知能力尚处于蒙昧状态,对自然界的诸多现象没有正确认识,将自然力与人力混为一谈,便把自然力人格化。如雷电、风雨、做梦、疾病、死亡、生育等,皆认为是超人类的某种神秘力量所导致的结果,认为人类对自然界无能为力,唯有通过祈祷与敬畏,来获得自然界的力量,形成了早期宗教信仰仪式的缘由。铜鼓舞产生于太阳崇拜的祭祀仪式,其原因正是与先民祭天祀地以祈祷风调雨顺,希望五谷丰登的人类早期核心诉求——生存祈愿紧密相关。因此,铜鼓舞在早期最为重要的一个功效,是作为“神器”,在“天”与“人”之间起到传达、沟通的效果。
既然铜鼓舞的作用,是通过祭祀、击鼓、起舞等方式传递祭祀者的愿望,使之达到人神互通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推定,铜鼓的本身就是自带神性的神物。人们借助于铜鼓的神力,通过敲击铜鼓起舞的方式形成天人合一、人神互融的精神理想状态,以实现自身的愿望。而铸刻在铜鼓身上的纹饰则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在某种特定的民族社会条件或族群心理狀态的影响下所集中体现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从对贵州铜鼓的考究中得出,“太阳纹是早期铜鼓上流传下来的唯一的写实纹祥,也是铜鼓上唯一具有实用意义的纹饰。”[2]可见,人类以铜鼓的声音传递自己的心声,通过铜鼓的纹饰强调献祭的核心,以诉求人类对于生存的渴望。换句话说,铜鼓上的太阳纹饰是整个铜鼓文化的符号,是铜鼓文化诠释的精神内质。对自然物的崇拜,实则是对自然物的依赖;而对太阳形象本体的崇拜,实质上是对太阳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膜拜与敬仰。
综合此前论述、史料记载与田野调查,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太阳纹的发生是太阳崇拜这一苗族先民早期宗教信仰的具象符号,铜鼓上的太阳纹饰就是对太阳神崇拜观念的物质反映。事实上,太阳作为万物生长之本,是整个人类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是先民在社会萌芽时期的普遍信仰。人类的生存繁衍离不开太阳,根据太阳周而复始的规律,先民们深信太阳意味着生命的循环往复。以农耕稻作为主的苗族先民,对于太阳则有着更为直观、深刻的依赖。原始时期的苗族先民早已意识到太阳对整个农业生产与谷物丰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将太阳纹饰刻画在铜鼓的最中心位置,深刻反映了苗族族群强烈的太阳崇拜心理。铜鼓中央的太阳纹与外扩的光芒体,体现出古代苗族先民对社会与自然最初的认知反映,是太阳崇拜意识的早期彰显。以太阳纹为中心,象征着太阳普照大地带来生命的繁衍,也寓意着所有的生命都能在阳光下生根成长,生生不息。
鉴此,铜鼓上的太阳纹,是苗族先民对太阳的崇拜与对生命的崇敬。苗族先民以农耕为业,在原始部族中以铜鼓舞这种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祈求生产丰收、风调雨顺,逐渐形成了太阳崇拜仪式。苗族先民将自己对太阳的敬畏与信仰裹之在平日的生活中,在铸造铜鼓时进行艺术的想象与加工,创造了太阳纹饰。“铜鼓不仅是太阳和社的象征,而且正是祭社礼日的对象也即‘替代物。最后我们当能指出铜鼓图像纹饰细部中那些直接表现礼日祭祀的仪节,否则我们也将不能解释象征太阳的太阳纹为何置之于鼓面接受打击的中心和重点。”[3]100简言之,铜鼓舞最初的发生是古代苗民对太阳崇拜的反映与表达,而太阳纹的出现、发展、纹饰变化以及舞蹈内在语义的转换都承载了苗族先民对早期世界的认知感受。以铜鼓舞为载体,将太阳崇拜融于太阳纹之中,逐渐成为苗族族群信仰的符号,在上千年的流传中呈现出古代苗民的精神世界。
二、成熟于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的产生建立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基础上,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信仰文化现象,是原始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自然崇拜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人类早期信仰意识,图腾崇拜是人类对生物灵魂产生的崇拜心理,而祖先崇拜则是对人类自身祖先灵魂的崇拜观念。“人类学意义上的祖先崇拜,是指以相信已故的成员给某个集团的现有成员的生活带来影响这一信仰为基础的民俗信仰体系。”[4]祖先崇拜是祖灵观念和祭祖行为的复合体。祖先崇拜得以形成,源于生者对死者的怀念与期颐,希望保佑自己以及所属集团的延续和繁荣,帮助“子孙”获得更有利的生存条件。
祖先崇拜的发展是从部族、集体祖先崇拜到家庭、个人祖先崇拜的仪式活动的嬗变过程。纵观历史的发展脉络,祭祖的对象最初为本氏族团体、族群部落的共同祖先,尔后随着家庭模式的出现,逐渐转变为本家族先祖。
从祖先崇拜的产生与发展中可看出,祭祀对象的本身多是与祭祀主体有亲、血缘关系的善灵,而祖先崇拜所祭祀的祖灵通常会被升华为氏族(或家庭)的“保护神”符号。其特征主要是祭祀主体与被祭祀主体之间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认为,为了确保继续获得祖先庇佑,不懈地感谢和祈祷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崇拜,掺杂着与亲切怀念的思想感情结合在一起。正如恩格斯在书中所言:“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非人间力量的形式。”[5]311
苗族的祖先崇拜观念形成于母系氏族时期。该时期的妇女在农耕生产与日常生活中占主导性地位,苗族祖先崇拜中的“蝴蝶妈妈”、“姜央”等均为女性形象。苗族古歌记载:“有一年,某地突发瘟疫,死伤众多;又一年,整年大旱,粮食颗粒无收。于是,姜央(苗族创世传说中的始祖)认为,这是由于没有祭祖,得罪祖先而降得灾难。于是决定祭祀祭蝴蝶妈妈,以祈祷降幅子孙……祭祖之后,祖先治愈瘟疫,普降雨露,庄稼年年丰收,百姓日日平安。姜央感恩祖先庇佑,定下规约:从此每隔十三年祭祖一次,代代相传,变成风俗。”由此可见,苗族对祖先、祖灵崇拜的心理发生、情感观念等意识活动的具象表现形式为宗教仪式。即说明,仪式是苗族祖先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祖灵的祭祀与信仰都需通过仪式表达。
雷山苗族铜鼓舞从早期信仰中产生,其本身又自带有与神灵对话的力量,在苗族的祖先崇拜仪式中当之无愧的起着核心的作用。如今的铜鼓舞用于苗族集体性的年节活动或祭祀活动当中,具有严格的仪式性与强烈的群体特征。铜鼓舞活动大多在传统佳节或祭祀仪式中举行,如吃新节、过苗年、鼓藏节等。以雷山县为中心的十三年一次的鼓藏节是整个苗族最盛大、最重要的祭祖仪式,仪式活动的祭祀舞蹈就是铜鼓舞。铜鼓舞动作不多,舞蹈节奏随铜鼓的敲击节奏而定,基本动律与木鼓舞大体相似,多为四拍子和三拍子。据雷山县掌坳村苗族“铜鼓舞”演员吴道雄说:该地区传统的铜鼓舞有十二段,现在掌坳地区的苗族人只能演奏11段,分别为:捉蟹舞、赶鸭舞、赶走斑鸠舞、打猎舞、捞虾舞、送客舞、祭祀舞、骑马舞、放牧舞、团聚舞、团结舞。演奏铜鼓舞没有规定顺序,跳舞者根据鼓点的变化去判断是哪一段舞蹈。每一舞段都没有固定的长短,可根据舞者祭祀仪式中的内心情绪、外在环境等多重原因自由的增加或减短每一个舞段的表演时间。整个舞蹈仪式颇带神秘感,其审美特征是象征性、寓意着抽象而威严的狞厉之美。
祖先崇拜是苗族先民原始宗教观念中最典型的表现。苗族先民的祖先崇拜不仅体现在对自然万物神灵、民族图腾文化的崇拜,更突出、更核心的是对本民族的民族英雄、精神领袖、祖先神灵的缅怀与崇拜。祖先是本族的创业者,他们的灵魂自然是本民族的保护神。苗族有“老鸦无树桩,苗人无家乡”的苗谚,在苗族古歌中有大量关于战争、逃亡的叙述,使苗胞对祖先寄予深切的怀念和崇敬。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仪式化,苗族先民将一切神灵都被赋予人格化、神圣化的特性,认为祖先神灵主宰人世间的一切。苗族铜鼓舞就是在仪式中陳述了这种神灵人格化的苗族原始宗教思想,即对客观世界的虚妄反映,它表现的是神灵庄严肃穆的神威,它使人们相信人类与无所不能的神灵共存,这些神灵眼观八方、天地皆知,惩恶扬善,消灾免难。其实,铜鼓舞对祖先崇拜意识的实质意义就是借助集体性的仪式舞蹈来强化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提高民族声望与身份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三、传承于祭天祀祖仪式
古代血缘宗法关系得以长期遗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体模式。至今,苗族社会的氏族关系都未曾正式接替,原始社会的机制一直没有完全转变,血缘纽带一直绵延于整个苗族历史。此外,共同的始祖崇拜,也使得苗族同胞在缅怀祖先的心理支配下唤起民族激情与民族凝聚力。祭天祀祖仪式是以祖先崇拜观念为心理引导,逐渐形成具有程式化动作与严格流程的苗族祭祀文化活动。基于苗族“无字”的文化特殊性,在苗族传播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动态传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民族志与舞蹈史论记载、历代前辈的田野或文字资料整理、数次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雷山苗族铜鼓舞的舞蹈动律特征与风格特点几乎是固化的、无任何艺术添加或改动的,其缘由正是与铜鼓舞是祭祀活动中的一项重要且严肃的仪式项目有关,它所涵盖的人文内涵在今日的民间舞蹈传承过程中十分宝贵。
首先是对雷山苗族铜鼓舞动律特征的传承,主要有:1甩:根据腿部动作的节奏,双手大幅度的前、后甩臂,与脚同边,突出舞蹈动作的自由与大气。“甩”的动律具有典型的山地民族原生态舞蹈特征。2拧:脚下动作向前行进过程中,以腰为轴心,左右拧腰。“拧”的动律具有幅度大、艮劲足的特征,主要运用在舞蹈的第十段,亦属于苗族舞蹈中较为罕见的一种形式。3踹:主力腿向上跳跃时,动力腿做“前踹步”,动作自由、奔放、幅度大,主要运用于“集体大狂欢”等表达喜悦情绪的段落中,给人酣畅漓淋之感。4摆:随出腿的顺序,上身进行同边的左右摆晃动律,以腰部为轴心。此动律属于苗族舞蹈的典型动律之一。由此鉴见,在雷山苗族铜鼓舞的纵向传播过程中,传递媒介的符号化和凝固化会成为该仪式世代连续传播的一套规则与形式。
其次,雷山苗族铜鼓舞风格特点从整体而言,动作质朴、自由随性,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手部:双手击掌的动作贯穿于全舞之中。通过击掌配合铜鼓的节奏随之而舞,以凝聚群体心理、调动群体在舞蹈中的主动性与心理情绪建设。2上身:舞蹈以腰部为轴心,带动上下四肢的动作,强调协调感。对比大体上主要以腿部动律为主的苗族其它舞蹈而言,这种上下一致的协调感是由“天人合一”、“人神相融”的宗教信仰所提炼出的独特的舞蹈风格特征与审美方式。3下身:蛙式腿型。在铜鼓舞中,许多动作的跳跃、行进步、摆步等等,膝盖向旁打开,形成蛙式腿型,这种特点是区别于其他舞种最具代表性的一点。以此类形象为基础,雷山苗族铜鼓舞随之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原型,以家族权利为中心的向心意识,并逐渐成为祭天祀祖仪式中代表性的固化符号。
除此之外,雷山苗族铜鼓舞所用的铜鼓也值得我们考究。它是一种中空无底,一头有面,呈平面曲腰状的乐器,表演时无需其它乐器配合,独自击奏。铜鼓可根据音色分为公铜鼓和母铜鼓,公铜鼓的音色浑厚、低沉;母铜鼓的音色清脆、响亮。铜鼓调式与木鼓完全一致,音乐调式十二种,舞蹈动作五十余种。以前敲击铜鼓时:“以绳耳悬之。一人执木槌力击,一人以木桶合之,一击一合,使其声洪而应远”(《八寨县志稿》)。现在跳铜鼓舞,常见的是置一木架于亭前或场坝中央,将铜鼓悬挂其上,由击鼓者(也是铜鼓舞的指挥者)一手持木槌敲鼓腰,另一手执皮头槌敲鼓面击打伴奏,声音抑顿分明,铿锵有力。舞者围成圆圈,根据鼓点的要求与变化进退有节地舞蹈。旧时的铜鼓舞属于严肃的祭祀仪式舞蹈,今天的铜鼓舞主要在“吃新节”、“苗年”、“鼓藏节”等大型苗族节日的祭天祀祖仪式中表演。
(一)“吃新节”
苗语“哝莫”,是黔东南苗族地区十分隆重的节日,中心在雷山县、台江县等地。其中,雷山县的苗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的84%左右,有“苗疆圣地”与“中国苗族文化中心”之美称。雷山地区的吃新节来历有三:一是为了悼念开发该片区的苗族始祖;二是大忙季节已过,趁农事稍闲,休闲作乐,调剂生活;三是稻秧已孕穗、抽穗,预兆丰收,需要祭祀天公,感谢神灵的赐福。各地吃新节的过节时间不一,以家庭为单位,以糯稻的成熟阶段为标识,是糯稻插秧结束后至稻谷收割之前所过节日。大约在每年农忙之后的农历六月至丰收在望八月上中旬,于卯日开始。吃新节期间,每个家庭都需从自家田里扯几支秧苗(农历六月)或谷穗(农历八月)放在米饭之中,以祭先祖。第二天下午是苗族传统的斗牛活动,第三日下午,青年们汇集于寨中坪地上吹笙,击铜鼓起舞,以舞蹈的形式感恩祖先的赐予、预祝稻谷丰收、祈求子孙后代繁衍生息的宗族性节日。
(二)“苗年”
苗族称之为“哝梁”,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诸多苗族民俗、传统仪式的集中体现。因苗族各族群所居住的地点、气候、环境、条件不尽相同,农作物的生产与成熟期也各不一致,因此各地的“苗年”在节日的时间、活动、规模、仪式、方式上都有各自的特色,使得这些不同的苗寨在各自不同的“苗年”日子里,轮流成为该苗族区域的狂欢中心。苗年的起源是上古时代苗族先民农耕稻作,以求丰收的产物。雷山县苗族地区的苗年,四周弥漫着浓浓的苗族千百年来农耕文明发展的气息,让人欲割难舍、久久不能忘怀。打糯米糍粑和宰猪是必不可少的活动,这些食物连同鸡鸭鱼肉于卯日(或辰日)下午与酒一起放于祭台,祀物祭祖;祭毕,方可吃年夜饭。从第二天起,苗族的妇女不必再操持家务,可在场坝中连续五天跳芦笙舞或铜鼓舞,欢庆佳节、庆祝丰收、祭祀祖先。
(三)“鼓藏节”
又称“鼓社祭”,苗语“馕将略”,活动期共为三年,以宗族为单位举行,是苗族社会最隆重的祭祀大典与影响极深的一项民俗事象。关于鼓藏节的来源,老人的口述均不一致,根据鼓藏头的描述,苗族的鼓藏节是苗族先祖姜央为了祭祀自己的母亲蝴蝶妈妈而兴起的。姜央祭祀祖先,百姓康乐,风调雨顺,于是巫师祷告祖灵并允诺每年按照天干地支历法的十二地支举办小祭,每隔十三年举办大祭,以祈求谷米满仓,生活幸福。“鼓藏节”中的“鼓”有多重含义,一是指古代苗族社会中“鼓社制”的社会组织形式。二是“万物有灵”的苗族早期宗教信仰。“鼓藏节”以祭祀祖先为最高旨意,先使用木鼓,后发展为铜鼓,祭祖遂由祭鼓替代。祭祖活动有严明的程式化的仪式流程:第一年“醒鼓”、第二年“立鼓”、杀牯牛祭鼓、第三年“送(藏)鼓”。由此可见雷山苗族铜鼓舞中的“鼓”,在此象征的是祖先的符号,其形式和实践,均是一项典型的祭祖仪式。
雷山苗族铜鼓舞得以延续与传承,是由于在苗族的祭祖仪式中担任着祖灵与祭祀者之间沟通的物质媒介,逐渐转换为一种固定化的符号。一方面,以铜鼓舞的形式祭天祀祖,通过对民族共同的先祖群体与家族祖灵的祭祀,加强苗族同胞对家族与族群的“血脉”意识。另一方面,通过铜鼓舞的各项仪式确认家族内长幼级序、突出主干家族、始祖族源、各系别宗族,以强化苗族社会的伦理秩序。由铜鼓舞所呈现出的文化状态、表述的情感、传递的道德伦理、界定的人群关系、象征的社会或家庭节都等都与苗族社会组织结构的本质紧密相关。
结 语
以黔东南雷山县掌坳村为文化中心的苗族铜鼓舞,其发生缘由与苗族早期宗教信仰中的太阳崇拜观息息相关,以铜鼓舞为载体,将太阳崇拜融于铜鼓的太阳纹中,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民族信仰的符号。铜鼓舞的发展是苗族祖先崇拜观念最典型的表现,其审美特征是象征性、寓意性实质是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来提高民族声望与身份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铜鼓舞的传承则是基于苗族文化“无字”的特殊性,是祭天祀祖仪式的代表性符号。
对雷山苗族铜鼓舞文化嬗变的探寻与考究,实际上是和苗族社会历史、苗族文化进程的一次对话。当铜鼓舞承载着苗族历史、文化传承的脉络时,人们踏着铜鼓发出的深沉而凝重、浑厚富有节奏的鼓点,围绕着藏有祀日观念、祭祖心理的铜鼓不知疲倦地一圈又一圈地跳着,如同生命的循环往复。这种源于苗族先民古代社会巫教文化的铜鼓舞,以沿袭了上千年的舞蹈动态向世人昭示着苗族的祖先圣灵、世间万物的相融与沟通。这些厚重又信守古常的精神内质对创造舞蹈的主体、表演主体、观看对象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将前人的艺术经验、苗族社会的历史轨迹、苗族人民的心理状态变成一套仪式化的格式,将不同时期的生活要素融入其中加以修正剪裁,纳入定于一尊的现成格局,使舞蹈在阐述思维意识与文化认同中获得体验、寄托、宣泄,从而找到最终的归宿。
参考文獻:
[1] 杨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
[2] 席克定.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铜鼓研究[J].贵州文史丛刊,1989(04).
[3]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
[4] 色音.祖先崇拜的宗教人类学探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
[5]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