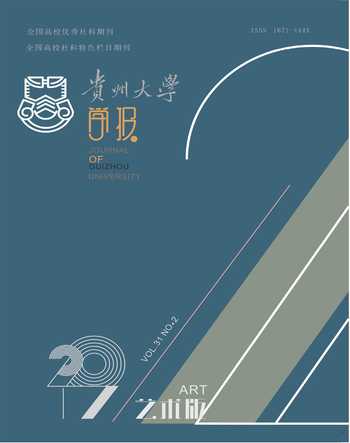论宋画中的闲臣主题图像
2017-05-30杨光影
杨光影
摘 要:南宋时期,闲官制度与养老优老政策的推行,以及士大夫对于“会昌九老”的追慕,造成了数量庞大的闲臣群体,形成了热衷文会雅集、企慕高寿长生的闲臣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士大夫阶层的稳定,维系统治者与士人阶层“共治天下”的紧密关系,因而得到统治集团的认可与推广。在此语境下,南宋画院画家创作了一批闲臣图像,形成以闲臣为主题的视觉文化。其中,“赐王都提举寿”的系列作品堪称典型。这些图像从修道养生之逸、世俗伦理之乐等层面呈现闲臣群体的活动情境,有的作品则将闲臣之志寄托于景物当中。同时,南宋皇帝以题诗为路径参与到视觉文化实践中,力图通过诗画互文,传达皇帝对于士大夫阶层的宠赐。这种互文不仅出于功用考量,更包含题诗者对闲臣生活的认同与向往。闲臣图像不仅盛行于当时,还影响到后世文人画创作。
关键词:南宋院体画;闲臣图像;视觉文化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2-0112-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7.02.019
“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祖宗之法”。在宋代,皇权集团与士大夫构成了政权的主体。对此,两宋统治者建立了宫观提举等闲官制度,同时倡导与实施优老养闲政策,以此稳定士大夫阶层。闲臣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随之形成。闲臣大多年事已高,坐地锦衣厚禄,追求修道长生,以此颐养天年。对于历经仕途沉浮的士人来说,这种中隐不失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对于统治者而言,优厚的政策待遇有利于提升士人阶层对于政权的认可,维护皇权政治的稳定性。统治者的倡导影响到士人的政治心态,“本朝士人多慕乐天”,白居易及以其为代表的闲臣群体“会昌九老”成为众人的理想。南宋时期,统治者继续奉行这一政策,且较北宋更盛。在此语境下,一批以闲臣为题材的作品得以生成。其中,马远所绘、宁宗题跋“赐王都提举寿”的一批诗画堪称典型。
在这些作品中,《松寿图》与《踏歌图》最为知名。两幅图像与宋宁宗的题诗形成诗画互文,呈现修道养生、伦常之乐的闲臣活动场景,涉及道与儒、修炼与世俗两个层面,显示统治者对于闲臣的政策优抚与厚爱,以此提升士人对于朝廷的认同与忠诚度,维护南宋政权的稳定。
一、高寿的闲臣:“王都提举”身份考释
赐王都提举的画作共有五幅,分别为马远《松寿图》、《踏歌图》、《竹鹤烟泉图》,赵伯驹《月宫图》,另有一幅为“高宗题李唐画”(《珊瑚网》卷五)。这五幅画作分别有宋高宗、宋宁宗的题诗,形成了诗画互文。徐邦达先生认为,高宗与宁宗所赐者应该为同一人。那么,这位得到皇帝赐画的“王都提举”究竟为何人?其身份是什么?这一问题成为分析此类诗画互文的基础。
这五首题诗的内容关联密切,祝寿与修道成为共同的主题。事实上,仅从“赐王都提举寿”的题跋来看,祝寿之意已然明确。在题诗中,祝寿之意再次显现,如题李唐画“恩沽长寿酒,归遗同心人。满酌共君醉,一杯千万春”。该诗实为宋高宗袭唐人权德舆《敕赐长寿酒因口号以赠》,见于《全唐诗》卷329,第29页。除祝寿之外,其余题诗均与修道相关:《题松寿图》诗云“成不怕丹梯峻,髓宝常欺石榻寒。不恋世间名与贵,长生自得一元丹”;《题赵伯驹团扇<月宫图>》诗为“清凉境界火云藏,但觉仙家日更长。千载寿松谁宴坐,星君午夜吐光茫”;《题<竹鹤烟泉图>》诗为“仙酒红生颊,永保长生道自成”。
由于题诗内容与修道相关,加之《松寿图》对于修道场景的描绘,美国学者李慧漱断定“王都提举”是一位王姓的道士。这一结论有待商榷。在南宋时期,负责宫观的道士被称为“观主”和“知观”。[1]尽管在《洞霄图志》中,确有一名王姓的知观,但“都提举”显然不是道士的称谓。
在宋代,“都提举”意为总掌管,这一称呼可以指涉多项官职,如“市易司都提举”、“剑南道都提举”等。就题诗来看,“王都提举”既是一位高寿官员,又是与修道长生活动密切相关的人物。在《宋史》职官志和《宋会要辑稿》所记载的官职中,与高寿、修道同时相关的提举官只有“宫观提举”的官职。所谓宫观提举,是一种名义上管理道教宫观,实际领取俸禄、不做实事的闲官。任命为宫观提举的大臣,要么年龄偏大,退位养老,如宋孝宗时期的宰相王淮,年过六旬后,改授“洞霄宫提举”;[2]要么是党争失势,贬黜闲置,如宋高宗时期的名将李纲,宋宁宗时期的朱熹。因此,“王都提举”应是这类名义上提举道教宫观的闲官。此外,宋代皇帝有善待老臣的传统,如宋真宗在元宵夜宴时,宣召老臣,赐坐于一旁,倾心交谈。赐画老臣,以此祝寿不失为优抚闲臣的一种方式。
不過,关于“王都提举”究竟为何人,一时难以确定。傅伯星先生认为,此人为宋宁宗的内侍王德谦。受赐之人最可能是皇帝身边的重臣。据《宋史》宦官传记载,王德谦在宋宁宗登基的“绍熙内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问题在于,赐画的嘉定年间,王德谦早因“骄恣逾法”而“诏降团练使、移居抚州,他事勿问”[3],即使赐画予他,他的称位不再是“都提举”。因此,“王都提举”不可能是王德谦。由于缺乏史料的证据,难以确定王都提举究竟为何人。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王都提举”是一位高寿的闲臣。
二、闲境坐忘乐高寿:闲臣主题诗画互文的修道之维
在《松寿图》中,诗画互文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诗歌并未对人物展开具象描摹,而是点明人物以内丹法进行修炼,达到了良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境界。画面则将这种精神状态落实到人物的修行活动中,突出了“坐忘”的修道状态,以此表现追求长生的理想。
首先,题诗中“长生自得一元丹”点明图中道士以内丹修持的方法进行修道。这种元丹“自得”之法,是指以身体(尤其丹田)为丹炉,以精气神为药物,通过一定的方法,使得精气神在体内凝成丹药的内丹修炼法。道教的丹道分为外丹与内丹。外丹以东晋葛洪为代表,以松脂等炼成丹药服用,由此进行修行。外丹修炼弊端在于,丹药包含铅汞等毒性成分,且炼丹之时存在诸多危险。北宋时期,内丹术逐渐兴起。天台道士张伯端入蜀得“至人”指点,写《悟真篇》,提出了内丹修炼的理论。至此以后,内丹派盛行于两宋。宋宁宗嘉定十年,白玉蟾创立金丹派南宗,提出“内炼成丹,外莲成法”,在江西、浙江等地影响颇大。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兴起于唐末的内丹炼养热潮流入两宋,愈益波澜壮阔。尤从北宋神宗朝起,内丹空前盛行,其学说趋于成熟,呈取代内丹以外一切道教传统炼养术之势中。”[4]内丹派认为,佛教重修性而轻修命,儒家重修命而轻修性,道家需要兼取众长,达到性命双修。“性”关乎道,“从道受生谓之命,夫道者,性之本也(《太上老君内观经》);[5]命即物质性的生命,关乎器。“身者,道之器也”,性命双修意味着身体的修养与修道同等重要。事实上,内丹派将修养身体视为长生的基础,先命后性,先术后道。身体长存意味着内丹丹炉长在,“道”可以以此为“器”,通过体内精气神的返璞归真,获得长生,修成仙人。诗中第二句为“髓实常欺石塌寒”,髓实是指骨髓充足,精力饱满,明显是经过内修,身体发热,以至于坐于寒石之上,却不觉寒冷。需要补充的是,调养身体,获得高寿,原本就是道教的内容。《道德经》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强调对身体的后天养护。李道存《性命圭旨》则说道“老氏之教,教人修性命而得长生”,[6]进一步强调修养性命与长生的紧密关系。
与诗歌包含的内丹养生相呼应,图中道士身穿薄衣,胸怀微敞,坐在寒冷的山石上,呈现出“髓实”之体。更值得注意的是,道士的动作及其呈现的状态,体现的是内丹修炼所需的“坐忘”之境,而物我两忘的“坐忘”正是求得长生的路径之一。道士斜倚在石榻之上,这种坐姿也出现于马麟《静听松风图》中的人物。据《南史》隐逸传,南朝道教宗师陶弘景在所居宫观栽植松树,以听松自娱。另据此书记载,陶弘景年轻时因为貌美,常被众人注视,他自觉烦恼,常拿一把扇子,遮住脸面。《静听松风图》的人物沉浸于听松中,通过松风,与松交流。旁边的童子则拿着主人的扇子,可以推知,图中人物确为陶弘景。同时,马麟《秉烛夜游图》中的人物,也是几乎相同的坐姿。人物在园林之中,夜赏海棠,完全沉浸于眼前美景之中。以此二图作参考,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坐姿中的人物与景致交互,达到了物我交融,进而物我两忘的“坐忘”状态。这种抛却杂念,与道合一的状态,正是修炼内丹所需心境,如内丹经典《黄庭经》所说的“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7]。另外,我们从赐予王都提举的其他诗歌中,佐证图中人物的“坐忘”状态。《题赵伯驹<月宫图>》全诗为,“清凉境界火云藏,但觉仙家日更长,千岁万松水宴坐,星君午夜吐光耀”。宴坐原为禅宗术语,正所谓“宴坐山林,下中上修”(《楞伽经·一切佛语心品之一》),强调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亦不依地静坐修行。星君是道教神仙,联系修道长生的主题,这里的“星君”应指掌管长寿,度化过彭祖的南斗七君。“清凉境界火云藏”则透露了修炼过程中的阴阳交互。“清凉境界”与《松寿图》题诗中的环境类似,都是丹梯之上,寒石聚集的深山之境。“火云”则描述了此环境中的炼丹过程。云为水,水为阴,火为阳,水火相济,阴阳互补。据此,这里的宴坐依然关涉道家修炼。它所达到的这种状态与“坐忘”是相通的。由于此诗与松寿图题诗同赐一人,内容也有相似之处。可以推断,图中人物的斜倚放松之状,乃是不拘常理,物我两忘的“坐忘”的修炼状态。“养生之术在忘物我之情,诚忘物我之异,使此身与天地相通,如五行之气中外流注不竭,人安有不长生者哉”,这种“坐忘”之态,正是求得长生的理想途径。
与此相应,图中童子的装束也透露出内丹派的影响。首先是童子挂满斛叶的衣服,与内丹派始祖钟离权的装束相似。在南宋院体画中,童子的形象并不鲜见,他们作为主人活动的陪侍,出现在绢素之中,如文人高士从事赏月、观瀑等雅趣活动的《邀月就梅图》、《高士观瀑图》等图像,又如道士修行的《静听松风图》。但除了《松寿图》以外,童子的衣饰均为宽裹。唯独该图的童子身披树叶。这种树叶作衣领的服饰,与山西博物馆所藏金代八仙砖雕中的钟离权极为相似。金国是与宋并峙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军事敌对的同时,文化交流不断。内丹派的南北两宗皆尊钟(离权)、吕(洞宾)为祖师。因此我们可以说,《松寿图》的童子装束可能参考了钟离权的形象。钟离权原为东汉大将,与吐蕃交战兵败,遇到东华帝君度化得道,“道成,束双,衣槲叶,遂成为真仙”[8]3,图中童子的发式亦是束双,挂满槲叶。这种装束在马远的另一幅作品《三教图》中也可以看到。图中儒生、和尚、道士三人坐而论道,画面右边为道士。这位道士全身披满斛叶,发型为童子髻。这一形象,也是画家受内丹派影响,进而参考钟离权形象作画的又一佐证。
更为重要的是,其他院画作品中的童子,均处于画面的边缘位置。尽管《松寿图》中的童子亦作陪衬的角色出现,但相比于其他作品,画家明显给与了更为精细的描绘,其画面位置与画面主角更为接近。画家对童子的精心刻画,或许与呼应长生主题有关。在道教中,童子暗喻长生。因为在道教看来,长生不死的表现之一就是童颜永驻,如《庄子·大宗师》中的寿者女便是“色若孺子”。陶渊明将青松与道教用来托寓长生的“童子”并列,隐含其中的长生意蕴已不言自明。图中童子鹤发童颜,与主人相互映照,凸显长生的理想境界。
除人物的坐忘状态外,《松寿图》还创构出与之相应的闲静清幽之境。这种清净之境与诗中语像形成互文。诗中为“道成不怕丹梯峻”。在古代诗歌中,“丹梯”凌云之山,如李白《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诗:“遇憩裴逸人,巖居陵丹梯。”王琦注引吕延济曰:“丹梯,谓山高峰入云霞处”[9]。同时,丹梯还被引申为升仙得道之路,如唐杜甫《赠特进汝阳王》诗:“鸿宝宁全秘,丹梯庶可凌。”邵宝之注:“丹梯,山上升仙之路。”[10]图中的清幽之境,呈现了诗歌所言及的“丹梯”之上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此境之中的寒石老松、午夜圆月、灵芝等图像符号均包含长生之义,这些符号组合将画中的闲静之境升华为长生世界。
首先,寒石老松指向悟道与长生。松在中国文化中的意涵较为丰富。在南宋院体画中,松同样包含多重含义。根据图像主题,我们可以粗略的分为以下几种:其一是烘托玩赏的氛围,如马远《对月图》、《月下把酒图》、马麟《秉烛夜游图》;其二是与文人雅趣相组合,如《观瀑图》、《高士携鹤图》、《林和靖图》;其三则为高士谈道悟道提供荫泽,如《松荫谈道图》,《松崖客话图》等。《松寿图》中的松树明显与悟道有关。如上文所分析,画家极力描绘人物的坐忘之态,而坐忘的目的之一是题诗中所说的“道成”。图中人物坐于寒石之上,松荫之下,仰望月夜天空,感悟天地间大道。道家认为,道难以显露与把握,却又实实在在的往复天地之间,因此,修道者可以通过体悟自然来体验至道。松荫则为在自然中悟道提供了一片理想的境地。此外,松樹还指涉长生。刘向编撰的《列仙传》中,有一位神农帝时期的雨师,名叫“赤松子”,具有“能入火自烧,随风雨上下”[8]1的仙术,他可能是道教推崇松的发轫。葛洪《抱朴子》说,“大岭堰盖之松,大谷倒挂之柏,皆与天齐其长,与地等其久”[11]。松被视为长生的象征,道教徒通过服食松叶、松根以求长生。
其次,图中的圆月寓指长生世界。月是南宋院体画常见的图像符号。马远《月下把杯图》、《松萌玩月图》中,月是文人举杯欢饮的娱赏对象。刘松年《月夜观潮图》描述了中秋夜观潮之景。在这些图像中,月皆出于边角之上,作为点缀之笔存在。与之不同的是,在《松寿图》中,月却出于画面的正上方,是占据重要位置的远景。从观赏的角度来讲,将月绘于此处,影响了远山的空蒙之境。更为重要的是,人物视线与月并无交集,使之显得可有可无。作为声明显赫的画家,马远不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因素。那么,图中月有何用意呢?如果我们从长生的图像主题考察,月在此处确有增益主题的作用。在道教文化中,还存在意指长生的月仙信仰。月仙即嫦娥,传说嫦娥为后羿之妻,偷食西王母的长生不死之药,飞仙入月,化为蟾蜍。战国时期的《归藏》、刘安《淮南子·览冥训》、张衡《灵宪》均有记录。因为长生的月仙的存在,月也具有了长生的意义。画家将月绘于画面的重要位置,力图用月作为长生符号,建构画中的长生世界。
最后,图中童子手捧灵芝,寓意长生世界。在宋代花鸟图像中,灵芝并不多见。但参照明清的灵芝图案,我们能确定童子所捧的确为灵芝,而非他物。例如,在明代画家蓝瑛的《松石灵芝图轴》中,灵芝的形状、颜色与《松寿图》中童子所捧之物就极为类似。灵芝为道教升仙的仙草,葛洪《抱朴子》多次记载服食灵芝升仙的轶事。显然,图中的灵芝有求长生之意。然而,与单纯的花鸟图像相比《松寿图》的灵芝并非单独的长生符号,它与图中环境紧密联系,指涉整个长生仙境。图中灵芝为童子手捧灵芝,低头不语。这两颗灵芝不太可能是随身携带之物,而是童子在山中采摘所得。童子摘得灵芝,欲告知主人,但又怕打扰主人修行,于是立于一旁,等待主人的注意。在古代文化中,采食灵芝的地方都是长生不老的神仙世界。如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昆仑山仙人耕种,采食灵芝。《海内十洲记》更描述了“仙家数十万,耕田种灵草”的海外仙屿。因此,《松寿图》中的灵芝暗示,图中世界不仅是清幽之境,更是随时可以采食灵芝的长生乐土。
简言之,画家运用松、月、灵芝等包含长生之意的图像符号,在阐释诗中闲静之境的同时,将之升华为长生世界。同时,图像符号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配合。松为长生世界最为显要的标识,月为长生世界的远景,灵芝则成为最具想象空间的长生符号。
不过,由于画作是为王都提举贺寿之用,作为御用宫廷画家,马远深知皇帝题诗的真正意图与图像的功用。《松寿图》所营造的长生世界并非不接地气,而是处处包含与世俗的联结,同时暗示祝寿之意,与题诗隐意形成互文。
与世俗的联结首先体现在,图中人物并非真正的道士,而是闲来无事的官僚。在马麟《静听松风图》中,陶弘景脚边有一个拂尘,手中握住近似打鬼绳的法器。相比之下,《松寿图》中的人物则没有这些器物。更为重要的是,《静听松风图》中的陶弘景在风中胡髯飘逸,显得仙风道骨。《三教图》中的道士则遍穿斛叶,奇妆异貌,也并非凡人。与之相比,《松寿图》中的人物显得仙气不足。同时,《松寿图》的童子手拿策杖,可知其主人是居于俗世、入山修道,而《静听松风图》中的陶弘景本在山中,其童子手拿主人的扇子,并无用于登山的手杖。可见,双方的修炼境界不同,前者的登山宴坐更接近世俗世界,是一种闲趣。
此外,图中的松和灵芝兼含祝寿之意。在赐“王都提举”的诗画中,另有一幅《松鹤图》,题诗为“恩沽长寿酒,归遗同心人,满酌共君醉,一杯千万春”。吕天成的《神镜记》记载了这样一个轶事,有一对夫妇,其宅院后种有一颗孤松。百年后,夫妇死去,化为白鹤,常绕松而飞。松故而包含长寿之意。在《松寿图》中,松树是画面的主体之一,其祝寿之意非常明显。除了松树之外,灵芝也兼有长寿之意。图中灵芝颜色偏红,其品種为赤芝。早在汉朝,汉乐府诗《长歌行》便明确记载赤芝延年益寿的功效,“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发白复又黑,延年寿命长”。此外,童子腰间的葫芦也有贺寿之意。“仙葫”是道教的标识之一,在《老氏圣迹图》中,老子仗上栓葫芦;八仙之首铁拐李的法器为葫芦,另还有“壶仙”的传说。同时,葫芦亦有长寿之意。民间年画的寿星形象,其策杖上面均栓有一支葫芦。在与道教有关的麻姑献寿图像中,麻姑一手捧灵芝酿的酒,进献王母娘娘,一手也握有拴着葫芦的策杖。
三、伦常有序伴高寿:闲臣主题诗画互文的世俗之维
与《松寿图》形成对应的是《踏歌图》。作为赐予王都提举的另一幅画作,其中的诗画互文呈现出闲臣活动的世俗维度。图中老者为高寿的士大夫,他与士人装束的男子以及老妪婴孩共同构成一个伦常有序的家庭,并以踏歌为契机表现出闲臣的伦常之乐。
目前,学界对于《踏歌图》中的人物身份存在争议,但从装束可以断定,图中人物为士人阶层。在以往的研究中,《踏歌图》常被视为民间风俗图像,图中踏歌之人则被看作农民,例如对图像内容的描写“壮丽的石山下,白云缭绕,殿阁半露,几个走在田埂上的老农,看禾苗茁壮”(胡德智《中国人物画经典·南宋卷》)。但近年来,图中人物的社会身份获得重新审视。这种审视基于以下两点考量:其一,农民并无闲逸之志,体察物阜民丰,进而踏歌而行;另一方面,图中前行的三个男子均带璞头,牵酒葫之人则头戴幅巾,这些装束为南宋士人甚至社会名流所用。在服饰等级制度分明的古代,这些头戴璞头或幅巾的男人,肯定是士人而非农民。[8]1应该说,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其论证还需要一些补充。在两宋时期,服装等级制度虽被明文规定,但在市井生活中,僭越之状屡见不鲜。例如,朝廷规定百姓服色为黑白,不得添彩,但事实却是“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燕翼诒谋录》卷二)。因此,仅凭服饰等级推断图中人物身份,还是存在漏洞。但从院体画创作的角度来看,《踏歌图》为获得皇帝御笔的立轴之作,图中的人物身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应该作为某一阶层的代指。人物装束恰好发挥了这一指代作用。同时,反观院画中的农民形象,多衣衫褴褛,或有多处补丁,或身披蓑衣,指代贫民阶层,如李迪的《风雨归牧图》中的牧童,佚名《丝纶图》中的村妇等。
然而,士人是外延宽泛的社会阶层,从卖“眼药酸”的落第秀才到位及宰辅的士大夫,都可归于士人。那么,图中人物究竟为哪类士人群体?此图亦有宁宗所书“赐王都提举寿”。对于受赐者而言,皇帝所赐的立轴大作肯定有所寓意。如果说《松寿图》呈现了闲臣的修道养生之举,《踏歌图》则体现了闲臣外出郊游的娱乐场景。在该图中,几位士人装束的男子踏歌而行,其情境颇具戏剧性。其中,袒胸露乳、回首祈望的老者是中心人物。这位老者不失为高寿闲臣的指代。除了老者之外,踏歌之人还有三位中年人,一位老妪与孩童。这些人实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样的描绘屡次出现于院画之中,是画家的有意安排,例如在《丝纶图》中,老妪、少妇纺丝,孩童在河边玩耍,丝纶隐喻和谐的家庭关系与伦常。在《踏歌图》中,这种和谐的伦常得以再现,旨在说明踏歌而行的闲臣不仅自身高寿,还享受着天伦之乐。此外,宋宁宗的题诗也透露了“闲”的信息。宋宁宗所题之诗为王安石的《秋日偶成》,虽为前人所作,但该诗与图像构成的关系非以诗歌为话语资源进行图像演绎,而是皇帝借用此诗解释图像语汇。
如果说《松寿图》描绘的长生世界,表达了统治者对于闲臣的政策优抚,那么,与之互补的是,《踏歌圖》通过图像语汇的空间安排,隐喻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暗示闲臣政策的效用,宣示皇帝对于士人的格外恩宠。这种精心安排充分地展示于《踏歌图》中。图中的闲臣踏歌于山麓之下,山间云雾缭绕,偏偏显露出一簇建筑与一处爬廊。从被画家正面描绘的建筑形制来看,其屋顶的形制为重檐庑殿式。这一建筑与赵伯驹《宫苑图》相同,应为南宋宫苑建筑。同时,山间的爬廊为南宋宫苑的建筑特色。南宋宫苑皆依山势而建。山势起伏,且江南多雨,为宫殿之间行走方便之用,南宋宫廷修建了这种爬廊。此外,建筑周围有两棵松树,其树枝颇具特色。这两颗松树还出现在《华灯侍宴图》之中。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图中所绘的建筑群乃是南宋宫苑,山水则为宫苑所在的凤凰山。在宋代图像中,宫苑往往成为政权与皇权的象征,如北宋赵佶的《瑞鹤图》,一群白鹤升腾于宫苑之前,暗喻天佑皇权的祥瑞之兆。由此来看,一群闲臣在南宋宫苑之下愉快地踏歌,体现的是朝廷与士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当然,这种和谐关系并非相对平衡的,它依然以皇权至上作为前提条件,强调闲臣活动出于皇权的恩荫。这种恩荫也暗含于构图之中。北宋郭思的《林泉高致》说道“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道出了山水画中位置安排的象征意义。在宫廷画家画作,这种象征意义更加浓重。《踏歌图》中的重檐歇山顶的宫苑在高山之中,其山位于画面中央偏上的位置,“其小幅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角”,暗示了皇权的高高在上。同时,宫苑恰好位于画面中央,表明皇权的政治地位,这一位置安排不失为“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的活用与拓展。
此外,大斧劈皴所描绘的刚猛山势则强调了皇权的威严。唐五代乃至北宋,江南山水常用以董巨的披麻皴,以呈现山水的柔美。由于南宋院体画“系出李唐”,表达北方山水的斧劈皴为南宋院画画家所继承。马远的大斧劈皴的源流在此。有人认为,大斧劈皴象征故国之思与恢复中原之意。但结合作画语境与画家生平分析,这一结论实属臆断。《踏歌图》题款为“嘉定十三年”,此时距离宋金嘉定和议过去了十三年,南宋社会得到安定与发展,北伐的呼声已渐消弭。此时的院画作品尚有展示恢复中原之志,显得不合时宜。同时,图中的大斧劈皴也不可能是马远的“讽谏”之举。马远生出光宗朝,并未经历北宋亡国之痛,马远没有李唐的曲折经历与复国热情,在其传世作品中,并无一幅诸如《中兴四将图》一类的画作。不仅如此,马远还时常迎合各种政治势力,既给显贵张兹(张浚之孙)创作屏风,也为理宗朝势力颇大的宦官创作“有辱圣人”的《三教图》。因此,“讽谏”在《踏歌图》中出现的几率实在不大。况且大斧劈皴运用广泛运用于供人把玩的团扇、图页之中,作为泛化的图像语汇,它的内涵较李唐笔墨已经发生流变。在《踏歌图》中,山水气势宏大,与富贵的宫苑互相呼应,组成了一组图像符号,意指皇权的威严,强化了君臣和乐的前提。
四、儒道融合,闲逸乐寿:闲臣主题诗画互文的综合考察
结合《踏歌图》与《松寿图》来看,两幅诗画同赐“王都提举”,应该是统治者的有意为之。两者呈现了南宋闲臣活动的两个层面。前者是伦理世俗层面,是儒者所喜好的伦理之乐,后者则是修道层面,是道家的修仙长生之趣。两者相显溢彰,构成南宋闲臣的理想境界。进言之,统治者所赐的“王都提举”不仅是具体的某位大臣,更意指闲臣群体的典型代表。画中的理想境界既体现了皇帝对于大臣的恩宠,也宣示了对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优厚待遇,有利于巩固与维系统治者与士人阶层“共治天下”的紧密关系。
闲臣文化可溯源到北宋“九老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在洛阳人履道里的宅院,白居易与其余六位高寿官员举办“七老会”,后来时年136岁的李元爽与95岁的僧如满加入进来,始有“九老会”。[11]北宋时期,在闲官政策的推行下,官员纷纷效仿,据邵伯温《邵氏见闻录》记载,梅尧臣尹洙、欧阳修等在任洛阳的官员“会于普明院,白乐天故宅也”,举行“老人会”,互相以老为号。但事实上,梅尧臣、尹洙时年仅31岁、欧阳修26岁,由此足见老人会风气之盛。[12]在此语境下,《会昌九老图》在宋代士人阶层广为流传,如范仲淹在《与韩魏公书》奉劝韩琦致仕之后“必传上《九老图》也”。所谓“九老会”,其内容就是唐人所称的“文会”,是文人或机缘巧合,或相约已久的酬唱、会文的聚会。王昌龄贬谪江宁,常与会于“琉璃堂”,唱和诗文。单从宋代文化来说,九老会又与文人雅集相似,只不过九老会的参与者均为“雪作须眉”高寿之人。
与之相比,南宋时期的闲臣生活显然更为丰富,既有道教的修仙求长生,也有儒者的天伦乐趣,其中还有民间踏歌习俗的渗透。不过,两宋的闲臣活动并非互相割裂。可以说,南宋闲臣活动是北宋时期的继承与发展。首先,南宋时人同样追慕九老之风。白居易“九老会”为南宋文人周密尊为闲臣之首,《会昌九老图》也不断被模仿与传播。南宋院体画《会昌九老图》为摹写李公麟之作,并获得宋高宗的题诗。另据《式古堂书画考》记载,刘松年、马远均绘有《九老图》,马兴祖也有一幅《香山九老图》。其次,无论《松寿图》的修道求长生还是《踏歌图》中的丰年踏歌,均为“老人会”主题的延展。后人之所以追慕“九老会”,要因之一在于向往高寿长生,正如明人王世贞于刘松年《九老图》的题跋所云,“不为僧赞宁者,当为百三十六岁之李元爽”。《松寿图》中的闲臣于山间
图1 (宋)马远 《松寿图》,立轴,绢本设色,122×527cm,辽宁博物馆藏
之中修道养生,无疑延续了君臣追求高寿的愿望。至于《踏歌图》中的踏歌情境,将民间的踏歌习俗融入闲臣活动中,拓展了以文人雅集为主的聚会。踏歌原是盛行于民间百姓的娱乐方式,唐代的《朝野佥载》曾记载,元宵之夜,长安宫女与市民同欢,“灯轮下踏歌三日夜”。同时,踏歌之俗也存在于士人阶层,李白的《赠汪伦》描述了踏歌送别的情景。不过,宋代闲臣的踏歌活动有着自身独特的背景。两宋时期,坊市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空间孕育的民间文化深刻影响到士人、皇族的生活。在此语境下,踏歌不仅是一种生活习俗,还富有戏剧性与娱乐性。这种戏剧性更出现在宫廷文化之中。例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了皇帝寿宴上的情景,“第八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13]宋孝宗时期,南宋宫廷废除乐坊,临时招募民间舞者,在《武林旧事》宋理宗“天宁节”的表演节目单上,我们看到踏歌取代了教坊队舞的表演位置,成为重要的舞蹈表演节目。由此观照《踏歌图》中的踏歌情境,我们就可以理解画家进行戏剧化描绘的文化缘由。
综上所述,闲臣主题的诗画互文呈现了以“王都提举”为代表的闲臣生活,这种呈现基于世俗伦理与修道养生两个层面,与闲臣“高寿”、“求长生”的特征相符。这类诗画互文是《会昌九老图》的延续与演绎,是南宋士大夫“企慕乐天”的表征。在宫廷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南宋皇帝以题诗的方式参与闲臣图像的创构之中,力图调和君臣关系,柔化君臣的等级膈膜,彰显出皇恩对于闲臣群体的宠赐,以此稳定士大夫阶层与政权统治。
参考文献: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474.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954.
[3] (元)脱脱.宦者四王德谦传[M]//宋史(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13674.
[4]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12.
[5] 太上老君内应经[A]//道藏(第22册)[M].上海:上海出版社1988:128.
[6] (宋)李道纯.中和集[M]//东方修道文库[G].徐兆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76.
[7] (宋)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792.
[8] (汉)刘向.列仙传校笺[M].王叔岷,撰.北京:中华书局2007:3.
[9] (唐)李白.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A]//李白全集汇释集评(卷18)[M].2894-2897.
[10] (唐)杜甫.赠特进汝阳王[A]//杜诗详注[M].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65.
[11] (唐)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外集(卷上)[M].谢思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2911.
[12]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7.
[13]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9)[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