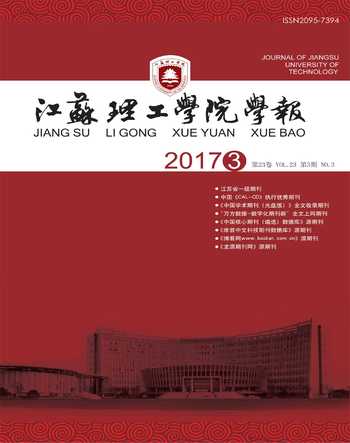解读《女勇士》与《喜福会》的叙事相似性
2017-05-30金婕煜丛佳红
金婕煜 丛佳红
摘 要:作为当代闻名遐迩的华裔女作家,汤亭亭与谭恩美都为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作出了卓著贡献。凭借独特的叙事魅力,汤亭亭的《女勇士》与谭恩美的《喜福会》一经出版便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通过比较分析两部作品在叙事策略上的东方特色和叙事结构上的西方特质,归纳总结出缀段性叙事、传统元素及“四季”原型结构在两部作品中的运用。同时,基于两位作家的华裔女性身份,简要概述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叙事声音及其创作意图。
关键词:女勇士;喜福会;缀段性叙事;传统元素;原型结构;女性主义叙事學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7)03-0053-04
19世纪中期,面对如火如荼的淘金热,大批华人开始涌入美洲大陆。侨居异国的他们渴望过上富足的生活,拥有令人钦羡的社会地位。然而,美籍华裔的身份却制约着他们在新环境内的进一步发展。为寻求更多的发声机会,华裔作家们纷纷执笔,试图通过文字来宣泄情绪、吐露心声,这也使得华裔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文坛发展的新生力量。在诸多闻名遐迩的华裔作家中,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与谭恩美(Amy Tan)可谓是两座高峰。不同于一些旅居异乡的海外作家,汤与谭都是第二代美籍华裔,自幼便生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两种文化的交织对二人的创作产生了非凡的影响,使其作品独具多元化的叙事特点。同时,身为女性作家,独特的叙事声音也让二人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女性特色,为其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汤与谭的诸多作品中,《女勇士》与《喜福会》一经出版便在美国文坛内享有盛誉,颇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本文拟从叙事相似性入手,着重探讨两部作品在叙事策略、结构及声音方面的相似之处,从而归纳总结出叙事特点对于作品成功的重要性。
一、突显东方神韵的叙事策略
汤亭亭与谭恩美的母亲都是讲故事的能手,所以二人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也深受母亲的影响。汤亭亭曾在与张子清的访谈中提到,父母常在睡前给她讲述各类东西方的故事以至于这些故事在头脑中都出现了混淆,而这些混淆又为她日后的创作拓宽了思路。[1] 193 同样,母亲娓娓道来的东方故事也激起了谭恩美的创作灵感,其处女作《喜福会》中的部分情节便是改编自母亲和外婆的真实故事。因此,通过母亲维系起来的中国情结也左右着二人在叙事策略上的选择。细考《女勇士》与《喜福会》的叙事策略,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采用的主要是缀段性叙事和传统元素的穿插。
(一)缀段性叙事
“缀段性”(episodic)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他看来,如果缀段性情节之间毫无因果关系,那便是所有情节中最坏的一种。[2] 31 因此,缀段性叙事起初在西方小说中并不常见,相反,该叙事策略却在中国的明清小说中颇为盛行,主要代表作有《水浒传》《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等。不同于西方小说的严谨叙事,缀段性叙事往往是将多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其中的联系却不紧密,这也使得小说整体缺乏“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整体感。[3]同时,缀段性叙事下的每个故事都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单独拆开也可自成一篇,十分便于读者的间歇性阅读。
《女勇士》全书分为五个章节,涵盖了汤亭亭及周遭女性的五个故事,分别是:无名女子(姑姑)、白虎山学道(花木兰与我)、乡村医生(母亲勇兰)、西宫门外(姨妈月兰)和羌笛野曲(我)。其中,“白虎山学道”是对巾帼英雄花木兰故事的改编,不满于生活现状的汤亭亭将自己想象成花木兰,进山学艺、带兵杀敌、铲除恶霸,最终成为敢于反叛的女勇士。因此,该章节也可被纳为汤亭亭自己的故事。尽管故事的主人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故事本身既独立又完整,成功塑造出五个截然不同的女勇士形象。同样,谭恩美在《喜福会》中也采用了类似的缀段性叙事。全书共四部分,包含了四对母女的十六个故事。每个完整的故事都相对独立,却又因为母女间的交叉叙述而产生联系,既能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母女间的矛盾与冲突,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射出中西文化的碰撞。
此外,这两部作品在创作的意图上也符合缀段性叙事的创作特点,即以叙事映现社会。缀段性叙事起初被广泛用于“说书故事”中,而后得以发展,成为章回体小说的主要叙事特点。晚清以后更是出现了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作者们采取缀段性叙事的创作意图也由此被进一步丰富。采取缀段性叙事的小说往往更关注于社会问题和时人的日常生活。[4]这一点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同为华裔女作家,汤与谭面临着相似的社会问题,即“社会地位被白人为中心的主流社会和男尊女卑的华人团体双重边缘化”。[5] 因此,二人在创作时也有意地将政治、种族、文化等社会问题融入作品之中,从而实现了以叙事映现社会的目的。
(二)传统元素的穿插
好的作品往往离不开巧妙的叙事策略。《女勇士》与《喜福会》的成功也离不开其中所穿插的传统元素。首先,汤与谭在作品中引入了许多中国传统意象,例如,《女勇士》中的“白虎(white tigers)”“花木兰(Fa Mu Lan)”“西门(the western palace)”及《喜福会》中的“月亮娘娘(The Moon Lady)”“红烛(red candle)”“麻将(Mahjong)”等。传统意象的融入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二人还在作品中引用中国俗语并对部分的俗语进行加工整合,使之更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例如:
“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 [1] 4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棒子嫁根杵子,为它守节随它一辈子。”[1] 177
“施比受更有福。”[6] 22
“一个贪心不足的姑娘肚子大了,她怎么也不肯说出怀的是谁的孩子,后来她服毒自杀了,人们剖开她的肚子,发现里面是一只大冬瓜。一个贪心的人,到头来什么都是一场空!”[6] 30
中国俗语往往来源于民间哲理,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汤与谭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中国俗语及其他传统元素更表明了她们对于华裔身份的认同感。同时,也正是由于二人的这种中国情结,才使得两部作品在叙事策略上都能彰显东方神韵。
二、暗含西方特质的叙事结构
尽管汤与谭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更偏向于东方色彩,但其作品在叙事结构上却仍暗含着西方特质,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弗莱的“四季原型结构”。近代以来,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进一步蓬勃发展,这离不开加拿大学者诺思洛普·弗莱的卓著贡献。作为该理论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弗莱在其著作《批评的剖析》中强调神话是所有文学模式的原型,从神的诞生、历险、胜利、受难、死亡直到复活,包含了文学所涵盖的一切故事。[7] 在弗莱看来,西方文学主要可被分为两大类,即喜剧与悲剧。同时,他也认为,西方文学的叙述结构,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对自然界循环运动的模仿。因此,文学叙事结构又可被下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喜剧(春天)、浪漫(夏天)、悲剧(秋天)和讽刺(冬天)。[8] 喜剧象征着春天,二者都充满生命与活力;浪漫象征着夏天,浪漫作品中会出现激动人心的高潮,就好比夏天是四季的顶点一样;悲剧象征着秋天,秋天万物枯萎,而悲剧往往伴随着主人公的死亡;讽刺象征着冬天,二者都与绝望、阴暗相关。[9]
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汤与谭在其作品中也采用了类似的叙事结构。《女勇士》全书共五章,对应的四季结构分别为:“无名女人”讲述了姑姑与人通奸并最终自杀的故事,属于悲剧,对应秋天;“白虎山学道”中的花木兰在带兵杀敌时,偶遇丈夫,怀孕生子,属于浪漫,对应夏天;“乡村医生”中的母亲勇兰意志顽强、战胜了“压身鬼”,最终成为一名经济独立的医生,属于喜剧,对应春天;“西宫门外”讲述的是姨妈月兰被抛弃并患上臆想症的悲惨遭遇,属于讽刺,对应冬天;“羌笛野曲”是汤亭亭成长经历的回顾,其中引用蔡琰与匈奴的故事,表达了作者顽强进取的决心,属于喜剧,对应春天。因此,《女勇士》的叙事结构也可被简要概括为:悲剧(秋天)——浪漫(夏天)——喜剧(春天)——讽刺(冬天)——喜剧(春天)。[10] 同样,《喜福会》中也暗含“四季原型结构”。全书分为四部分,对应的四季结构分别为:“千里鸿毛一片心”主要包含了四个母亲在中国的遭遇,属于悲剧,对应秋天;“道道重门”则是四个女儿在美国的故事。这时候四家人已经定居于美国,生活质量处在上升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浪漫,对应夏天;“美国游戏规则”涵盖了女儿们的爱情故事,但四人的爱情都不算如意,丽娜和露丝的爱情都纷纷出现危机,而薇弗莱与里奇的感情也受到了母亲的质疑,四则故事透露出阴暗与消极,属于讽刺,对应冬天;“西天王母”的四个故事中,母亲们吐露了自己内心埋藏许久的故事,与女儿之间的隔阂也在逐渐消除,最后,精美更是與中国的姐姐们相认,属于喜剧,对应春天。因此,《喜福会》的叙事结构也可被简要概括为:悲剧(秋天)——浪漫(夏天)——讽刺(冬天)——喜剧(春天)。
对比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不同于四季应有的顺序,两部作品都是始于秋天,终于春天,始于悲剧,终于喜剧。同时,作品都是在经历阴暗的冬天之后,又最终回归到明媚的春天。这其中也暗含着华裔女作家的心声,即使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她们也对未来充满期冀,翘首以盼属于华裔们的满园春色。
三、独具女性主义的叙事声音
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提出,该理论将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结合到一起,打破了传统叙事研究的局限性,为学者们对文本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拓宽了新思路。兰瑟在其著作《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对作品的叙事声音进行划分,主要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作为华裔女作家,汤与谭在作品中也有意将女性塑造为叙事权威。同时,也融入了兰瑟所提出的三种声音,本文将着重探讨两部作品中的“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
所谓“个人叙述声音”就是指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事声音,故事的主角便是讲故事的“我”。[11] 20这一点在《喜福会》中十分明显。全书的十六个故事,几乎都是通过主人公自己的叙述而展开,鲜有夹杂作者的声音。同时,《女勇士》中的“白虎山学道”也采用了个人叙述声音。作者对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将自己想象成巾帼英雄花木兰并以木兰的口吻来叙述整个故事,使得读者们可以任意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这种借助“个人叙事声音”来发声的作法,不仅避免了作者在特定场合下直抒胸臆的尴尬,同时还能巧妙地传达出作者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展现出当代女性打破沉寂、击碎枷锁的美好愿望。
此外,两部作品中还夹杂着“集体型叙述声音”。在兰瑟看来,所谓集体型叙述是“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授权的个人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分别为:某叙述者代表某群体发言,即为“单言”(singular);复数主语“我们”共同叙述,即为“共言”(simultaneous);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即为“轮言”(sequential)。[11] 23 《女勇士》中的“羌笛野曲”便采用了“单言”的表现形式。在篇章的最后,汤亭亭以女诗人蔡琰的故事结尾。在匈奴堆里生活十二年以后,蔡琰用歌声打动匈奴,使之感受到其中所饱含的伤感和怨愤,最终被赎回,还从蛮人那里带回了《胡笳十八拍》等三首歌。[1] 192 作者也有意借此来代表广大美国华裔发声,寻求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相互包容。同时,借助蔡琰的故事,汤亭亭不仅表达出华裔女性寻求发声的渴望,也为处于边缘的华裔女性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12] 不同于《女勇士》所采用的“单言”手法,《喜福会》全篇呈现出“轮言”的表现形式。十六篇故事的主人公皆为女性,母女们轮流发言,诉说着自己的苦楚与心声。全书男性声音的集体缺失造就了绝对的女性叙述声音。借助集体型叙述声音,完整地表达了女性从逆来顺受到坚强独立的全过程。
四、结语
面对双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华裔女性并未踟蹰不前,而是努力冲破桎梏、寻求发声。正如蒲若茜所说的那样,“身处弱势种族和边缘文化的人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其发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颠倒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的位置,她们想要表达的是对于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向往”。[13] 60 因此,出于华裔女作家的本能,汤亭亭与谭恩美都有意借助复杂的叙事技巧来包容生活的复杂性,通过叙事策略与叙事结构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再加之独特的女性叙事声音,完整地诠释出华裔女性对突破性别性别二元对立、文化二元对立的美好向往。
参考文献:
[1] 汤亭亭. 女勇士[M]. 李剑波, 陆承毅,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8.
[2]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3] 段江丽. 譬喻式阐释传统与古代小说的“缀段性”结构[J]. 文学评论, 2009(1): 81-87.
[4] 张蕾. 论“故事集缀”型章回体小说[J]. 文学评论, 2010 (4): 135-141.
[5] 刘卓. 解读被双重边缘化的文化屬性——试论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谭恩美的《喜福会》[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6): 452-454.
[6] 谭恩美. 喜福会[M]. 程乃珊, 贺培华, 严映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7] 黄明嘉. 寻觅莱茵河底的“宝物”——伯尔小说的神话原型蠡测[J]. 外国文学评论, 1998(1): 81-87.
[8] 诺斯洛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 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8-10.
[9]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158-242.
[10] 王小彤. 从叙事及文化差异解析《女勇士》和《喜福会》[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05.
[11] 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M]. 黄必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2] 赵文琼. 《女勇士》的叙事模式和女性视角[J]. 文学界(理论版), 2012(1): 103-104.
[13] 蒲若茜. 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