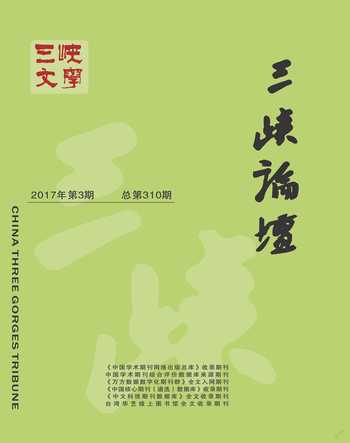消解、反抒情与冒犯式书写
2017-05-30刘波谢文娟
刘波 谢文娟
摘要:自1990年代进入诗坛以来,伊沙一直以口语方式进行诗歌创作,他传承并拓展了1980年代“第三代”诗人的日常书写,以调侃和反讽消解了诗的某种崇高之美。他这种口语诗歌被归属于先锋写作范畴,因为对浪漫主义诗性的拒绝,其作品也相应地引起了很大争议,包括他那些短频快的极端“口水”诗、反抒情的立场和做减法的写作行为,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伊沙式诗歌心理学”。而从伊沙作为个体的写作历程,我们也可以返观口语诗歌近三十年来整体所遭遇的历史和现实困境。
关键词:伊沙;口语诗歌;先锋;反抒情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3-0056-06
伊沙在当下是个颇具争议的诗人。他以比“第三代”诗人更极端的口语诗登上诗坛,声称要将口语写作进行到底,这是诗歌的幸运还是不幸?他说自己是一个诗歌上的严肃主义者,但我们从他的诗中看到的大多是嘲讽、玩笑和恶作剧般的调侃;他说自己对语言很讲究,但很多人说从他的诗里读不到语言创造的新奇;他说他的写作讲究明快、清晰,有人说在他的诗作中寻找不到诗美和诗意。这样一些矛盾与错位,在伊沙和读者之间发生,到底是诗人的技艺问题,还是读者的鉴赏力问题?伊沙身上的冲突感,随着他写作的成熟是在减少还是在增加?在这样的疑问中,伊沙作为当代诗坛“刀锋”的存在,就显得更尖锐,也更丰富。
一、如何处理口语和先锋的关系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坛,口语写作几已成为先锋的代名词,与其形成对应的,就是语言在诗歌中的核裂变。只要你用口语写作,就自然地被划归到先锋的行列,这种划分已变得理所当然。相反,不用口语写作,或者返回古典与传统,会被认为是保守的。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口语诗具有先锋的天然优势,而非口语诗好像就是先锋的原罪。伊沙是口语诗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在他的写作历程中,伊沙=口语=先锋——这个等式是成立的。但口语不是伊沙的首创,在他之前的“第三代”诗人群里,韩东、于坚等人的口语实践都要比他早,他只不过是将口语写作作了更为彻底和极端的实践。“从语感到口气。从前口语到后口语。从第三代到我。”[1]125这是伊沙给自己的定位,他在前人基础上的超越,是给自己套上了后现代的标签。
伊沙说他要将口语写作进行到底,这才是真正的先锋。而且在很多人眼里,真正的先锋诗歌就是口语诗,所以,伊沙头顶上无论何时都戴着一顶先锋的帽子。这顶帽子从他写作《饿死诗人》、《车过黄河》和《结结巴巴》时就已经戴上了,现在看来,这几首诗成就到底在何处?对后来者形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需要另当别论,但它们的确代表了1990年代解构主义的美学。在年轻人都崇拜汪国真的时代,伊沙却写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之诗,不仅“格调低下”,而且还带有玩世不恭的嬉皮意味,这与众不同的杀手锏,决定了伊沙此后的诗写之路不会太平淡。现在,先锋诗人是伊沙的标签,在他这里,先锋好像对应的就是口语。他的诗里没有长句子,也无多少修饰,甚至很少出现意象,大都是生活流的一种反讽的变形。“城市的陷阱/仅仅是一些/下水道的井盖/被揭开了 不见了/据说是被偷了去/当作废铁卖掉//城市的陷阱/出了人命/使另一些人/无端负伤/落下残疾//使一个人/在失足跌落/仰卧井底之后/看见了罕有的/城市的天空/他喃喃地说/是圆的//没错/这个人/是位诗人”(《城市的陷阱》)。这就是一场经历加经验的独白,如同生活的流水账,有人说这样的诗,没有难度,读完后没有值得回味的深意。如此期待,对于伊沙来说是不成立的,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简单好读,通过语感来呈现诗意之美。
他的诗就是通过口语的表达,为我们提供一种简洁的风格,不容你质疑,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可供回味的诗性空间。也就是说,他所提供的诗意是快速的,甚至转瞬即逝,所以,他需要源源不断地随时寻找主题来写作,以保持他的先锋形象。正因其诗歌的口语化,伊沙的写作很多时候不是在被分享,而是在被消费。伊沙似乎又很享受这种被消费,这样的形势难免让他的写作成为诗歌的快餐。伊沙说他要将口语写作进行到底,这已是既成事实,由此我们是否可以作一个推测:伊沙的口语写作,其先锋性已经终结,因为他在形式上再难有变化,如果不在精神上作更深入的探讨,其止步、停滞甚至倒退就会顺理成章。这样的推测可能会引起伊沙本人的反感,但是,诗歌写作最终还是要靠文本说话,它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什么样的诗是好诗,而什么样的诗不入流,其实有的读者比诗人更清醒。尤其是在口语诗方面,很容易给人造成模糊的概念:本身是口水,可能在一些诗人那里是好诗,而在读者那里或许毫无诗美可言。伊沙运用口语,但不排斥口水。“口语不是口水,但要伴随口水,让语言保持现场的湿度,让飞沫四溅成为语言状态的一部分。”[1]125这是伊沙的口语逻辑,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如此,且往往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才会有人追问:完全的口语不带一点创造的陌生感,诗意何在?口语诗的诗意靠什么来凸显?感觉抑或领悟?有人就是领悟不出口语诗的美感,这是不是一种诗歌欣赏的原罪?其实,伊沙诗歌所带出的疑问,或许比他的诗歌本身更有價值。
口语写作就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人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也从侧面降低了我们理解语言的能力。新世纪的诗歌创作潮流,明显倾向于口语,似乎大家都意识到了书面语的局限,它没有口语那么新鲜、有活力,容易进入。口语写作当是进入诗歌的一道方便之门,因此,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跨进来。到底是口语的容易才让他们将其作为首选,还是有伊沙这样的诗人在前方铺出的先锋之路让口语美学成为了时尚?口语诗与先锋的关系,在伊沙诗中所体现的,肯定不是一劳永逸的真理,它仍然需要辨别。没有限度的绝对自由,是一种乌托邦,这种限度可以是外部契约的规定,也可以是自我内心的约束,而口语诗一旦缺乏必要的限制,必定导致极端的口水泛滥。伊沙在这方面的表现,还不是最彻底的,以他的理解,口语诗不仅仅是写作的策略,“而是抱负、是精神、是文化、是身体、是灵魂和一条深入逼近人性的宽广之路,是最富隐秘意味和无限生机的语言,是前进中的诗歌本身,是不断挑战自身的创造。”[1]224在伊沙的视野中,口语诗创作是“一条伟大之路”,他为此努力过,这努力中有期待、彷徨和兴奋,且让我们来看看诗人在这些年的口语实践中是如何一步步完成自己的语言狂欢和身份认同的。
二、当写诗成为一种日常功课
伊沙是一位高产诗人,这一点想必不会引起过多质疑。他足够勤奋,精力充沛,除了教书,写作可能是他不可多得的安慰。当这成为一种日常功课后,伊沙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写作的呢?互联网时代,坚持每个月贴出自己的新作,这是事实,这事实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写作心态,首先还是以量取胜。“我自知我是这样的写作者,需要一个有形的现场,让表现欲和创造力结为一对孪生兄弟。我需要一个舞台。”[2]2对于伊沙来说,舞台是用来干什么的?表演。只有表演才需要舞台。那么,伊沙的写作都是在表演吗?从其文本来看,确实不排除他有表演成分。从早期的成名作,到新世纪以来的诗歌,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伊沙的功课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写作练习中将自己推向文学史的位置,他对自己有着足够的自信,“我写的就是最好的”,因此,写诗的信念就成为不竭的动力。
现实中的伊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太清楚。但从他的诗中,能见出一种张扬之意,但那种张扬不是用激烈昂扬的语言来表达的,相反,他还比较节制、干脆。这样,他的外部内敛和内部张扬,恰恰构成了他在写作上的特点:以反叛的形式进入,以妥协的方式出来。就像他在一首名为《原则》的诗中所言:“我身上携带着精神、信仰、灵魂/思想、欲望、怪癖、邪念、狐臭/它们寄生于我身体的家/我必须平等对待我的每一位客人”,此诗就四句,似乎概括了诗人的全部人生。我们甚至可以将此看作伊沙的自画像,这位诗坛好斗争勇之人,其实非常清楚自己的脾性,他的张扬影响了他的诗歌,而他的诗歌又促成了他继续在张扬的路上更深地认清自我。
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伊沙的人生和诗歌经历让其写作获得了发酵,他没有像后来的年轻诗人那样将一切和盘托出,而是有选择地暴露了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它们构成了伊沙诗歌写作中的资源。他的书写就是日常生活的记录,貌似流水账,其实如他在“自画像”中所言,就是情绪的反应,我们需要将它记录下来,以达成一种写作的见证。他从叙事开始,到叙事结束,中间的分行看起来就是语言能指滑动的自然呈现,那种反讽的使用,瞬间增强了诗性效果:前面铺陈了那么多,就是为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当我们往上去追溯伊沙的写作时会发现,他在细节处理上,包括语言创造、修辞运用和意象叠加,都没有多少想象的痕迹。而他的写作主题,基本上都源于其日常生活状态,他的想象力是用在了整体表达上,而非诗歌的细节呈现里。既然他在语言创造上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有创造力的尝试,那么,其诗歌价值到底何在?如果说从他的表现主题上可以获得一些与众不同的美学感受,那么,他最终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是“思维的乐趣”,而不是题材的新颖。他少有去触及历史和想象未来的诗,他书写的大多是当下,是现实。比如《告慰田间先生》,开始写的是一出家庭情景剧,但到了后来,他将家庭剧变成了一场政治戏,田间的诗被移接到了他的诗中,在这种转换里,诗歌瞬间有了戏剧性效果。正是戏剧性,让伊沙的诗在相同模式里还能赢得读者,他善于营造戏剧性氛围,由小到大,由浅入深。
如果说《告慰田间先生》是伊沙从生活的日常转移到精神的日常之典范的话,那么,另一首同样写儿子的诗,则又是一番味道:“韩东的电话打过来/我儿子正从外面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袋方便面/和两块找回来的零钱/他问我:爸爸/我可不可以干吃/我回答说:可以/电话里的韩东/听到了这番父子对话/夸我是个好父亲/我说我不是/好父亲哪有让儿子/自买方便面充饥的/韩东坚持说是/韩东说是/那就是呗/虽然他目前还不是一个父亲/但写过《爸爸在天上看我》/那样的诗/就一定有着对父亲/以及如何做父亲的/独到见解”(《我是不是一个好父亲》)。韩东、伊沙和儿子三个角色构成了这首诗的全部,诗人们之间讨论的父子之情,并不显得复杂,一个从世俗的角度来理解,而另一个则从精神的高度来理解,所以他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不管诗人们之间是否相互认同,他们就日常生活所得出的观点,仍然适用于诗人。伊沙就是这样将他每天的经历或遭遇表达出来,以日常替代那高高在上的神性,同時,也以一种世俗的真实对抗虚构的感受。他就是直言其事,不加任何修饰,也不去精雕细琢,这种原生态的呈现,或许正是伊沙“祛魅”写作的明证。他的口语化写作引起争议,但都趋于明晰,“拒绝隐喻”,字里行间暗含着一种雄辩的意味。这可能与伊沙本人富有攻击性有关,他几乎能在所有的文字里引入浓烈的火药味,这就是他直白其心所造成的“麻烦”——他的诗有人非常喜欢,有人却极度厌恶。不管伊沙怎样认为自己在写作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他肯定不是完美的。他有自己的优点,但也是缺点多多,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刀锋”,他究竟以什么样的文本和气场为我们提供了他长久立足于诗界的依据?而他所占据的位置,到底是与他的文本相关,还是和他诗歌之外的综合能力有关?
三、反抒情的立场与干净之诗
伊沙的诗歌在当年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和他坚定的口语写作有关,他没有像很多诗人那样将诗歌导向空洞,这是他的优势。同时,他又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认为他写的口语诗很无聊,这可能与口语关系不大,而是和他的反抒情立场有关。运用口语,反抒情,这两点正是中国诗歌书面语和抒情两大特点的反面,也就是说,伊沙面临的可能就是对传统的反叛,这种反叛在那个转型时代确实成就了他,让他有了先锋的面貌。作为1990年代诗歌的先驱者,他走在了很多“第三代”诗人前面,从现代直接迈向了后现代。后现代的碎片化和冷抒情,在伊沙这里不是作为理念被接受,而是一种彻底的实践,他早就喊出了“我是个彻底的反抒情诗人”,没有余地。为此,他还给自己制订了原则:“我知道诗歌的本质很可能永远都是抒情的,诗的现代化所伴随的智性趋势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但我仍要高声强调反抒情。因为我知道太正确的理论往往没用,而有用的说法又不那么正确——这也是常识。” [3]200这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当很多人都认为诗歌要抒情时,偏偏有人要以反抒情的方式来写诗。当然,反抒情策略也不是伊沙一个人在践行,但似乎只有他做得最为决绝和彻底。既然反抒情,伊沙在写作上奉行的就是直截了当,有时候是开门见山地进入叙事,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转化为文字,并让人能看清他文字背后的生活,这是伊沙写诗的初衷。
早在1991年,伊沙寫了一首《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可以明显见出他对抒情的反叛,这不是下意识的自觉,而是一种刻意:面对梅花这种最能引人抒情的意象,他就是要反抒情。“我也操着娘娘腔/写一首抒情诗啊/就写那冬天不要命的梅花吧//想象力不发达/就得学会观察/裹紧大衣到户外/我发现:梅花开在梅树上/丑陋不堪的老树/没法入诗 那么/诗人的梅/全开在空中/怀着深深的疑虑/闷头朝前走/其实我也是装模作样/此诗已写到该升华的关头/像所有不要脸的诗人那样/我伸出了一只手//梅花 梅花/啐我一脸梅毒”。这是诗人对抒情诗结尾作精神升华的一种反讽,带有自嘲意味。前面的叙事还有一点诗歌的神秘,但到最后,梅花和梅毒相遇,一切诗意全无,诗性也瞬间被消解了。伊沙最热衷于消解诗意,似乎不能容忍情感的升华,因为那样会显得不真实,缺乏诗的流动感。
现在看来,伊沙似乎一直在做减法,去掉了很多佐料,拿掉了一些修饰,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简单的陈述,或一场事实的罗列。这种减法的写作还有没有继续深入的可能?如果说它代表一种风格的话,那么这种风格是否已经达到了极致?对日常的书写,伊沙已经将其延伸到了现场,只有现场感,才是其诗歌的活力所在。此外,他还有自己的另一种抱负:回到传统中去寻求资源。他曾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中国当代诗人仅仅以西方诗人作为标杆和借鉴对象,是一种对自身传统的不自信。伊沙从这样的自我反思中找到了突围的方式,由对李白、杜甫等唐朝诗人的敬重,他曾以一首长诗《唐》来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拓展,那是想象与现实的融合,而历史在中间起着纽带的作用。大量唐诗进入到了他的文本中,这是技术上的互文,也是一种大气的盛唐之精神的流露。伊沙由关注具体,到触及一种抽象,这不是后退,倒更像是他敞开自我的尝试。“缅怀盛世的诗人/寻找着昔日的大明宫//我家就住在大明宫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几块石板/若隐若现//据说从前/在这石板的上面——//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只有经常上这儿来的家伙/方能写出《阳春白雪》般的曲子//长安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唐》节选)。我相信,这样的诗是伊沙在写作之路上的一次出轨,他的书写和诗意恰好契合了这个时代对传统的召唤,这是一种性情的书写,一时间与口语无关,只符合内心的真相。伊沙曾谈到过“如何在诗中用力”的问题,它是技艺,也是自我期许:“让力化为气,灌注在你的诗中。反过来,读者会从你的诗中读到一股气,充满着力。”[1]124这不是一般的纸上谈兵,而是有他的实践基础,当他将心思真正用在了写作上,在诚挚中透出瓷实,那样的写作方可获得更多的认同。
伊沙的诗歌之所以在某些方面还有他的读者市场,并不是完全由他的口语写作所带来的长期效应,而是他在反抒情中注重细节的刻画,就像他在写小说时看重故事,在诗歌中,他要用细节来支撑诗意。只有细节的呈现,才会显出诗歌的尖锐和力量来,否则,一堆抽象之语的组合,难免走向空洞和虚无。既然伊沙拒绝抒情,那么空洞对于他来说就是写作的大忌,他也试图做到尽量不用大词。但他的诗歌之路如何持续性地走下去,这确实是摆在他面前的问题。
四、伊沙式诗歌心理学
伊沙曾说他是靠意志写作的,而不是虚荣的名利,我相信这一点。从他的勤奋(至今出版的各种文学作品已近50部)就可以看出,意志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强劲意志是他写作的动力,他可能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在写作上的失败,因为他始终在诗歌的现场。对于“现场”,伊沙的确堪当其任,自出道以来,他真的没有离开过这个现场。从纸质时代到网络时代,伊沙有一种如鱼得水般的惬意和昂扬。“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似乎每天都在感受幸福:网络使你过去的成就变成可现的东西,所谓'影响'具体为你创造的诗歌方式和语言被更多的人越来越普遍地消费着,而你的新成果又再度陷于新一轮的争议之中,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你的过去作为抨击你现在的标准和理由。”[2]2伊沙懂得经营之术,对于自己的诗歌作为商品被消费,那是一种荣幸。他享受的不是艺术之美,而是快感,一种语言和诗境在他笔下自我生成的快感。
伊沙的自我感觉很好,即便是在《扒了皮你就认清了我》中有自我批判,但到最后仍陷入了自我辩护:“因为在语言上获得了某种天赋,我对母语是负有天命的……”[1]125在现实中,如果一个诗人没有反省,自信可能变成自负,而自负也可能变为狂妄。当狂妄成为一个诗人的常态,他的写作又如何持续精进?就像他的那首无字诗《老狐狸》,除了标题,内容部分是一片空白,只在最下面以括号标注了一段说明:欲读本诗的朋友请备好显影液在以上空白之处涂抹一至两遍,《老狐狸》即可原形毕露。当伊沙得知真有读者这么做了时,我能想象到他那种窃喜的表情。一个玩笑变成了一场恶作剧,这种“意想不到”正是伊沙想要达到的效果,他自称是一场诗歌的行为艺术,而且像这样的行为艺术在他的写作中还不少。他有一首诗为《畅通无阻的秘诀》:“你怎样穿过/拥挤不堪的人群/一声大喝:'硫酸!'”当他把想象的场景搬到了诗歌中时,诗人所要寻找或得到的,究竟是美感还是快感?我想更多的还是快感,但这样的诗作,形式早已大于了内容。
一直以来,伊沙就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他不仅认为自己各种文体的写作属于上乘,而且也认同自己其他各方面能力,“我之能言善辩在诗界是很有名气的,无耻的是:我深知这能言善辩所以时常有意炫耀之。”[4]在他看来,这是对综合素质自信的表现,但在他人看来,他这种自信显得盲目,陷入了狂妄的自负。他坚持将口语写作进行到底,最终带来的是口语诗歌的审美疲劳。虽然他一直保持写诗的状态,每年都有不少作品出来,但能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似乎很少。那种泥沙俱下的写作很容易,但对读者来说,披沙拣金的阅读,肯定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对于惯用口语的诗人来说,如果不能跳出语言的无变化所带来的局限,他的写作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一场美学的灾难。
在此,我没有为伊沙所引起的争议辩护与翻案的意思,他作为当代诗坛“刀锋”的地位,似已无可动摇,但是,他的争议当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个诗人如何在语言创造中把握自己?而把握住了自己以后,他又怎样面对不断重复的写作?这些质问对于伊沙来说,或许本身就构不成问题,他从不掩饰自我标榜。韩东说伊沙是一个“伟大的小丑”,而伊沙在《自画像》中也对自己有个形象的定位:“诗歌的流氓/生活的恶棍//但请不要说/你很了解我//生活的行僧/诗歌的圣徒//你很了解我/但请不要说”,还是诗人最了解自己,他让别人不要说,但他自己说了出来。他的暴露,有时针对的是他者,其实也是自己。伊沙对自己认识得很清楚:“我的语言飞翔感太差了!”所以,他那些直白的语言,经常会引起争议,有时甚至让人无法作出判断。从伊沙这些年的自我经营来看,他足够冷静,深谙媒体炒作之道,也懂得如何在收放自如中保护自己。但他诗歌大面积无厘头的平面化和貌似有趣的小聪明,让他在解构的狂潮中始终缺乏一种沉淀下去的力道。
伊沙的诗歌写作所形成的效应,一方面是引起了更多人对其的效仿;另一方面,则是他的自我复制。诗歌写作上的难度,其实是值得伊沙反思的问题。短频快的写作节奏,的确是他在这个时代的优势,但又让他很难有更深入的突破。但如果说伊沙的写作也就是到此为止,这无异于否定了他的全部,因为他仍然还有抱负,他已将文学当作了自己的信仰,是个“天注定”的诗人,肩负着母语诗歌的使命感。“现在,口语诗已经达到很提纯的高度,我想让它更丰富,让它更意象化、抒情化,其他对各种元素的吸纳,口语为主,吸收意象诗歌、抒情诗歌的长处,这是我正在走的路。”[5]伊沙的这一言说包含了某种反思,我更愿意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诗人的愿望,他的这种自我期许表明他还是希望深入,因为飘浮着的写作,已难以将他的才华再次激发。当他认为自己的经验很足时,如何将这丰富的经验进行更多元的转化,则是伊沙所面临的抉择。
注 释:
[1] 伊沙:《无知者无耻》,朝华出版社,2005年。
[2] 伊沙:《我的英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 伊沙:《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4] 伊沙:《伊沙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狄蕊红:《伊沙改变了诗歌的言说方式——一个人的诗江湖》,《华商报》,2010年3月29日。
责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夏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