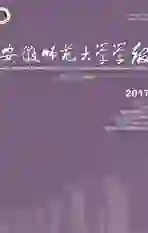近代法制背景下侠义复仇案件的传统运行模式
2017-05-20李晓婧
李晓婧
关键词: 近代法制;施剑翘;侠义复仇;社会舆论
摘要: 侠义复仇乃公权力缺失的产物,随着公权力的逐步确立,理应退出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生的侠女施剑翘复仇案,从一审到二审再到三审以至最终的政府特赦,我们不难看出侠义复仇案件之传统运行模式在近代社会再次上演。清末的“礼法之争”并未终结,“情与法”的纠缠仍是近代司法的主题之一。一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却向我们展示了影响民国司法的众多因素。一方面,舆论对案件的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族危亡之际民众对英雄式人物的迫切需要和对反面人物的极力打压影响了案件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舆论对案件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正是当权者所需要的,那么,当权者将会迎合舆论,并通过舆论来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中图分类号: G44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35608
Key words: modern legal system; Shi Jianqiao; chivalrous revenge; public Opinion
Abstract: Revenge case is the product of lack of public power.With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power,revenge case should exit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From “Heroic Woman Shi Jianqiao Revenge Case” which happened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from the first instance to the second instance to the third trial as well as the final government amnesty,it can be seen that “Traditional Running Mode” of chivalrous revenge case staged in modern society again.“The Debate between Propriety and Law” in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did not end.The raveling of “Propriety and Law” was still one of the modern judicature themes.A seemingly ordinary criminal case shows us many factors affecting judicature in Nanjing Government of Republic China.On the one hand,public opinion on the process of the case played a fueling role.People in urgent need of heroic figures and people on the villain strongly suppressed in the occasion of national peril affected the outcome of the case.On the other hand,if the impact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case was the authorities needed,authorities would cater to public opinion and convey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through public opinion.
俠义复仇是一种历史现象。复仇,尤其是血亲复仇,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原始人群亦是如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侠义复仇现象屡见不鲜,王立在其著作中已有详细论述。[1]关于中国古代侠义复仇现象的法文化解读,霍存福在其著作中,对传统中国刑法文化的三个主要文化元素——复仇、报复刑、报应说进行了分析,包括复仇事实与观念、法律中的报复刑因素及其表现、报应(恶报)理论的内容与特征,涉及到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三种主要存在形态——习俗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很好地解读了作为社会现象的侠义复仇行为。[2]近代社会,西方法治理念被引入中国,各种案件的审理过程不再是传统社会那种“青天大老爷坐镇衙门拍板定案”的场景了,出现了法官、检察官以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等角色,欧风美雨下的中国司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法治初创的民国时期,发生了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侠女施剑翘为父复仇案。当时的媒体争先恐后地报道该案件的发生及审理过程。关于这一案件,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林郁沁(Eugenia Lean)。她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她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并激发同情,是因为它与性别规范之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孰轻孰重以及国民党政府扩张威权统治等社会性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这次审判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挑战民国之政治权威这一更大问题。[3]本文则将施剑翘复仇案纳入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加以分析,该案虽然发生在民国,但从案件发生时当事人、官方以及舆论的态度来看,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于是形成了传统法律文化与近代法治理念的冲突;面对冲突该如何抉择不仅是当时的人们更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从这一层面上,清末的“礼法之争”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破解。笔者还对影响该案件进程及结果的其他社会因素,诸如舆论、政治等,进行了分析,这对我们今天法治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司法与媒体及其他因素的关系提供了思考的历史素材。
一、施剑翘为父报仇:任人情而蔑国法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是原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施从滨的女儿。1925年,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据有闽、浙、赣、苏、皖五省,自命五省联军总司令。他为了扩大地盘,引兵北犯,首先进犯山东省,山东都办张宗昌派施从滨率部迎战。因孤军深入,施从滨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尽管周围不少人替施从滨求情,可孙传芳不仅将施从滨斩首示众,将其首级悬挂在蚌埠车站前的一根木杆上,而且还暴尸三天,不准施家人前来收尸。[4]
施从滨家人获知噩耗后,悲痛欲绝。那年施剑翘还未改名,仍叫施谷兰,当时正是20岁的年龄。她是施从滨的长女,下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施剑翘奉行“父仇不共戴天”的古训,立志为父报仇。施剑翘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为报生父仇,手刃孙传芳》中提到,当时她听闻噩耗,特作诗一首以表为父报仇的决心: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动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5]159
但是当时的施谷兰毕竟只是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够手刃仇人呢?于是施谷兰先后将复仇的希望寄托于堂兄施中诚和丈夫施靖公的身上。然而,时过境迁,这二人再也不提报仇之事。时光如白煦过隙,转眼已是十年。一天晚上,施谷兰想到家仇未报,心里难过,便仰望天空,吟诗一首:“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从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也想以此激励自己,要用自己手中的剑为父报仇。
1935年,施剑翘探知孙传芳已经失势解甲,蛰居在天津,便赶往天津寻找孙传芳。后经多方打探得知,一年前,孙传芳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来到草厂庵,办起居士林。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以“智圆大师”的名义担任理事长,每逢星期一、三、五及星期日为诵经期,孙传芳届时往该处诵经。在做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之后,1935年11月13日,施剑翘在居士林成功刺杀孙传芳。在行刺得手之后,現场一片混乱,施剑翘乘此机会散发之前准备好的《告国人书》。这些卡片的一面印的是两首诗: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卡片的另一面印的是:
(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
(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上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施剑翘想通过她抛撒的《告国人书》,声明自己此行的原因是为父报仇,而后从容不迫地等待警察将她带走。
追溯东汉时期的侠女赵娥为父复仇案,可见施剑翘的行为与赵娥如出一辙:赵娥,东汉酒泉郡禄福县人。丈夫庞子夏,表氏县人。庞子夏去世后,赵娥在禄福县抚养其子庞淯。她的父亲被李寿杀死。灵帝光和二年(179)二月上旬的一天早晨,赵娥在都亭前与李寿相遇,她奋力挥刀杀死了李寿,随后到了都亭尊长的面前认罪服法。《后汉书》卷八十四《烈女传》第七十四。施剑翘和赵娥杀死仇人的原委都一样,即为父报仇,并且在刺杀之后都没有逃走,且没有否认“杀人的事实”,最终等待公权力的处置。其实,赵娥心中明白,按照汉朝的法律,“杀人者死”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施剑翘也清楚,按照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刑法典的规定,杀人者不管基于何种目的杀人,都属于犯罪行为。该刑法典第271条第1款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她们终究还是杀人了,尽管她们杀人的目的是基于报父仇。施剑翘和赵娥虽身处两个时代,但面对为父报仇这种事时,其内心是如此之相似,即任人情而蔑国法。
二、法院判决结果:伸人情而屈国法
案发后,施剑翘被移交至天津地方法院,等待法律的审判。同时,孙传芳之子以原告身份请求审理施剑翘杀人案。1935年11月25日,天津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施剑翘一案,文人豪担任主审法官。开庭当天,有超过200人到场旁听,这也是因为此案关系到两个背景复杂的家族。孙家与施家也是各自使尽手段,孙家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大律师孙观圻孙观圻,字补笙,江苏无锡人,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宣统三年(1911)九月,经学部验看考试列最优等,赏给法政科进士。曾任大理院推事、北平地方法院院长、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二庭审判长推事、嘉定地方审判厅厅长、天津地方审判厅厅长、山西第二高等审判分厅监督推事、开滦煤矿法律顾问。194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第二、三、四界政协委员。、张耀曾张耀曾(1885-1938) ,中华民国政治家、法学家。字镕西,云南大理人,白族。190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官费选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和李根源、赵坤等创办《云南》刊物。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南京任孙中山秘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约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帮助孙中山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从1913年起,历任众议院议员、云南都督府参议。。孙观圻接受孙家延聘以后,当即具呈请求天津地方法院依法严惩凶手。同时,施家一直在设法营救。其正在山东上大学的妹妹施纫兰专程由济南赶来探监,其弟施中杰延聘了当时的著名律师余其昌、胡学骞出庭辩护。施剑翘之夫施靖公也忙着找关系。法庭上双方请来的著名律师激烈交锋,案件的审判也越显复杂。根据当时的法律,杀人犯因情况不同可判十年以上徒刑以至死刑。但若凶犯自首成立,可将十年的最低限减为五年;再若“情可悯恕”成立,又可将徒刑减至二年半。因此这两个减刑的构成要件也就成为法庭上双方的争议核心:一是施剑翘是否有自首情节,这关系到审判结果的具体量刑;二是施剑翘的复仇理由是否应该得到宽大处理。[6]
施剑翘一方提出的证据有刺杀当时散发的《告国人书》,而她本人也没有逃跑的打算,在警方随后来到现场后从容接受逮捕,有很多证据能证明这一点。而孙家则不认可这一说法,他们认为这是施剑翘事先计划好的减刑之法。由于孙家的说法只是对施剑翘动机的揣测,不足以推翻施剑翘一方所提出的证据,法庭最后确认施剑翘确实有自首情节,可以酌情减刑。
之前提到的杀人罪第二个法定减刑事由“情可悯恕”,其实就是得到社会和法律的怜悯、宽恕。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施剑翘,其重要原因便是传统侠文化的影响。施剑翘基于孝道的复仇,被当时媒体称之为“现代侠女”,这种孝女复仇的故事理所当然地感动了国人,社会各界通过请愿等各种方式要求政府释放或宽大处理施剑翘。
庭审之时,双方关于是否仇杀也多有争议。孙家认为,施剑翘之父当时是死于军法,战场之上死伤在所难免,孙传芳杀施从滨并非出自私怨。但施剑翘一方明确指出施从滨并非死于沙场,而是作为俘虏且未经军法审判,被孙传芳个人杀害。关于这一点,不但被告如此供述,即使孙传芳之子孙家震也不否认其事,法庭对律师关于施从滨死于军法的辩护未予采信。
但是孙家的律师棋高一着,见复仇之说无法否认,就从更高层面彻底否定“为父报仇”这一行为的正当性,认为“复仇”之说是传统社会的余孽,完全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背离,若人人相互私杀而了结私仇,置法律于何地?民国已建立民主法治,子报父仇之说已不适用。寥寥数言,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西方法治观念与中国传统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经过十多天的审判,1935年12月16日,天津地方法院以“诉字第622号刑事判决书”对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案做出判决。判决书肯定自首成立,以“其主观方面,纯为孝思冲激所致,与穷凶极恶者究有不同,合于上述自首减刑,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从结果来看,认定了施剑翘的自首情节,却否认了“情可悯恕”环节的认定。
一审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无法接受。施家认为量刑太重,孙家则认为量刑太轻,于是此案上诉至河北省高等法院。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对施剑翘案进行了复审。在孙家的活动下,复审判决否定了施剑翘的自首行为。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官涂璋援引“六法全书”条款,指出自首情节不确。因为警士王化南未到居士林之前已知道肇事,进庙后即知道犯人在电话室,且均在被告向警士声明自首之前,被告虽有自首之意,而事实尚不明显。施剑翘至多不过是自白,声称此种认定,皆有居士林和尚证明。河北省高等法院认同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官涂璋所提自首一节不能成立的抗诉。如果施剑翘不是自首,必然还要加刑。在各界人士吁请、谴责、抨击的强大声势之下,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不得不重新做出判决,完全推翻了一审的判决结果。首先依旧否认了一审所确定的“自首”情节,但是确认了一审所没有确认的“情可悯恕”,在此基础上再度减刑三年。至此,法庭庭长宣布二审结果,“原判决撤销,施剑翘杀人处有期徒刑七年。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二发,没收。”[7]55
虽然刑期稍减,但因自首一节被推翻,施剑翘对此十分愤慨,于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与此同时,孙家震方面对复勘减刑更为不满,特加聘律师撰状,要求检察官提出上诉。双方于1936年2月先后提出上诉,但直到8月1日,最高法院才做出判决,将上诉驳回,维持河北省高院的原判。
该案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广泛关注,并得到了一些政要的支持。在多方努力之下,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特赦令中这样写到: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即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以一女子发于孝恩,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68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有期徒刑7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8]
就这样,在狱中度过九个月零二十六天的施剑翘被特赦出狱,重获自由。
施剑翘案的判决结果可以说是赵娥案的近代翻版:赵娥为父报仇杀死仇人之后,并未逃走,而是等待官府的拘捕。当时禄福长尹嘉,不忍心给赵娥判罪,便解了印绶,辞去官职,驰法纵之。赵娥说到:“仇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狱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贪生以枉官法?”守尉不敢公开释放赵娥,暗里让赵娥走去自匿,赵娥高声抗争说:“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仇人已雪,死则妾分,乞得归法以全国体。虽复万死,于娥亲毕足,不敢贪生为明廷负也。”守尉不听劝告,赵娥又说:“匹妇虽微,犹知宪制。杀人之罪,法所不纵。今既犯之,义无可逃。乞就刑戮,陨身朝巿,肃明王法,娥亲之原也。”表情严厉,毫无惧色。守尉知道赵娥很难顺从,就强迫她回家。赵娥仍坚持已见,毫不服从。守尉无奈,只得收她入狱。后来,遇到大赦,赵娥获释,被送回。《后汉书》卷八十四 《烈女传》第七十四。赵娥为父复仇,虽历经坎坷,最终被朝廷所赦免,赵娥也因此获得自由,重返家乡。施剑翘虽开始被判处徒刑,但最终却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特赦,重获自由之身。从立法层面上来看,不管是传统社会的东汉,还是法治初创的民国时期,都不会纵容杀人行为的,换言之,杀人行为是立法所禁止的。但在司法层面上,官方却对情理文化钟爱有加,传统伦理道德仍然是严酷法律的缓和剂。最终,“法”在“情”、“礼”面前让步了,官方的举措都是伸人情而屈国法。随着案件当事人的被赦免,喧喧扰扰的案件暂告一段落,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却延绵至今。
三、公众舆论导向:重人情而轻国法
施剑翘案案发数日内,国内几乎所有权威的媒体,如天津《大公报》、北平《实报》、上海《申报》、南京《中央日报》等都以《血溅佛堂》为题对此案作了详细报道。该案的一审结果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社会舆论认为,一个弱女子为父报仇,尽孝道,显侠风,难能可贵。至于说孙传芳,残杀俘虏,征伐杀戮,死有余辜。而后,案件上诉到河北省高等法院,该院认同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官涂璋所提自首一节不能成立的抗诉。此事一经媒体报道,顿时天下哗然,各地几乎每天都有声援施剑翘者,指责河北省高等法院和天津地方法院的文章也时常见诸报端。在强大的舆论声势之下,河北省高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最终判施剑翘有期徒刑七年。对此结果,一部分社会舆论仍然不能接受。施剑翘矢志不渝、舍生忘死的壮举感动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入狱后,她见狱中女犯多数因家庭贫困,没有钱买过冬的棉衣,就捐资帮她们买冬天的囚衣,被當时的人们称之为“义侠”。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都发文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施剑翘,如当时的《妇女月报》《妇女共鸣》《女子月刊》《玲珑妇女杂志》《新女性》等期刊都为之呼喊。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司法院相关档案卷宗显示,从案发不久的1935年11月直至二审结束后的1936年三四月间,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及个人相关请赦函电雪片般纷至沓来,除安徽省桐城、霍山、舒城、合肥县的党部、教育会、农商会及妇女会、芜湖律师公会、旅京安徽学会、旅苏安徽同乡会、徽州师范学校等施女原籍所在皖桐地方机构团体外,还有全国妇女会,河南省妇女会、商联会,开封县总工会、农会、商会、妇女会,江苏省、南京市及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湖南省及桃源县妇女会,云南省妇女会、湖北省教育会、杭州市及嘉兴县妇女协会、浙江省立高级蚕丝科职业学校、上海市高级职业学校、江西赣城中等教职员联合会等先后向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相关司法机构联名上书,历数孙传芳暴虐杀戮、危害民国的罪行,褒扬剑翘女士忠孝壮烈且智勇兼备,“不仅女界特色,抑为民国历史光荣”,吁请司法当局援照三年前为报叔父之仇枪杀张宗昌的郑继成案之判例,法外施仁。如,当时的芜湖农职校师生发表电文希望政府特赦施剑翘,电文如下:
全国各报馆均鉴,查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业经天津高等法院判决处以徒刑七年,查孙传芳曩年阻挠北伐,残杀党人,龙潭一役,震撼京畿,往事思维,弥深怆痛。十四年孙张启□,施从滨先生受于国民军,以期消灭反动,不幸被孙俘虏,惨杀于蚌埠车站。施剑翘以一弱质女郎,抱必死之心,溅血于从容之念,为国除奸,为父报仇,忠孝义勇,震铄古今,荆卿死士尔,食德报恩,乌足与剑翘同其芳烈,史迁尤秉笔哀之。我国忠孝立国之精神,几濒破产,如剑翘女士者诚足以超沉寂之人心,挽颓风于常世,前邓继成为叔报仇,犹蒙特赦,剑翘女士竟处以徒刑七年,其从容自首之行为复被抹杀,法律待遇,未免不公,深愿全国同胞,一致呼吁,请求特赦,以维忠孝,而彰公理。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安徽省立芜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全体师生同叩号。[9]
该案件还惊动了冯玉祥将军。《冯玉祥日记》1935年11月30日记载:“同施则凡、施中达二世兄去见焦易堂、居觉生先生,专为大赦施剑翘女士之事。”也就是说,施剑翘案还在审理时,冯玉祥在南京就已经活动施剑翘的特赦问题了。根据《冯玉祥日记》记载,冯玉祥曾为施剑翘的案子找过时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的傅汝霖,以及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居正、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焦易堂等当时司法界的大佬,为施剑翘说情。这些掌握司法的大员们当即表示:特赦施剑翘一案,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肯定没有问题,只是特赦问题还需要国民政府主席来颁发命令。[10]于是冯玉祥又找到了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国民党内联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中央委员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营救正在服刑的施剑翘;此外,国民党两位女中央委员张默君、陈璧君也出力甚多。如今,我们还能在司法院“特赦施剑翘案”档案中看到密密匝匝署名于呈文后50名中央委员的签名,其中不乏孔祥熙、戴传贤、朱家骅、张继、吴敬恒、邵元冲、曾养甫、甘乃光、洪兰友、谷正纲、叶楚伧、张厉生、褚民谊、周佛海、陈璧君、鲁涤平、马超俊、李宗黄、王懋功等民国政要。最终,施剑翘在多方努力之下重获自由。
可以说,施剑翘最终获得政府特赦的结果与公众舆论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我们再看赵娥案,赵娥刺杀仇人之后,同乡百姓都为这位侠女悲喜、慷慨、感叹,支持她为父报仇的孝义行为。在赵娥最终获朝廷大赦后,当时的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人共同上表朝廷,禀奏赵娥的烈义行为,刻石立碑显其赵家门户。黄门侍郎还著书追述赵娥的事迹,为其作传。两起案件发生后,上至官方要员,下至黎民百姓,舆论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即重人情而轻国法,给司法者以极大的舆论压力,这也是被告人最终获释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评价与思考:民国司法运作的多维面相
纷纷扰扰的施剑翘案,涉及的不仅仅是原被告双方,媒体、法庭、政府都一一粉墨登场,最终以“施剑翘被特赦”的结局拉下帷幕。其实,施剑翘案反映的只是一个微缩的“民国”。民国伊始,法制初创,处于新旧交替背景之下的一个普通刑事案件折射出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第一,“情与法之纠葛”再次上演。在我国传统社会,私力复仇虽然具有历史文化惯性,并获得民众心理认可,但是私力复仇的泛滥无疑会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威胁君主的统治。君主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自己的最高权力,在法律文本上对私力复仇进行了严格限制。但是由于皇权的有限性,无法保障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能受到处罚,另外侠义复仇不仅具有统治者所倡导的“礼”“孝”等价值秩序的正当性,而且具有历史文化的惯性和民众内心的认可,因此,统治者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对复仇者给予从宽处理,甚至给予褒奖。这种矛盾的背后蕴含着传统法律文化中“礼与法”的冲突与融合。儒、法两家的对抗是在战国时期。礼治抑或法治只是儒法两家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秩序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方式而已。西汉以后,这种思潮的争辩渐趋于沉寂,儒法之争走向了儒法融合。在法典编纂过程中,本属于“礼”的内容被纳入法律文本之中。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官吏审判案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置现成法律文本于不顾的情形。直到唐朝“一准乎礼”法律原则的确立,礼与法在中国传统社会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施剑翘案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情与法”的纠葛。一方面,当时国人深受传统法文化的影响,认为一个弱女子能够不忘父志,十年潜心报父仇,其志可哀,其情可喻;这种重视忠孝伦理道德的行为是值得称颂的,理应被政府赦免。施剑翘的辩护律师陈沅在《为施剑翘呈请特赦书》中,把施剑翘与历史上为父报仇的汉代赵娥、唐代无忌相提并论,“施剑翘以一女子,手无缚鸡之力,在家为军务帮办之爱女,出嫁则为高级军官之夫人,且也青年伉俪,儿女成行,乃能念念不忘泉下之故父,隐忍从事于报仇,虽与汉赵娥之伺仇都葶,唐无忌之刺杀卫长,同一为其父报仇,名垂不朽。然欲其事之布置周详,弹无虚发,事后之从容自首,视死如归则又不如施剑翘之孝烈可嘉,智勇兼备也”[11]125。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法制不断健全和完善,侠义复仇的生存空间理应受到限制。侠义复仇行为只不过是公权力空缺时期的产物,随着国家的出现以及公權力组织的逐步建立,复仇已渐为法律所不容许。在社会舆论多数倾向施剑翘一方的同时,也有人提出应该按照法律条文来对施剑翘进行惩处,而不应该考虑过多的道德因素;否则,整个社会就会“把施剑翘塑成一个侠义的孝女的偶像,利用人们有限度的同情和痛快的心理,来提倡旧伦理,旧道德,旧礼教,作为复古运动的张本,诱引一切活着的女性,以及现代人们,迷恋着中古世纪遗传下来的一些骸骨”[12]。
经过法庭和社会各方围绕施剑翘的种种行为在罪刑与义举之间的反复博弈,最终随着施剑翘的特赦,民国初期轰动一时的大案至此画上句号:“法”在“情”面前示弱了。这引起了我们对“情与法”之关系的再度反思。笔者认为,道德是一个社会的理想,而法律则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不能因为道德的因素去干扰法律这个底线,同样也不能因为法律这个底线去干扰对道德的追求。当产生矛盾的时候,既然它是一个司法问题,就要站在司法的角度上去解决它,那么道德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该案说明了我国法制近代化过程的困惑和曲折。
第二,舆论对案件的“推波助澜”。施剑翘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国人对传统孝文化之“集体无意识”的诉说与表达,还有两个重要的现实因素:民族危亡之际对英雄式人物的迫切需要和对反面人物的极力打压。
纵观中国历史,侠在整个传统社会几乎都受到了政府的严厉打击;但侠仍然存在,只不过侠的发展轨迹举步维艰,同时春秋战国时淳朴的侠风、侠义行为在东汉以后也日益衰微,因为江湖与庙堂的严重对立逼使侠不得不寻求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久而久之,就集成地方帮会,被视为地方流氓,失去侠原本的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东汉以后,侠作为一种文化或概念积淀在民众的心中,贯穿于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并传承至今。尤其是当社会转型、历史转折的“乱世”之际,或者民不聊生甚至民族危亡之时,侠文化总是由“隐”而“显”,焕发出勃勃生机。施剑翘案发生在1935年,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在这种民族危亡之际,民众出于拯救国难怀“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希望英雄式人物的出现。因此,施剑翘成功刺杀孙传芳后被民众称为“义侠”,堪比“荆轲、聂政”[8] ,“当场奋身,则英风凛凛,事前送母,则孺慕依依,志定不挠,神间不乱,英雄儿女,可泣可歌”[8] 。诸如此类赞语,可以看出民众已将施剑翘视为国难之际的侠义之士。当时还有人写信给狱中的施剑翘,赞赏她的刺杀行为,并同意她的看法,“要叫对方看出我们民心未死,要叫列强看出我们血气未凉,我们先要拿出我们自己的力量来”[13]。施剑翘被视为“民族英雄”的代言人。
施剑翘刺杀的对象是军阀头目孙传芳,在当时可谓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舆论之所以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与旧军阀在公众心目中的恶劣形象有直接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众普遍有一种反对军阀的情感倾向。军事将领(军阀)通常被看作卖国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施剑翘将孙传芳击毙在佛堂里的消息传出,许多人都感到无比痛快,认为施剑翘不仅是为自己的父亲报了仇,也是为民族除了害。当时著名的女报人邓季惺在《新民报》发表的《对施剑翘判决书之意见》指出:“孙传芳系祸国罪首,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本应处极刑,国民政府也曾通缉在案。诛杀国法不容之人,古今均不为罪,施剑翘一弱女,诛杀了因租界荫庇,政府无能追捕的凶犯,法庭却判以十年、七年之刑,实欠公允。”施剑翘利用了民众对于军阀的仇视心理不但将孙传芳推到了一个舆论的绝境,而且也为自己的杀人行为开脱赢得了非常有力的支持。所以,后来的审判已不单单是简单的杀人案件。这也是施剑翘为什么没有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由于当时的媒体大篇幅报道此事,使得社会各界关注越来越多,同情施剑翘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法庭最后用了最轻的量刑标准。这也是法律向舆论妥协的结果。
第三,当权者态度与舆论“不谋而合”。舆论可以影响案件的进程,而如果这结果正是当权者所需要的,那么,当权者态度与舆论将“不谋而合”,舆论客观上也就成了当权者传达自己态度的媒介。看起来本属法律問题的施剑翘案因此更多地掺杂着时代的“政治调味剂”。
一方面,施剑翘为父报仇所体现的“孝”正是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所阐释的一种本土民族主义。这一运动不是“复辟”传统社会,而是“复活”或者“复兴”传统文化;“不是通过对古老社会的重建而是对作为古老社会之根基的永恒美德的重建来达到民族的重生”[14]168。而传统社会中的孝文化恰恰在新生活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易劳逸所分析的那样:“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想到的程度。”[15]146
另一方面,当权者也是想通过施剑翘案这个契机来达到惩治异己的目的。如果没有施剑翘案的发生,通过一般的法律程序是无法惩治孙传芳的。“孙传芳原只是一只害群之马,他生前的罪恶,罄竹难书,我们还正恨他不得置之典刑,国家在他的恶势力崩溃之后,让他逍遥法外,优游岁月,毫不追究,已经待他至厚了,像他这种神人共弃之徒,还用得着保护么?老实说,施剑翘不杀他,更有谁来过问?这正是司法界的耻辱,施剑翘不过犯了越俎代谋之罪而已!”[16]可以说,施剑翘案的结果——孙传芳命毙居士林,恰恰是当权者无法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所能获得的。当权者对孙传芳的不满与孙传芳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的暧昧态度有直接关系。施剑翘案发生前的一两年间,日本侵略者不断制造事端,妄想把中国的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为了实现这一罪恶企图,他们就加紧在华物色傀儡。在这个过程中,昔日的军阀就成为日本侵略者重点拉拢的对象。孙传芳早年留学日本,他在日本陆军市官学校的不少教官、同学,后来都成为日本军界的重量级人物,孙传芳与他们交往密切。孙传芳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就曾聘请昔日的教官冈村宁次做高等军事顾问。他退出军界、住进天津外国租界以后,仍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日军侵华集团的核心人物时有来往,舆论界不时传出他可能会出山与日本人合作的消息。虽然他本人曾以一心向佛、无心政治等理由回复舆论界的传闻,但与吴佩孚严厉斥责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鲜明态度相比,孙传芳的态度就显得暧昧多了,这也使得朝野中的许多人对他不满。施剑翘成功刺杀孙传芳,赢得了舆论的赞赏,这也是当权者所愿意看到的。在众多政要的积极努力之下,施剑翘被政府特赦,与其说是迎合了舆论,照顾了民意,还不如说是当权者“借他人之手”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侠义复仇案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在我国传统社会,它体现了礼与法的冲突与融合,交织着民众心理与统治者利益的复杂关系。到了近代,它又纠缠出西方法治与我国传统法文化、历史传统与现代转型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判决的“侠女施剑翘复仇案”为中心,纵观案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历史上发生的同类案件的影子。换言之,我国传统社会的侠义复仇案件之司法运行模式仍然影响着近代侠义复仇案件的处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它是在法治的框架和程序下进行的。民众、媒体、政府对司法运作的影响在这个案件中发挥到极致。如何能夠发挥这些力量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对当今的法治中国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霍存福.复仇·报复刑·报应说——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文化解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蔡惠明.施剑翘其人其事[J].法音.1988(10):36.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G].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6]任伟.施剑翘案:“罪行”与“义举”[J].看历史.2011(5):6669.
[7]周利成,王向峰.旧天津的大案[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史料一组:国民政府指令[J].民国档案,2008(2):824.
[9]芜湖农职校师生.芜湖农职校师生请特赦施剑翘[J].妇女月报.1936(3):42.
[10]王晓华.孙传芳案与施剑翘被特赦真相[J].中外书摘.2012(10):8385.
[11]施羽尧,沈渝丽.女杰施剑翘[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12]朴.施剑翘刺孙复仇[J].女子月刊.1936(1):5.
[13]庄子华.寄给为父报仇的施剑翘女士——从为父报仇说到为国雪耻[J].读书青年.1936(9):2731.
[14]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M].陈湘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5]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M].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6]黄佩瑜.评施剑翘代父报仇事[J].新女性.1935(34):15.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