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腔”和配乐
——略谈诵读和音乐的关系
2017-05-17杨军图片网络
本刊记者_杨军 图片_网络
“朗诵腔”和配乐
——略谈诵读和音乐的关系
本刊记者_杨军 图片_网络

网络栏目“为你读诗”2016夏季诗歌音乐会现场。图为朗诵艺术家李立宏朗诵诗歌《和弦》
说到诗歌诵读,“朗诵腔”和诵读配乐是必然绕不开的话题。尽管这两种形式近年来遭到越来越多批评,但在实际教学中仍是标配。因此,到底为何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还必须回到语言文字与音乐的关系上。可以明确的一条主线是,传统关于这种关系的探讨主要存在于历代韵书制定,所谓“雅言”系统。韵书的主要目的即用于诗歌和韵文等创作,旁及经典诵读。而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一是源于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写作代替文言写作成为主流,二是翻译和欧化汉语的影响。这二者实际打破了传统以来以文言为主的诗词格律系统,破坏了原本汉语音韵和音乐的平衡关系,因此,重建语言和音乐的关系,就成为现代诗诵读和写作撇不开的话题。
从本质上说,诵读的腔调指向语言内部的音乐性(即韵律),而配乐则类似歌曲的旋律和伴奏,属于语言音乐化的一面,尽管诵读时并不唱。
(注意,为简便,本文一般将“朗读”和“朗诵”合称诵读,有时混用或称“阅读”,即指以日常说话调读书或背书,古文曰“讽诵”即是。以与古诗词的“吟诵”“吟咏”“吟唱”和一般意义的“歌唱”区分。)

抗战时期的朗诵诗是面向群众做宣传的,图为“狂飚诗人”柯仲平
为何“朗诵腔”遭人反感
首先,现在我们一般说的“朗诵腔”是指那种常见于舞台表演,表情手势夸张、语调高度形式化的诗歌诵读。事实上,这种“朗诵腔”的争论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早在上世纪白话文运动开始,白话诗诵读的问题就被提出了。抗日战争后,作家朱自清就曾为当时的争论连续写了三篇文章。
在《论诵读》中,他就将白话诗朗诵的实践分为战前和抗战两个时期。在战前,朗诵是“要试验白话诗是否也有音乐性,是否也可以悦耳,用那一种音节更听得入耳些”,目的是为“白话诗建立新的格调,证明它的确可以替代旧诗”。但抗战开始后,朗诵的目的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为抗日救亡做政治宣传。他指出,“这种朗诵,边诵边表情,边动作”,本质是将诗歌“戏剧化”。但并不是所有诗歌都适合朗诵,故而就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朗诵诗”的特殊体裁。
虽然朱自清一再强调,必须考虑朗诵诗的特殊地位和功能,避免将其扩大化,然而,他可能没想到,正是这种朗诵诗形成的腔调经过建国后的不断发展,确立了“朗诵腔”在教育教学上的独占地位。
在另一篇文章中,朱自清就直接指出,朗诵诗的本质是宣传,是类似戏剧的对话,“直接诉诸紧张的、集中的听众”,因而是“群众的诗、集体的诗”。“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它表达这些情感,不是在平静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强调那现场。”“朗诵诗要求严肃,严肃与工作。”并预言,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加强,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论朗诵诗》)
这当然是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需要的。但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这种激烈的宣传和运动退出舞台,人们开始习惯日常的说话调(尤其是电影电视相声小品等艺术的台词也逐渐趋向说话调),就自然不再习惯特殊的“朗诵腔”。
换言之,朗诵腔对于不适合那种朗诵方式的诗歌,就完全是一种外在的、人为做作的情感,不仅无法融入,反而破坏了诗歌原有的情感表达,自然无法触动观众,甚至招来反感。
明了这种关系后,我们就有必要回到朱自清,重新讨论现代诗朗诵的腔调问题。诚如朱自清指出,这并非否定朗诵诗和“朗诵腔”的独立地位,而是对其它诗歌,尤其是“朦胧诗”之后的新诗及翻译诗,应该发现它自己的腔调。
现代诗的音乐性
新诗又被称为“自由诗”。所谓“自由”,自然是受白话和翻译文学双重影响,但人们通常会有一些误解,以为“自由”的诗即是完全不用格律、不关心压韵、平仄的诗。甚至还有认为,自由诗就是把一句话拆开来分节写(如“梨花体”之争)。但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即使按胡适的说法,自由诗的初衷也是“打破七言五言的诗体,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谈新诗》)“不拘”并不是不要、不管。这就是朱自清所言抗战之前关于白话诗音乐性的实践。尽管这种探索直到“朦胧诗”之后才趋于成熟,形成白话诗自身的审美。

1966年,金斯堡在华盛顿广场公园集会上读自己的作品

狄兰 · 托马斯坐在BBC麦克风前读诗
在本期选题中,我们已在其它文章谈到了现代诗阅读的意义及译诗问题。确切地说,白话诗到底怎么读仍然是争议很大的。如宗争写到的年代,青年们为了新诗是否可“诵读”还会干一架。但语言写出来,自然是可读的。
只是读的方式自然不是“朗诵腔”,也不是任何形式化的“腔调”。新诗阅读的腔调来自诗歌语言内部的音乐性。
首先要说,新诗虽然在形式上打破了旧诗格律,但实际只是打破了那种词句整齐、平仄对仗的格律(这一点从诗词曲的演变本身也是格律的突破),而并不是打破了汉语内部的音韵(音乐性),换言之,正如开头说,只是使之失去平衡。
比如,争议最大的压韵问题。格律诗之压韵,就其外部,是寻求音乐化(谱曲吟唱),而就其内部,是因为词句整齐,压韵是一种协调,以使内容和音韵达到“整体性”(类似太极);但对新诗,因为词句完全不求整齐和平仄对仗(工整),也就不可能强行压韵,尤其是尾韵。
然而,新诗仍然是有“压韵”的,它建立了新的平衡(为区分严格意义的“压韵”,以下称为“协韵”)。这种韵在词句内部的音韵上。如柏桦《在破山寺禅院》第一节:
“我们是否真的生活过?”
他在破山寺禅院内独步、想着……
一阵凉风吹来,这轻于晨星下的风
令他不寒而栗,他默念出一句长调:
寿命尚如风前之灯烛,
匆匆春已归去
听杜鹃声过,鱼儿落泪,
我的俊友,已向那白鹤借来了羽毛。

古代韵书的制定与写诗读诗有关。图为广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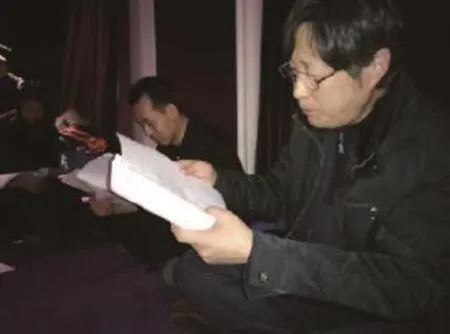
读诗会和一般舞台表演的读诗不同,都是清读
在词句内部,“生活过”“想着”“杜鹃声过”“白鹤”“凉风”“晨星下的风”“寿命尚如风”即存在自然的协韵(注意,这和一般外语格律诗所谓行内压韵不同)。又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全诗并无整齐压韵。但在核心意象上,“大雁塔”和“爬”,“上去”“下来”“英雄”的重复都是构成协韵的。但这种协韵显然不是由格式化或格律完成的,而是通过意象和意义的连接。作者写作时大多是无意识的。与其说是协韵,不如说是汉语自身韵律的显现。
更进一步,我们会在一切汉语散文中也发现这一点。这本质上是汉语音韵本身造成的,而协韵只是诗歌韵律的一部分。其它如汉语四声的阴阳平仄、双声叠韵、韵的旁转对转关系等,都是韵律形成的重要条件。
举个反例,如《诗经》,因为汉语音韵的变化,它的很多尾韵早已不压韵了,平仄也不平仄了,但是,即使不协韵和变调,我们仍可体会其词句内部的韵律之美。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诗句内部的双声叠韵、韵的对转旁转现象非常多,大于简单的行尾压韵。双声叠韵,语义原出自反切,被切字与反切上字为双声,与下字为叠韵,汉语双音节词(包括连绵词和合成词)大量存在双声叠韵现象,如《关雎》中“关关”“窈窕”“参差”“辗转”乃至“左右”。阴阳对转,即鼻音韵尾和元音韵尾相配互转,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等,现在看起来完全不压韵,但因为即使按普通话也是同属阴声韵,实际读起来并没那么大冲突,只是简单的元音音位高低。对转旁转现象在清代音韵学研究中非常详细,兹不赘述。我们由此再看《在破山寺禅院》和《有关大雁塔》,可见没有格律诗的压韵并不是要紧的事,汉语的阴阳韵之间本来可以相配互转的。
所以,对新诗的审美,有人就常说,新诗的语感语调最重要。所谓语感语调,即是作者在生活中使用语言形成的感觉(或通感)。有些词语或意象的关系,作者可能在生活中反复琢磨、体会过,才会在事物涌入的某一瞬间,将那些感觉连成诗句。
事实上,无论是古人写格律诗,还是现代人写自由诗,这些都是一样的。再以《在破山寺禅院》为例,其第二节就直接引用了白居易的“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新诗中杂入格律诗句,分析韵律,并无违和感。柏桦诗好引用古诗,多有此种情况。有人将此看作“化欧化古”的新诗发展隐喻,是不无道理的。
可见,意象、意义和韵律不是强行连接的,诗歌是意义寻求形式,而非形式寻求意义。此即杜甫所谓“下笔如有神”。否则,也只是如现在流行的计算机写诗软件,根据程序,寻词摘句即可,可和生命、生活毫无关系。
如何读现代诗?
近人胡兰成在谈到自己对新诗态度转变时曾说:“新体诗当然可以有前途,但那新体必要是中国的,不可像西式女装的斗新鲜设计。”(《中国文学史话》,下引同)
对新诗造形,他还提出了三个原则:一、诗的形式必是简单的;二、诗的音乐性在汉字的音韵阴阳;三、诗有调,但不是旋律。这里第二第三条都是讲白话诗的音乐性。在“朦胧诗”之后的新诗写作中,早已得到证实。
由此,他也就区分了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只用眼睛看的诗”的说法。他强调诗的音乐性正是礼乐之“乐”,而非单纯流行歌曲的“乐”。(参考《礼记·乐记》)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学校诗歌教学中的“读诗”和近期新媒体平台兴起的不少“读诗”节目就可看出一些问题。
很多人读诗喜欢配乐,这似乎是“诗可以歌”的潜意识证明(尽管是读不是唱),但效果并不如人意。因为一般人通常不会作曲,他们选择音乐时只会根据感觉大概去选择“舒缓”或“强烈”的音乐;考虑要读,一般都是轻音乐,否则音乐就盖过了语音。但是,由于被选择的音乐本身表达的情感就和诗歌有差距,事实上必然会喧宾夺主,而不存在所谓烘托效果。这种配乐本质上和“朗诵腔”是一样的,是外在的情感,很难跟诗歌本身的表达融合。
在这里,我们并非完全反对配乐,因为,只要音乐和诗歌情感内在一致,那种烘托是会很好的。如前几年上映的电影《星际穿越》,其中引用狄兰·托马斯的《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不要走进那良夜),配合电影配乐和画面是传神的。再如现代民谣,其中很多歌词即是诗或诗性的。如周云蓬的《九月》,改编自海子同名诗歌。又如擅长作词的腰乐队、五条人乐队等。去年诺贝尔奖颁给鲍勃·迪伦,就称其为“伟大的诗人”,并认为他“在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尽管后者拒绝领奖,但这个说法是公认的。诗和歌的根本差别其实并不如“诗歌音乐分离论者”所说那么大,本质上只有意境的差别。
一般来说,如果认同“诗言志”“言为心声”,我们就知道,诗歌不唱只读的话,它的清读效果是最好的。只有清读最能体现语言本身的音韵魅力和意义。这一点,实则古今中外皆同。如在《左传》中,就有当时贵族在外交场合赋诗的记载。赋,就是“不歌而诵”(《汉书·艺文志》),是“恻隐古诗之义”(《艺文类聚》),即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的意思。《周礼》:“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可见赋诗、讽诵是古人常用的,关注意义,和歌唱的音乐化不同,更不用说配乐。
在《中国文学史话》中,胡兰成就说:旧体诗有不属乐府的诗,不配乐,“单是吟吟的诗或倒是乐府诗的基本”。但他转而又说“新诗朗诵像话剧的动作与说话表情都太多”“朗诵注重旋律,夸示感情与意义,那是西洋诗的读法”,则受当时流行的“朗诵腔”影响,有所误解。
诚然,西方语言由于是字母文字,读法自然和汉语有别(如轻、重音形成音步和汉语单音节声调形成平仄不同),但不是根本的。这一点,网上可找到很多西方现代诗人读自己的诗,听一听就可知道。一般来说,句式整齐、压韵严格的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旋律性更强,因为它们本身是要和音乐化配合的。而句式自由、不拘格律的诗旋律性就较弱,以说话调诵读,反而能凸显词句内部的音乐性。(此可对比狄兰·托马斯和艾伦·金斯堡读诗的差别,狄兰诗压韵多,金斯堡几乎不压韵。此外,喜马拉雅网站也可找到国内很多诗人读自己的诗。)
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通常,诗人读自己的诗效果是最好的。用方言读又比标准的普通话更有味道(此可参考2016年上映的电影《路边野餐》)。这里并不是说诗人和方言剥夺了诗歌诵读的权利,而是说,这样更好地体现了语言本身的韵律,因为毕竟大部分人日常生活都说一种“方言”。事实上,诗歌大多是用标准语写成的,即使方言诵读,也要替换相关词语的方言音或词才有效果。

民国《琴学管见》记载的《关山月》琴谱
诵读和乐教
最后,还必须提及一点,现在很多人诵读古诗或韵文(包括经典)时也要配乐,这是非常尴尬的。且不说很多配乐不伦不类。正如我们说现代诗诵读配乐和真正的歌唱配乐不同,实则古代诗词歌唱的配乐也是如此,要需要考量诗词韵律本身传达的情感而加以音乐化,并不是简单的附会。真正用于古诗词歌唱的乐谱现在大多已失传了。可参考李白《关山月》的歌唱,是有古谱传下的。
古诗词的歌唱、吟诵和讽诵都有,而吟诵和诵读是主要的。关于吟诵,目前国内也已有不少讨论和实验,讨论私塾吟诵调的传承等,因不是本文主旨,不再讨论。事实上,由于语言音韵本身的作用及变化(如入声等韵尾和复声母消失),吟诵和朗诵效果并不是如有些人想象的差别那么大。盖私塾调本身也是受“佛教徒‘转读’经文的影响”,不尽是汉语音韵的问题(《论诵读》)。
胡兰成说,“吟诗随各人,没有一定规则,但自然有调,因为一首诗的平仄与韵都已排好,你只照着长短缓急高低虚实来念,加以你自己的节拍发出抑扬顿挫来就好了。”是这个意思。日本人学习中国诗词,也有日语音韵产生的“诗吟”。
以下讨论诗歌音韵和意义的关系。朱自清在《论诵读》中说,吟和唱是音乐化,是“将意义埋起来或滑过去”,而诵读是音乐性,关注意义。“现在我们关注意义,就不要音乐化”,“就是文言,也还该以说话调的诵读为主。”就阅读关注意义的层面,他是对的。前面已说,即使古代贵族在外交场合也是赋诗,不歌不唱。赋是“恻隐古诗之义”的。
但是,我们既然谈到古代韵书制定和新诗音乐性,其实就是说音乐性,也不仅是关注意义的。不论是乐府诗的吟唱,还是带点唱的吟诵,还是朗诵、朗读,都是在讲音韵的作用。这一点,明代王阳明在《训蒙大意》说得极清楚:“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发其志意”是关注意义,而语言的韵律则可“泄其跳号呼啸”“宣其幽抑结滞”。这就和现代人解闷去唱卡拉OK是一个道理,不是去理解歌词的。
那么,王阳明说“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是何道理呢?这还得从古代乐教传统说起。即胡兰成所谓“礼乐之乐”,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乐”,而非今天单纯的“音乐教育”。众所周知,上古诗乐舞不分。言“乐”通常也就包涵了诗(言)和舞。盖诗乐舞本起于酬神,带有天人沟通的巫术含义。
“成于乐”,乐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而其起处,在“兴于诗”。“兴于诗”又讲究“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历代韵书保守“雅言”系统的意义。古代经典诵读把这一阶段叫“小学”。(《汉书·艺文志》)
经典诵读必先正音、正形、正义(因而有音韵、文字、训诂)。所谓“雅言”,即正言,不是指说普通话。因为诗书执礼之语言都和祭祀宴饮有关,要求言语中正平和。如孔子师徒日常之“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子之所慎:齐、战、疾”,辩论、祭祀、军事、生病时的言语自不同;又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正言,就是正各个场合说话的礼,于音义皆有关系。《周礼》谓之“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
单论诗经,《论语》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外交场合,言语慎重,今人所谓“外交辞令”,而春秋外交独赋诗。这其中道理,就和诗经的音韵体系相关。我们知道,在古汉语音韵中,平声一调,仄声三调,但平声字和仄声字在数量上却差不多,这在诗经和后代诗词中都很明显。盖平仄交替不仅体现韵律之美,本身即表现“中和”之气,故孔子谓诗三百思无邪、恶郑声。《乐记》曰“声音与政通、乐者通伦理”。此外,五行学说以土为中,古人便将五行与五音(喉齿牙舌唇)、五声(宫商角徵羽)对应。音乐上调首宫音、宫音为君、宫音主思,音韵上喉音为中。现代语言学研究也证实上古汉语有丰富的复声母和韵尾,其中多喉音(包括影晓匣三母)前加音、后加音。《乐记》所谓“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而“郑卫之音,则比于慢矣,乱世之音也”。
汉语音形义一体,不仅形义相关,而更首要是音义相关。其最大特点即同音字丰富,同音近音相假义。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礼,体也,履也”“老,考也”“孝,好也,享也,子承老也”“悌,弟也”等等。包含经传、字书等各类典籍中的同音相假、同音比义、双声叠韵、对转旁转现象本身就成了语言学者重建上古音的重要手段。正如清人王念孙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可以说,不通音韵,几乎无法理解古人利用同音现象构拟的“声音与政通”的伦理世界。
这一点,实际在西方“乐教”中也是类似的。学者研究认为,古希腊所谓“音乐教育”“谬斯的艺术”是诗乐舞一体的,诗乐在“文词”和“调式”上都讲究“中正无偏”。可参考王柯平《论古希腊诗与乐的融合》,此不赘述。
可见,诵读还是包含乐教之义的。至于今天,我们具体如何操作,还是一件需要继续讨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