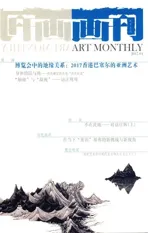在当下“重识”基弗的新挑战与新视角
2017-05-17王鹏杰
王鹏杰
当代批评
在当下“重识”基弗的新挑战与新视角
王鹏杰

《狭窄的船舶》 安塞姆・基弗 2002年 © Anselm Kiefer
基弗(Anselm Kiefer)自上世纪80年代被中国艺术界熟知后,近几十年来成了很多艺术家尊崇的偶像,其作品的风格与图式还被很多艺术家直接拿来“引用”,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实际发展历程。中国艺术界对基弗的了解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他的“形象”从架上绘画的捍卫者、传承德国文脉的文化英雄逐渐演变为日趋立体化的实践个体。尽管“基弗热”在国内从未降温,但今天对基弗艺术实践的理解却似乎更加困难,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伴随着社会整体转型的急剧变化,使我们与基弗的艺术世界进一步拉开了距离;此外,互联网科技和图像阅读经验极大改变了我们观看和理解艺术的方式,也使得像基弗这样充满复杂性的艺术家更容易被符号化、景观化地看待。出于偶然的契机,我决定重新认识这位“老”艺术家,于是做了一些案头工作。在这一重读基弗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一种熟悉的陌生之感,之前虽然对其作品面貌已比较熟悉,但将他的创作实践当作完整个案来思考时才发现里面涉及的问题异常庞杂,牵动了很多原来不常涉及的知识系统,这进一步让我认识到重新理解基弗的困难与必要性。限于篇幅,本文只谈我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
1.基弗艺术思想中的神秘主义问题。基弗的宗教观念带有非正统性和反叛性的特点,比如他对莉莉丝(Lilith)形象的喜爱,和对犹太教异端教派代表人物以撒・卢里亚(Isaac Luria)宗教理论的热衷,他花了20多年研究卢里亚的神秘主义理论——卡巴拉(Kabbalah)神秘主义。从这种晦涩而带有强烈启示性的神学理论中,基弗生发出创作的动力和信念。他有一件重要作品,叫《容器的破碎》(Breaking of theVessels),是1990年的装置,这一时期正是他调整自身创作方向的转折期,是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尚热衷于拷问现实转向90年代诗性表达的当口。从这件作品的“容器”概念出发,我查找到它的一个思想来源,就是以撒・卢里亚神秘主义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容器”,在撒・卢里亚对《光辉之书》(Sefer ha Zohar)的解释当中被重点讨论过。他把“神圣真实”分为十层,“神圣真实”只有隐藏在“容器”中,这十层才会按部就班地各就其位。其中的六层是不稳定的,会游移和运动,这会带来“容器”的破碎,由此神圣之光开始四散,世界进入混沌状态,事物不再处于应在的位置,神圣的火花从稳定框架中流放出来,来到无形的荒地。这一理论化描述与基弗很多作品所呈现的精神质感和艺术面貌十分吻合。就《容器的破碎》而言,基弗直面生命和文化的毁灭与死亡,他将这一悲剧看作新世界诞生的起点,甚至在审美情感上对崩坏与消亡充满迷恋之情。卡巴拉学派里还有一个“回归”的概念,也给予基弗不少启发,“回归”不意味着上帝(万能之神)集中于某一点,而是表明上帝会后退出这一点。这种后退对于人类和世界来说是积极的,正因为上帝的“隐退”和“回归”,才为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流出了存在的空间,这是一个“空的空间”。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正是因为死亡有了它的承担者,未来的再生者才有了必要的空间,肯定了死亡其实也肯定了存在的意义。这样的精神取向也和基弗作品中的美学气质相符合,从这里面我发觉以撒・卢里亚的神秘主义几乎笼罩在基弗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所有作品中,这种影响使他的作品都带有迷幻而混沌的叙事性。极强的混沌性使作品的表达无法具体化和观念化,若我们整体回顾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主线就会发现,具体性的观念表述是大部分艺术家采用的主流策略,这样的方法可以为作品迅速概念化、问题化并被有效传播、接受提供方便。但基弗却不喜欢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他的创作是一种反具体化的状态,对当代艺术越来越具体化的态势形成了挑战,也挑战了现代以来强大的进化论意志以及知识体系不断细化、专门化的整体潮流。这是一种具有激情和张力的实践,我们无法洞见这种对抗的结果,但似乎结果的成败对基弗而言也不打紧,在他看来,似乎这种张力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他面对强大艺术史的这种反驳式实践,其实是为另一种更加神秘、具有超越性的艺术创作保留空间。
2.视觉性的损耗与系谱化的阅读。今天再看基弗的作品,不能再以视觉体验作为审美判断的依据。比如大部分中国艺术家在上世纪80、90年代看他的作品会觉得很震撼,到了2000年以后就已经对这些作品的形制与效果习以为常了,这种审美心理就像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所说的“语言自动化”现象。由于“语言”在表达中的不断重复,读者在阅读中逐渐丧失了感受的新鲜感,而认知与体验逐渐被持续的惯性所替代。由于基弗的作品在近几十年的艺术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因而会有很多机会被我们接触到。今天再用视觉化的角度观看这些作品常常会使我们的感官变得更加迟钝,作品中包含的丰富内容会被观看的惰性所遮蔽,越是视觉化地观看,越是对其作品核心意义形成损耗。因此今天再看基弗,我们应该采用一种反视觉化的方式。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知识谱系、问题范畴极为繁杂庞大,神学、哲学、政治、社会、历史、文学、美学等学科皆与之关系密切,这样的艺术家对今天阅读他的人提出了很高的知性要求,据此也可引申出另一个问题:艺术史上出现的大量重要个案不啻是一个个沉重的包袱,整体性地考察艺术家的时间成本越来越高,面对那么多艺术家,对哪些进行知识化、系谱化的阅读,我们需要进行甄别和选择。这可能是今天的艺术受众面对艺术时必须要处理的严峻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基弗是一个明显反对机械理性和科学主义至上的人,也是一位反对用知识化方式阅读艺术作品的艺术家,他以精神性为归旨。但正是因其作品影响力太大、流传太广,今天的观众已经对他作品的大部分视觉表征免疫了,如果想重新激活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深入到其精神内部世界中,我们就必须用一种知识化、系谱化的方式去展开更加复杂的阅读实践,但这正好与艺术家的初衷相背离。

《玛格丽特》 安塞姆・基弗 1981年 © Anselm Kiefer
3.基弗对纳粹的复杂态度。从他的大部分作品来看,基弗对纳粹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对纳粹的滔天罪行持明确的批判态度,但另一方面其内心深处可能对纳粹仍怀有某种怀念性的深刻情感。这种暧昧的复杂性,似乎可以与海德格尔进行类比,如果我们将视野进一步放大,似乎许多经历过二战的德国文化人和艺术家都对纳粹的精神遗产保持审慎的惋惜态度。他毕竟是德国人,与上一代人的情感、价值观的割裂不可能是决然的。他在访谈中也谈道:他并不只是想用历史化的图像去揭露什么,也绝不想去扮演“罪行考古者”的角色,他希望以更加复杂的视角去呈现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其实他对德国往昔罪恶一面的批评是有所保留的,或者说他持有与人道主义普遍观念相异的认识,这也说明艺术家个体思想情感的真实性与道德律令的普遍性之间的明显差异。现代艺术本身就以伦理与审美的分离为标志,由于艺术显然的自律性,很多艺术家并不认为“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有时他们甚至有意对世俗世界的“普世价值”进行艺术化的反诘,对于基弗在纳粹问题上的态度,我们也应该保持开放性的理解。
4.基弗跟新表现主义群体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新表现主义开始在欧美流行,其代表人物吕佩尔茨(Markus Lupertz)、彭克(A.R.Penck)、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伊门多夫(Jörg Immendorff) 等人,包括基弗,在图像和叙事方面都有针对历史、政治、社会问题的明确表达。有趣的是:大约自80年代后期(这些艺术家的艺术史地位已经基本得到确立之后),他们的态度和立场就出现了分化,比如吕佩尔茨在后来的多次访谈中就反复这样表述——他的艺术创作不涉及政治、历史、社会等其他艺术以外的问题。他不再承认当时新表现主义之所以获得成功,其重要的历史原因(至少是部分的)在于他们站在欧洲艺术的立场面对美国新艺术潮流(如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的压抑进行有目的的反动,也不承认他的艺术思考跟德国战后社会现实、历史遗产等问题的刺激有关。在他的自我描述中,这位艺术家似乎从未将社会现实信息注入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他一直在一种很纯粹的艺术状态里从事着很纯洁的伟大艺术,并且还透露出这样的意思:他其实只是一个致力于艺术本体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天才画家,因为他画得太完美太出色,所以他在当代艺术史上才如此重要。与吕佩尔茨的这种对自身艺术历程进行“重塑”情况类似的还有巴塞利茨等人,只不过他们并没有吕氏表达得那样露骨。
但基弗却与吕佩尔茨、巴塞利茨等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走向艺术本体内部的方向截然不同,他更加坚决地走向装置以及多种媒体的创作实践。我们今天无法再用新表现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定义和理解他,否则将是对他完整意义的阉割。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他在走向多媒介、开放式艺术创作状态的同时,绘画性在他的各类作品中仍顽强地残留着,绘画的感性已嵌入他的身体。通过阅读他的相关文献,我发现对基弗自己而言,绘画性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他并不是刻意非要画画,只是觉得画画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就画了,没有把介质的前卫与否当成一个问题,在这点上,他的认识与大部分中国艺术家很不同。
中国的画家处于多重历史文化的交错挤压之下,对绘画这一古老媒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焦虑是群体性的,他们总是很关心架上艺术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以及架上相较于其他新媒介的本位价值。相反,基弗不仅对绘画的媒介正当性不甚在意,他对其他媒材也一视同仁,对材料问题的悬置,说明其创作形态的推进(比如从绘画进入装置、戏剧等媒介)从来不是为了材料、方法的更新,新的媒材与手法对他来说没有任何艺术价值观层面上的优先性,他对媒介和方法的选择只是出于表达的需要而已。在艺术方法论上,他显然是一个反进化和反进步主义者,这种“停顿”状态也违背现代主义以来线性的、进步论的、不断前卫化的主流演进逻辑,因而其中蕴含的挑战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5.对于“乌托邦”精神的期待与重建。综观基弗的艺术实践生涯,他在用尽可能多的努力去构建一种十分崇高、庞大的具有超越性的乌托邦体系。它不完全是宗教、历史、政治的,它不是任何一种单向度的形态,我只不过暂时用“乌托邦”这个词来指代它,因为它在宏观上确实具有这样的精神特质。此处“乌托邦”必然与某种意义上的宏大叙事紧密相关,基弗开启了一种在今天语境里重新认识宏大叙事的思路。他并未简单否定宏大叙事的崇高价值,反而在提醒我们对于它的否定和排斥是否过于武断?我们在警惕宏大叙事的同时,是否可以再思考一下它在艺术表述方面的可能性?当代艺术文化是否还应该为这种宏大、整体化的创作形态留下出口?如果没有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精神领域存在,那我们在进行判断和实践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陷入虚无化的困境。基弗也很清楚,他在确立这种乌托邦系统(或者说这种宏大的整体性)的同时,也十分警惕与之相关的、可能随之到来的话语暴力,避免重新走向历史中诸多罪恶“乌托邦”(例如极权主义)的老路。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用一种既开放又有针对性的方式进行了回应,通过反思历史结构中的“恶”和高扬具有精神超越性的文学和神学力量,对新的“精神独裁”进行制衡。但他的回应毕竟是在战后的历史时空中做出的,未必在今天的语境中还有切实的参考性。那今天我们又如何来处理这一重矛盾关系?这是我(既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同时又是一个理论研究者)在当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许这个问题在未来会变得更为紧迫。
从以上这五个方面的论述中,能够看到在当下情境中重识基弗的新挑战和新困境,从中衍生出来的新问题和新视角不仅关涉对基弗个体艺术实践的认识,更与当代艺术理论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紧密相关。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追究和讨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自我检视的机会,这才是重新理解基弗及其艺术创作的价值所在。
2017年4月5日

左・《夜的秩序》 安塞姆・基弗 1996年 © Anselm Kiefer

右・《容器的破碎》 安塞姆・基弗 1990年 © Anselm Kie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