寳島先行:低薪籠罩下,勞、資、政大鬥法
2017-05-14邱駿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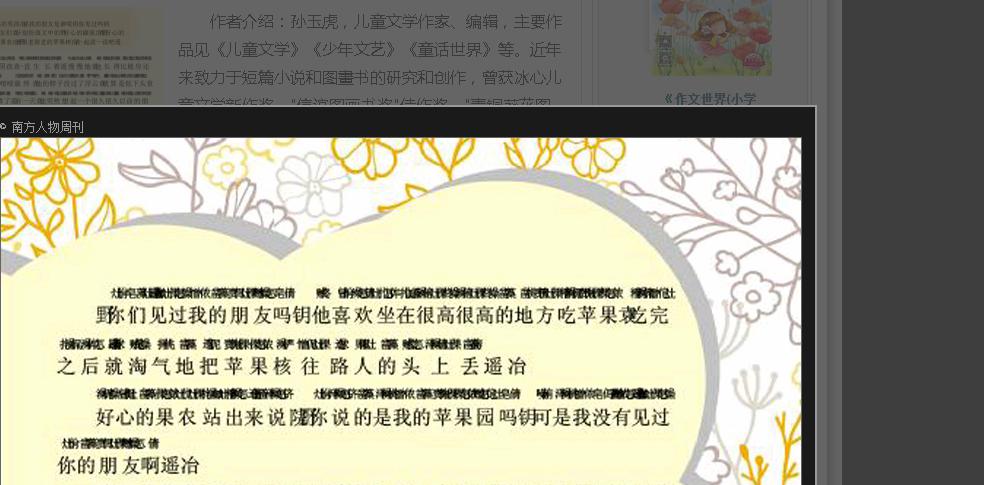

政治變革,勞權突破
台灣的勞動環境處在一個變化的過程中,特別是自1960年代經1970年代至1980年代,這20年之間是台灣經濟發展快速起飛的時期,1985年後期受到兩次能源危機、臺幣大幅升值等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腳步開始緩慢下來。在這段時期,雖然台灣政治上處於戒嚴時期,勞工運動的力量被壓制到幾乎為零的狀況,但人民的一般生活水平也隨著經濟發展,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攀升。這一時期台灣人民在政治力量的長期壓制下,除了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人不懂也不敢去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那時的勞動環境是特定的安排,勞工很少去主動維護自身的權益,勞資雙方力量是極度失衡的。
而1987年台灣解嚴後,民主意識開始蓬勃發展,勞工組織也開始活躍起來,但勞工團結的能量終究需要時間的累積與醞釀,沒有辦法瞬間成長與爆發。雖然解嚴後勞工團結組織有了比較自由活動的空間,但政府長期以來對於勞工團結組織一直抱持著愛護又怕受傷害的態度,加上自1984 年《勞動基準法》開始施行以來,台灣政府就一直有個去不掉的觀念枷鎖,那就是用“勞資雙方大家依照勞基法來,穩定和諧勞資關係,努力發展經濟”的想法在形塑台灣的勞資關係。因此在解嚴以後到現在,勞工團結組織的力量雖然有逐漸成長的趨勢,但是還不到能夠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擬的地步。
再者,因為這些年台灣政經發展情勢的變化,在面臨2000年以後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勞工團結組織未能即時扮演維護勞工權益的角色。在金融海嘯期間,政府也疏忽了對勞工薪資水平的掌控,導致近20年來台灣勞工的工資額度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到15年前的水準。2000年前後成為台灣勞動環境的一個大的分水嶺,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當時的政府出現了一個很大“敗筆”的政策,政府為了鼓勵企業廣泛聘用員工,提出特殊時期補貼2萬2新台幣的基礎標準,因為相關規定未有強制性,結果大量的企業認為政府提出最低薪資2萬2的標準,不少企業開始給新僱員特別是年輕人22K,瞬間台灣的一般薪資從2萬8千新台幣變成2萬2千新台幣的基準,自此22K的陰影一直揮之不去。再加上勞工退休金條例中對於個人給付標準的規定,客觀上在2000年以後加重了勞工、企業的雙重負擔,當企業成本增加則變相影響加薪,逐漸造成了“低薪”困境。同時,因為在全民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國家政策主導下,長工時現象一直無法得到有效改善,甚至在2016年OECD的統計中,台灣工時總數在全世界長工時的評比中位居第五名。在如此長工時、低薪資的狀況下,零職災的勞動政策也就很難輕易落實了,造成台灣許多人對於勞動條件和勞工環境有了血汗企業、血汗勞工的印象,這確實是台灣當前無奈的困境。
工會弱勢,勞資失衡
在勞工面對著低薪資、長工時等困局下,自然會想到屬於工人自己的維權組織:工會。而台灣的工會組織也確實是扮演著勞工維權的重要途徑之一。但在現實層面來看,台灣的工會組織在嚴格的法制規範下,其實並沒有實現真正的組織自由化。
在台灣,工會依法只能組成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這三種。雖然全部的工會數量高達5400餘家,但絕大多數都屬於職業工會,共有4000多家,產業工會150餘家,企業工會更不到1000家。工會整體組織率雖然高達34%左右,但過去以來,會員勞工覆蓋率最高的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比較少能夠發揮真正的勞工維權功能。當然,最近勞工團結意識逐漸覺醒,若干職業工會(像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例如高等教育教師產業工會)等有了比較蓬勃的活動力,其工會活動也顯著有了影響社會輿論的功能。但總體來講,原本應該比較容易凝結團結力量的企業工會,其組織力、團結力、活動力相對來講,反而比較弱勢。
這最主要的原因乃在於全台133萬家企業中,絕大多數接近97%屬於中小企業,而工會法規定籌組工會必須至少30人以上,因此絕大多數企業並沒有企業工會的存在,比較有活動力的企業工會反而是國營事業單位。相對於港澳7人可以籌組工會,大陸25人可以組建工會,日本10人組工會,韓國只需要2人就可以成立工會而言,台灣的工會組織條件太過嚴苛,顯現出政府從內心并不願意看到企業工會的發展,因此現有的企業工會的功能與效果,充其量只局限於自己的企業內部。所以我們期待台灣能有更具有自發性、有力量的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發展起來。特別是通過2016年的空服員罷工事件,整體社會開始認識到罷工其實並非什麼洪水猛獸,它可以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到工人維權的必要性與社會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從“太陽花學運”以來,我們看到台灣年輕人對於體制、現狀的不滿與衝撞,新一代越來越不受政府的高壓控制,展現出的自主性在不斷增強,因此未來出現更多數量的企業工會、職業工會等都是有可能的。
當然,除了工會的維權外,工人最基本的依靠就是現實的勞動法律。在台灣的勞動法制中,對於勞資爭議處理可以說是規範比較完善、運作比較正常的一個領域。勞資爭議當事人除了可以上法院訴訟外, 絕大多數都會先透過勞資爭議處理機制來尋求解決。包括調解、仲裁、裁決等機制,大概能解決掉所有勞資爭議的近70%左右。特別是第一線的調解機制,在消弭勞資糾紛上扮演了重要的功能。至於集體的勞資爭議,特別是有關於不當勞動行為的爭議,在勞動部底下設有裁決委員會專門處理,近年來被利用的頻率很高,功能比較顯著。
另外,企業內有關勞動條件提昇的勞資爭議,有工會的企業當然會由該工會出面與僱主進行團體協商,台灣也有幾家比較有力量的企業工會代表會員勞工與僱主展開周旋談判的成功案例,例如:大同公司、各個銀行員工會、中華電信、中鋼、新海瓦斯等等。
即使在現行的框架內,解決爭議的機制和途徑都不少,但是台灣的勞資關係仍舊緊張,特別是每每只要有新的法案預備出台或新的勞動政策需要開展時,就是台灣勞、資、政三方亂鬥的時候。
回顧歷史,台灣勞資關係正常發展,可以說是1987年解嚴以後才開始,至今不過30年的時間。這30年之間又歷經幾次的能源危機、世界性經濟不景氣,以及金融風暴等因素,台灣勞資雙方互相學習如何相處的時間並不長。勞資雙方是否能正常相處,取決於雙方如何對話。勞資雙方最在乎的就是勞動條件的提升與經營成本的控管,而不管勞動條件或經營人事成本,都會跟每一個不同的企業規模、行業特性息息相關。因此勞資雙方應該本著自己企業特質來談判協商自己的勞動條件。
但台灣過去33年來,政府的政策也好、勞資雙方的認知也好,都一直認為“只要依照勞動基準法”來做就是不違法,而忽略了勞動基準法只是勞動條件的最低基準,勞資雙方都應該形成努力向上提昇優於勞動基準法的勞動條件的正確觀念。例如勞動基準法有基本工資的規定,許多企業都只是給與部分工時勞工時薪133元新臺幣的基本工資而已,甚至離開北部地區往南部看,許多企業仍未給予這樣的基本工資。再加上台灣有許多的企管顧問公司,會教僱主們如何規避法令,當然這些規避行為本身就是脫法行為,沒有被揭發出來以前,僱主會很高興地以為節省了許多的人事成本,一旦被檢舉,進行勞動檢查後,就會被罰以鉅額罰款,更大大增加了成本。這些種種現象導致勞資雙方的內在矛盾與日俱增。而勞工在多有委屈求助無門時,最後就會把怨氣出在政府身上,以選票來制裁政府。
因此,從整體上來看,台灣的勞資關係,很重要的是大家必須認知到勞動基準法只是勞動條件最低基準,必須努力向上提昇。而努力向上提昇必須借助於勞資雙方的團體協商。因此首先是工會組織率必須加強,特別是在企業工會這一塊,法規必須鬆綁組織工會的門檻。其次,政府要想辦法鼓勵勞工組織工會,與僱主盡快開始學習如何協商談判,唯有在和諧理性的談判協商中,才能推動各家企業特有的勞資關係正常化。
一例一休,匆忙上陣
而這一年來,在台灣有個很奇怪的現象,一個法案同時得罪了資方和勞方,那就是“一例一休”,外界不少評論認為“一例一休”是失敗的法律與政策。其實,我們必須理性看到勞動法律得罪勞資雙方未必就是不好,雙方都叫好的勞動法律也未必就是好的法律。
從開始討論到最後在2016年底立法通過的“一例一休”制度,其本身是為了完全週休二日而設計的制度,而週休二日是為了縮短工時絕對必要的制度。過去33年以來,勞動基準法都只規定週休一日,而台灣企業依照勞基法來做的不在少數,如果法律一下子要改為週休二日,恐怕會對企業帶來過大的衝擊,因此就採取了比較緩和的“一例一休”。
所謂“一例一休”制度就是,每七日中要有兩日的休息,一日為例假絕對不可加班,另一日為法定不用上班的休息日,但僱主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例外讓勞工加班。而為了避免僱主不會濫用休息日加班,以達到完全週休二日的效果,因此採取了高額的加班費制度。所謂高額加班費措施,採取兩種手段。一是加班費比平常日加班、國定假日加班都來得高;二是休息日加班,只要加班1個小時,僱主就必須給4小時薪水,加班至5小時,僱主要給8小時薪水,加班至第9小時,僱主要給12小時薪水。就是因為這鉅額加班費的規定造成僱主們的反彈。另外,在本次勞基法修法中,也一併將特別休假制度做了一些變革。例如繼續工作滿半年就會有3天特休,滿一年有7天,滿2年有10天等等。另外,年度內特休未休完者,僱主必須给予工資。這也是增加了僱主的成本,自然就從一開始就引起僱主的強烈反彈。
而對於勞工而言,政府在實施“一例一休”縮短工時政策時,卻同時砍了勞工7天的國定假日,以致勞工每年從原本19天國定假日,變成只剩12天。其次,來自於僱主們的反彈,開始不讓勞工加班,寧可聘請臨時工解決工源不足問題,勞工們的加班減少,工資收入自然隨之減少,也變成了對這個制度不滿的原因之一。而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其實就在於資訊揭露不足,法律內容宣導不足,導致大家的誤解很深。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勞動政策,而勞動政策在釐定時不一定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就能如數炮製,必須考量到每一個國家、社會自己的特性來適當地修改。以我個人專攻勞動法的觀點來看,“一例一休”應該是一個對台灣有用的勞動政策與法律規定。因為它能比較和緩地改進與達成目標。因此有問題不是“一例一休”本身,而是法律開始施行前,並沒有足夠時間向民眾、企業宣導、以及政府部門沒有事先將全部配套的解釋等準備到位,等於是邊做邊推出一些法令解釋的內容,而這些法律解釋內容往往仍有若干尚存疑慮之處。
特別是由於當初立法時沒有法令施行的猶豫期,因此實施迄今半年來政府都處於只是宣導、適應階段,沒有強力要求企業現實達成。而在這一段時間,政府透過種種方式在宣導法令,在我看來,勞資雙方對於“一例一休”新法令的理解增多,反對的聲音也有一點一滴在消退中的趨勢。
當然一套新的勞動政策或新的法律,開始施行二、三年後,一定要有全盤的檢討修正。在這兩、三年內,新制度的基本規定不宜貿然再有新的重大變革,否則只會導致勞資雙方再一次與政府的對立。
當然,回到勞權保護上,目前,台灣的勞動法令體系建構比較完整。惟,政策釐定與法令制定上往往受到政治力介入頗深。政黨輪替的頻繁與政治上藍綠的惡鬥,使得原本單純的勞工政策充滿著政治、選票的算計,往往朝令夕改,傷害了政策的持久性與法律的公信力。而對於廣大台灣勞工而言,往後應該更關心工會,把工會當成自己的家,看成可以保障自己權益的避風港;而工會也應該扮演好監督僱主守法以及維護勞工權益的角色。與此同時,僱主應該把勞工當成事業經營的好夥伴,而不只是幫忙僱主賺錢的工具;政府應該不偏不頗確實立於中立者角色來解決勞資糾紛,也只有如此,勞、資、政三方才可以盡快走出目前大亂鬥的困局,提升整體台灣的勞動環境和經濟環境。
邱駿彥: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台灣勞動部法規委員會委員、勞資爭議主任仲裁委員,台灣勞動法學會第二屆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