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图
2017-05-12李天斌
古人写清明,多落寞之叹。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如“一沾春雨一断肠,飘零无计觅君乡”,人生世事落在清明,似乎都是愁字当头。我今写我逝去的乡村的清明图,虽亦有生活之苦辛,更多的却是陌上花开的恬然之景,甚至一如世外之桃花源。
我村虽不如桃花源偏僻避世,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往前,却也如桃花源一般不为外界所染。一个极小的村落,山环水绕,唯中间留出一块平地,平地之上便是零星居住的人家,户数不过二三十户,人口不上两百,自我们李氏一世祖在此拓荒以来,百数年间,一村人只自于此看花开花落,经历生死,虽亦有缴粮纳税之官事,但毕竟在精神秩序上,亦只如桃花源般淳朴简单。
山不高,水亦不深,却算得上灵秀。河流亦算不上“正经”,只是从田野的某处突然就冒出那么一股,水不大,却常年不断,河身不长,只百数米,却终年流淌不息,而且水质毫无例外地都清澈可口,村人在田间耕作累了,随便俯下身子,便作牛饮状起来,一切都只是简单从容,妙韵天然。河流之上,便是田坝,亦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根本。
清明时节,雨水接连落了几天后,便有成群的鯽鱼自水底冒出来。一只只鲫鱼浮在水上,水草亦随着水波摇曳起伏,四周蛙声如清音,一切都仿佛在画里,浅墨般生动。一边忙着打新田,一边也忙着往河里放鱼篓。鱼篓一般都做得精致,葫芦一般大小,入口处平滑,且放了香料作诱饵,入口的底端,却都是锋利倒立的竹钉,鱼可以进去却无法出来。鱼篓放下之后,便不再有人管,至少三五天后,才一个个捞起来。鱼篓放在那里,也不会被旁人取走;而且单看那鱼篓的样子,就知道放鱼篓的人是谁,虽然鱼篓照例都是竹子所做,也都是同样的形状大小,可不同的人制作的鱼篓毕竟各自有异,再加上使用久了,似乎就染上了主人的某种气息,所以放在同一条河流里的不同人家的鱼篓,即使被流水冲离了原来的位置,即使所有的鱼篓混杂在了一起,等捞起来时,自然都不曾拿错过。
那时候鲫鱼特别多。跟父亲到田里帮他掏沟引水,还能看见三两尾不知怎的就跑到田里来了,于是掏沟引水这样的活干起来也不累了,虽然总被父亲催着,但还是一边答应却一边欢天喜地捞鱼,父亲似乎亦不强求,一边继续催我一边却笑意盈盈地看着我捞鱼的样子。也许在父亲看来,这实在便是我应有的童年,虽然日子总是艰难,可他亦希望我在这艰难之下总有一份欢喜。而在多年之后,除了感知父亲的一份内心之外,我还看到的是,我一边掏沟引水一边捞鱼的场景,实在算得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亲,只可惜后来随着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这样温馨可亲的场景便只能成为记忆中一个美丽的童话了。
几阵新阳春雨,阡陌之上便有无数的小朵的野花绽开了,白的鹅肠草,红的矮牵牛、黄的迎春花、紫的二月兰等等;白的蝴蝶,黑的蝴蝶,彩色的蝴蝶,也一下子在那里飞舞起来,正应了古词“陌上花开蝴蝶飞”的春明之景。不过其时我并不知这世上还有这样的诗句,我只是在看着那些花朵以及蝴蝶时,心里总觉得清爽,总觉得行走在这阡陌之上,便是最美最好的日子。其时我还没到感知人世的年龄,即使到后来历经了人世的沧桑,我亦觉得其时自己的感觉真是对的,那样的场景,真是人生难得的风景。
入夜之后,蛙声也开始响起来了,虽然没有夏夜里稻秧长起来时万箭齐发般的轰然,但那三三两两的和奏,亦是铮然有声,在几粒星子的照耀之下,仿佛神祗降下的幽妙的微明,在那夜的上空里浮着,似乎托起的,便是村子清明简静的梦。青蛙是随春水而生的一族,凡有春水处,即有蛙声,可奇异的是,当你蹑手蹑脚偷偷靠近一洼春水,想要看那青蛙的真身时,那声音往往“倏”的一下子就不见了,那声音始终就响在几步之外,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亦停,总之就跟你保持着这样匀称的距离,就仿佛跟你捉迷藏一般。我小时在夜的田野里摸爬,从未真切地看到一只青蛙歌唱时的姿势。只是后来在小学课本上读到了“坐井观天”的成语,老师在黑板上讲解时,我一直为青蛙抱不平,我始终觉得发明这个成语的人才真正的是坐井观天,我始终相信,一只只青蛙就像春夜里的精灵,在它们不断移动的美妙的乐声里,它们拥抱自己的同时,亦拥抱整个天空。
到了白昼里,昨夜的蛙声全都止息下来,田野里仿佛柔和了许多,经过一夜蛙声的浸泡,一切事物都更加明媚可人了。新阳亦只暖暖的,落在身上心上,都只像爱的抚摸;草木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吮足了汁液,新长出来的枝叶沾带了露水的气息,更加柔嫩清新;几只鸭子,正在河流上悠闲地浮着,亦不觅食,亦不出声,只仿佛三五友人泛舟湖上的游春图,一切只在那默默的注目和默契之中。就连畈上春牛的那一声长哞,亦只传递着温馨的声息,直让人想起“吴农耕泽泽,吴牛耳湿湿”一类的古词,这古词里所描绘的陌上图,亦是我村春耕人的真实写照。
布谷鸟也开叫了。自从惊蛰过后,布谷鸟便出现了。说不清是在某个早晨,或者是午后,再或者是某个寂静的夜里,总之第一声布谷的啼鸣就从山野的远处响了起来,“栽早包谷——栽早包谷——”,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也响起来了,一声接一声,声音清寂空旷,田野和村子似乎就显得更加悠远。村人之中很少有人知道布谷鸟又名杜鹃,更不知杜鹃啼血的传说,却都知道布谷鸟一开叫,便意味着春耕时节已经到来了。我小时听布谷鸟的叫声,亦受大人们那一份潜移默化所感染,每一次都有一种肃穆,深怕因为一丝一毫的不敬亵渎了那声音;也因为这样的心理,总觉得布谷鸟的声音就仿佛来自大地和庄稼的神谕,除了人世的一份贞亲外,更有着仙界的仁慈厚爱。
阎王刺亦在此时说开花就开花了。
阎王刺开花的时候,就像大地做了个梦。一排排的阎王刺花往往在一夜之后就铺满了道路两旁。它们从不在白天开花,只是在人们纷纷入梦的夜里,很神秘地就展开了它们的繁华。待人们看见它们时,它们早已在阳光下,仿佛来此多时了。人们也往往都入了梦境一般,都会使劲揉了揉眼睛,恍惚自己跟大地一起,都刚刚做了个梦,或者索性就还置身于那梦的恍惚里。
那些时候,阎王刺花是作为神祗供奉的。作为跟布谷鸟一起报春的信物,或许因为布谷鸟来无踪去无影,只作为“无形之身”存在,而阎王刺花却就那么真切地绽开在肉眼里的缘故,这“有形之身”让村人一下子寻找到了膜拜的实物,所以每当阎王刺花开时,村里的寨老便会代表所有村人为其送上一丈二尺长的红布(其尺寸的选择亦是暗合一年有十二月、月月有红利的意思),并总要焚香燃纸祈祷,希望阎王刺花神能保佑村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之后,家家户户便从楼上一一抬出了农具。
還在上年秋收结束时,家家户户就已经把清洗得干干净净的农具抬到楼上搁好了,犁头、镰刀、锄头……一件件摆放得整齐有序。在村人看来,摆放农具,就跟摆放庄稼一样,丝毫不能马虎,在既定的秩序之内,一事一物的生命都必须给以其必要的尊崇和善待。
落雪的冬日,有事无事,一家之主们亦总会爬到楼上,站着,或是蹲着,对那一长排的农具东瞅瞅、西瞧瞧,有时还要伸出手去,仔细地抚摸它们,整个冬日的时间都交给了这些已经歇息的农具,就像一个人的梦境,时刻都落在某个柔软的点上。
在村人们眼里,一具农具,连着的是庄稼和大地。
现在,站在春天的门槛上,家家户户都要把这些农具一一抬出来,一一地在阳光下晒晒,一一地小心擦拭,歇息了一冬,总要把那些难免会发霉和生锈的部分彻底祛除,在就要开始种植庄稼的时刻,保持一具农具锋利的质地,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也仅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实际上,在多年之后,当我再一次凝视村庄跟那些农具的影子时,我便会再一次想起某种宗教般的仪式。我固执地相信,在迎接春天以及一株庄稼到来的时刻,人们一定是借助一具农具的指引,去表达他内心的某种肃穆,并由此保持人生的一份庄严。
农具擦拭完毕,无论大人小孩,便都一起被喊到了田畈里。大人要劳动自不必说,七八岁的小孩,亦要在这个时刻亲自扶犁耙以学习耕种,藉此行成年之礼。一直以来,一个村庄亦以此作为根脉有继并土地兴盛的标志。上流社会或是一般富贵之家,男孩的成年礼至少亦要到少年之时才落成,并且一定是华服冠盖以示隆重。而在我的民间乡村,却只在七八岁上下,而且是以扶犁耙的方式,命运之大相径庭,由此可见一斑。我七八岁时,亦没逃脱这样的成年礼。虽然我后来并没有按着这一古礼去行我人生的轨迹,可只要一想起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就在那雨水汤汤的田畈里长成,虽亦有人生的一份心酸苦涩,却也觉得那质朴的陌上画卷亦算得上花开粲然的清明上河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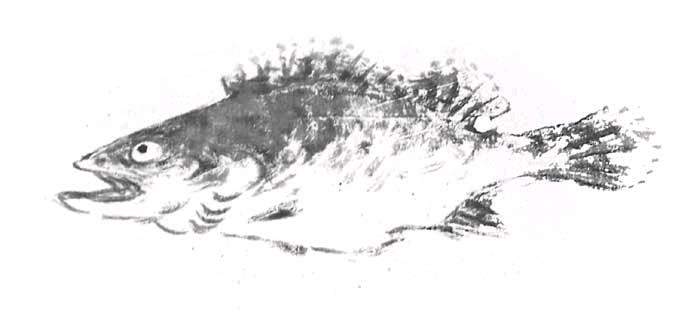
【作者简介】李天斌,男,黎族,1973年生,贵州关岭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北京文学》《天津文学》《红岩》《散文海外版》《雪莲》《作品》《鸭绿江》《四川文学》等。获贵州省专业文艺奖,贵州省高端文艺平台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