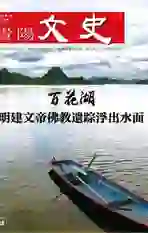我与张仃先生的艺术缘分
2017-05-06刘雍
因为命运的安排,我一生没有机会进入任何美术院校学习,也没有机会在任何名家门下拜师学艺。但在成长为一名职业艺术家的过程中,我却得到过许多前辈艺术家的教诲、关心和帮助,他们的作品和对我的指点在我对艺术的领悟理解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张仃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张仃先生和我的个人交往虽不算频繁,但是张光宇——张仃体系的艺术风格对我的风格形成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可以斗胆地说,我与他在艺术上是有缘分的。
我最早见到张仃先生的作品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大刊物上:如《人民画报》上的《纸老虎》;《新观察》杂志封面上的《放风筝》、《春牛图》;《漫画》月刊的封面《孙悟空跳出老君炉》、《东风压倒西风》、《新斯芬克斯之谜》、《天官赐福》、《巴黎组画》;《全国漫画展》招贴画;《装饰杂志》上的《十二生肖》图案等,这些作品浓厚的装饰性、强烈的形式感、深厚的造型功力、简练但瑰丽的色彩令我深感震撼,和当时流行的苏派讽刺画一比,高下立判,喜厌立现。从此我就爱上了张仃先生的装饰漫画,花了不少时间钻头觅缝地在当时有限的报刊中寻找。在那个文化极端贫乏的年代,这些作品在我从学龄前到高中毕业这段苦涩岁月里,给了我不少审美上的慰藉,也帮助培养了我最初的非写实审美意识。
我最初能有幸接触张仃先生的装饰艺术理论,则是因为1966年“文革”初期一个特殊而悲伤的原因:为寻找当时家里被抄家抄走的藏书藏画,我潜入纸厂待销毁的“废纸库”,结果被抄的藏品没找着,却意外找到一本由张仃先生作序的《张光宇插图集》。在《张光宇的装饰艺术》一文中,张仃先生对张光宇先生的藝术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和概括,这本画集便成了我当时学习装饰艺术的主要教材。后来我经常用张仃先生的序文对照张光宇先生的画,反复琢磨“以小见大”、“奇中寓正”、“方中见圆”、“先放后收”这些说法,使我对装饰艺术的规律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
而我第一次见到张仃先生的原作就更有悲剧色彩了:1967年,我作为化工厂的学徒工从贵州去东北学习。在北京等待转车时逛到了市中心,结果在王府井的一个橱窗里看到了批 “二流堂”的 “大批判专栏”,其中张贴有包括张光宇、张仃、张正宇、叶浅予、丁聪、黄苗子、吴祖光、赵丹等 “二流堂” 成员的合影。橱窗里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大批被打着大黑叉的张仃先生原作!旁边附带有无限上纲的批判,比如说:“《孙悟空跳出老君炉》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东风压倒西风》利用风向标会转向的特性,暗示有时西风也会压倒东风……这些恶毒的语言在令人不寒而栗之余,也让人惊叹这些无中生有、罗织罪状者的想象力。同时被打黑叉示众的还有张仃先生在西双版纳和大理等地创作的一组极富形式感的写生画。这些画不是对风景和人物照相式的平淡记录,而是在高度概括总结了对象的特征气质后的夸张、变形、组合和再创造。我还记得其中一张《集市上的傣女》,画的是个卖布的女孩,眼睛奇大,慵懒地躺在各色花布中间,仿佛一只可爱的小猫。
另一张《哈尼族女民兵》是用立体派的画法,塑造了一个坚毅如山的女民兵形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超长的脖子和几何造型。还有一张《苍山牧歌》中的山羊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这些作品正是对张仃先生所主张的“毕加索加城隍庙”创作理念的最好诠释,启发了我后来有意识地把中国民间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融为一体的创作思路。如今50年过去了,我也老了,多少宏大叙事、恩怨情仇早已遗忘,昨日之事,今日记不得那是常态,但当时挂在橱窗里的那些打着黑粗叉的画却至今历历在目,纤毫清晰,仿如刚才亲见一般。我想,这就是真正的艺术的特征和力量吧。
当时我完全沉浸在对这些伟大作品的欣赏里,忘记了正身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突然,呼喊的口号声又把我拉回到残酷的现实,胸口上仿佛被人深捅了一刀,疼得喘不过气来。我徘徊在大批判专栏前,直到天色已晚,再也看不清画面,才在悲愤中含泪离去。谁能想象一下,久思而不得见的女神,见到她时她却正遭匪徒强暴蹂躏,而你站在一旁却无能为力,这是种什么滋味、何等的悲愤?!张仃先生和我在艺术上的缘分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场景中产生。我们相逢于前辈伟大艺术的毁灭,而这毁灭的场景却又如燃灯薪火,在与后辈的心灵的一触之中便完成了艺术的相承延续。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这就是命运,这就是艺术。悲耶?!奇耶?!
同年回到贵州后,我把这些感受构思了几件漫画,这便是《有奶就是娘》、《为虎作伥》和《被丑吞噬的美》,到20世纪80年代又做成了相同题材的雕塑。后来看到张仃先生的讽刺画《狼孩》,竟然和我的《有奶就是娘》不约而同,看来我们对于“文革”的认识也是灵犀相通的,这是不同年龄的作者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的共同思索。
“文革”结束以后,我又在各大报刊上看到张仃先生的不少作品,尤其是关于批判“四人帮”的系列作品《立此存照》,使我欣喜。我也开始在多种报刊上发表漫画作品,由于我的漫画作品也追求装饰趣味,在当时也算别具一格,便自然得到了张仃先生的关注。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的《讽刺幽默》1981年曾经把我借到那里去实习和进修。编辑部收藏有一套1949年前的漫画杂志,使我大开眼界,对中国的漫画史才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见识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漫画的辉煌。尤其是《时代漫画》、《救亡漫画》、《上海漫画》、《抗敌漫画》,老一辈漫画家的作品不但在政治上尖锐辛辣、在思想上深邃、题材广泛,而且手法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其中张仃先生创作的《兽行》、《收复失地》等系列抗日漫画特别有力度,使我十分震撼。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在“苦难”、“有亡国灭种之虞”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 尚能产生这些伟大璀璨的批判艺术,反观在如今盛世,我们的漫画艺术却退化萎缩到了如此的地步?
1982年7月19日,我参与筹备的《贵州学习民间工艺美术新作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我本人也有50件陶艺作品参展。全国美协举办了专家座谈会,那时张仃先生已恢复了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职务,他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了我们的探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仃先生本人。1989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圆厅举办个人作品展《一个夜郎人的世界》期间,张仃先生不在北京,但他还是关注着我。不久他来贵阳,在大会上他特别问到:“刘雍来了吗?”可惜当时我不在场。真正和张仃先生有了直接交往,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后,他担任理事长,全国主要从事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专家都聚集到他的周围,我也是理事之一。每次年会,大家都展示自己的收藏和研究成果。我带去了大量的贵州民族民间艺术品,并在会上作了我的作品幻灯讲座。张仃先生和夫人理召对此很是赞赏,从此我们便熟识交往起来。
后来我曾多次登门到张先生家请教,我提起当年在王府井大批判专栏看到的那些作品,他难过地悲叹:“唉,都毁了! ” 他说起“文革”期间,不但自己受到残酷的批斗,作品被毁,他的儿子张郎郎也和遇罗克关在一起,九死一生。理召先生还说起一些延安时期的往事,张先生在鲁艺任教时,她还是儿童团员……张先生向我展示了他“文革”后画的一些新作,尤其讽刺“四人帮”系列装饰漫画特别精彩,手法千变,如《女巫的赌博》色彩高雅,而《净土变》色彩则十分华丽,在挂毯《女娲补天》中,敦煌壁画的艺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灰娃肖像》则有马蒂斯的余韵……张仃先生所刻画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角色,都给人极大的审美享。最令我钦佩的是先生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大手笔,他能把原始的、古典的、現代的、民间的、宫庭的艺术及文人画等诸种似不相容的因素,有机地熔铸进他的作品,使作品具有音乐的节奏、舞蹈的韵律和戏剧的魅力。同时他又能将其艺术风格广泛地运用到漫画、装饰画、壁画、书籍装帧,以及广告、邮票、动画、服装、美术字等设计中去。
中国的动画片中,我最为钦佩的是张仃先生的《哪吒闹海》和张光宇先生的《大闹天宫》,其成就至今在中国仍无人能够超越。他向我展示更多的是焦墨山水画,张先生说,他现在集中力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力求有所突破。我感觉他的这种画法和风格是前所未有的,笔法苍劲、构图雄浑、气势磅礴。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继黄宾虹、李可染之后最重要的山水画家。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常务副院长杨永善先生曾提议由我筹办成立一个新的系,专门研究把民间艺术转化成现代艺术,得到张仃先生的支持。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93年,张仃先生还专门写信给他熟识的贵州省省长陈士能,请他支持清华大学的邹文先生和我对贵州民间艺术的研究工作。由于陈士能不久调任轻工部部长,惜此愿望未能实现。
1999年,我为贵州省图书馆作了公共艺术整体设计,张仃先生看了十分赞赏。他担心该方案不能实现,便专门与曹振峰、杨永善、张守智等中国工艺美术界的权威一起致信贵州省政府举荐。当时张仃先生正在病中,于是口授请夫人理召手书由他签字。在张仃等诸位先生的关怀下,这件作品后来得以局部完成。同年,贵州省图书馆设计获当代中国建筑艺术成就奖,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55件优秀设计之一,也算没有辜负张仃先生的热心支持。
后来我的作品集《刘雍作品集》编撰时,我请张仃先生题写了书名,他也为《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题写了书名,并撰写前言,他在序言中呼吁用贵州民族民间艺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来,张仃先生年事渐高,住到了郊外,我再也难以当面请教。但我每有新作,直到他去世之前,都设法将图片请人带给他过目,向他报告我的创作进展情况。
中国漫画界的传统是:“对前辈敬重、对同辈友爱、对后辈提携”。张仃先生屡屡在我面前提到张光宇等前辈对他的栽培,并希望这种传统能在中国漫画界传承下去。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诲正是这种精神的实践和延续。我将永远缅怀这位中国工艺美术界的宗师和漫画大家!
(作者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