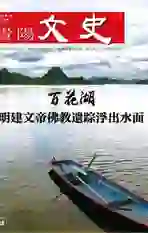祸国殃民的告缗令(下)
2017-05-06于民雄
于民雄
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政策,但“告缗令”的颁布表明汉武帝不是缺乏对儒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全面了解,就是根本置之不理。
二
比较一下“通缉令”和”告缗令”之异同,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通缉令”和“告缗令”都是国家发布的,代表国家意志,具有法律效应。但是,两者存在原则区别。重大在逃罪犯一旦被捕,“通缉令”就自动撤销,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告缗令”则异于是。“告缗令”结束之日,正是商业贸易流通彻底凋敝之时。事实上不待“告缗令”结束,从“告缗令”启始之日起,恐怖的气象笼罩四野,一片肃杀声中整个中产阶级、商人集团望风披靡,正常的商业活动已经不可能。“告缗令”窒息了汉帝国的正气,摧毁了汉初几十年渐渐恢复的经济活力;它的后遗症之一,是汉帝国的衰亡。100年后王莽篡权就是汉王朝走投无路的产物,时代危机呼唤改弦易辙。当时民间普遍出现的拥戴王莽的呼声,折射出来的正是对黯淡现实的普遍不满与绝望。
第二,“通缉令”以重金悬赏为诱饵,这种洞悉人心的策略从古至今都是有效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重赏是有条件的,以能否提供准确的情报,能否为破案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准。因此,能够得到重奖者只在一人与数人之间,倘若罪犯自投罗网,悬赏从结果看只是一句空话。与“通缉令”只是针对一两个罪犯不同,“告缗令”针对的是整个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一瞬间成为国家打击的目标,全体商人的私人财产一瞬间成为瓜分的对象,恐惧与肆虐交织在一起的混乱局面绝对是触目惊心的。除了受害商人集团的绝望之外,任何人都看到了希望。暴力与诱惑的联姻,实现了全社会层面上的财富重新分割。一个检举者获得被检举者一半的财产,汉武帝却获得所有被检举者的一半财产,汉武帝成为最大的赢家。更可怕的是:“告缗令”为人们突破道德底线提供了通道,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导致告密成风,让原本不光彩的偷偷摸摸的行为公开化、合法化,为一切不逞之徒的假公济私、见利忘义、乘火打劫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致使一向本分、怯弱的人此时此刻都可能跃跃欲试,共同为去道德化推波助澜。于是,人心大坏、民风败恶,千百年历史过程演化出来的道德意识毁于一旦。
第三,“通缉令”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正常生活,交通要道的封锁,更为严格的身份检查可能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可能让人们产生程度不同的紧张感,但这种影响只是局部的、随机的,严格说它的负面效应的辐射范围相当有限,人们照例可以自行其是。而“告缗令”导致的是社会震荡,和因社会震荡导致的社会分裂。汉武帝极不公正地把穷兵黩武的恶果转嫁在商人头上,挑起本来相安无事的人们彼此结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结仇,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结仇。破产的商人集团同时面对两个敌人:一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一是告密者、揭发者、检举者。仇恨布满在社会有机体上,盘根错节,一个好端端的民间社会就因“告緡令”而四分五裂,罪魁祸首是汉武帝。没收商人财产以充盈国库,其代价是整个工商业的全面萎缩,是国计民生的全盘溃崩,利与害的倒置满足了汉武帝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却证明了他的目光短浅。汉武帝的盲点与他的气质、智力和视野有关,但至高无上的权力表面上可以掩盖这一切。汉武帝高高在上,他未必愿意倒行逆施。但一个恼羞成怒的独裁者他纵然知道自己在倒行逆施依然要倒行逆施,他不受约束的权力使他的倒行逆施成为可能。
三
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政策,但“告缗令”的颁布表明汉武帝不是缺乏对儒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全面了解,就是根本置之不理。“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温和的汉宣帝口气尚且如此,何况他不可一世的曾祖父汉武帝。孟子明确提出,设立关卡向商人征收关税是非法的暴力行为,商人在社会分工中具有独立的价值,商品流通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重农抑商是法家的主张而不是儒家的主张。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悝都是重农抑商的积极鼓吹者。韩非在他的代表作《五蠹》篇中,把工商业者看作是危害国家的五种蠹虫之一。汉武帝打击迫害商人,与儒家的思想扯不到一起,却可以从法家找到理论根据。法家耕战为本的策略在战国群雄争霸的特定历史时期是有效的,但在和平时期也许就不适用了。韩非强调打击工商业者,有他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看问题的视角,他的冷酷与无情不乏敏锐与深刻,但时过境迁,机械地把商人视为异己力量,是盲目的教条主义。汉武帝是一代枭雄,气质刚愎而强悍,他不必对儒家思想阳奉阴违,阳奉阴违的最大可能是底气不足,是力量不强,是弱者的策略。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在漢武帝眼中只是统治的工具,他更可能采取实用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立场看待历史上承传下来的各种治国经验,他甚至可以不要任何理论。汉武帝滥用权力没有底线意识,他一贯意气用事,凭一时的喜怒发布他的旨令,不管其后果如何。虽然从长时段的历史看,是制度的性质而不是君主个人的气质决定社会历史的面貌,但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与一个专横残暴的君主气质上的差异,往往可以决定具体事态发展变化的结果。“告缗令”性质上更像法家的严刑峻法,但恐怕只是汉武帝唯我独尊一念之差的产物。“告缗令”的背后隐藏着汉武帝的报复心理,“算缗令”遭到普遍抵制让汉武帝蒙羞,他需要出重拳打击商人的嚣张气焰,宣泄自己的愤怒,挽回皇权的权威。汉武帝的做法与儒家的“仁政”格格不入,也未必是简单因袭法家“严刑峻法”的产物。“告缗令”只是临时性的措施,与法家稳定的、一贯的“严刑峻法”的统治策略形式上不尽相同,只是碰巧如出一辙而已。
汉初奉行黄老政治哲学之术,采取放任主义、与民休息的政策,短短几十年间,人口繁衍起来,生产发展起来,社会繁荣起来,出现了中国传统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是大气候、大环境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使统治得以巩固,社会秩序井然让人民各安其位,这种双赢的好事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繁荣作为一个结果,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这其中就包括商人的贡献与功劳。既然国家欣欣向荣源于放任主义、与民休息的政策,就应该遵循过去行之有效的治国经验,不必另起炉灶。可悲可恨的是:汉武帝置国计民生的根本于不顾,“告缗令”的出台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另起炉灶,而是公开的祸国殃民。汉武帝猖狂一时,其实是自掘坟墓,历史就是如此无情。他金碧辉煌的陵寝,是民脂民膏堆积起来的,其中包括商人的血与泪。他后来发布“轮台罪己诏”,也许是他最后的良心发现,但对于既成事实的衰败之势,“轮台罪己诏”已经无济于事。
商人有钱,但他们政治上没有发言权,他们财富的保障缺少稳定的制度基础,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低恐怕还不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要命的是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让他们担惊受怕。一个政策、一条法令就可以让他们前功尽弃彻底覆灭。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资产阶级要幸运得多,强大得多。虽然资产阶级只属于第三等级,僧侣集团、贵族集团可以轻视他们,但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他们有力量与损害他们利益的力量争锋相对,他们是一个成熟的有思想武装有合法社会地位的利益集团,他们已经试图跃跃欲试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是新世纪的开路先锋。这里无须比较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异同,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带来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自由,更大的繁荣,虽然这个制度依然问题多多。
中国中产阶级从来没有真正强大过,其原因极其复杂至今众说纷纭。中国商人即使腰缠万贯,商人的财富即使占有半壁河山,在皇权面前依然是弱者,国家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一网打尽。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富可敌国者极少纯粹的商人,更多的是皇亲国戚,是官僚集团。以凿壁偷光留名后世的匡衡就是汉成帝时代数一数二的大富翁,但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官僚;汉成帝的舅舅王立一次倒卖良田,按今天的购买力计算,就净赚数亿的钱财;汉成帝宠臣董贤,死后抄家发现其财产竟高达100亿。商人只是中产阶级,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他们与那些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们不可同日而语。
仅仅有钱没有制度保障是靠不住的,仅仅有钱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依靠也很难是可靠的。在一个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国度里,官僚的财产也是没有制度保障的,但他们的权势可以比较有效地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侵害。商人无权无势,自然容易成为他人鱼肉的对象。不待国家公开的暴力掠夺,污吏贪官都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对他们进行敲诈。捐官的钱不是白花的,它是一种策略,积极意义上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消极意义上可以比较有效保护自己,可以减少财产无故损失的可能。洛克的财产权无疑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它可以最有效地实现人格独立,它构成以国家名义侵害个人权利的天然屏障。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保障人的权利的制度。一个“告缗令”就可以把中产阶级斩尽杀绝。
商人有钱是商人被勒索的原因,商人被轻蔑是敢掠夺商人的原因。如果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商人遭到损害的可能性有所减少。商人成为国家强势集团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满足了强势集团嫉妒心轻蔑感得以宣泄和实际利益满载而归的双重需要。官僚本来就瞧不起商人,商人凭借自己的财富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可以在经济上和官僚阶层平起平坐是官僚阶层不可接受的,商人的生活水平超过官僚则是让官僚们不能容忍的。他们貶低商人其实是出于嫉妒,而官本位立场则让这种阴暗的心态变得冠冕堂皇,振振有词。“告缗令”虽然是汉武帝个人意志的产物,但却代表包括酷吏张汤、义纵在内的官僚集团仇视商人的共同心理,代表他们固有的利益倾向。这个倾向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某种意义上说,商人不与政府合作,拒绝政府的要求是商人的觉醒,只是这个觉醒在汉武帝时代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现代法治社会,民众不与政府合作是常事,一个政策遭到民众的普遍反对往往会导致政府垮台。人民是强大的、自主的,舆论是有效的、公开的,人权是普遍的、是神圣的,是民主的根本标志。因此,在法治国家,试图像汉武帝颁布的“告緡令”那样,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收刮民脂民膏是骇人听闻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法治社会不可能的事在专制社会往往可能。专制社会,统治者是强大的,舆论是封锁的,人权是缥缈的,因此统治者可以自行其是,除了少数例外,它可以利用暴力做到想做的一切。“载舟覆舟”云云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更多暗示的是人民被动的消极性反应,表明一个不得人心的王朝被推翻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社会各阶层都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具有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可以有效制约统治者对权力的滥用。
暴力的本质就是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众暴寡,这一通行有效的模式是人们崇拜暴力、依附强势集团的原因,但它的强盗逻辑又是人们批判、诅咒暴力揭竿而起的原因。简单地、一味地信奉暴力是暴君的哲学。我相信,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人们已经不自觉地遗忘了暴力的功能,已经丧失了对暴力滥用的想象,人们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被检验后被证明是货真价实的,人们视权利为理所当然,人民固定的思维模式让全民的权利意识坚如磐石,于是滥用暴力销声匿迹了。既然权利是护身符,可以保证人们在社会上立足,就没有必要依附强势集团,至少这种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少。为什么专制让人们对权力趋之若鹜,因为权力是硬的,权利是软的。权利无非是镜中花而已,任何人一眼就知道它的虚假性虚幻性。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性循环,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屡屡中途夭折,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是原因之一,骇人听闻的“告緡令”就是证明。
四
善恶泾渭分明,不待知识、经验,仅凭良知就能准确判断。告密要不得,不待知识、经验,仅凭良知就能准确判断。
汉武帝颁布的“告缗令”导致告密成风。20世纪后半期在同一片土地上,检举、揭发、告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其甚嚣尘上之势,持续数十年之久。两者相距二千年,但性质并无差别,其产生恶果完全相同。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谁说不是呢?!(完)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