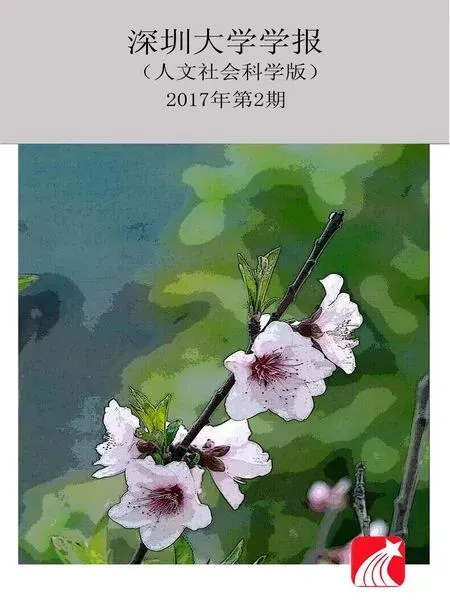汤一介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及其启示
2017-04-26胡治洪
胡治洪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汤一介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及其启示
胡治洪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汤一介先生至迟在1983年就已思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他着眼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对于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前景而强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理想、实践品格、人的本质、对立统一方面具有契合点,在经济、法治与传统、道德方面存在互补处,这些契合点与互补处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汤先生的思考表现出文化自信、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对于建设既具固有性、又具权威性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使中华民族达到高度思想认同,从而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汤一介;儒学;马克思主义;契合;互补
汤一介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在儒学的特质及其当代意义、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道教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玄学的产生与影响、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互鉴乃至中国解释学的建构等多方面都做出了具有开拓论域、引领方向意义的重要成果;而他至迟在1983年就已提出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的观点,以及后来主持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国家重大项目,更是开辟了一个兼备学术性与实践性、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研究领域。
2013年11月28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汤先生向会议提交了同年9月3日在中国国学中心所作的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发言记录稿,这份文稿后来被收入《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汤一介卷》(华夏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改题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比勘原稿与正式出版物的文本,后者的文句显然经过校改而更加整饬流畅,但却删除了原稿的诸多重要观点。根据《汤一介卷》“导读”作者干春松教授所谓“2014年9月8日,汤一介先生不幸去世,故而《汤一介卷》的编辑工作有赖于孔子研究院的同仁完成”①,似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文的删改乃由后学捉刀而非汤先生本人所为。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原稿更加充分地反映了汤先生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深长思考,所以本文拟围绕汤先生原稿展开论述。
一
汤先生说:“处理好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之能共存共新,互利互补,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研究的大课题,认真地说,我是不具备研究这一课题的知识和智慧。但是,这个问题却是在我心中常常想到而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回忆起来,在1983年,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年夏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 ‘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题为《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在发言后的讨论时,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刘述先教授撰写的《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记行》中有如下一段记载:‘汤一介讲完后,在讨论时间,(台湾)冯沪祥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问汤一介讲的这一套究竟与马克思主义有怎样的关联。汤一介的回答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之间至少可以看出三个契合之处:(a)二者都重实践;(b)二者都取理想主义态度;(c)马克思主义有矛盾统一律,过去毛泽东强调斗争,以至产生偏向,如今应该强调和谐,乃和儒家有契合处。’”②由此可见汤先生早在1980年代前期就开始思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的问题,而当时思想领域的状况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具有至高无上、不可企及、更不容挑战的地位;风靡于知识界乃至社会诸层面的则是西化思潮;儒学的社会影响还相当微弱,不仅尚未完全洗刷“文革”所强加的污名,而且又被时人扣上“文革”的历史根源的帽子,几乎被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在那个时候提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问题,虽然不再如“文革”期间有身家性命之忧,却是被立场观点各不相同的人们所嗤笑和攻击的,但这恰恰表现出汤先生的文化自信、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正因此,汤先生于1984年创办了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旨的中国文化书院。
汤先生的文化自信、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来自他对影响历史和现当代中国最为深广的两个“传统”及其显见或潜在的重大现实作用的深刻认识。他说:“影响着我国社会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国学’,即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老传统’;另一个是近百年影响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社会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传统’。我们必须‘传承’这两个传统,并且要逐步使两个传统在结合中‘创新’,使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利发展,适应当前世界已经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势态的需要。”
之所以说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 “老传统”,是因为“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中华夏、商、周三代文明,实际上它成为支撑着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支柱”,“在历史上长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生长、发育的儒学,曾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子”,正因此,“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后代子孙是不能、也不应该人为地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把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学抛弃掉,无疑是宣告我们这个民族曾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不复存在,或者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自身生命力的中华民族不复存在,而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这就明确指出了儒家传统与中华民族密切依存的关系,儒家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则是儒家传统的物质载体。设若丧失儒家传统,中华民族也将丧失固有的认同感、凝聚力及其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从而无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这种假设决不可能实现,儒家传统终将与中华民族同在,“民族的复兴必然要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也就是说,任何社会文化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它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这就是汤先生文化自信的原因。

从现象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长期处于紧张对立状况;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儒学在前30年更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压制、批判、打击、禁锢;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的态度日趋缓和,但前者的优越和后者的疏离甚至反弹至今仍历历可见,因此一般认为这两种传统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但是汤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反复说:“面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着‘传承’和‘创新’的巨大任务,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全面实现,这样中华民族将对人类社会做出史无前例的重大贡献。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如何‘传承创新’儒学,也需要考虑如何‘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这就涉及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大事。”“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许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可以创造出新型的‘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例。”“我们必须‘传承’这两个传统,并且要逐步使两个传统在结合中‘创新’,使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顺利发展,适应当前世界已经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势态的需要。”这是着眼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对于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前景而强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必要性。尤有进者,汤先生还表达了对于这两个传统在相互结合中的地位的看法,他说:“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重大发展?从一方面说,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要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接轨,特别是与儒学的有机结合。”除了现实要求的优先性之外,在两个传统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最终必须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成为其组成部分。汤先生的这种看法乃是基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前瞻,直到今天仍然体现出他的文化自信、远见卓识和理论勇气。
二
汤先生不仅指出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必要性,而且论证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他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既有相同的契合点,也有虽然相异但却可以互补之处,这些契合点和互补处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除上文提及的二者都重实践、都取理想主义态度、马克思主义矛盾统一律与儒家和谐观有契合处之外,汤先生后来还补充了一点,他说:“21世纪初我主持编纂 《儒藏》,由于对中国先秦的‘礼’有所涉及,又接触到先秦儒学如何处理‘人’的问题时,注意到儒学是在社会关系中定义‘人’。因此,可以说,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至少有四个可能的契合点。”
汤先生对这四个契合点展开了论述。首先,从《礼记·礼运》篇对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可以看出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也许是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话:‘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这段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上引《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是有某种契合点的。特别是‘大同’理想中提出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颇有相合之因素”。儒家“大同”理想不仅一般地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相契合,它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儒家的‘大同’对中国来说则更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毕竟需要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素”,“儒家的‘大同’理想无疑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极有价值的理念”。
其次,从《尚书·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直至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和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所谓“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以看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注重实践的学说,“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有其比较完整的一套哲学体系,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实践’”。不过马克思主义比较重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而儒学比较重在修养主观道德的实践;由于每个人或一切人的道德改善乃是整个世界改良的前提,所以“革命的理论如果要实现‘改变世界’,那就一定要见之于实践,必须吸收‘知行合一’中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合理因素,这样才能摧毁人剥削人的旧世界,而最终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 ‘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就显然将儒家重在道德践履的“知行合一”说视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必须吸收的要素了。
复次,从儒学大量阐述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类人伦礼制和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所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来定义“人”,而不是从抽象的个人来定义“人”,“就理论上说,马克思当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较之儒家思想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从思路上说,儒学关于‘礼’所包含的理念和马克思的思路是有一致之处的”,所以“我们应认真发掘中国古代‘礼’文化中的某些有益的意义”。
最后,从贾谊《过秦论》、张载《正蒙·太和篇》和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可见,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主张自然社会万事万物通过斗争而最终达到和谐。从自然现象看,“例如阴阳、刚柔、寒热、生杀等等是一对对相对的矛盾,有这种相对矛盾,在他们运行中就会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就一定会有斗争,但是矛盾斗争到最后终究要和解,以达到和谐”。在人类社会中,“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行‘仁义’之道,否则政权是保不住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天天斗’,而是最后能使社会最终实现和谐”。可以说,肯定斗争但却以和谐作为终极目的,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宇宙观。
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互补之处,汤先生说:“也许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纠正:一是,儒学必须特别重视‘经济基础’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学是十分欠缺的。二是,必须克服儒学过于重视‘人治’,而忽视‘法治’,也就是说要克服‘道德至上主义’。‘道德’对人生十分重要,但一个健全的社会是要由多方面来维系的,如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社会的健康发展是要由多方面共同协调发展的,不能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那么,儒学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可补充和纠正之处呢?我认为,至少也有两点:一是,‘要重视传统’。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句话,在马、恩当时的情景下,我们也许可以给以同情的理解,但是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来说是片面的。我想,这方面可以从儒学十分重视‘传统’方面得到一些补充和纠正。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的问题不多,但在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也许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理念。”汤先生在此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缺失也许把握得不是十分确切。例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表明他们十分重视历史,而他们所要彻底决裂的传统观念可能是要加以限定的;又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既是经济制度构想,也是道德原则构想。具体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就说过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表明他并不是始终一贯地反传统;而他对道德的强调更是所在多有,《纪念白求恩》、为雷锋题词、“六亿神州尽舜尧”诗句等等都可证明。至于儒家也并不轻视经济基础,《易传》备物致用,《尚书》六府三事,《论语》庶富教,《大学》生财之道,《孟子》制民之产,都表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儒家反对无止境的增长和无节制的攫取,这恰恰体现了儒家可大可久的德慧;而一个健全的社会诚然要由多方面来维系,单任一方面都决不能脱离道德的引领或制约,否则就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因此儒家的“道德至上主义”是颠扑不破的。不过汤先生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各有长短可以互补的观点却是颇有见地的,例如儒家心物一体本体观和执两用中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本体观和对立统一方法论显然相异,但在文化多元化的条件下恰恰可以互利互补,共存共新。
三
汤先生自谦没有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一课题的知识和智慧,但是实际上,他对这一课题长达30余年的思考相当系统深入并且富于睿智。他肯定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中国影响最为深广的两个传统,这两个传统不仅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存在相互结合的必要性,而且因为二者的契合点和互补处而具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汤先生的这些思考对于当今中国思想界颇具启示意义。
毫无疑问,儒学是中华民族最为悠久、博大、深沉的文化传统,它全面继承了华夏初民在漫长的世代中自然发生的、作为族群心理之表现的“亲亲仁民爱物”生活规范,并对其加以理论提升和经典表达,从而通过强化传统生活规范、启沃族群生命意识而与民族心理形成深刻的同构关系。正因此,儒学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故园,是民族成员无论在何种时空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安顿自我的根本。儒学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对当代中国必然具有巨大影响力,它的教言或示范在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人心世道、自然生态、核心利益以及国际形象等重大问题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样一种悠久、博大、深沉且极富现实意义的文化传统,非但决不能割弃,反倒必须积极继承并大力弘扬。
同样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通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运用,不仅挽救了中华民族,而且奠定了中华民族重新走向繁荣富强的坚实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毋庸讳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对当代中国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基本上处于紧张对立的状况,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批判、打击、禁锢为主,而在解放前后的不同阶段以及解放后的大陆和海外不同地域,激起儒学方面的反驳、抗争、疏离、攻诋;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态度日趋缓和,但惯性至今犹存,儒学方面则多应之以疏离与排拒,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事业,亟须加以改变。马克思主义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儒学作为中华民族贯穿始终的固有精神命脉这一特质,更加主动积极地融入这一精神命脉,从而完成其中国化过程。儒学也应该更加平情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进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乃至巩固政权的特殊阶段对于温和保守的儒学采取否定态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策略必要性,更加深入地体会马克思主义所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对于儒学复兴的吊诡意义,从而尊重、亲合、接纳马克思主义。双方应该不断找出愈来愈多的契合点和互补处,使相互结合的可能性愈益充分,并努力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只有实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既具固有性,又具权威性,才能使中华民族达到高度的思想认同,从而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所有这些就是由汤先生长达30余年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深沉思考所得到的启示。
注:
① 《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汤一介卷》,华夏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导读”第5页。
② 本文所引汤先生言论,均见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原稿,该原稿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办公室王文利女士提供给“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会与会者。引用时基本上遵照原稿,仅对个别显误字符径予改正。
③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一语的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可见汤先生对这一点的重视。
【责任编辑:来小乔】
TANG Yi-jie’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and Its Revelation
HU Zhi-hong
(The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udies,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TANG Yi-jie explored ways to combine Confucianism with Marxism no later than 1983.He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combining Confucianism with Marxism with an eye to achiev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mankind.He pointed ou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in social ideals,practical character,human nature and unity of opposites,and they are complementary in economy,law and tradition,and ethics,so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ombine Confucianism with Marxism.TANG’s thought reveals his 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great vision,and courage as a theoris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contemporary Chinese ideology which has inherent quality and authority to make Chinese nation highly identified ideologically so as to be united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ANG Yi-jie;Confucianism;Marxism;correspondence;complementary
B 2
A
1000-260X(2017)02-0063-05
2016-11-08
胡治洪,哲学博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