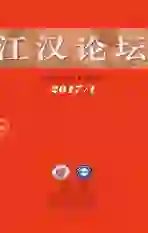“道”、“因”、“权”、“义”与《淮南子》政治哲学的结构
2017-04-18何善蒙
摘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淮南子》是黄老道家政治哲学的典范性作品。《淮南子》以其宏阔的视野,在汉初黄老政治实践的基础之上,以道家哲学为根基,以“道”、“因”、“权”、“义”四个观念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圆融、自洽的政治哲学系统,并在回溯道家哲学的历史资源和回应现实政治问题两个方面都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尝试。《淮南子》的政治哲学逻辑连贯、完整,并非像通常论者所认为的杂家的特点或存在着自身的矛盾,深入研究《淮南子》政治哲学思想,能够对道家政治哲学的现实展开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道;因;权;义;混冥;《淮南子》;政治哲学
基金项目:贵阳孔学堂年度项目“历代阳明祠与阳明学发展”(项目编号:kxtyb201601)
中图分类号:B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1-0084-11
引言:作为黄老道家政治哲学典范的《淮南子》
《淮南子》一书的编撰,与汉初黄老之学盛行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初黄老学的集大成之作。因其所涉及内容广泛,通常是以杂家称之。然高诱却明白地指出了该书的基本倾向乃是道家,“其旨近《老子》。澹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高诱《淮南鸿烈解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纲,兼摄儒、墨、阴阳、名、法等诸家,将道家的观念融入到了对于现实事务的处理和把握之中,这与作为全书总纲性质的《要略》里面的说法也是符合的,“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沉浮。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因此,《淮南子》的写作遵循“纲纪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的原则。这样的一种理论旨趣和抱负,很明显与刘安作为宗室的政治立场以及黄老之学盛行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在《要略》中,作者明确地把《淮南子》称为“刘氏之书”,“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以上均见《淮南子·要略》)。《淮南子》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故刘安在撰成之后,即将此书献给了汉武帝。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黄老的政治地位因为汉武帝的“表彰六经”而终结,但是黄老道家政治架构的努力还是有着重要意义。如果我们从中国社会演变的基本事实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脉络,那么将秦汉以来的哲学传统视为政治哲学(或者说以政治哲学为基础)应不为过①。秦代的法家哲学,汉初的黄老之学,汉武帝之后的儒家哲学,可视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接续,最后儒家哲学取代了黄老之学以及之前的法家哲学,成为政治哲学中的一统,奠定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本特质,这是由思想与社会的需求关系决定的。
一種思想形态,它要成为政治哲学,就必须要回应社会政治的现实问题。从黄老之学的具体演变来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积极回应的努力:从战国晚期开始,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儒家等的观念被不断地吸纳进入道家思想体系,从而成为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略;同时道家人物不断地出现在现实的政治舞台。在汉初60余年的时间里,黄老之学确实也赢得了政治哲学的基本地位,并以社会发展繁荣的事实,无可置疑地表明了其对于现实社会治理的价值。其间,其政治哲学的理论也得到不断完善。
但是,在汉武帝亲政之后不久,作为政治哲学的黄老之学就退出了政治实践的核心,被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哲学所取代。我们不能说这一取代的过程是偶然的,虽然在某些面向上它确实表现出偶然性,但是,此后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一尊的事实,却绝非偶然可以概括。这里就必须要看到哲学观念的差异性和由此所导致的应对社会现实的差异性。道家哲学原本所指向的乃是个体精神的提升与超越,强调的是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永恒价值,用庄子的话来说,这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篇》),就是逍遥游。可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就必须处理现实的社会问题,提出诸种解决方式,换而言之,这个时候它又必须是面向社会的当下存在,并且是深入其里的。而显然,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距离。反之,儒家哲学原本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再加上至汉武帝时代,社会民生已非汉初之凋敝,故一味地清静无为、修养生息,自然也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在这样的状态下,黄老之学被取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作为政治哲学的黄老之学就此离开了政治舞台,但这并不表明黄老之学对于现实的政治毫无意义,至少,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它已然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如果从黄老政治哲学的现实努力来说,如前所言,《淮南子》应该是黄老道家在政治哲学架构上的最为典范的作品,从《淮南子》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作为政治哲学形态的道家哲学,以及一种建立在道家哲学基础上的典范性的政治哲学形态。
一、“道以无有为体”:《淮南子》政治哲学的本体基础
《淮南子·氾论训》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所谓“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这实际上说明,在《淮南子》看来,所有的思想密切关注的都是现实政治的问题,或者说,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乃是一种思想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根据。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现实政治秩序和价值的确立。同时,所有的政治实践、政治形式的建构,都是有其哲学根据的。比如说“道”,它在中国传统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础性观念而存在的。对于“道”的不同诠释,在这个意义上,就构成了不同政治理念的哲学基础。
因此,《淮南子》要建立独特的黄老政治哲学,其逻辑的起点,必然也是它对于“道”的独特阐释,因为,不同的“道”实际上是对于不同的政治哲学的本体“承诺”。所以,在讨论《淮南子》的政治哲学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淮南子》如何讨论“道”?
作为黄老道家,在《淮南子》中,对于“道”的讨论是非常常见的,其中《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精神训》等几篇中的论述最为集中和最具代表性,学界对于《淮南子》道论的分析,总体上也是基于这几篇的论述。要理解《淮南子》之中的“道”,需要合理判断《淮南子》道论的基本性质,这也是对于《淮南子》思想讨论中最为基础的、核心的问题。对此,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看法,可以代表学术界的基本观点。
《淮南子》同先秦道家一样,以“道”作
为其体系的最高范畴。但是其间也有不同。先
秦道家讲道,虽然也讲宇宙的发生和发展的过
程,但主要是从本体论方面讲的,就是说,它
主要讲的是宇宙的构成。《淮南子》讲道,虽
然也讲宇宙的构成,但主要是从宇宙形成论讲
的,就是说,它主要讲的是宇宙的发生和发展
的过程。《淮南子》继承稷下黄老学派,提出
了一个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宇宙形成论。但是
《淮南子》不出于一人之手,所以它的宇宙形
成论,在《原道训》中所讲的,跟在《天文
训》和《俶真训》中所讲的,很有不同②。
按照冯先生的看法,由于作者的不同,《淮南子》的不同篇章对于“道”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甚至存在着前后矛盾的情形,而这种相矛盾的情形,当然和它杂家的风格是一贯的③。冯先生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许抗生先生的继承,许先生说,《淮南子》与《老子》一样,书中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它一方面主张无中生有说,认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天文训》)和‘道以无有为体(《说山训》):另一方面又认为‘道并不是‘无,道含阴阳二气(‘含阴阳),世界的开端是气。这样一来,就与《天文训》中所说的‘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的说法发生了矛盾④。
许先生在这里同样也是首先判定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的讨论的内在矛盾,并认为这样的矛盾是与《老子》中的讨论一致的,这似乎就意味着道家传统本身对于道的认识存在着内在矛盾⑤。沿着这样的思路,许先生认为,《淮南子》中虽有很多篇章涉及道论思想,但主要可以分成三类:一是以《原道训》、《精神训》为一类,二是以《天文训》为一类,三是以《俶真训》为一类。第一类视道为物质性实体,道含阴阳二气。第二类视道为“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主张有生于无说。第三类似是前两种视角的结合,既讲天地万物的本原为气,又讲有生于无说⑥。
这样,从冯先生到许先生,对于《淮南子》中的“道”给予了一个相对容易被大众接受的解释,即《淮南子》的“道”是多层次的,是矛盾的,存在着三种不同形式的道论,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淮南子》的道论,就必须要具体地分析其立论的角度与立场,不能一概而论。这似乎是理解《淮南子》道论的一种比较科学、客观的方式,似乎也是最为平实的、可靠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方式恰恰是有问题的。因为,首先,《淮南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延续,在其作品中,在诠释“道”的时候,出现与老庄、稷下黄老道家相一致的观念,不能视为是一种矛盾,而应当视为《淮南子》对于道的理解是在一个历史脉络中展开的,从老庄道家,到稷下道家,再到《淮南子》的道家,这是一个历史的、逻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种内部矛盾丛生的解释系统。所以,不能在同一个横切面上把《淮南子》的道论视为矛盾的杂糅,而应该在历史的维度中去理解道家对于道的理解的历史性变化,从而深化对于道的内涵的把握。其次,如果仅仅是从矛盾的角度来看待《淮南子》中的道论,那么,除了矛盾之外,我们对于《淮南子》道论的特殊性,或者说,《淮南子》对于道的解释的那种时代性就会失去准确的把握。换而言之,矛盾性并不是《淮南子》对于道的认识的最为重要的呈现,我们需要透过这些看似矛盾的梳理,来发现《淮南子》对于道的特殊理解。《淮南子》中呈现出来的老、庄或者稷下道家对于道的解释,那是应该站在历史继承性的意义上予以确认的,而《淮南子》对于道的独特理解方式,则是应该站在时代性的意义上予以肯定的。由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淮南子》道论的深刻内涵。
那么,《淮南子》对于道的诠释,其特殊性在哪里?根据前面的讨论,结合《淮南子》的文本,大体上《淮南子》对于道的论说,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淮南子》强调“道以无有为体”(《说山训》)。这是《淮南子》对于作为本体的道的最为直接的表述,也是最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诠释。什么是以“无有”为体?如果我们说老庄哲学在总体上是以“无”来描述本体的道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冯先生和许先生所说的所谓“无中生有”或者“有生于无”的这种本体论的讨论形式。但是,《淮南子》却说“道以无有为本”,该如何理解?
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
有为体。”魄曰:“无有有形乎?”魂曰:“无
有。”“何得而闻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
耳。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冥者,
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闻得之矣。
乃内视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
可得而见,名不可得而扬。今汝已有形名矣,
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独何为者?”
“吾将反吾宗矣。”魄反顾魂,忽然不见,反而
自存,亦以沦于无形矣。(《说山训》)
这是《淮南子》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道的寓言,正是在这段魂魄之间的对话中,《淮南子》阐述了“道以无有为体”。很多人在解释“无有”的时候,直接把无有解释为无,我认为这个解释是不恰当的,假如无有即是無的话,那么,文本当直接以无称之即可,不必以无有的形式出现。既然称无有,那么我想至少这里有两层很重要的意思。首先,道是无的,这是从老庄道家对于本体之道的基本限定上来说的,只有作为无的道才能成为万物存在的基础;其次,道是有的,有表达出道的真实存在的一面,道对于世界来说就是有的,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揭示出来的是存在义;最后,道为无有,这是《淮南子》特别强调的,如果从无有的这个提法来说,《淮南子》更侧重道之作为存有的一面,而无则是明示道之作为最高本体的意义(故而是无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有不是有或者无,而是强调作为本体的有。《淮南子》对于道的阐发恰恰是重在道之有的意义上,这才与其整体思路是相吻合的。因为《淮南子》主要是要通过对于道的阐发来实现其对于现实政治的哲学建构,而现实的政治既然重在现实,必须从“有”的意义出发,因此,“无有”的提法,对于《淮南子》的理论完善来说具有突出的意义。
第二,既然道是无有的,那么,这个无有和现实之间的关联在哪里?如果我们说在《淮南子》这里,对于道的“无有”的限定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在《淮南子》侧重对于道的现实展开层面的讨论(主要是政治意义)过程中,气(阴阳)是道的这种“无有”的最佳呈现。所以,在《淮南子》对于道的阐发中,气成为了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汇。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
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
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
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
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
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
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
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
辰,地受水潦尘埃。(《天文训》)
《天文训》中的这段说法,很清楚地描述了从气到天地万物的过程,气构成了万物的根据,万物是禀气而来的,由此,阴阳二气的变化对于现实的人事有着极为深刻的解释意义。当然,这里更需要关注的是“道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的说法,如果按照一般的解释,那么这是一个不断创生的序列,“道—虚霩—宇宙—气”,但是,我想这个解释可能需要进一步推敲。如果是按“道—虚霩—宇宙”的创生过程,那么,气作为这个创生过程的结果,就不具有本体的意义,而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然而从后文的描述来看,气又无疑具有一种根基性的意义(尤其是当我们把这个气和黄老学派的精气、元气联系在一起解释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在气之前的序列是一个逻辑描述意义上的界说,不是一个时间序列的创生过程。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说太昭、道、虚霩、宇宙的时候,并不是说在时间序列上是这么产生的,而是说从逻辑意义上来描述本体的道的时候,它必然是太昭、虚霩,必然是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的,获得了这样的本体特征和时空意义的时候,气才进入了它的创生过程。所以,这是对于气作为本体的存在状态的描述,而非一个事实意义上的创生过程的说明。
第三,道是一。如前面所言,在冯先生和许先生看来,《淮南子》对于道的论述存在着矛盾,即存在着三个层面的道的意义。然而,我认为这种矛盾说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言说道的角度和侧重不同,不存在着三种道。如果我们把《淮南子》看成一个整体,那么也很清楚,道的观念在《淮南子》中也应该是一贯的。与其说是三种道论,毋宁说是对于道的不同解释的综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淮南子》就是一种综合,当然,它的综合是建立在它自身的理论建构需要之上的。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
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
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像
之类,莫尊于水。出生入死,自无跖有,自有
跖无,而为衰贱矣!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
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
也。肃然应感,殷然反本,则沦于无形矣。所
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
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
贯九野。员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
叶累而无根。怀囊天地,为道开门。穆忞隐闵,
纯德独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视
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
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
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
出于虚,天下为之圈,则名实同居。音之数不
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
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
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故音者,宫立而五
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
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原
道训》)
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
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天文训》)
用“一”来界定道,这在道家(甚至是整个中国哲学)的传统中极为普遍,这种一既是对于本体的确定,又是对于创生过程的确认。因此,当我们说道是一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是具有宇宙生成论的意义。如果说《淮南子》中对于道论的诠释有着怎样的特殊性,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在《淮南子》中,宇宙本体论和生成论路径对于道的解释被打通成为了一个,从而《淮南子》之道论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总之,《淮南子》对道论的阐发,应该不存在前后矛盾,它是将宇宙本体论和生成论融为了一体。如果说在老庄那里重视的是对于本体论的道的阐发(更多是呈现出道家的超越境界),在稷下道家那里对于道更多是从宇宙生成论的意义展开(突出道对于现实的意义),那么在《淮南子》这里则是把本体论和生成論打通,在强调道作为超越本体的同时更强调道在现实意义上的展开,由此为解释、建构现实政治找到了一条非常有效的路径。“道以无有为本”,这样的说法,既使得道在现实政治层面的展开具有了必然的根据,又为这种现实的展开找到了本体论的根基。
二、“因”与“无为”:《淮南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
就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我们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老子所强调的“无为”,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无为而治”成为了对于道家政治哲学的最为直接的表达,作为道家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淮南子》的政治哲学自然也是以“无为而治”作为基本特征的,当然,《淮南子》对于“无为而治”有着自己的理解: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
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
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
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且夫圣
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
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之为水,以身解于
阳盱之河。汤苦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圣人
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
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
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
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
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
用车盾,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
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修务训》)
从《修务训》的这段话对于无为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淮南子》的立场。在《淮南子》这里,无为绝对不是什么都不做,即“寂然无声,漠然不動,引之不来,推之不往”。通常人都会有像“或人”一样的理解,认为既然是无为,那么就是什么都不做。这样的方式无论是从理上还是从事上来说都是不恰当的。从理上来说,如果无为是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又怎么可能达到无不为的结果呢?如果无为是取消人的一切行为方式的话,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也会由此而被取消。从事上来说,古来圣人的种种方式,恰恰都是积极有为的,神农、尧、舜、禹、汤莫不如此。其次,无为是一种特殊的为的方式,按照《淮南子》的说法,就是“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也就是说,无为并不是取消个体的为,而是强调不能基于个人的私欲、个人的私心而任意妄为,必须按照天理(道)的要求来规范个体的行为,由此呈现出来的就是无为⑦。
那么,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无为?《淮南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因,当然不是《淮南子》首次使用的,在之前的黄老道家传统之中,已经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而在《淮南子》这里对于“因”给予了特殊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因”构成了《淮南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因此《淮南子》说“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原道训》)。
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因”,是来自于对天道的遵循,所谓因自然,由此整个政治的基础及其行为方式得以确立。简而言之,所有的政治行为必须是在因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无不为的效果。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
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
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
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
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运转而无方,
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
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
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听治也,
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
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
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
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
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众人相一,则百人
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
乘众人之制者,则天下不足有也。(《主术训》)
政治统治之道,就是对于天地之道的效法,是因循自然之道而已。在《淮南子》看来,君主是用道德来治理天下,而不只运用个人的才智,是依顺万民之利益来办事处事,因而他稍抬脚便能让天下人获得利益。这样,百姓即使将君主顶在头上也不会感到压迫、放在眼前也不会感到碍事、举过头顶也不会感到高不可攀、推崇他也不会产生厌恶感。君主治国方法灵活圆通,周而复始而运转不停,孕育万物神妙无比,虚静无为而因循天道,常居后而不争先。而下属大臣办事处事方方正正,言论得体、处事恰当;遇事先行倡导,职责分明而不推诿,以此来建立功绩。所以君行无为之道、臣行有为之道,君臣异道天下太平;反之君臣同道则天下大乱。也就是说君主清静无为,臣则恪守职位,各自处在应处的位置上,这样上下便能默契合作、互相制约和促进。君主治理天下,心胸虚静而心志温和,清明而不昏昧,这样,群臣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轴一样入朝辅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能的还是不才的,无不各尽其能、各尽其力。从而君主能充分驾御下属大臣、下属大臣能充分事奉效力君主,这就是治国之道。周文王聪明而且好向别人请教,所以他圣明;周武王英勇而且好向他人讨教,所以他能取得胜利。所以说凭借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利用借助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千钧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不能举起来;众人一起用力,那么上百人就够了。如果只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去炫耀;而借用众人的智力,那么天下也就小得不够你治理。而能够达到这种统治效果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因”。
“因”就是因循、随顺的意思,所因、所顺的对象就是自然之道,政治的基础由此得以确立,这当然是合乎道家哲学的基本规定的,而且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所谓“三代之所道者,因也”(《诠言训》),正是在因的基础之上,三代之治才得以可能。
圣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
而涤荡之,故因则大,化则细矣。禹凿龙门,
辟伊阙,决江浚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
后稷垦草发灾,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
因地之势也。汤、武革车三百乘,甲卒三千人,
讨暴乱,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则
无敌于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
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
不可斫;而木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窬木
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
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自然也。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
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
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绖哭踊之节。故先王
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
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
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
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
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惯
用兵也,入学庠序以修人伦。此皆人之所有于
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泰族训》)
圣人之治,无非因而已。所以,從政治的有效性来说,因顺自然是最佳的选择。从《淮南子》文本中对于“因”的重视程度来看,我们说“因”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围绕“因”,《淮南子》对政治哲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构建。首先,“因”的根据在于天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其实就是一个因顺、效法的过程。而对于《淮南子》来说,很清楚,自然之道是构成一切行为方式的基础,也为一切行为方式的有效性做了规定,只有符合“因”的,才是真正有效的政治行为;其次,“因”的基本内涵是去除私意和私欲,自私用智是人类的基本特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人类社会所有纷争、混乱的基础;第三,“因”是一切具体政治行为的有效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就是因顺人之本性,也就是说,政治统治要达到真正有效的目的,就必须是因顺人的自然本性,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天下莫不治的结果;第四,“因”是真正有效的统治方式,也是真正的“无为”的表达。道家讲无为并不是无所为,而是在因的前提之下的积极有为;第五,所“因”不同,决定了君臣异道,君臣之道都是因的结果,但是,因为“因”的对象不同,君道效法的是天圆,而臣道效法的是地方,由此,君道和臣道在现实的展开中具有了各自丰富的内涵。
由此,“道—因—无为”构成了《淮南子》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尤其是通过“因”,《淮南子》的政治哲学不仅具有了切实可靠的基础,而且也能为现实政治行为的有效性提供支撑。可以说,对于“因”的政治哲学讨论,是《淮南子》政治哲学的关键点所在。
三、“权”与“有为”:《淮南子》政治哲学的现实展开
作为一种政治的原则,“因”的确立表明了从理论上《淮南子》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独特系统的成立。但是,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乃在于现实的政治。换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中,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较之理论上的完满性,现实的有效性是政治更为关注的重点。《淮南子》以道为基础,以“因”为基本核心,强调的正是其政治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有效展开。一旦要在现实中具体展开,就会遇到是理(哲学观念)和事(政治事实)之间的协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淮南子》的解决方式也是值得思考的,它在现实的处理层面,引入了“权”的概念,来强化其政治哲学的现实有效性。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
“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
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
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
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昔者,《周
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
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
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
虽有直信,孰能贵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
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
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
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
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
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尪、养由基、
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礼,黄
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奋体
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
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
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
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
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夫君臣
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
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
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
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
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
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
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
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
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
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故礼者,
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
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
于宜,不结于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是故败
事少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氾论训》)
权,即权衡。在早期文献之中,当以孔子在《论语》中所言“可與共学矣,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最为著名。按照通常的理解,这种权衡就是圣人应对各种具体事务的智慧。毫无疑问,在这里,《淮南子》也是非常认同于这种权的智慧的。武王消灭殷王朝后,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周公马上说:“不可。这太行山区是固塞险阻之地,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德政,那么天下各地来朝拜进贡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如果我们实施暴政,那么就使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完成他们的使命。”这就是周王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夺的根本原因。所以,周公也真可谓是一个能正确处理盈满而不覆的人。因此,《周书》上说,“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道理。”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只有君子圣人才知道权变的道理。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这是天下公认的高尚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检举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但女子失约,而尾生为了守信约,站在桥下任上涨的河水淹死。正是直躬为正直而检举父亲、尾生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他们虽然正直和守信,但又有谁来推崇看重他们的行为?作战中伪造命令、假传军令,这是错误中最大的一种。但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时,经过东周向东进发,郑国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贩牛,在途中碰到了秦军,于是弦高假托郑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知道这次偷袭计划而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撤退,从而保存了郑国,使之不至于沦为秦国的“殖民地”。所以说,当紧急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不知道权变,只知道忠厚老实,反而会酿成大错,而像弦高那样欺诈一下倒能立下大功。什么叫失礼却反有大功劳?过去楚恭王在鄢陵与晋国交战,被晋将吕目规射伤眼睛后被俘,这时楚国的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冒死冲入敌军中将恭王抢出;而这时的恭王已吓得瘫在地上失去威仪,黄衰微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仪,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脚,恭王猛然清醒,并被黄衰微的失礼行为所激怒,挣脱了众人的搀扶而站立起来,于是四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战车逃了回来。还有,以前的苍吾绕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就将妻子让给了兄长哥哥。很显然,这种“爱兄”方法和“忠君”的做法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但是知道权变的圣人就能根据事情实际情况,能随之伸缩俯仰,没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条条框框,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当应该柔弱时,他就柔弱得像蒲苇一样,但他这柔弱并不是慑于威势;而当应该刚强猛毅时,他就刚强猛毅得能气冲云天,但他这刚强猛毅也绝对不是狂妄骄暴。他的这两种态度均是为了应对时势的变化。从对这些事例的分析当中,《淮南子》让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权”的重要性,而周公明显是一个非常善于用权的圣人形象。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
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
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
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
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
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
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
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
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
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
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
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
中权亦明矣。(《氾论训》)
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权的存在,圣人才将大道在现实中很好地体现出来。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权的重要性。权就是圣人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形,随时处变,将道落实到现实的社会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权的智慧,道只能是一个空疏的概念。而生活世界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暂时性,也藉由权的智慧得以与道关联在一起,从而道也就无所不在,所适无非道了。
从《淮南子》上述对于权的论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在《淮南子》的政治哲学系统中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权的提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所谓“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氾论训》),权是与道相对而言的。道是固定不变的,是永恒的,即“道犹金石”;而权则是变化的、暂时的事实,即“虽日变可也”。由此,权的提出就是为了应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的需要,是一种应对现实的智慧;第二,既然权是应对现实的,那么,权就是一种暂时的手段、方法,是“应时而变”的,如何改变?取决于前文所言的“因”,也就是说,这种改变是顺应外界的状况而进行的,并非是出于一己私心的结果;第三,“权”是圣人才能实现的,只有圣人知权。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对原则、制度进行随意的更改,而是说,这种改变唯有在圣人通达时变的意义上才被允许。圣人行权,落实于现实之中,就是王者应当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形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第四,权的实现方式是“应时偶变”,任何权衡改变的出现,都意味着充分考虑到了现实的状况,时和变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通达,唯有如此,权作为一种应对世事的智慧才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五,权的行为特征是“先忤后合”,忤、合的对象都是经(也就是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则)。“忤”恰恰是变化的表现,是对于现实的承认,任何改变的发生都是出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而不是抽象的原则。为了应对现实,我们的具体方法必须是随时改变的,由此,我们才能够得以游刃有余。然而,如果这种改变最后是背离原则的,那么,这是不被允许的。所有的改变,都只是暂时的,是为了使道能够实现出来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方式,其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合于道的。
因此,在《淮南子》这里,权是一种现实的智慧,表达的是在现实世界之中道的积极有为的展开方式。如果说因是《淮南子》政治哲学的基础的话,那么,作为应对现实情境的智慧,权是在因的前提下展开的。黄老的智慧在应对现实层面上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因之得以充分表达。
四、“義”《淮南子》政治哲学的实践特征
如前文所言,在《淮南子》的政治哲学中,权是极为重要的概念,正是因为权的存在,现实的、积极有为的政治行为获得了重要的意义,也确保了道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的展开。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如何用具体的方式(权)来实现原则(道)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实现方式的特征总是“先忤后合”的,那么,何以保证我们在现实中以权的方式背离经(原则),又最终能够返回到经(原则)呢?在这个意义上,《淮南子》特别强调义。
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从
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遍知万物
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
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
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
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
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
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
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
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者为正,
错者为权,其义一也。(《主术训》)
义,以通常的理解就是宜,也就是强调人的行为的恰当性。在这里,《淮南子》对仁、智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进行了分析。它指出,全面了解万物而不知道社会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人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可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得不割爱,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有时碰到烦难之事,但他那聪慧的心志还是会呈现出来。心地宽厚的人能经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会强加给别人;由近而知远,由己而知人。这就是仁智结合运用的结果。对细节加以矫正,才能全大体;对小的过错及时纠偏,才能保平安。这正是出于爱护同情之心才推行的做法,也是智者的决断做法,而一味讲仁的人是难以做到这点的。所以仁和智有时错开有矛盾,有时又结合相一致。仁和智结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时仁和智错开不相合,就是权变做法。当然,不管是仁,或者智,都是出于义的。由此,在义的高度,作为统治方式的“仁”(经)和“智”(权)得到了统一。也就是说,不管是遵从经的形式,还是遵从权的方式,对于任何一种治理的形式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合乎义,也就是恰当。只要是在恰当的时候,采用恰当的方式,都是被认可的,因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经还是权。这样经和权就在义的层面实现了完满的结合。所以,《淮南子》说,“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氾论训》)。如果在前文讲“先忤后合”还是一个比较抽象化的理解的话,那么,这里以“义”为原则,实际上就是以现实行为的有效性来保证了经和权之间的必然相合。既然义能保证经和权的必然相合,那么它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具有的重要性就是不可小觑了。
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
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
众适者也。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
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
绳乎唯恐失仁义。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
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
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
观其所惧,知各殊矣。(《缪称训》)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仁义的价值在《淮南子》这里得到了确认,小人和君子之分,也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实现。仁、义作为一种价值,在《淮南子》的这个框架中,得到了很好的接纳,因为仁义不过是强调人现实行为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更多是在权的意义上,由此,在权(现实)的意义上,由于“义”的引入,《淮南子》思想具有了更为广大的包容性和有效性,这种包容性和有效性除了仁义的价值在其系统之中得到了确认之外,法的观念也由此而获得了存在的可能性。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
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
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
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
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
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
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仪者,
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
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法生于义,
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
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
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主
术训》)
战国以来,基于法家思想的重要成就,诸子在讨论治道的时候都无法回避法的问题,比如荀子对于“隆礼重法”的强调等等,甚至于是否有效地将法收纳到自己的理论系统中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种政治哲学的现实价值。黄老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是积极的,比如《黄帝四经》里对于“道生法”的强调,事实上就是在道的意义上找到法的根源,从而可以有效地将法纳入到道家的政治哲学系统中来。而《淮南子》的解决方式无疑也是值得肯定的,它把法置于义之派生地位,认为“法生于义”。义是现实的有效性,强调的是具体行为的恰当性,因此,当《淮南子》强调“法生于义”的时候,首先它确定法只具有特殊的、现实的、暂时的意义,不是最高的价值;其次,法以义作为标准,重视的是法在现实问题解决上的有效性,是属于“人间”的,是人主的一种统治工具而已;再次,这种工具的使用(赏罚)必须是恰当的,必须是在“义”的限定下进行的,这是现实统治的保障。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淮南子》引进“义”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首先,义是经和权统一的标准,经和权统一于义,就是统一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恰当的行为。其次,由于“义”的概念是现实层面的,是针对人的现实行为而言的,所以,在现实的意义上,《淮南子》很好地实现了对于道德和法的价值的统摄,这使得《淮南子》的政治哲学呈现出强大的实践的特征。
五、混冥:《淮南子》的理想政治形态
任何政治哲学的描述,其最终的指向,都是一种理想社会的形态。换言之,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描述,在政治哲学中之所以不可以缺少,是因为这种理想的形态是和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于理想形态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价值的取向,以及在此价值基础上对于现实的批判意义和重构意义。
《淮南子》也不例外,其政治哲学的建构,自然也表达出它的独特的价值理想。那么,《淮南子》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什么?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氵闲之域,而徙倚于汗
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万物,以鸿蒙为景柱,而
浮扬乎无畛崖之际。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
而群生莫不禺页禺页然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
莫之领理决离,隐密而自成。浑浑苍苍,纯朴
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是故虽有羿之
知而无所用之。(《俶真训》)
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
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当此之时,风雨不
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
丹书,河出绿图。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
得达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天下之心,是以
人得自乐其间。(《俶真训》)
古之人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
物恬漠以愉静,搀抢衡杓之气莫不弥靡,而不
能为害。当此之时,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含
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
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谓大治。于是
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
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
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而难以
算计举也。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
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古之真人,
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
雜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
乎?(《俶真训》)
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
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
五谷不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
地怀气而未扬,阴阳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
俗,斟酌万殊,旁薄众宜,以相呕咐酝酿,而
成育群生。是故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
之所生。由此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
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是故明于性者,天地
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圣人
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古之人同气于天
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
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而
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本
经训》)
在道家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之中,“至德之世”是一个时常被提及的语词,在《淮南子》中,也不时会提及“至德”、“至德之世”,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表达出《淮南子》所具有的毫无疑问的道家色彩,而非杂家可言。当然,最具有《淮南子》自身特点的用词应该是“混冥”。“混冥”和“至德之世”,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道家理想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当然,如果我们从混冥的角度来略作分析,我们可以对《淮南子》的理想社会形态的特征有更细致的把握。
第一,这是一个恬淡、宁静的自然社会。恬淡、宁静来源于道之本体的特征,或者说,来自于天地之和,之所以说是一种自然社会,是因为欲望或者人为的种种造作,在这里都被取消掉了⑧;
第二,这是一个充满着快乐的社会。当然,这种快乐不是基于欲望、追求被满足之后的快乐,而是发自于内心的、真正的快乐,或者说是禀性自足的快乐。而且,这不是一种抽象的快乐,而是“含哺而游,鼓腹而熙”的快乐⑨;
第三,这是一个自由高于秩序的社会。自由是这个社会最高的价值,因为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可以获得自我的满足和快乐,这就是最高自由的表达。当然,它也并不排斥秩序,秩序显然是存在的,治理的形式也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秩序和治理并不违背人之本性,不对人的本真的行为构成限制,所以,它是满足于或者说从属于人的自由的需求的⑩。
这样的世界,大概就是《淮南子》所向往的“混冥”,或者说是一个充分自由的快乐世界,也只有这样的世界,才是真正合乎道的方式的世界。这样的理想世界,在《淮南子》之中有怎样特殊的现实意义,我们已经很难还原,因为当汉武帝确立儒学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之后,《淮南子》的这种政治理想已经宣告了事实上的终结。但是,从作为一种价值引导的意义来说,或许,《淮南子》的政治哲学由此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批判的意义。
六、结语
《淮南子》以其宏阔的视野,在汉初黄老政治实践的基础之上,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建立了一个圆融、自洽的政治哲学系统,在回溯道家哲学的历史资源和回应现实政治问题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尝试,其特征也非常鲜明。
第一,《淮南子》的政治哲学,建立在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基础上,圆满地实现了从超越的本体向复杂多变的事实转换的理论架构。事实上所有的政治哲学其理论旨趣都是要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的政治实践的。道家哲学作为一种超越境界的哲学,如何有效地契入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淮南子》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将“道”与“无有”结合在一起,有效地实现了超越的“道”向现实的“有”的过渡,并且,这种过渡既保持了道家哲学的一贯内涵,又兼顾到了现实的理论需求。
第二,《淮南子》政治哲学的立足点在于天和人的双向贯通。天和人的关系,是政治哲学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然而如果只是强调天道对于人道的决定意义(比如儒家的传统),会使得人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特殊的、主体的意义被掩盖;而如果单纯强调从人的角度来构建政治(比如西方的契约政治传统),则会使得人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失去神圣性根源(即天)。而《淮南子》的处理方式,既考虑到了天道的决定性意义(道的本体),又注重了人的行为的有效展开(因)。
第三,灵活的现实应对策略。脱离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于道家哲学的最为集中的批评。而《淮南子》的政治哲学,从现实展开的层面做了深入有效的探讨,并通过权和义,使道家政治哲学对于现实的政治方式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包容,这对于其现实展开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注释:
① 可能很多人会对中国早期哲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提法提出疑义,其实不仅是秦汉以来的哲学,先秦诸子之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大体是一种政治哲学。 关于这一点,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为代表,传统已有比较多的论述。撇开诸子出于王官说,我们事实上还可以从诸子论说的本身特点来思考,诸子之书,大体上立足于“化成天下”,为“礼崩乐坏”的社会重新确立秩序,这是诸子所真正关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哲学是诸子学的核心,当无疑义。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141页。
③ 事实上,学界对于《淮南子》道论性质的理解,很大程度受到了對于《淮南子》书作为杂家性质的定位的影响,从杂家的起点出发,道论的内在逻辑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
④ 许抗生:《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212页。
⑤ 我认为许先生的这个判断事实上是不太恰当的,道家(尤其是老庄那里)对于道的判定不能说是存在内在的矛盾,而只能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道的时候,存在着视野的交融和重叠。从最为直接的角度来说,判定道是“有”和“无”并不构成矛盾。因为,“有”其实侧重的是道作为真实存在的意义上来讨论的,而“无”其实侧重于道作为最高的根据而言的,道既是“有”的,又是“无”的,“有”、“无”是道的一体两面,因而说矛盾似乎不太妥当。
⑥ 许抗生:《〈淮南子〉论“道”》,《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⑦ 事实上,道家的无为观念,从老庄开始,一直就不是什么都不作为的意思。“无为”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为”,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表现在对于“为”的这个基本事实的否定,而是对于“为”的形式的特殊限定,即需要取消掉主体所具有的强烈的主观意志。这种强烈的主观意志,一般来说是和私欲相连的,是必然背离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淮南子》在这里,其实是对老庄道家的这种“无为”的具体阐发,完全是合乎老庄哲学的一贯理路。
⑧ 以恬淡宁静作为对于理想社会的一种价值设定,无疑表达出来《淮南子》的政治哲学的道家价值倾向,是道家最基本价值的传达。
⑨ 对于“乐”的这一点的强调,尤其是各得其性的乐,这和儒学的价值有着密切的关联,乐可以作为儒家对于理想境界的最高描述。而在《淮南子》对于乐的境界的吸纳和阐发来说,事实上更多关注的是其政治哲学的现实有效性,或者说,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于其现实性的观照。
⑩ 自由高于秩序,这是道家精神价值的内核,也是儒道的差异所在。在儒家政治哲学的意义上,秩序是高于自由的,或者说,秩序是用来保护、实现自由的,秩序具有比自由更为基础的含义。而在道家那里,自由是作为人的自然本性被认可的,是道的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
作者简介:何善蒙,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310058。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