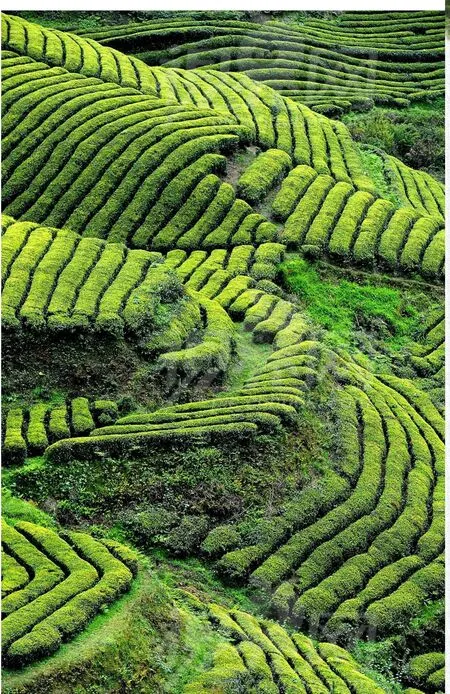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湄江吟社》咏茶诗词赏析
2017-04-16刘丽
刘 丽
茶诗指“专写茶的诗”或“诗中写有茶”的诗。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也是最早发现和饮用茶的国家,《诗经》中的“荼”这种苦菜就是茶,《诗经·大雅·绵》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诗句,《诗经·邶风·谷风》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许慎《说文》认为:荼、茶同为一物。由此观之,茶与诗的结合由来已久。诗歌史上吟咏茶事的诗词有几千首之多,其中以唐宋时期最为突出,唐宋时期很多名诗人都吟咏有茶诗,黄庭坚的《阮郎归》与《煎茶赋》还写了遵义务川的都濡高株茶,“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胯斗园方,研膏人焙香;青箬裹,绎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
茶的核心是茶道,茶道是由茶引发的思想和审美境界。陆羽的《茶经》认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将饮茶与德行相提并论,唐代刘贞亮则在《茶十德》一诗中将茶德推广为“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意、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赏味、以茶修身、以茶雅心、以茶行道”。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认为“此物清高世莫知”指出了茶超凡脱俗的高尚品格。宋代,产生了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等专著,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僧人刘元甫开设的茶禅道场,确立了“和、静、清、寂”的茶堂清规,将茶的品质定位于内在的人格品性,他的思想直接影响到日本茶道。从此以后,茶的“精行俭德”与茶的“致清导和,韵高致静”,就成为中国茶道的精髓所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浙大终于在颠沛流离中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落脚点——遵义、湄潭。并成立了“湄江吟社”,定期聚集,以抒发他们忧国怀乡之情,表现其在国事艰难时期吃苦耐劳、积极乐观、坚守不渝的人格。“记存一段文字因缘,藉为他日雪泥之证”。其中湄江吟社的第四次集会时间,正是茶叶的丰收时节,时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茶场场长的刘淦芝教授邀请浙大教授品评新茶,以助诗兴,于是就有了以咏新茶为题的十六首诗和四首词。这些咏茶诗,深深地渗透茶的“德”“品”,不仅有“和、静、清、寂”,更有“精行俭德”。在品茶论道中,我们读到的是“高节伴灵筠”“竹窗一几话松筠。”具有屈原一样的节操与品行,松竹一样的气节,这是浙大教授的“德”;“若余犹得清中味,香细了无佛室尘”这是浙大教授的“清”“寂”,“乱世山居无异珍,聊将雀舌献嘉宾。”“茶德”与“茶品”丝丝相扣,既是咏茶,又是明志,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承。
湄江吟社咏茶诗的第一首是王季梁的《试新茶得“人”字》,诗一开始,将受刘淦芝先生邀请喝新茶的心情展露无遗,“急折柬”“净扫小阁”“尽罗列”“呼童汲水”,忙得不亦乐乎,原因是“许分清品胜龙井”,湄江的茶是否也和西湖龙井一样?清冽的泉水,玉一般碧绿的茶色,煮沸时的香气,使饮者通体清新,一种飘飘欲仙之感油然而生。
如果说王季梁的诗从茶品坚定人品,江问渔则在品茶中表达了“倦游”他乡的豁达。战乱之中难得的闲情,在一个“惊”和“惜”字中,被打乱了,匆匆春又归去,客居他乡之痛,在清涩新茶的之中得到化解,在试新茶中,诗人领悟到,大自然用他的规律证明:万山之绿不会因诗人之痛而黯淡而是用翠绿给我们打扮出一个绿茵茵的世界,让你不得不由衷赞美。
祝廉先在品味湄江新茶时,兴致最高,一连写下了五首诗歌,表达了品茶的快意和恶劣环境下人格的坚守。“曾闻佳茗与佳人”,从视觉、嗅觉到味觉,将诗人品茶不可言传的感受,转化为具体可感、美妙动人的形象,传达出品茶的审美愉悦,接着用辩才和尚及惠远的典故,写出诗人们无拘无束、任意而为、自然率性的追求及对社会平和的期望。“佳境每从清苦得,芳甘原属岁寒身。”品茶如同品人生,苦后方知甜,经历战乱后寄居湄潭,才更深地体会到能安宁的快乐。寄身湄潭,品茗作诗,弹琴戏水,把酒斗茶,清心寡欲,自得自在。清新的湄江茶,流动的活水,充满生机以活力,洗掉了诗人身心的烟尘,使诗人在自然天地之中,任性而为,惬意可心。然而,“劳薪慎勿饷劳人”的重字和典故运用,使我们看到诗人隐藏于心的感伤,国破家亡,狐兔纵横,冉冉老迈,何时返乡?
面对湄潭新茶,苏步青更是感概万千,一口气写下了七首诗词,从“客中何处可相亲?”的寻觅,到“碧瓦楼台绿水滨”的诗友相聚,碾茶、煮茶、茶香缭绕中的“鬓丝几缕未归人”,时间之快,感慨之浓,画面感极强,好像时间被浓缩了,愁思染鬓的过程就在一瞬间完成。一松一紧,一张一弛,兴亡之感在品茶的闲情之中得以强化。然而,终究是“翠色清香味可亲,”静寂、清淡、高雅的茶之味, 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之味,让人感受家的味道、和谐的喜悦。在茶清香氤氲的气氛中,将杂念沉淀,将心中的阴霾扫走,让心灵澄明,不再为羁旅他乡所困,不为“何处可相亲”所烦, 在旷达的人生中,静下心来领略茶的万种风情,品雅致,避炎热,脱俗情,求宁静。在日常品评中,随缘自便,这就是茶的真味,也是浙大文人的人生态度。但毕竟湄江不是钱塘江,西南不是江南,“祁门龙井渺难亲,”家乡沉沦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家的滋味不是在禅中可以化解的,所以,在前一首诗中,看是平息了内心的思绪,不过是“强自宽心”。由此可见,亡国之痛之深切难已。“乳雾看凝金掌露,冰心好试玉壶春。”化用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在如烟似梦的茶雾中,如看到象冰一样晶莹纯净高洁透明的心。人品高雅,人事和谐,满屋生春。这三首诗组成一组,韵式完全相同,均为“滨、春、尘、人,”在整齐划一中又显灵动,在韵律上给人一种和谐的美。
在《南乡子》这组词中,起笔似乎不写茶了,是在写“梦”“残灯”“夜雨”“渔火”“鸡鸣”“秋风”等等,但是时时归家梦,天天不得归。归家的急迫和不能归家的无奈,梦中之归与醒后的不能归对比,将疼痛的伤口拉裂开来,清晰地展示了诗人的心理落差。而“残灯”“夜雨”意象,让人仿佛听到李商隐在唱“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在春雨“滴答滴答”的旋律中,生命深处的感念油然而生:人生如梦,年华如轮,抓住现实,热爱生命,收获了一片沉淀苍凉和感伤后的宁静。“只怕秋风白鬓须”,担心忧愁使人老,担心时光催人老,担心回家人已老。面对时局,诗人不再感伤,而是给世人的告诫:不要虚度人生,不要因为身处逆境就自甘堕落,而是要胸怀大志,坚信胜利。故乡遥不可及,只能在回忆中再现,挥之不去的乡愁,“合魂销”的旧事,家事国事天下事,历史现实未来,每件事都总叫人魂牵梦绕,每件事都让人放不下心来。看到春雨砸坠了树上的樱花,仿佛听到恋人哀切的古筝,心也如樱花般地纷纷委地,“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没有人给予安慰,没有认可倾诉哀伤,没有寄予思念的“锦书”,也没有人给予问候的彩笺,思念的情感啊,寄放何处?
二十首诗词中,胡哲敷还有两首《试新茶》,赞美湄茶之好,抒发怀念故乡之情。湄潭山青水秀,溪流纵横,处处“活水”,虽无名泉但胜于名泉。因此用清澈的泉水煮高贵的“龙芽”,冒出“蟹眼”的初沸之水泡出的新茶,其饱满秀丽,色泽碧嫩光滑,尤如国色天香之佳人,让人深感作为“灵草”的无穷韵味,也让人再次品味到两腋清风生的飘然。品茶与喝茶不同,喝茶是满足解渴的生理需求,品茶则是重于“品”,在细细品味中,体验茶的独特韵味,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美的享受,进入一种“临风一吸心自省, 此意莫与他人传”的美妙境界。
张鸿谟《试新茶》虽也写了乡思,但更多地是表达诗人与诗友们聚饮时欢愉的情态及其对湄潭“龙井”茶的喜爱,“露香幽寂”“花乳轻圆”,在视觉、味觉上都给人一种审美感受,刘淦芝对茶的精心培植,使湄茶列入“佳人”之列,在品评湄江茶的美好时刻,诗人想起了故乡。
钱琢如《试新茶得人字》写暮春品茶,茶香氤氲,在精细的煮茶过程中,修行宁静,心中不悦也消失于专注之中。心平气和的心态,是品味茶美的最佳心境。饮茶使人进入清澈明朗的境界,心境决定环境,茶让人感到如清风扑面,满城芬芳;满目的春色使人心旷神怡。茶的清香来源于对茶的制作过程中细心和耐心的“揉焙”,正是这种“揉焙”的制茶技艺,让人联想到故乡西湖,沦陷的故土,而今怎样?心中的痛,一带即出,让人感到说不尽的悲怆。
刘淦芝是这次集会的发起人,也是试新茶活动的组织者与主角,他的《试新茶》起笔就交代了集会试新茶的时间地点,展现了诗人一种谦和的态度和待客之热情。在乱世山居的环境中,能请来浙大师友,以茶资诗兴,在主客相聚中高谈阔论,是难得精神慰藉。
人们都说饮茶能宁神静心,能让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在湄江吟社诗人们与茶对话中,大都是勾起对家乡的无限情思,可见“家乡”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家乡虽暂时沉沦,但每个诗人在品茶时,都能感受到故乡渗透于心底的文化。就此而言,茶为他们提供自由的心灵空间,提供了才华施展的场所,在茶里他们尽情享受心灵的自由,享受诗意化的人生,让文人理想与文人情怀落到实处。